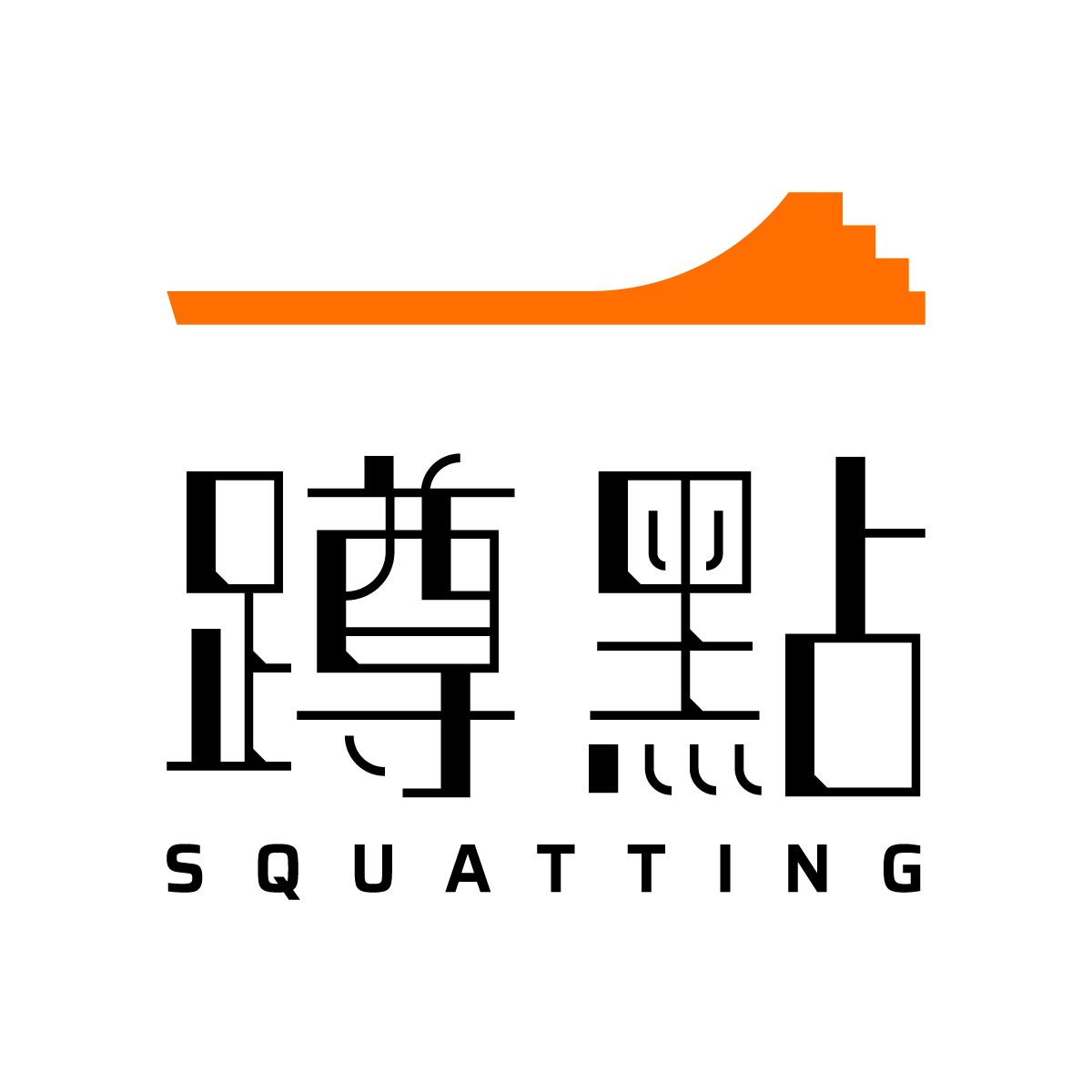【六四卅一】香港從不(永不)缺席

按:今年是八九民運三十一周年,港府託防疫之詞,首次禁止支聯會在維園舉辦燭光晚會。網民紛紛發起遍地開花式悼念六四,讓這個在過去幾年被評為「行禮如儀」、「他國的事」的日子,頓時變得切身相關,抗爭意味亦更為強烈。這個變化的主要原因當然是來自政權的打壓,由反送中到國安法,越來越多人感受到政權的壓逼無遠弗屆,就算傾和理非、勇武之力,依然是強弱懸殊;即使早有「攬炒」預備,一旦政權反撲,氣氛依然恐怖。 可能來自同一政權的強烈打壓,讓更多人感受到當年八九民運的慘況。我們看到,不少人轉發關於六四的資訊,又呼籲大家冒著法律風險,到維園悼念。但我們必須指出,悼念六四不能僅僅是反對國安法的這個獨特歷史時刻的「又一次動員」。因為,回看歷史,我們知道八九時的政治經濟轉變——全面的市場化——和今天中港兩地面對的問題一脈相承、八九民主運動也是不少人的政治啟蒙、兩地民眾亦曾因為八九而經團結在一起。這些歷史遺產,在今天並不是負累,反而是聯合對抗暴政的基礎。
文/是但啦
今天是六四三十一周年。然而香港這個堅持了三十年、每年紀念六四的傳統,很可能被中斷。港府為了禁絕一切讓市民動員和聚集的機會,以原本用以應對疫情的「限聚令」為名,禁止支聯會在維園舉辦六四燭光晚會,是三十年以來首次。圍繞八九六四有很多問題,例如他不單純是一場「愛國民主運動」,還有背後的政經結構。但我在本文中只想談談今年應該如何看待六四。
因為去年至今的反送中運動,所有的傳統示威遊行都成為動員抗爭的機會,諸如六四、七一、十一。不知大家是否記得,一年前的六四晚會,是在政府不理市民反對,硬推「逃犯條例修訂草案」的背景下進行,「反送中」是2019年六四晚會的口號和人民參與目的之一。民怨和泛民的動員合流,令30週年的晚會參與人數達18萬人(支聯會數據),是2014年雨傘運動後的新高;支聯會亦籌得275萬港元,是1993年以來最多。如果今年政府沒有禁止集會,相信參與人數會再創高峰。
歷史在笑。今年香港人面對北京和政府的強烈打壓,尤其是剛剛由人大通過的港版國安法,為香港政治帶來極低氣壓。但這股低氣壓似乎亦掃除了人們過去幾年對「悼念六四」的批評——「行禮如儀」、「他國的事」、「阻礙建立香港人民族身份」等等。今天再看這些批評,並不是說支聯會「改善」了什麼,或者在民族身份這個問題上,思潮有什麼轉向——哪怕這兩個問題並不能推導我們應該不理會六四——而是政權的打壓逼使我們用盡可以動員的機會,團結可以團結的人。但我想,這種團結不能建立在浮沙之上,今天我們重看這幾年來對六四的批評,是否更容易用一個尊重和理解的心態去看待這件——其實與過去香港的政治發展不可分割,又其實影響香港政治走向的事?
港人當年在現場
要講團結,必須得回到歷史現場,看當日八九港人對運動的參與。講起參與,很多人都知道支聯會發起的「全球華人大遊行」,這是開埠以來,繼省港大罷工後最具規模的遊行,有150萬人參與,是很多當其時的年輕人、今天的80後的政治覺醒。

除支聯會的大遊行之外,香港民間亦有很多其他自發組織的行動。1989年5月20日凌晨,李鵬宣佈北京戒嚴,人心惶惶。宣佈戒嚴當晚,香港新華社門外就有4萬名學生和市民頂著8號風球遊行。但新華社遠在跑馬地,凌晨有何交通工具讓人前往?前中大學生會會長蔡子強在《人民不會忘記》這樣說:
那時尾班火車早已開出,我們唯有打電話上電臺,呼籲司機大哥駕的士到中大門口,載我們過海到跑馬地新華社。結果,不消十數分鐘,中大門外真的出現了長長之的士車龍,蔚為奇觀。載我及另外幾位同學的一位司機大哥,當到達新華社門外後,堅決不肯收我們車錢,他說:「我都是中國人。」
當時香港人不單止在香港發聲,更是把籌得的資金和物資直接送上北京,幫助廣場上的學生和民眾捱過酷熱和物資短缺的五月。社會學者趙鼎新在《國家・社會關係與八九北京學運》裏提到:
到五月二十七日,總指揮部之剩下五千元了......局面似乎到了僅是質感問題就足以逼使學生撤離廣場的地步。而在這個節骨眼上,來自香港的資金就顯得很關鍵了......不但是這些帳篷,而且這一時期發生的幾乎所有重大事件,包括民主女神像的建造、廣場民主大學的設立,甚至還有四位知識分子的絕食,多少都是因為香港資金的支持而成事。
這種帶點犧牲精神的跨境團結,不單體現在學生身上,當其時的左派亦有道德勇氣表達不滿。例如在6月7日,裕華國貨在明報、東方等五大報章刊登「停業一天」的啟示。運動被打壓後,中共秋後算帳,要把香港支援的痕跡抹去,例如貼在主要建築物(例如新華社和伊館)牆上的大字報。但當時的新華社社長許家屯在其回憶錄指,一間中資清潔公司堅拒這筆生意:
由於貼大字報所用的膠水洗不掉,行政處就請中資機構屬下的清潔公司幫助清洗,當然也是要給錢的。但是「左派」機構的清潔公司知道清洗的是新華分社大樓壁上的大字報,堅決不肯接受。
重提這些歷史不是要強加這些記憶於任何人身上,而是證明八九六四本來是香港人的一部分。即使我們沒有經歷過這段歷史,依然可以感受這段歷史的沉重,依然可以和曾經經歷過這段歷史的人對話、連結。
本土,還是愛國:雨傘後的低潮
六四之後的香港更是年年沒有忘記廣場的的人們,舉辦紀念活動,其中群眾參與度最高的當屬支聯會每年在維園舉辦的六四集會。但群眾對支聯會晚會的批評也存在已久,有人不喜歡他們成日悲天憫人,不喜歡他們對中國當下境況脫節等。2013年後,本土思潮勇氣本土或也加入了爭取六四解釋權的陣地,為「擊倒」反對支聯會的愛國立場,具體表現為和支聯會「同台競技」,和支聯會在同一時間舉辦的「尖沙咀六四集會」。這個集會由本土派力量每年舉辦,及後見變成五區集會,主題為「本土、民主、反共」,並在2016年加入「建國」。
反對支聯會綱領中的中國人身份的當然不止本土派團體,還有大專院校的學生會。2014年雨傘運動後,「大台」被指要負上最大責任,當中包括學聯和當屆的大專院校學生會。於是在2015年初,多間院校學生相繼發起「退聯公投」,同年的支聯會六四晚會,學聯首次缺席。翌年4月,學聯更退出了支聯會和民陣。
這幾年有關支聯會六四晚會的發展,歡迎各位上網搜尋了解,但必須要說,不少對支聯會的厭惡和批評未必公平。例如2015年的晚會就加入了雨傘運動被捕者家人的心聲,支聯會亦有逐漸變得年輕化,近幾年亦新增了提及內地維權人士的環節,這些轉變不能被忽視。其次,眾多「無用論」、支聯會和泛民「永續論」,今天看來應該被唾棄吧?反送中運動白熱化後,出現了「不是end game」的說法,呼籲群眾長期抗爭;我們又堅持在每月的21號到元朗西鐵站靜坐抗議。同樣地,是否也能理解很多人年復年悼念六四的心情?
我不是說支聯會不能被批評,我也覺得不去支聯會的晚會沒有什麼問題,我們大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悼念。但以上的原因從來未可說服我放棄「悼念六四」、「討論六四」。眼見中國內地仍然有人支持香港的民主運動,尤其是雨傘運動時有內地人因而入獄,可見依然有人在極其高風險的情況下堅持中國的民主化。如果我們是民主主義者,就絕對應該支持所有地方的民主化;更何況中港政治關係本來就千絲萬縷,悼念六四和講述六四也是香港人的自我對話。
國安法下的六四:香港人永不缺席?
最後我想分享一點本人的六四經驗,我是90後,進大學後才接觸政治和六四,同期也是在本土思潮最為蓬勃的時候。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每年都會遇到內地來參與悼念的人,他們通常都很樂意接過其他人派發的傳單、刊物,有時甚至會多拿幾份。每次見到他們一個人,或者用普通話和身旁的人說話,我都會想,到底他們要怎樣把這些傳單和刊物拿回內地?到底要冒多大風險?或者他們在過關前要把這些物品清空,然後如何回到不能公開言說和分享六四的環境,但又堅持一年復一年地來香港——這個中國境内唯一可以公開悼念的地方?
眼下港版國安法已經通過,支聯會是鐵定會被「整治」的組織,假若明年疫情已經完全退散,還會不會有六四集會?我們還能否公開、無風險地用我們的方法悼念六四?如果今天,內地異見者和港人都無法在這片曾經和六四緊密聯繫的土地自由地紀念那場運動,這是否能讓我們在卅一年後重新連結起來,去沖破同一堵牆?一想到這些,我又覺得當下和八九無比地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