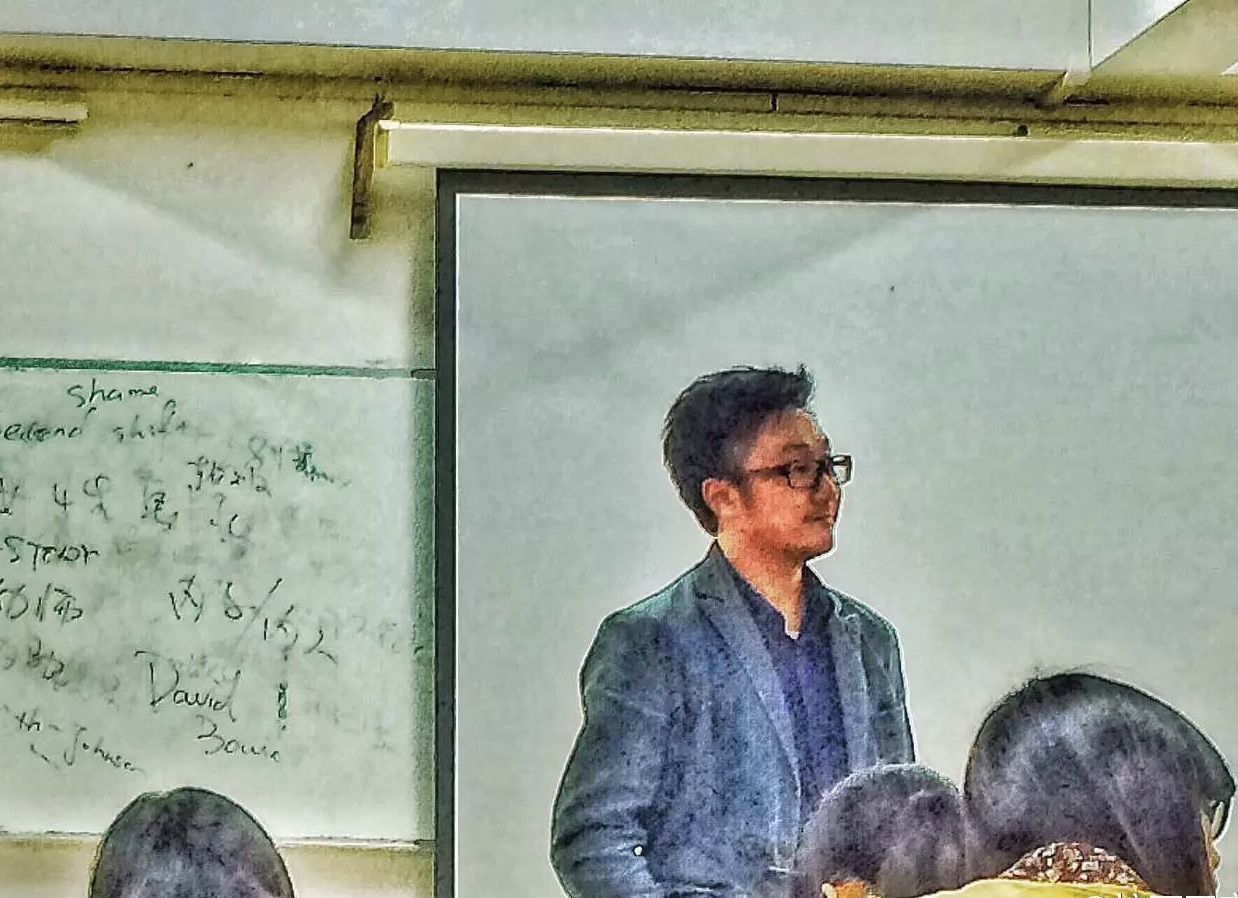美国反堕胎法案:女性与胎儿之间的权利竞争?
本文首刊于澎湃新闻·思想市场
过去几个月,美国数个州议会相继推出了限制女性堕胎的法案,包括上周阿拉巴马州议会通过了法案,几乎禁止所有堕胎,除非怀孕对孕妇产生生命威胁,因强奸或乱伦造成的怀孕也不能例外。密苏里州议会也在周五通过了反堕胎法案,称只要有胎心跳动即不能脱胎。
两个法案引起激烈的争议。一个好奇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不同州都相继推出如密苏里州的胎心法案呢?为什么是“胎心”作为禁止堕胎的标准呢?在美国,关于堕胎或女性堕胎权的争论往往将人们划分为针锋相对的两个阵营:生命权派(pro-life)和选择权派(pro-choice)。除了奇怪的得克萨斯州,pro-choice表示支持公民选择枪支的权利以外,pro-choice一般指的是支持女性拥有选择是否进行堕胎的权利;相反,pro-life一方认为,因为未出生的胎儿拥有生命权,所以不允许女性随意进行堕胎。这样的框架下,关于堕胎的争论就被重塑为关于女性和胎儿之间的权利冲突。所以,选择“胎心跳动”作为禁止堕胎的标准,也是如此塑造争论的选择。
但这样的重塑,合理吗?
胎儿的生命权
在《纽约时报》去年底关于堕胎的系列社论中,有一个案例很值得再次讨论。在2008年,怀有五个月身孕的Katherin Shuffield不幸被枪支击中。Shuffield最终幸存,然而她却悲剧地失去所怀的一对双胞胎。这一案例掀起激烈的讨论。持枪者Brian Kendrick该被控什么罪名?如果以伤害罪甚至杀人未遂指控他,那死去的两个胎儿该如何对待?最终,Kendrick被控谋杀两个胎儿。
在这一案例以后,不少州开始加强关于杀胎的法律,将杀胎视作谋杀或过失杀人。我们似乎有这样的直觉,如果单单只以伤害罪惩罚犯人,失去的胎儿并不能获得正义的对待,理由正是,似乎有一种更强的权利要求更强的惩罚。于是乎,胎儿的人格生命权,就被引入来解释我们的直觉。只有我们相信胎儿具有生命权,杀死胎儿才能被视作谋杀或过失杀人。
这样的直觉,似乎也就出现在我们关于堕胎的权利冲突的讨论框架之下。因为胎儿具有生命权,所以,堕胎时杀死胎儿,自然就是侵犯了胎儿的生命权,于是堕胎就成为了女性对身体的选择权与胎儿的生命权之间的冲突。
关于胎儿是否具有生命权的讨论已经有很多,也得到很多的公共关注。因为本文的关注目标是这种对堕胎的争论的重塑是否合理,我们在此就不详细讨论。但有几点,应该值得我们注意。首先,作为法律后果,赋予这种意义的胎儿生命权,甚至可能让怀孕的女性受到严重的惩罚,尽管她没有选择堕胎。比如,当医生建议孕妇多卧床时,她简单出门购物,回来时流产了,这甚至可以被视作罔顾胎儿的生命权导致的误杀。我们会认为这是过分严重的惩罚,甚至是毫无理由的惩罚。
另外,上述案件中,并非只有设定法律上的胎儿生命权才能解释我们的直觉。我们可以将对孕妇的伤害视作特别伤害,尤其是对胎儿产生伤害的时候,这些行动可以被判作对孕妇的特别伤害罪,给予更严重的惩罚。受伤害的仍然是孕妇的身体,权利的主体依然是孕妇。这既符合我们认为需要重判的直觉,也避免了上文提到的过分的法律后果。事实上,科罗拉多州议会正是采取这样的策略,拒绝承认胎儿人格权(fetal personhood),在2003年通过法案,将伤害孕妇的妊娠定为非法终止妊娠罪,最高可判罚32年监禁。这意味着,设定胎儿人格生命权实际上并非必要。
权利的冲突?
不过,我们大可先设定,胎儿真的具有生命权。在反对堕胎的生命权派看来,胎儿的生命权与我们的生命权是一样的,即便女性对自己的身体具有自主权,生命权是比身体自主权更强更基本的权利,所以在两者冲突的情况下,也就是堕胎的情况下,生命权优先与孕妇的身体自主权,所以堕胎是不允许的,因为堕胎侵犯了胎儿的生命权。
关于堕胎的争论如此尖锐,大多数情况下在于双方在两种权利的冲突下无法退让,仿佛两种权利在互相竞争。然而,把堕胎塑造成两种权利的必然冲突,在讨论中争执谁更优先,可能是有问题的,恰恰掩盖了重要的可能:在堕胎的例子里,个人的生命权与身体自主权其实根本没有冲突。美国哲学家Judith Thomson的名篇《为堕胎一辩》(“A Defense of Abortion”)提出了著名“捆绑的小提琴家”例子,正是要说明两种权利并无冲突。
Thomson让我们设想这样的例子。假如睡醒的时候你发现自己跟一位著名的小提琴家绑在一起,身上都插着管。医生表示,只有你的血型与小提琴家一致,如果不把你们连管的话,小提琴家就会死。不过你不用担心,只要九个月,小提琴家就可以痊愈,到时你也可以离开了。如果你现在把管拔掉,小提琴家就会死掉。此时的你,应该被允许拔去身上的管吗?
应该很难说明,为什么你不允许被拔去身上的管。在这个例子里面,我们并不需要否定小提琴家的生命权,而是,小提琴家具有生命权本身,并不能够推出,她拥有其他人为她提供自己的身体供其使用的权利。就算这时候,你选择了继续提供自己的身体来帮助小提琴家痊愈,这并不是因为小提琴家的生命权本身,而是出于你的慷慨,更重要的是出于你的同意。也就是说,小提琴家的生命权本身并没有产生对你提供身体的义务。一个人的需要未必是她可以宣要的权利,特别是涉及他人的时候。
同样地,小提琴家的例子与堕胎的例子是相似的。从胎儿怀上到出生,她的各种需要都通过怀孕的女性来提供。女性提供胎儿所需要的东西同样也会让女性承受十分大的代价成本。所以当女性坚持怀孕到生出孩子,女性就像上述例子中的“你”,慷慨的选择了提供这些胎儿的需求。但这完全不等于说,胎儿的生命权本身就蕴含了女性如此这般的贡献。另一方面,选择结束妊娠的女性,也就像上述例子中的“你”选择不再为小提琴家提供帮助,这并没有违反道德的要求,因为在道德上,胎儿的生命权不蕴含女性如此的义务。甚至就算胎儿的生命权和你我的生命权同样重要,女性也没有这样的义务。
所谓生命权与自主权的冲突,可以说实际上是误会了两种权利的内涵,特别是胎儿生命权的内涵。假设我们承认胎儿具有生命权,但这不等于保证拥有使用或继续使用他人身体的权利。Thomson的论证也称为“好撒马利亚人”论证,借用圣经中好撒马利亚人的典故。一位撒马利亚人在途中遇到受伤的犹太人,尽管两族人世仇隔阂,但是撒马利亚人还是救助了犹太人,而且施予了极大的帮助。一个极好的撒马利亚人可能会是在那个犹太人被强盗袭击的时候挺身而出,我们会认为这是做了超义务的行为,而基本好的撒马利亚人,可能就是帮忙报警,可以的话施予救助。这算是道德上的基本要求。
在怀孕的过程中,女性需要付出很多代价,如果女性自愿选择继续妊娠,这当然就是一种好的撒马利亚人的做法,甚至是极好的撒马利亚人的做法,如果我们要赞美母爱的伟大。然而,要求女性都成为极好的撒马利亚人,这是有问题的,道德上说不过去的。同样,法律也不应该如此提出过分的要求,正如法律不能要求在一个人在犯罪发生的时候必须挺身而出,甚至都不要求必须去救助受伤的人,那么法律就不应该要求女性在怀孕的时候必须做好的撒马利亚人的行为,更别说要求做极好的撒马利亚人了。
所以说,当我们把堕胎的争论塑造成生命权与自主权的冲突的时候,我们会混淆两种权利所包含的内容。Thomson的论证,就是要反对这样的论述框架,并且反对,当堕胎杀死胎儿时,堕胎侵犯了胎儿的生命权。事实上,生命权派的如此论点,预设了胎儿生命权过多的内容。没有我们的同意,生命权不蕴含女性必须提供自己身体的义务。
自愿的性行为就是自愿选择生育?
为了反对女性对自己身体的自主权,通过禁止堕胎法律的州议员甚至会提出各种莫名其妙的理由。比如密苏里州的共和党州议员Barry Hovis表示,就算是强奸,有些强奸是互相同意的强奸,所以也不能允许堕胎。尽管事后他辩称并非“互相同意的强奸”而是“互相同意或强奸”,至少没有说清楚。
先不理Hovis的奇怪辩解,似乎就算承认Thomson的论证,反对堕胎者仍然可以认为,在自愿发生性行为的时候,女性知道性行为可能会引起怀孕,这时候她仍然选择进行性行为,这就表明她默认同意了其后的怀孕中提供胎儿支持。所以,既然同意了并且涉及到了胎儿的生命权,女性就不能随意进行堕胎。这个同意等同于女性放弃了身体的完全自主权。
回应这一类反驳的关键是,只愿做出一个行为,并且能预见其后的结果,并不能充分地说明一个人给出了对此结果的默认同意。要说明这一点,科罗拉多大学哲学系教授David Boonin在《为堕胎辩护》(A Defense of Abortion)给出了一个有趣的例子。设想一下两个人,Bill和Ted去餐厅就餐。Bill在吃完之后,从口袋里拿出钞票放在桌上,然后去买单离开。服务员收拾餐桌的时候将Bill留下的钞票视作小费收好。而Ted就餐的时候,觉得钞票在口袋里不舒服影响就餐,于是把钞票先放在餐桌上。假定有朋友简单,提醒他说他可能走的时候会忘记钞票,然后服务员最后会当作消费收起。Ted听了,甚至没有做任何的提醒措施。最后就餐结束,Ted果然忘记了放在餐桌上的钞票。离开餐厅之后Ted才发现忘记了钞票,于是回到餐厅进行商议。
在Bill和Ted的例子里,两人都自愿地把钞票放在餐桌上,都可以预见到服务员可能会把留在餐桌上的钞票视作小费收好。Bill的例子里,他当然是默认同意放弃钞票的所有权了。但是在Ted的例子里,我们似乎并不能充分地说他给出了默认同意放弃所有权。或许,当一个人自愿做行动引起这一结果的时候,她就算给出了同意。然而,一个人在自愿做出一个行动,并且可以预知这个行动可能引起的结果,并不能够得出她对这一结果的同意。两者有着细微却十分重要的区别。这个差别就是要说明,自愿做行动、行动引起了结果、能够预知结果发生,三个要素加起来也不能充分说明个人给出了对结果的默认同意。
在怀孕的例子里也一样,女性主动或自愿与一个男性发生性行为,并且可以预知这可能会引起怀孕,并不能够认为这等于她给出了对怀孕这一结果的同意,因为我们很可以认为,她并不是主动要引起怀孕。这跟主动寻求怀孕是不同的两回事。所以,当女性发现意外怀孕后,立刻尝试终止妊娠,其实就如Ted想起钞票留在桌面后马上回去商议取回一样。对她们来说,发生的是一个预见到但是并非有意而为的结果。既然如此女性主动或自愿发生性行为,并不能够表明,她同意承受其后(意外)怀孕的所有负担,正如Ted没有同意承担钞票被当作小费收走的结果,更加不能说明她等于默认同意放弃部分的身体自主。反对堕胎一方的回应,认为女性主动自愿发生性行为,所以不应该允许堕胎,这样的回应是无效的。
这样的回应也预设了一种极有问题的社会文化,在这种社会文化里面,女性的性被看作只有生育的目的,而女性的性主体被彻底掩盖。只要是女性的主动/自愿性行为,这种社会文化就将这当作女性进行了以生育为目标的活动,完全不将女性的主体性当作考虑因素。所以反观起来,承认女性的性主体地位,我们就应该注意女性的实际同意以及默认同意的满足条件。既然自愿行动、引起结果、能够预知都不是充分条件,那么就就应该警惕这种反对堕胎,要求女性将性行为等价于生育行为的社会文化。
避免陷入错误的权利冲突争论
如果Thomson的论证以及Boonin的回应是有效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当下流行把关于堕胎的争论塑造成胎儿生命权与女性自主权之间的冲突,其实是有问题的。这种重塑争论,某种意义上是用来模糊在堕胎中可能出现的其他问题,比如在当下社会中,女性在性方面自主权的缺失,社会在性方面对女性地位的不尊重,怀孕中女性事实上承受的巨大负担和伤害,等等等等,这些其实都应该是在堕胎的讨论中给予重视,是支持或反对堕胎的重要因素。单单只谈胎儿生命权与女性自主权的重复,无法理清堕胎在道德和法律上所会引起的难题。
既然胎儿生命权与女性自主权本无冲突,我们就应该避免陷入这种错误的权利冲突框架,而是更认真地聆听女性在怀孕、在选择堕胎中的真实过程和经历,而不是像阿拉巴马州议会中25名白人男性决定了女性不能拥有选择堕胎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