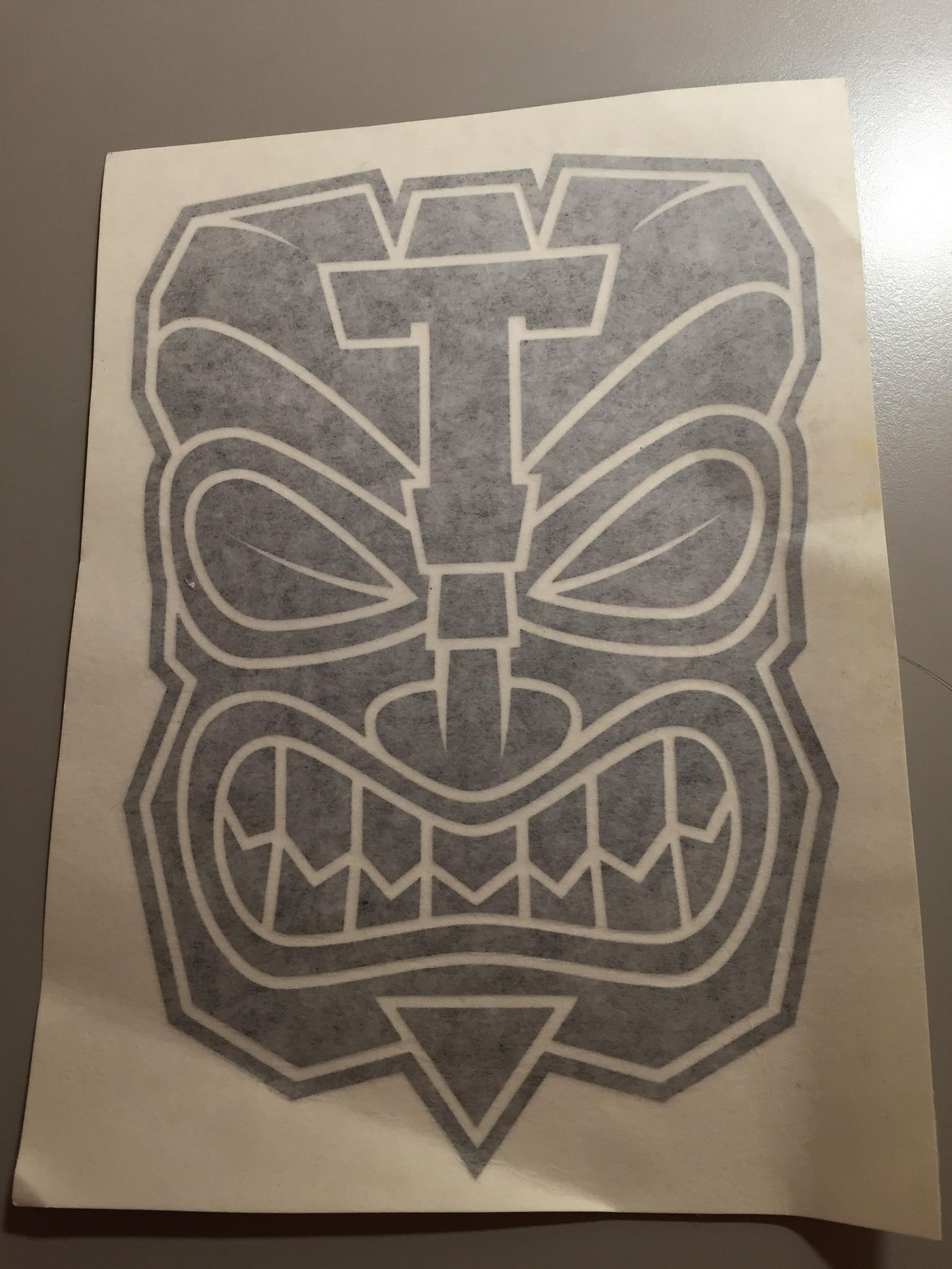長春
18 September 2017
寫在三萬英呎的高空,我坐在飛機的中後段,周圍嘈雜的人聲,已分不清台語還是東北話。今天上午九點十八分,走在瀋陽的主幹道十一緯路上,空襲警報響起,然而道路依舊車水馬龍,行人們講著手機,交警攙扶一個老人過馬路,讓我不禁想起,這是一個如何值得銘記的日子?
如果沒有日本與中國的戰爭,外祖父不會從軍成為飛行員,也不會因為一場空難英年早逝,甚至可能追隨他的兄長,憧憬一個積極改革的社會加入共產黨而留在中國大陸,外祖母也會完成在北京的大學學業而不會跟隨外祖父搬來台灣。又或許,少了這些複雜的外界因素,母親的生命也可能有所不同,會嫁給她婚前的那個日本朋友。
但歷史就是一連串的偶然與不可複製。去年在新疆伊寧遇見的A,父親因為是黑五類隱姓埋名於邊疆,這樣的家庭背景,讓A對於來自台灣的我特別好奇。
國家認同常常是個虛擬的議題。比方說,我們的祖輩當年從閩粵之地乘船東渡,但假若他們的船被風吹到了更南邊呢?試想看看,菲律賓的宿霧,新加坡,台南府城,下緬甸仰光,越南西貢… 這些地方都是當年大批閩粵移民移居海外的第一個落腳處。隨著祖輩們下船地的不同,我們今天的生活又會有什麼變化?齊齊哈爾的C也是這樣想的,他甘願做一個全年無休的環衛隊員,因為那能給予他退休金和醫療保險的保障;但是他也想過,如果他的父母像他的姨一樣,選擇在四九年隨國民政府搬來高雄呢?現在的他是不是就可以像我一樣,有錢和時間來旅行?
今年四月我參觀了廣島的平和紀念資料館,那是一個極為催淚的地方,無分膚色許多遊客淚流滿面,在喚醒人們對於和平的期盼上是極為成功的。但令人詫異的是,這樣的一個博物館卻缺少了歷史的縱深,對於戰爭前的背景及軍事衝突的過程隻字不提,難道如此是對於記憶的最佳註解?
這次我驅車前往距哈爾濱市區尚遠的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這個在哈爾濱平房區樹立起的博物館,其實留下的當年建物並不多,因為日本軍隊在離開中國前已炸毀了大部分實驗設施。令人感慨的是,當年主事的科學家多在第一時間逃回日本,躲避了軍事法庭的審判,並紛紛擔任各著名大學醫學院、製藥公司、綠十字等機構的重要職位;相較之下,這次我也經過了內蒙古的葛根廟,當地除了有一座東北地區最大的喇嘛廟之外,其實在1945年還發生了葛根廟屠殺事件,據信近千名未能在第一時間返回日本的關東軍軍屬及開拓團,在逃亡到葛根廟一帶時被蘇聯紅軍及東北抗日聯軍掠奪、姦淫、屠殺,此外也有不少關東軍和滿洲國官員被流放並死在蘇聯伯力的勞改營中;相較那些戰後享盡榮華福貴的人體試驗決策者,令人不勝唏噓。日本政府的不願面對史實,是否也是造成這些悲劇歷史事件刻意遺忘的間接推手?
當然,歷史沒有絕對的對與錯,多年前拜訪胡志明市的戰爭遺跡博物館(舊稱中國與美國戰爭罪惡館),似乎又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定義所謂的受害者與加害者。每次旅行所獲得的生命經驗積累,讓我有機會逐步拼湊所謂的歷史全景。
回到個人,其實才是最令我感興趣的,那是長春的T。
真正開始注意長春,是去年偶然讀到中山大學辛翠玲教授所寫的一篇文章,後來又去買了日人遠藤譽所著的「卡(ㄑㄧㄚˇ)子:沒有出口的大地」。這本書寫的就是1948年長春圍困戰的歷史,而這個事件,緊緊圍繞著我在旅行中所遇到兩個長春人的家族生命經驗。
我在內蒙阿爾山的旅行其實是不太快樂的,因為當時的我還不熟悉大陸熱門景區的經濟生態,服務業與顧客病態的共生關係。在阿爾山的最後一天,我索性花大把銀子去當地民眾幾乎不去的中國溫泉博物館泡湯,偌大的博物館裡當晚只有六個顧客,我用了將近三個小時的時間與其中兩位訪客深度交談,其中一位哥(東北人喜歡這樣親暱的稱呼)正是老長春人。「我母親就是圍城的倖存者」「其實國民黨不像我們電影裡演得那樣壞;那個非常時期他們和我們一樣餓到沒東西吃了,一戶戶敲門拜託賞口飯吃」「你看看長春城裏漂亮的建築,哪個不是日本人留下來的?當年新京可是超過東京,是亞洲的第一大都市啊!」
後來我乘坐綠皮火車,沿著日本人留下的森林鐵路,經過內蒙古興安盟的首府烏蘭浩特,再轉搭八月剛通車的長白烏高鐵,抵達了不太算是旅人目的地的吉林省會長春。T是我在北國春城新認識的好友,透過他的解說,我眼下的東北風景又有了另一番詮釋。T的祖父在日據時期是個大學生,精通日語,卻因為異議思想被日人關進牢裏;後來國民黨來了,這個坐過日本人牢的經歷讓他備受禮遇,但不久共產黨也來了,T的祖父買了一張到台灣的船票,他打算先熟悉一下新環境,再將母親、夫人、及孩子們接來台灣,但他不曉得接下來要面對的竟是四十年的天人永隔。曾經有一段時間,大陸與香港間的流通還是相當程度地自由的(這也是我的great uncle的逃亡路線啊,那又是另一個故事了),無奈T的祖母一人帶著孩子們在圍城時逃到四平後,不久就精神崩潰了,再也沒能帶孩子們到台灣與T的祖父相聚。後來T的祖父在台灣成為國民大會代表,眼看返回家鄉無望後,或許是出自政治的考量又與一位女國代另組家庭;T的祖母則是在生病後,孩子們不得不輟學、提早學會自立更生。我從未問過T,但或許這也是那個階級鬥爭的動亂年代惟一可能的生命出口?
我看著T,一個年齡與我相仿的男生,曾經因為我們祖輩不同的生命抉擇,讓我們的父母輩各自擁有迥異的生命體驗,任何交集在當時都是難以想像的;然後,到了我們這代,T和我都成為研究生畢業,專業認證都是我們想要立足於各自社會體系所必備的工具;雖然我們的家庭、社會、與工作煩惱有或多或少的差異,對於相同一件事物也可能有各自獨特的在地稱呼,然而全球化的腳步卻是一刻也沒有停下來。曾經有一個長春居民對我說:「戰爭難免有傷亡啊!我們現在需要的是快速發展,不會去想那些在圍城中死去的人們。」生活在同一座城市,T對於這種說法憤憤不平,他說,沒有人是白活的。
我想,是人類最原初的心靈悸動及善惡分辨讓我和T能夠無礙地對話。曾經在不遠的過去仍是絶無可能的,今天,我們相遇在一座上個世紀從無到有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