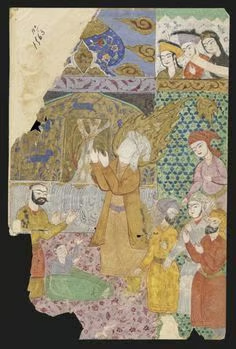詹卢卡·迪迪诺:抑郁现实主义
抑郁现实主义
詹卢卡·迪迪诺/文
王立秋/译
Gianluca Didino, “Depressive Realism”, 原发表于数字期刊Inspire the Mind,https://www.inspirethemind.org/post/depressive-realism。经作者和期刊授权翻译,译文仅供学术交流,请勿作其它用途。
在五、六年前,有一段时间,我对哲学上的悲观主义很感兴趣。那种认为用阴暗的眼光看生活实际上可以让你感觉更好的想法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也探索了这方面许多不同的,有时相互冲突的立场和观点——从作为悲观主义的早期形式的佛教,到西蒙·克里奇利的新存在主义。在一个一头奔向气候灾难或技术自我毁灭的世界中,在智识上“栖居于所有可能世界中最糟糕的那个”,在我看来实属明智之举。
我是一个从事非虚构写作的作家,在我的作品中,精神健康问题一直很重要。但很快,我就清楚地意识到,我对哲学悲观主义的兴趣不只是理论上的。不难猜测,那段时间也的确算不上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我几乎一直觉得很丧,有时甚至会陷入彻底的抑郁。也正是在一次探索“虚无土地”之旅中,我第一次遇到了所谓的“抑郁现实主义(depressive realism)”。
这个概念是两位美国临床心理学家,劳伦·阿洛伊(Lauren Alloy)和琳·伊芳·艾布拉姆森(Lyn Yvonne Abramson)于1979年提出的,当时她们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合作。阿洛伊和艾布拉姆森的研究领域是情绪障碍,比如说抑郁。
在一项144名抑郁者和144名非抑郁者共同参与,后发表于《实验心理学学刊》的研究中,她们发现,在她们要求研究参与者对现实做出评估的时候,抑郁的个体的看法更准确,而没有抑郁的个体,则往往会高估自己掌控外部世界的能力。
换言之,他们认为,在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掌控自己的生活环境这个问题上,抑郁的人更加“实事求是”。与没有抑郁的、经常过于乐观的人相比,“做最坏预期”的倾向使抑郁的人能够对现实做出更好的判断。
阿洛伊和艾布拉姆森的目标,是理解抑郁的生物学机制,她们的研究并无哲学底色。但从哲学的观点来看,其含义是明确的:看起来,抑郁有助于人“如实地”、而非一厢情愿地理解现实,叔本华——一位超-悲观主义的哲学家——势必也会完全赞同这个想法。
而且,抑郁现实主义这个概念也响应了在阿洛伊和艾布拉姆森研究出版一年前提出的另一个有趣的心理学假设,即所谓的“波丽安娜效应”(Pollyanna Principle),亦称“积极偏向”。
在1978年的同名著作中,认知心理学家玛格丽特·W.马特林(Margaret W. Matlin)和大卫·J.斯唐(David J Stang)认为,人对积极事件的记性比对消极事件的记性,而这反过来又意味着,人更可能把自己的行动和信念,建立在对现实的过度积极的感知的基础之上。
“波丽安娜效应”和“抑郁现实主义模型”都肯定了同一个核心哲学观念,那就是,除非我们在临床上抑郁了,否则我们倾向于把现实理解得比实际情况更积极。
因此,抑郁不再(或至少不只)是一种使(行动)无效的情绪障碍,它也是一扇门,通过它,我们得以窥见“现实本身”。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些想法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临床实验心理学领域。但在新世纪,随着哲学上的悲观主义开始显得好像是面对我们艰难时代的挑战的有效方式,这些想法又开始重新出现并逐渐脱离了起初的学术语境,被应用到像政治和文学那样的多样的领域。
举几个例子来说。人们会联系法国作家米歇尔·韦勒贝克的作品(它描述了社会和性达尔文主义的压抑现实)和克里斯汀·斯摩伍德的处女作《心智生活》(用贾·托伦迪诺的话来说,它描述了“我们想的和我们实际上做的之间的深渊”)来讨论抑郁现实主义。虽然没有直接提到抑郁现实主义,但托马斯·利戈蒂的《反人类阴谋》显然也共享抑郁现实主义假设的核心观念。利戈蒂很可能是我们时代最有影响力的恐怖作家,他笔下古怪、机械的世界源自于抑郁视角看生活的“思想的零度”。
我不否认,那种认为抑郁是一种看待现实的优势视角,认为抑郁能够以更清晰、更“客观”的方式来看现实的想法,在当时——差不多就在我对哲学上的悲观主义萌生兴趣的时候——的我看来颇具吸引力。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依然为之所吸引: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悲观主义是一种理解当下、并在智识和政治上对之做出行动的有效工具。可这些年来,我越来越相信,在这种被泛化的抑郁现实主义观念中,隐藏着可能带来危险的潜台词。换言之,抑郁现实主义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建构。
我发现这点很重要:抑郁现实主义和波丽安娜效应假设都是20世纪70年代末在美国——也就是说,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诞生的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出现的。在英国,最早把新自由主义经济和“现实主义”观念关联起来的,正是玛格丽特·撒切尔。众所周知,撒切尔说,资本主义之外“别无选择”,也就是说,“现实主义”的人不会梦想另一个世界,更不会为之而斗争。文化批评家马克·费舍把这种压抑的社会变革观恰当地称作“资本主义现实主义”。费舍一辈子都在和抑郁斗争,并最终于2017年轻生。
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在研究抑郁者的现实主义的时候,阿洛伊和艾布拉姆森是在制定什么政治计划。但当时的时代精神,可能的确影响了她们的研究兴趣,或至少,她们的发现助长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政治氛围。尽管如此,撒切尔自我实现的预言还是成为了现实:数十年来,抑郁一直在增长,并且已经有充分的理由表明,抑郁人数的增长,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与资本主义及其后果(如气候变化)相关。这也正是马克·费舍一辈子都在论证的观点。
把抑郁当作看待世界的“优势”视角——仿佛抑郁的人更客观——可能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会使我们认为,我们必须接受在当下的政治和经济系统之外“别无选择”。
在我们的哲学工具箱中,悲观主义可能是一个有用的工具:它有助于我们看到令人不适的真相。在气候灾难和大规模灭绝的时代,作为一种思辨实践——也就是说,想象我们的行动可能导致的最坏结果并在为时已晚之前对之做出行动——悲观主义可能是必要的。
但“思考可能的世界中最坏的那个”不应妨碍我们“为未来想象一个更好的世界”。
它不应成为阻止社会变革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