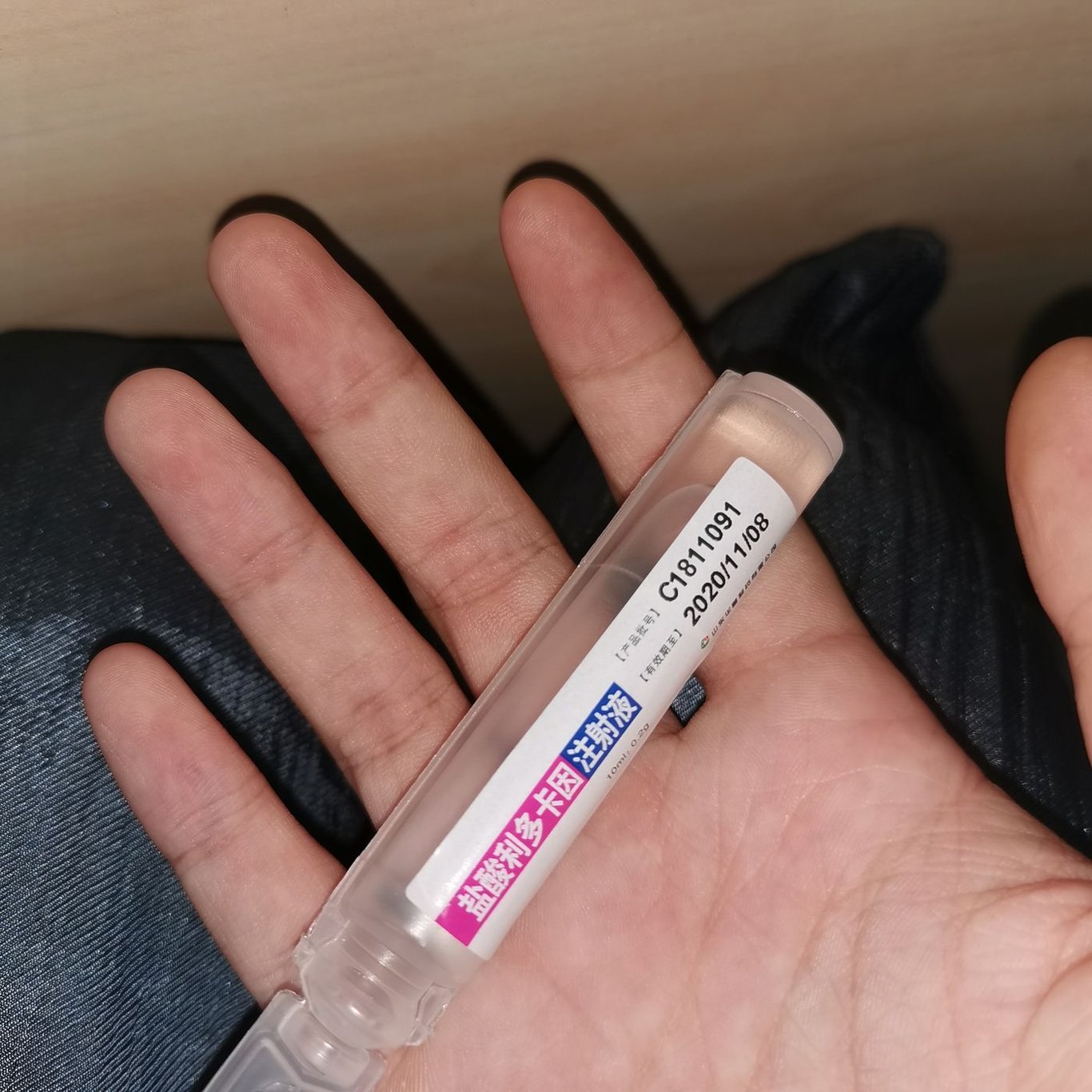非论文写作 01
“非论文写作” by Sane 你可以把这看作是一个专题,这是第一篇。 关于情境的描述,意淫的抽象,或是一切与规范的、逻辑清晰的、精英主义的词汇相悖的写作。我永远无法将它们组织于理论文章中,也同时无法将理论嵌套在碎片化的气味里。讲述故事是被允许的,但是它们却又无法成为“故事”,这其中的内容都是非虚构的,但碍于个人的有限能力,我暂时不会将此称为“文学”。

情感素/Affect
十月,跟导师吃饭。连同几位同门。席间谈到一篇关于Affect(情感素)的文章,大抵描述一种情境。如果关于性少数者,或少数者面对大多数人时的尴尬,相伴着是在同类中找到互相慰藉的信心。这种信心或是安稳、瞬间的精神富足、彼此确认,大抵就是所谓的Affect。
一月,参加一场工作坊。文化研究的学者提出命题,“描述你觉醒到你自身性倾向的瞬间”,一个女孩写下:“她一定是太漂亮了,所以我色灵智昏”。大家都笑了。我很喜欢这个词,“色令智昏”,类同喜欢大多数成语,用严肃的最精简的文字,描述最微妙的场景。
我意识到我突然想要变成她,或者将要变成她,或这是在归家日无端气馁的源头。
离开上海时,收到她的消息,而非常难过。
因为被睡眠困扰而几乎误机,加上飞机落地后堵车2h的换乘——我认为这就是让我不要回家的信号。2020年(农历新年意义上的)是奇妙的,大多数时侯,我希望依靠直觉让“奇妙”继续。直觉引导我掉入爱丽丝的洞穴,直觉引导我仔细查探她的过往。
夜里,同样的睡眠障碍。我开始看她的微信,检索她的信息,想了解她的故事。看她的照片,每一条动态,从2020年,到2016年。双指放大,再缩小,再放大。记住她的昵称,她的“艺名”,她的账户id,她的真实名字。
突然间我产生一种幻觉:在我们第一次认识时,这些图文——某种意义上非常“不精致”的图文——早就与我邂逅了。强烈的所谓Deja Vu,和匪夷所思伴随着。双指放大,再缩小,再放大。图片太过不清晰,不对焦,不明亮,不精致,没有滤镜,没有pose,没有刻意的涂画。放大,缩小,再放大。没有隐秘的宣告,没有精心构想的文字。而这些我大概已经见过:2019年,她发过一组穿水手服的照片,而今天再看,这实际是2016年发布的;2018年,她发过一双黑色的皮鞋搭蓝色长筒袜,而今天再看,这双鞋子在她2019年才出现。
我还发现,她一直是这个发型,维持了四年没有变过——当然,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发型。
我还发现,她多年前的搭配,到今天见到时还是同样的,因为,她拍了照片。
我发现她去过我去过的地方,去过我想要去的地方。她几年前穿着与我现在类似的裙子、长靴,类似的皮鞋,长筒袜,她几年前出现在我现在喜欢出现的地方,还有那些地方隔壁的熟悉的夜宵店。
我突然产生的幻觉,也许今年31岁的她,是多年后的我。
所以我意识到我突然想要变成她,或者将要变成她。
这可以被允许吗?我们是真的居于“不同的世界”吗?我从未对她,和她们抱有的想象,是站在冷漠的距离上的。就像第一次拒绝她的邀约,在于认为我们不会再相见的笃定。虽然事实仍旧可以通过“直觉”解释,但似乎直觉并不能够占据全部。
但这些又有什么要紧呢?在每一个深夜,蛛丝马迹都尤为脆弱,而我只是抓住了那个游动的信号,它说着我的失望和后悔:希望跟她呆在一起,尽可能多的时间。而可能我们共同渡过一个除夕,在危险的病毒和细菌中,故事就一定会发生变化,我与她一定会发生变化。
这超过了我对大写的“研究”、“学术”、“理论”、“写作”的追求,甚至我可以大言不惭地承认,我对这些从来都没有追求。我只是喜欢小写的“故事”和“秘密”。我当然是一个,非常不合格的研究者了。
迷恋不同的人,迷恋不同的故事。迷恋她,迷恋她恰恰给我的最好的反馈。一次次地,我总在认为巧合出现在我们之间。反复地确认这些“巧合”并不是她兜售的把戏后,迷恋会加深,最后成为故事的粉墨。
她就是那一天在路边,上海的夏天,抽香烟,穿长裙,白丝袜。
我想要进入她的生活,我甚至能感受到,她在向我招手。
最后,这些幻觉、想象、和那些曾经的词汇都聚集在一起:我又想起那个“色令智昏”的女孩了,想起Affect那篇晦涩难懂的文章,想起无法描述的情绪。情感素。如果我们形而上地去追踪运用一个理论的“程序正义”,那么我这之前的所有文字都是徒劳。而拒绝关于“理论”理解中的碎片,也是一种微妙的冒犯——但所有的冒犯都是聪明和侥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