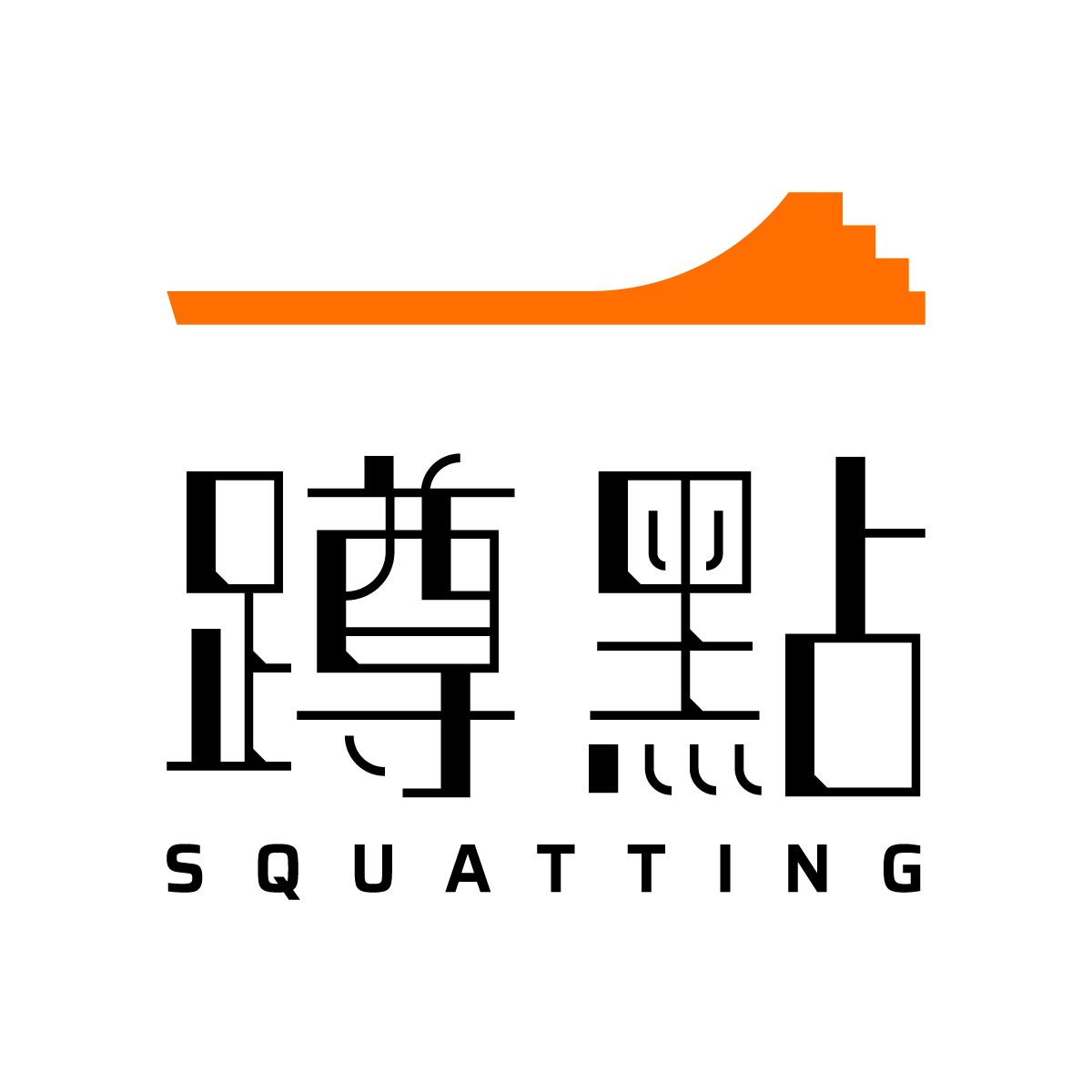左翼在運動中的姿態問題

編按:蹲點此前的「反送中一週年專題」始終關懷的問題是:左翼知識分子如何以自己的方式介入運動,而不是始終保持一種批判的高姿態做「冷氣軍師」,同時亦不隨波逐流、陷入與民粹主義的共謀?本文從理論層面做出了富於啟示的回應。
文 / 駱斯航
轉載自作者個人網站,原標題為:姿態問題
<姿態問題>一文寫於去年十一月。文章的寫作動機源於反送中運動中左翼知識分子,尤其是中國大陸左翼知識分子的尷尬處境。左翼知識分子學院化的批評,時常體現象牙塔內的「批判的武器」面對現實政治實踐中的「武器的批判」的無力感。學院的知識會滯後於現實政治的發展,學者如果濫用故紙堆中的理論知識,不僅刻舟求劍,也容易將自己置於高高在上的評判者的地位上。但反過來,缺乏理論作為線索的歷史,只能以堆砌事實的方式存在;缺乏理論作為線索的政治實踐,塑造議程的過程則更難以自覺,也更容易被切身感壓倒,失去在具體戰術層面之外反思運動策略的空間。文章試圖在左翼的話語資源內部探討知識分子這一身份在社會運動中所面對的張力,以及可能的應對策略。
正文:
左翼社會評論的姿態問題,在不同場合經常被討論。知識分子切忌在並未對抵抗運動做出實質貢獻的情況下覺得自己做了很多重要的事,把抵抗景觀化,這只會讓付出風險在抵抗的人無處容身。知識分子也不應當把自己的理論武器當作高高在上不可觸犯的佛像,否則批判性知識分子也就只不過是撞鐘的和尚而已。
學左翼理論不是為了塑造一個高高在上的神壇,讓自己站上去俯瞰眾生的。一旦理論變成神壇,只會生搬硬套理論的知識分子就難免傲慢地用理論的框架來鞭打和否定現實社會裡的種種不完美的實踐。而政治實踐總是不完美的,總是有風險也有缺陷的,永遠不會有一個讓左翼知識分子精神上完全滿意的實踐。墨守成規的左翼知識分子只會固步自封,空有精英主義的姿態,實際上在政治上極端無能。這還是相對好的情況。更嚴重的情況是,如果固步自封的左翼精英占據抗爭話語的話語權,那麼他們會霸占左翼話語的大量資源,使真正在一線的行動者無詞可用。這點上就不展開了,實例可以參見中國大陸的一大批國家主義左派。在冷戰期間的各個社會主義國家以及冷戰後轉型民主化的後社會主義國家,這種情況其實都有(參見Raymond Taras (ed.) , The Road to Disillusion: From Critical Marxism to Post-Communism in Eastern Europe)。哪怕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知識分子占用抗爭話語的現像也不能說罕見。
不管從哪個政治立場出發,每種從現實出發的社會批評都有精英主義的風險,但對於左翼來說這個風險尤其大,因為左翼往往以站在勞苦大眾身邊作為自己的立場,反對精英主義。如果左翼自己犯了精英主義錯誤,那看起來就動搖了自己的根本立足點,顯得雙重標准。因此左翼知識分子需要時時自省,需要不斷讓自己意識到,自己是自己所批判的社會現實中的一部分。自己作為知識分子,不僅帶有自身立場的利益和局限性,也擁有特權。換句話說,自認左翼的知識分子,永遠需要提醒自己精英主義的風險。
然而,「左翼知識分子的批判有精英主義的風險」這個批判只是姿態問題的一面。要更全面地理解姿態問題,就要理解這個批判的局限性在哪。如果沒有探討局限性,那「左翼知識分子的批判有精英主義的風險」 這個批判一樣也會被濫用。這背後的原因恰恰是因為所有反思都需要與社會現實拉開一點距離,哪怕是最從受壓迫的大眾的立場出發的反思,也需要這個反思的距離。
數十年前,無論是激進左派還是自由主義中間派都對社會中的受害人身份(victimhood)抱有一種懷疑。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這樣的激進左派曾在《傳統理論與批判理論》中指出,受害人身份保證不了受害者對自身所處的困境有真實的認識。因為既然人被壓迫,他的認知能力也可能受到限制,這本身就是壓迫的一部分。朱迪絲·施克萊(Judith Shklar)這樣的自由主義中間派則在《平常的惡》中說,受害人身份保證不了受害者在道德上的崇高地位,因為很多受害者搖身一變掌權的時候,做出和當初的施暴者一樣殘酷的事。
受害人身份保障不了知識,也保障不了道德地位,受害人身份能保障的是作為受害者所經歷到的、那些施暴者所經歷不到的事。他們因此有更厚重的生命體驗,也會成為潛在的反抗者。之所以受害者只是潛在的反抗者,而不是直接的反抗者,可能是因為他們尚未認識到自己被壓迫的本質;可能是因為他們尚未能夠正確地識別出壓迫的結構,識別出誰是壓迫他們的人(所以有可能做出無意義的殘酷暴行);也可能是因為受壓迫的他們,個人的力量是薄弱的。這就是為什麼社會需要左翼知識分子:稱職的左翼知識分子,會站到受害者的角度上,幫他們認清被壓迫的本質,幫他們識別壓迫者和壓迫的結構,幫他們連結起來,形成有行動能力的政治主體。
在左翼的視角裡,行動的主體是大眾,知識分子光憑自己的力量是代替不了這個功能的。但知識分子應該用自己的知識去和「大地上的受苦者」站在一起,去幫他們用受害者身份的理論建築行動的能力。這個「用知識和受苦者站在一起」的過程,不體現在「批評還是贊揚受苦者」這種膚淺的態度層面上,而是體現在能不能為受苦者提供他們不見得有條件獲取的知識。因而這個關係,永遠都是帶有一層精英主義的色彩的,只要我們假設,受害者不能輕易直觀地認清所有的壓迫關係,也不能輕易地自發形成反抗的力量——這種現像本身就是壓迫的一部分。但這種精英主義,是一種策略性的、有意識的精英主義(intended elitism),它要求知識分子有意識地利用自己在社會結構中的的某些優勢和特權,去為沒有這些優勢和特權的受苦者服務。
這層精英主義是不會被知識分子的反思和自省消解的,它植根於不平等社會的分工體系和再生產體系之中。如果反思和自省可以消解特權,那麼特權就不會成為特權。知識分子應該自省自己的精英主義立場,應該警示自己不要高高在上,應該主動從受苦者身上學習那些他幸運地沒有經歷過的壓迫和苦難。但他無法消滅這層精英主義,也不應該以消滅這層精英主義為目標。因為失去了這段反思的距離,他就失去了策略性運用自身特權來為受苦者服務的能力。如果一個知識分子這樣做,那他面對的是和開頭那種「為神壇上的理論撞鐘」的知識分子不一樣的一種風險:民粹的風險。他可以攀附上任何一種大眾中的主流觀點,聲稱自己永遠都站在大眾身邊,但絲毫不影響他對社會的結構性進步毫無貢獻。
總結來說,左翼知識分子的精英主義姿態問題,是個程度問題,而不是一個黑白對立的正義與邪惡問題。如果知識分子忘了自己總有一層精英主義色彩,那他很容易站到一個高高在上的理論高地上,硬搬經典理論來臧否現實社會裡的種種不完美的政治實踐。這樣的知識分子,政治上是無能的。但如果一個左翼知識分子某甲認為自己可以靠反省來消滅自己身上的精英主義姿態,從而達成 「始終和受苦大眾的立場和觀點保持一致」的成就,那這不僅是一種幻覺,更是一種危險的幻覺。對於受苦大眾而言,某甲沒有為他們提供知識分子本應提供的、超越他們局限性經驗的知識和力量。對於某甲而言,他獲得了一個左翼視角裡的至高光環——「始終站在受苦者身邊」。這層光環既可以成為打壓異見的緊箍咒,也可以成為個人崇拜的基礎。
這不影響知識分子本人同時也可以是行動者。抗爭不在書齋裡完成,讀左翼理論的目的是為了指導行動。知識分子可以有多重身份,可以自己參加組織工作,自己參與行動。但只要社會結構不完全平等,就會有一部分人因為更良好的出身和教育機會獲得一些更底層的人無法獲得的知識,知識分子的身份就始終會存在,姿態問題也就始終會存在。試圖抹殺自己身上的精英主義色彩,從而規避精英主義的道德風險,是一種自殘,也是一種自欺。對左翼而言,政治行動的第一目的不是規避風險(因為所有政治行動都有風險),尤其不是規避某個個人身上的道德風險。
霍克海默是批判理論家裡最常被指為精英主義者的人之一,但他骨子裡仍有一種民主派的底色。這種民主派底色不一定體現在政治制度的安排上,相反體現在教育理念上。左翼社會批評的民主底色,並不是體現在直接擁抱所有受苦大眾抱有的理念和常識,這是民粹。左翼反對知識分子的特權,但不反對知識本身。左翼社會批評的民主底色,體現在一種信念,一種堅信所有受苦大眾都能通過適當的幫助建立起自身的知識和信仰體系,來理解社會、理解他們自身處境的信念。這是民主教育的「信仰之躍」,用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話說,叫「人人都是哲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