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後:接近城市的權利
原本寫於北京時間2017年十一月北京市開始驅趕低階人口之際,徹夜無眠翻譯至凌晨,是寫給北京市民乃至全球市民的。現在,似乎寫給全2020年已封城或準備封城的市民也剛剛好。
本文翻譯自此書的第一篇。2017年是馬克思《資本論》一百五十年,列斐伏爾《接近城市的權利》(Le Droit a la Ville/TheRight to the City)發表十五週年。Verso出版社推出紀念文集,匯聚當代城市權利爭辯重要學者,討論我們時代最緊迫的問題:城市為誰而建?此紀念文集可在Verso網站免費下載 https://www.versobooks.com/books/2674-the-right-to-the-c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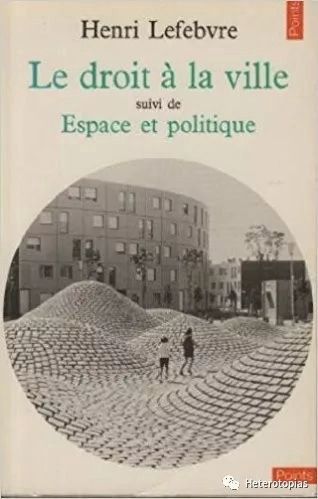
Fifty Years On : The Right To The City.
By Andy Merrifield
黃孫權譯
列斐伏爾《接近城市的權利》出版五十週年,他為城市生活要求更多的參與和民主之「渴望和要求」是所以值得慶祝和紀念的原因。在馬克思《資本論》發表的一百年後,1967年,他自認「隨意」的出版了《接近城市的權利》,將接近城市的權利視為人民企圖形塑自身認同的表現。他堅持參與使得都市生活成為戲,參與也使主動有潛能的市民能演戲。缺乏參與意味著城市死亡。
列斐伏爾生於1901年,永遠的民主派。在1930年代與超現實主義者共飲,與1940年代反抗運動並肩,1950年代在巴黎當計程車師傅,1960年代在多個大學教授哲學與社會學,與情境主義和Guy Debord成為同志。他是1968年學生運動教父之一。寫過六十多本書,引介黑格爾和馬克思進入法國,寫過無數有關都市論,日常生活,文學和空間的文章。遲至1966年他六十五歲高齡時才獲得學院穩定教職,1973年為了他的全球之旅而「退休」,他為了理解亞洲,拉丁美洲,洛杉磯的城市未來而寫作與演講,城市總令他痴迷和震驚。
列斐伏爾是邊緣人,他的接近城市的權利來自邊緣的觀點,目標在使得局外人成為局內人。
接近城市的權利有種模糊的人權概念,但有其具體內容。它要求人民有住進城市,在城市活著,與快樂活著的權利。有住的起房子,孩童能夠有適合的教育,能享受公共設施,有靠譜的大眾運輸。你的都市視域可寬可窄,與鄰居街道附近大樓結成同盟,或者超越他們。作為整體的都市是你的,你可隨意進出,探索,擁有,覺得自己就是主人般的按你所想。因此,參與不是將所有事情都政治化,你敲敲鄰居門,去聚會,同樣是你在都市中的歸屬,有著自己的幸福感。它意味著你有某種集體感,共享的目標,而非外於都市事務。
1960年代,列斐伏爾將接近城市的權利連結上「中心性的權利」,那時,他意思是地理學上的去佔據都市中心,因為市中心的房價居民無法負擔,晉紳化,成為遊客的景觀(如巴黎)。在美國則相反,市中心被棄置。富有白人急著逃離市中心,住到布爾喬亞的郊區去。城中心剩下襤褸碎片,無能移動者的居所。接近中心的權利要到90年代內城復甦運動後,開始驅趕窮人才開始有意義。
今天,我們要創造性的重構「都市中心性」,它是存在和政治的權利而非地理意義上的了。它表現一種慾望,人是自己生活的中心,發展的中心。可以簡單到讓鄰里成為可居的鄰里,如果位於邊緣的鄰里,那麼接近中心性權利就是使得邊緣成為存在的中心。
很大程度來說,世界絕大多數都市人口的未來是超越中心性概念的。隨著都市蔓延而無中心,至少難以清楚定義有其地理上的中心。接近城市的權利就是你可以留下的權利,選擇哪住的權利,能夠負擔你選擇哪住的權利,使得那裡成為你自己的。也是你接近中心的權利,任何地方你想存在,或你稱呼為家的地方,當外在世界背叛你,你願為之抗爭的精神慰藉根源。
1980年代,列斐伏爾堅信專業體制是參與的都市生活真正的敵人。他說,一個新的國家模式正在建立,市政法令很快就會被納進其中。他無法想像,在他1991年過世的後二十年間,他的猜想變得更真實更廣泛。而且他的先見之明:專業的「民主」已經再生產了自己的管理與統治傳統。毫不誇張的說,形式的市民權隨著實行這些權利越來越縮減。列斐伏爾說,市民權和歸屬管需要嶄新的視野, 1989年,一篇發表於《法國事業外交論衡》的文章〈當城市在全球變形中迷失〉(「Quandla ville se perd dans une métamorphose planétaire,」),他宣稱,「接近城市的權利意味著要有一個市民權的革命性觀念。」。
都市化過去是,現在仍然是一個「革命的」的過程。當今城市,各種統治階級扮演著治理的「革命性」角色。他們領頭驅動殖民和土地商品化的整體生產力。更甚,將民眾與自然價值化,好像瘋狂鑽井,從自然大地淘出利潤,對待人類本性亦然,從日常生活方方面面,從全面的公共領域中,淘出價值。
列斐伏爾沒想過都市化遍及各地,磚,機車,車道,高速高路佔據世界。當他說「星球都市化」時,他並沒有想到綠色將全轉為灰色。相反的,正如他紀念馬克思的《資本論》所暗示的那樣,他警告我們,戰後資本主義的特殊形式結束了,未來將不僅僅透過工業生產和農義生產模式累積,更多是透過空間生產本身。
系統將星球地理變成商品。純粹的金融資產,利用和濫用人與地方來累積資本,捲動所有人進入它的機制。都市社會被降維成可壓裂(譯注:通過向地下頁岩油氣層擠注水和沙子,使頁岩破碎釋放天然氣和石油)的空間單元之進步生產。
列斐伏爾對星球都市化最明確的觀點來自《法國事業外交論衡》的文章,死前兩年前所寫。他說「都市的星球化」的威脅在即。很明顯的,他不是指都市將蔓延整個星球,而是都市像漩渦一樣吞噬地球所提供的一切,土地與財富,資本和權力,文化和人民。
都市機器的劇烈動能使一切不穩定。一種能量和總體化力量,過程會產生列斐伏爾所謂的「殘餘」(residue)。隨著都市擴張,殘酷闊延吞噬了鄉村內地,同時也將不合宜與沒用的人驅除出去。
列斐伏爾觀察到任何大系統都會留下嚼碎殘渣。任何總體都會留下剩餘。這連結到《元哲學》(metaphilosophy)的概念,這是他研究傳統哲學,在《接近城市的權力》幾前年寫的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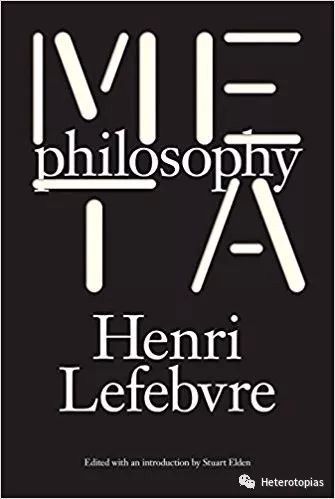
在《元哲學》一書,列斐伏爾認為總體化(totalization)就跟全球資本主義一樣,總顯露其裂縫,在結構與去結構中有內在衝突。總體化不是整體,有秘密和要排除它的他者-「殘餘元素」。總有人們是無法融入,不想融入,不允許融入全體的,他們是公制計算之外的,他們是哲學的反概念,剩餘的確定。
殘餘是人們在心中覺得邊緣,即便有時他們身在核心。殘餘存在於勞動的世界,臨時僱員,被裁撤工人,非正式和打零工的工人,小型服務業和農業工人,殘餘是那些沒有保障,固定薪水和固定時間上班,沒有保險和賠償的工人,他們是未來工作中無關緊要的工人。
殘餘是那些被排斥,被譴責,被建檔和被巡邏逼查,無論流浪何處的難民。他們是被迫離開土地,被無人性的資產市場和和暴力清除強迫離開住所的人們,他們的家被回收,他們蹣跚活在經濟和地理的邊緣。殘餘來自城市和鄉村,來自城鄉結合部,非傳統城市與非傳統鄉下的集合之處。我稱之為「全球特區」(global banlieue),是字面意義也是隱喻的,具體而有潛力的地方,是仍未清晰可見但為政治交遇的地方。
殘餘是三無(無收入,無工作,無資產)世代,(NINJA,no income, no job, no asset)。希臘人民面臨三巨頭(歐洲委員會,歐洲中央銀行,國際貨幣組織)撙節政策衝擊的感覺一樣。法國郊區流離失所的阿拉伯和非洲人,底特律人民欠「危機管理者」債務。巴勒斯坦人民向以色列坦克丟石頭。住在敘利亞北方的羅賈瓦庫德族。佇立西班牙街頭的憤怒者運動者。「六月六日」巴西抗議公共交通收費漲價的遊行。伊斯坦堡蓋其公園(Gezi park)的佔領者,香港佔領中環的雨傘小孩。名單還可以繼續下去。
《元哲學》的精神延續到了《接近城市的權利》。列斐伏爾覺得政治最急迫的是重新構造一種「市民權的革命觀念」。的確,這就是他長久以來接近城市的權力所說的意思。這是他工作假設在五十年後留給我們的遺產。接近城市的權力,現在,就是那些被驅逐-殘餘人民要重申,或首要申張的,他們有接近集體城市生活的權利,有接近他們所積極參與卻被剝奪公民權的都市社會的權利。
市民權超越了護照和任何官方文件證明,它不是由資產階級國家法律所表現的出來的。我們甚至可以說,革命的市民權必須經過鬥爭,去贏得,和創造一種新的,而非橡皮圖章的權利,否則它就不是什麼權利。我們所說的是沒有國旗,國家和邊界的市民權。現下這種時刻,我只能說這是幽靈般的「影子市民權」。
今天,影子市民權盤據在它的他者(影子統治階層)上空,影子統治階級操著看不見的線控制了專業民主。影子護照是世界上所有被剝奪市民權的人們潛在可能的承載物。
影子市民是新常態,是全球新的出廠設定。由是,殘餘不再是城市的排泄物而是城市本身的實體。人們被迫從界線中出走,因而界線的視域被拓展了,甚至創造了給市民權概念,給了一個新的還沒有主權的市民權更大的社會空間。這就是星球都市化,也應該是它的意義。
透過星球都市化的視角看世界,有著特定的進步優勢。尤其,強調共性(commonality)而非差異。在互酬分享的星球上,住著不同人,講著不同話,彼此不認識,其實比他們想得更具有共同性。
分享經驗,是彼此不滿,失望,受苦或者希望的共同增長。這種親近性很少人承認。接近城市的權利應該幫助我們去辨識此種親近的可認性,它是如何被顛倒星球的力量,將工作和所有人丟進糞坑的那種力量,給中介和破壞的。接近城市的權利應該幫助我們去形成一個新的組織,新的機構去跨越國族國家的鴻溝。我們如何去發明一種新的,更好客的市民權形式,去滋養認同感而不破壞他者本身的認同?人民─殘餘如何如何透過都市社會的連結去表達和成為他自己?
我們重新想像一個真實的都市的再-選舉權(re-enfranchisement)?讓城市成為一個民主的地方來保衛那些受壓迫和不滿的,提供我們之中的陌生人和移民者的庇護所?我們能夠界定一個新型的世界之都,超越國族國家的都市共同體?
也許我們現在需要的,讓我們的民主多點溫柔,成為一種新的市民廣場(agora),一個影子市民廣場,讓幽靈公眾可能長成真的市民的地方,一個革命的市民。如同古代的廣場可以是悲劇的舞台,讓影子市民可以宣洩演出。一個影子市民可以參與史詩劇的廣場,去辯論與爭辯,分析和糾正他們民主不足的廣場。
列斐伏爾偉大的視野,作為鬼魅如夢的新城市型態的思考為人眾知,接近城市和屬於城市的權利,一個屬於民主都市網絡的意志,同盟者聯手的共同體質問國族國家角色和政治本質。什麼是都市的市民?什麼是二十一世紀的城市居民?面對未來的挑戰,進步抗爭的啓發性答案早已佔據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