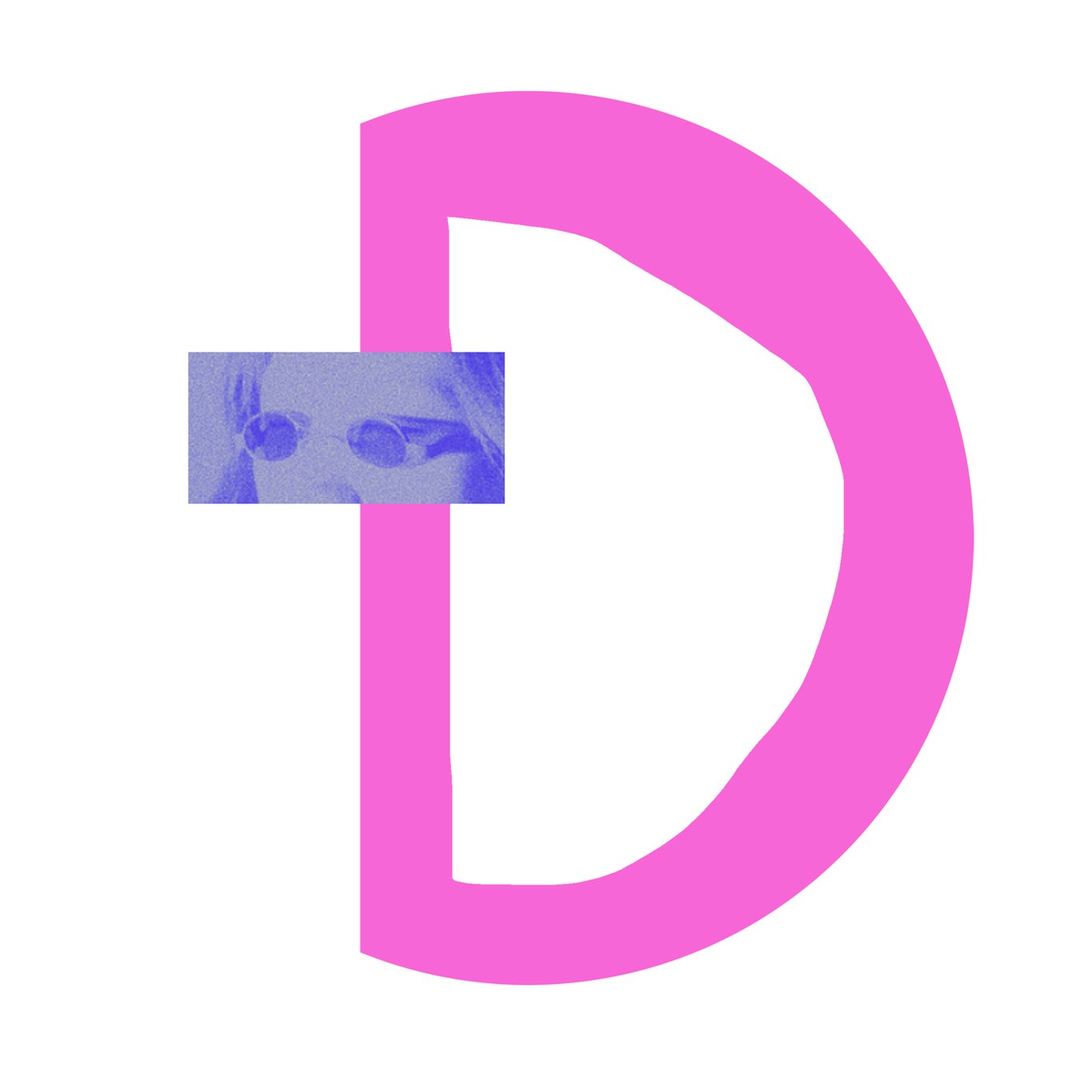拋掉電影上街去
上帝之手
最近重新看了一次保羅·索倫蒂諾的電影《È Stata la Mano Di Dio》。準確地來說,應該翻譯成:那曾是上帝的手啊。一個雙關的名字。一個改變了索倫蒂諾一生軌跡的「一隻手」,這「上帝之手」和馬拉多納一樣充滿了爭議,亦帶著那個時代複雜性。作為編劇和導演的索倫提諾講述了近乎於一個真實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十幾歲時,雙親因為去度假小屋而煤氣中毒突然地離他而去。電影里男主角的台詞說道:雖然我只看過4部電影。可他們說電影是另外一個世界。我不喜歡我這個世界了,我想拍電影。
我當時在想,一個人有可能只看過四部電影,但他可以想要拍電影,也能拍好電影;而我從初中擁有寬帶上網開始,最喜歡用電腦做的事就是看電影,雖然這兩年看得少了,但也看過起碼2000部片子....我開始思考電影到底帶給我什麼了?索倫蒂諾從最最真實的世界里、在那不勒斯的街道里、平凡卻迥異的親戚朋友中得到了創作故事同時使自己好好活下去的力量,從而製作了另一些世界-即電影。
而我可能相反,我似乎從電影里學習了太多「人生」,以至於我無法專注於自己眼前的人生。例如我追求苦痛虐戀,我認為電影里那樣的戲劇、悲痛或浪漫的完美的一幕幕才是我必須有的,我對自己的人生有一些執念,或者說是一種寫劇本般的訴求,更糟糕地,這種行為還是一種強迫症般的存在。我想到了寺山修司的電影《拋掉書本上街去》,剛進入大學的我,看這部戲的時候重點只看到前四個字。丟掉《三年高考五年模擬》唄,我們年輕人就是要反叛,我喜歡寺山,因為他說「拋掉書本」。如今我看到了後三個字「上街去」,這不僅僅是一種表面的叛逆行徑,我更喜歡寺山了,我覺得他要說的是走到街上去,走到生活里。答案從來都不在書本里,或者電影里。
父親的眼淚
講回真實的生活里,這兩天,我的奶奶因為新冠送醫了。
我的父親是個溫文儒雅的人。在外人看來他是一個非常冷靜可靠的人。我記得僅僅年長我三歲的小阿姨說夢想中的結婚對象就應該是我父親這樣-------溫和而可靠的。我當時吐槽到,他就是一塊大木頭,我的愛情可是要浪漫和驚心動魄的才行,絕不會選擇一個他這樣無趣又正經的人。那樣膚淺又幼稚的念頭,還是得要「怪罪」電影。苦笑。
幾天前,家人發現奶奶血氧很低,就趕緊送醫院。待了一晚就收到了病危通知書,在這個中國醫療系統已經陷入深深危機的時間段,根本找不到呼吸機和床位的供應,甚至連所有Icu都滿了,全家所有人焦頭爛額,只有父親耐心地在家人群里和小輩們說会没事的,已經在打點關係了,也安慰大家不要緊張,遠程地安排著一切事務和人員。
今天媽媽和我說,她接到了父親的電話,是他在哭。因為怕在外地趕回家的路上就失去清醒的奶奶。
彌留之際,你要什么?
我的奶奶目前還是清醒的,新冠病毒使她肺部嚴重感染外加器官衰竭中。我媽說她現在甚至力氣大到誰都攔不住她非摘自己的氧氣罩。醫生警告她,如果摘了氧氣她就沒命啦,可她不聽。她不願意使用尿不濕、不願意帶著氧氣罩。她摘下身上的管子們就自硬撐著去上廁所,上完又一直氣喘吁吁地,然後繼續和子女玩你戴我摘的遊戲。她難道不怕死嗎?我心想。她的幾個孫子孫女也都是沒怎麼受過教育的農村人,哄著的同時也不忘了夾雜一絲威脅:你要再摘了我們真就把你手腳都綁起來了!聽完她更生氣了。
她是一個一輩子生在農村的人,前兩年八十幾歲的時候,聽說她還能爬山,身體向來挺好的,但不識字。她也不喜歡來城市生活,所以和我相處的時間並不長,我對她也沒有很深的感情和瞭解。但總覺得晚輩們求的是她的一條長命,而她在人生的最終章里,求的一份尊嚴。
拋掉電影上街去
拋掉電影上街去吧,姐妹們,這是我年過三旬的忠告。
現在一些電影的價值觀可能漸漸傾向於平權,電影行業也在進步,观众的思想也在进步。但實話說,我看過的2000部旧片子大部分是充滿父權結構的。男人舞刀弄槍地散髮著魅力,女人苦苦尋覓男人的愛....看完了我們會感嘆,電影好美,我也想要。而在女性意識覺醒以後,曾經的電影和書本就直接顛覆了一些現有的三觀,文學作品當然存在著巨大的價值和美,但不能否認他們構築了堅硬的父權天塔。拋掉電影或者書本,重要的是上街去,走進真實的生活里去,去感受身邊的每一個人,在真實的發生里獲得能量。重要的是上街去啊。這也是一個雙關。
1月3号,米蘭,意大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