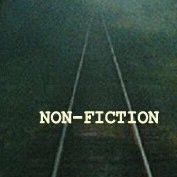记忆的幽灵:卡洛斯·绍拉早期电影散论
*本评论含关键情节剧透,建议观影后阅读
卡洛斯·绍拉(Carlos Saura)的《饲养乌鸦》(Cría cuervos,1976)中有这样一个场景:夜深时分,安娜心满意足地听着母亲(杰拉丁·卓别林[Geraldine Chaplin]饰)演奏蒙波的钢琴小曲。曲终,她正打算上楼睡觉,忽然听到开门的声响,父亲回来了。她转过身,见证了父母的一场争吵:母亲责怪父亲对她的漠不关心,父亲则要求母亲不要对自己进行道德绑架。母亲痛哭。下一组镜头:安娜慢慢走上楼梯、穿过走廊。就在观众以为这段场景即将结束之时,远景中一扇门打开,白色的灯光射进走廊,身穿睡袍的阿姨出现,让安娜赶紧回房间睡觉。观者意识到故事回到了其时间主线之中:那是安娜在父母去世之后,被阿姨看顾的暑假。


绍拉的时间魔术在继续:安娜回到房间,躺在床上,睁大眼睛望向空无一人的门外。她闭上眼睛,镜头推近。重新睁开眼睛时,她看到母亲经过门口,安娜露出满足的微笑,又闭上眼睛。再次睁眼时,母亲走进房间,坐在床头给安娜讲了“小杏仁”的故事。特写镜头对准了安娜专注的双眼。当镜头再次拉远时,安娜望向门外,母亲消失了。她唤着“妈妈”,泪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阿姨走了进来,安娜说她想死。阿姨说我给你讲个“小杏仁”的故事吧,安娜说:“我希望你死”。


通过这个场景,绍拉将现实、往事与梦境三个维度的时间交融在一起,展现了安娜的幸福、好奇、恐惧、惊喜、焦虑、愤怒与绝望等复杂的情绪,精准表达了一个父母双亡的儿童敏感而又脆弱的内心世界。绍拉邀请了在维克多·艾里斯(Víctor Erice)电影《蜂巢幽灵》(El espíritu de la colmena,1973)中扮演小女孩安娜的安娜·托伦特(Ana Torrent)来出演这个角色,安娜的双眼在这两部电影中成为一种超越语言的存在,由此展开的是简洁、精准、出自本能的表演。《饲养乌鸦》是一部嵌套着多层记忆的电影:除了童年安娜所处的时间点以外,还存在着由祖母的照片所构建的更为久远的记忆,以及来自“未来”由成年安娜所展开的口述记忆。
和《饲养乌鸦》一样,绍拉的其他电影往往以相同的空间(通常是一座充满历史感的建筑,以及建筑中的储物室空间)与同样的表演者(通常是由一人分别饰演两个角色)作为常量,透过各种各样的物件、声音、符号,带领观众进入主人公记忆的世界。这种世界中的时间通常不太线性,充满着倒叙、想象与旁逸斜出,现实、过去、幻想与梦境常常交织在一起,正因为如此,人们常常将绍拉的电影视为一种超现实电影。
然而绍拉的电影真的是超现实的吗?至少其早期的创作生涯并非如此。绍拉在电影生涯的起步阶段以现实作为主基调,例如1957年的短片《星期天的下午》(La tarde del domingo,1957)是一个典型的三幕剧,拍摄了一位女仆周末午后沮丧的经历。1958年的纪录短片《昆卡》(Cuenca,1958)描绘了这座西班牙村庄传统的生活方式。1960年处女长片《小流氓》(Los golfos,1960),则是一部典型的以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方法论创作的电影,展现了马德里近郊一群以盗窃为生的小混混的生活。他们的梦想是让其中一位成员顺利踏上斗牛士职业之路。电影无论从主题还是风格上,都让人想到同期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的《乞丐》( Accattone,1961)《罗马妈妈》(Mamma Roma,1962),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的《浪荡儿》(I vitelloni,1953)等意大利导演早期的新现实主义作品,与他们共享着这一流派的基本原则:对非职业演员的使用、街头实景的拍摄、对边缘与底层群体的关注等等。绍拉游刃有余地运用着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导演们的影像语言,并融合法国新浪潮中的一些剪辑手法,创作出一部极为成熟的处女作。然而,正如另两位导演未来分别探索出属于自己的凌厉的影像风格,绍拉也很快地发展出自己的电影语言。
导演对“现实”(reality)的定义决定了其影像现实的呈现方式。在德国导演维纳·赫尔佐格(Werner Herzog)看来,现实是由客观的物质、线性时间观、数学公式和算法所主导的,赫尔佐格认为这种“会计师的现实”(the accountant’s reality)十分无趣,他试图追求一种“狂喜的真相”(ecstatic truth),因此其电影经常拍摄极端环境中所激发的人类内在的激情。而绍拉的现实则更多与感知/想象/欲望/记忆的问题纠缠在一起。1967年,绍拉在《薄荷刨冰》(Peppermint Frappé,1967)一片的拍摄感受中阐释了他对“现实”的理解:
现实是人们可以直接、立即感知到的;现实也是人们所梦想的,是人们希望发生但并未发生的事情,是过去和未来……一切都是交织在一起的。
在这里,绍拉将个体的想象世界看作是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们不仅活在物质世界之中,更生活在由自己的欲望、梦想、记忆与无意识所驱动的精神世界之中,二者交融在一起。无疑,绍拉受其良师益友路易斯·布努埃尔(Luis Buñuel)极深的影响,他们都致力于以电影化的手法,展现超现实主义运动之父安德烈·布勒东(Andre Breton)所说的“思维的实际运作方式。”
《薄荷刨冰》正是绍拉关于这种现实观念的一种实践。在这部向布努埃尔致敬的电影中,绍拉展现了一个男人的欲望、嫉妒心与占有欲是如何将其扭曲的过程。他一方面运用薄荷刨冰、假睫毛、跑车、金发等象征意味极浓的物件符号表达一个中年男性的恋物癖,另一方面通过色彩的区分来展现他的欲望与现实世界:黑白影像代表了他朦胧的潜意识,彩色部分代表了他所身处的现实世界。


而在《饲养乌鸦》这样展现儿童内心创伤的电影中,绍拉的手法变得更加成熟,电影总体上按照安娜的心理与情感流动的逻辑来进行剪辑。在回忆部分,时间的线性关系被打乱,现实、记忆与想象的世界融合在一起。事实上,“儿童”在西班牙电影史中长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绍拉而言,儿童并非象征着纯真与无忧的小天使,而是成人的另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他们敏感地承受着周围发生的一切,他们会混淆现实、图像、听闻和想象,他们尚未习得成人世界的道德观念,因而可能展现出极致而强烈的力量,并做出一些出乎意料且他们自己也并不理解的行为。
《饲养乌鸦》中的记忆犹如幽灵一般占据了影像的空间。我们看到了成年安娜的口述式记忆,童年安娜的想象性记忆,以及安娜奶奶通过老照片所感知的无声回忆。这种关于记忆的层次精细的编织,或许与绍拉毕生对记忆之经典介质——相机——的痴迷有关(绍拉从小就是一位狂热的摄影爱好者)。而在其最具自传色彩的代表作《安洁丽卡表妹》(La Prima Angélica,1974)中,导演对记忆与现实关系的处理则更为复杂与精巧。我们可以简单分析电影中的两个场景:
电影开场,取回母亲遗骸(有一个显眼的头盖骨特写)的主角路易斯驱车前往故乡,他把车停在路边,眺望着卡斯蒂利亚原野尽头若隐若现的塞哥维亚城,忽然听到身后传来车门开启的声音,他转过身去,一辆二三十年代的老爷车出现了,着装考究的父亲与母亲走下车来,母亲给他涂抹了古龙水,他对母亲说自己不想离开父母去外婆家,母亲说你去年夏天在那里过得很愉快,于是把他拉上了车。
如同一本家用电器说明书首页导图,这个开场镜头为观者观看电影提供了一个风格上的指南,它提示了理解这部电影的两个要素:第一,这部电影将会是一场现实与过去的交织之旅。然而,关于过去的回忆不是通过传统的闪回形式,而通过某些特定的“媒介”来唤醒或激活,并与现实交融在一起。例如,在这个场景中,激活回忆的媒介就是通往故乡的公路与塞哥维亚城。第二,电影中的若干人物将参与到关于再现过去的建构之中。例如主演巴斯克斯(José Luis López Vázquez),以发福谢顶、饱经风霜的中年形象同时扮演着当下时间与童年回忆中的主角路易斯。


绍拉这种处理记忆的方法将在影片中多次出现,使我们意识到电影行云流水的转场镜头的真实用意,以及一人分饰两角在功能上的创新性。在电影后半段的一个场景中,中年路易斯与安洁丽卡在姨妈家阁楼(储物室)寻找他当年的教科书和笔记本,随后两人从一扇窗户爬了出来,坐在老房子的屋檐上,教堂的钟声在他们耳边响起,两人肩并肩靠在一起,相拥而吻。一个粗暴的声音打破了甜蜜的氛围,表妹的丈夫来找路易斯了,为了不让他发现他们在一起,路易斯从窗户钻回屋里。随后镜头回到表妹的丈夫,他大喊着找安洁丽卡,下一个镜头,摄影机在空荡的窗户上停顿了三秒钟之后,童年的表妹出现了。


当我们考察这第二个案例时,首先,记忆是如何被激活的?这里的窗户,如同片头的公路,是主角穿越时间的另一个隧道。而阁楼储物间、塞哥维亚老城、教堂钟声、笔记本与教科书等,以其恒常性,进一步将现在与往昔融合为一个有机的时空整体。其次是角色分饰两人的妙招。随着影片的发展,不仅是男主角巴斯克斯一人分饰两个时代的路易斯,小女孩也同时扮演安洁丽卡和她的女儿,并且两人身穿同一件圆领碎花连衣裙,中年男人也同时饰演童年安洁丽卡的父亲和成年安洁丽卡的丈夫。
由于这种巧妙的设置,安洁丽卡最后的现身又意味着这是一个过去的场景,这让人不禁想象:是否在童年路易斯与安洁丽卡情窦初开的某天,他们也曾一起爬出窗户,坐上屋檐,玩过类似的爱情“游戏”?这个场景是否是上个场景的某种镜像,即童年的路易斯躲在了外面?此种巧妙的处理,勾起观者无限的情感体验,两个孤独的中年人相互依偎、初恋的情愫、对于往昔美好岁月的感怀、被父权强行中断的梦幻瞬间……各种情感共同交织在这短短的三分钟时空之中。这是电影的魔法时刻。
既然《安洁丽卡表妹》是绍拉的自传性电影,自然涉及到影像如何表现作者的过去。绍拉不认同影像的自传是“以一种视觉日记的形式来回忆个人生活往事”的传统观点,他更愿意将自传视为一种自我通过各种媒介来创造性再现过去的方式。在他两个不同的访谈中,绍拉如此解释道:
即使有照片的帮助,我也不可能用我的眼睛和身体来重温小时候的事情。
我感兴趣的是在自己的生活中发挥想象力……大多数情况下,我看到的只是现在的自己,但却回到了二三十年前。这是促使我拍摄这部影片的基本想法——你不能把自己看成一个孩子。
惟有依托于现实自我的意识,在固定空间中对时间进行主观的重构,才是绍拉对于自传片的拍摄手法。因此,《安洁丽卡表妹》中的回忆场景被许多电影评论者认为介于普鲁斯特与伯格曼之间。这也让我们想到哲学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时间理论。柏格森将空间定义为不可移动和可测量的,将时间分成两种:科学/空间的时间和持续性/绵延(durée)的时间。科学/空间时间是宇宙的内在时空,独立于我们的心理体验。绵延的时间——意识和记忆(或无意识)——是一种异质的绵延,是一种内在时间,也是我们与科学/空间时间的接触点。
成年路易斯在影像中经历的就是这种绵延的时间,他的现实生活被不易变的过去的事物和空间所唤起,进而进入到自己的回忆之中。成年人扮演儿童角色的所产生的异质性和怪诞感,是成年人在回忆自己过往时的基本心理机制,所以它反而比让小孩来演自己要来的更加真实。
由同一演员扮演不同角色,不仅与个人感知时间的经验直接相关,而且还带有政治隐喻的功能。在《安洁丽卡表妹》中,同一个演员既扮演1936年安洁丽卡的父亲——一个彻头彻尾的法西斯主义者,又扮演她在20世纪70年代的丈夫——当时在西班牙刚抬头的新自由主义力量的捍卫者:在某种程度上,新形态的资本主义是独裁统治在经济上的延续。父亲和丈夫构成安洁丽卡人生不同阶段的梦魇与阴影,这是中年安洁丽卡感到孤寂的根本原因。
实际上,因受困于父权家庭而出现精神异常的中年女性,是绍拉钟爱拍摄的对象之一。《饲养乌鸦》中母亲的困境来源于不负责任的父亲,父亲以“我最讨厌别人对我进行道德绑架”来反驳母亲。在1969年的作品《蜂巢》(La Madriguera,1969)中,丈夫对同样由杰拉丁所饰演的妻子说过类似的话语。在两部电影中,男性均以道德绑架为由,躲避自身对妻子的情感责任,令深陷家庭的女性最终陷入精神失常的状态。两部电影结局有所不同:在《蜂巢》中,妻子通过射杀男性实现了复仇的快感。而在《饲养乌鸦》中,妻子因郁郁寡欢而染上重疾最终死去。1973年的《安娜和狼》(Ana y los lobos,1973)更是将这个主题推演到极致:英国女管家进入一个富裕的大家庭,渐渐认出家庭中三兄弟伪善的面孔。此类访客题材,令人想到帕索里尼的《定理》(Teorema,1968)。然而不同于帕索里尼的宗教色彩,绍拉基于西班牙灰暗的现代史语境,描绘了一位受到来自于一家之主(政治)、宗教伪善者(道德)与资产阶级(商业)三种权力之狼蹂躏的女性的形象。这可以说是他最残酷的一部电影。
我们不可避免地进入了绍拉电影中政治隐喻的讨论。隐喻意味着一种间接的、曲折的、创造性的表达。在佛朗哥独裁统治的四十年间,在严格的文化审查制度下,文艺作品中任何对于当权者、主流政治与内战史的批判都是不被允许的,这使得当时进取的西班牙导演们需要寻找与探索一些既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想法,又能够躲避政府的审查的方法。绍拉如此说道:
“在佛朗哥主义统治下的许多年里,我们所有拍电影、绘画和写作的人都在寻找一种方法,使我们的媒介更加有效,不仅在个人层面,而且在西班牙社会层面。我相信,当佛朗哥还活着的时候,我有一种道义上的义务——也许更多的是为了我自己,而不是为了社会——在我的工作范围内尽一切可能帮助尽快改变政治体制。”
在与严苛而狡黠的审查制度周旋和对抗的过程之中,绍拉拍出了他电影生涯中最具创造力的一系列作品。黑白电影《狩猎》(La caza,1966)中所设置的外景地是西班牙内战的战场之一,曾是一个血腥的杀戮之地。三个经历过战争的人在那里继续展开猎杀——不仅针对猎物野兔,也针对彼此。内战的幽灵依然在这个国家上空盘旋。《极乐花园》(El jardín de las delicias,1970)中家财万贯的失忆主角绝非哗众取宠的设计,因为他是由两个重要的西班牙现代人物拼贴而成的:独裁领袖佛朗哥与百万富翁商人胡安·马奇(Juan March)。前者彼时患上帕金森症没多长时间,后者代表着在内战后获得最大影响力并从佛朗哥政权中获利的商人的形象。
《安洁丽卡表妹》的片头片尾都直指内战创伤。片头是战争中遭到轰炸的学校餐厅,片尾则选在阳光明媚的一天,专制的中年男人用皮鞭惩罚共和军的孩子(共和军是内战中与佛朗哥政权对立的一支力量,这部影片也是西班牙第一部从战败方视角来展现内战的电影),我们再次看到一人分饰二角的神奇效果:安洁丽卡的父亲惩罚着看起来与他年龄相仿、穿着与发型也别无二致的路易斯。照进窗户的刺眼阳光似乎象征着光天化日之下的罪行一直延续到了当下,形象高度相似的两个人物构成的荒诞图像也会引起观众的恍惚和遐想。它让我们联想到历史学家保罗·普雷斯顿(Paul Preston)的巨著《内战之殇:西班牙内战中的后方大屠杀》(The Spanish Holocaust)的主要观点:内战中共和国军和叛军只是一体之两面,他们均以仇恨为由对西班牙部分民众进行系统性的镇压与屠杀,普通民众才是内战的真正受害者。


绍拉曾说,他的电影没有任何一个画面是偶然的,任何最小的细节都有其意义。《饲养乌鸦》更是一部用无数细节来构建政治隐喻的电影。片头安娜死去的父亲是佛朗哥本人的化身。20世纪70年代是佛朗哥独裁统治的最后几年,一个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时期。1975年,独裁者死去,西班牙人对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饲养乌鸦》就是那段时期人们对于未来的迷茫与忧虑的复杂情绪的影像记录,影片中的死亡气息萦绕不散。
父母的去世、众人的话语(片中至少出现30余处与死亡有关的表述。例如安娜说:“我希望你死了”、女仆人说:“你不愿意从娘胎里出来”)、奶奶对死亡的默许、奶奶的老照片(罗兰·巴特意义上的死亡媒介)、电影开场不久安娜站在高楼之上及后面的摇摇欲坠的主观镜头、三次出现在冰箱里的冻鸡爪特写、兔子Roni的去世与葬礼、电影主题曲“Porque te vas”中的歌词“望着窗外的城市,因为你已离去......”的歌词、安娜与姐妹们所玩的捉迷藏游戏、安娜对着阿姨与情人的枪,乃至电影《饲养乌鸦》这个名字的寓意……均指向死亡。这些细节共同强化了佛朗哥刚去世时社会的不安情绪。


1979年,绍拉的第一部喜剧问世,电影名为《妈妈一百岁》(Mamá cumple cien años,1979)。这部电影可以看成《安娜和狼》的姐妹篇,同样的乡间别墅,同样的女主角与男配角,同样的母亲。只不过,杰拉丁现在所面对的主要对象,已经由前作中的男性一家之主,转向了德高望重同时活泼可爱的妈妈。一家之主已经在三年之前死去,这是对佛朗哥的直白指涉。妈妈成为西班牙这个国家的当代化身——虽多灾多难但却依然健硕乐观,充满活力。她深知这个家族中哪些人居心叵测,哪些人值得信赖。尽管片尾她仍在诉说年轻时的苦难,但那已是一个重生之人对于过往的记忆连接。彼时的西班牙社会,民主化转型已初见成效,未来的方向日渐清晰,电影的尾声也预示着绍拉将从佛朗哥时期的对抗性创作自觉中抽身出来,进入他自己的重生期。
从那时起,绍拉的电影转向对西班牙传统音乐、舞蹈与绘画艺术的探索,这些元素一直是绍拉创作中重要的养分(他的母亲是钢琴家,哥哥是画家),也是他此前电影中不可或缺的伴随,从八十年代起它们成为电影的主角,成为他窥视社会、关照历史的通道,也被他赋予当代的情境与情感(“弗拉门戈三部曲”、《探戈狂恋》、《墙壁会说话》等)。其实,当我们回顾绍拉穿越佛朗哥统治时代直至当下的整个创作生涯,更能感受到一直令他着迷的弗拉门戈艺术中那种苦痛与力量之间的转化和流动。我想起诗人洛尔迦对于弗拉门戈、也对于西班牙精神的一段阐释:“在别的国家,死亡是一种结局。但在西班牙不是,西班牙向死亡敞开自己。”
(本文系为SIFF Screening2023年9月23日至30日举办的“西班牙电影大师展”所写的同名文章的完整版,官方版本请见该影展手册与SIFF公众号。文章作者gawe、充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