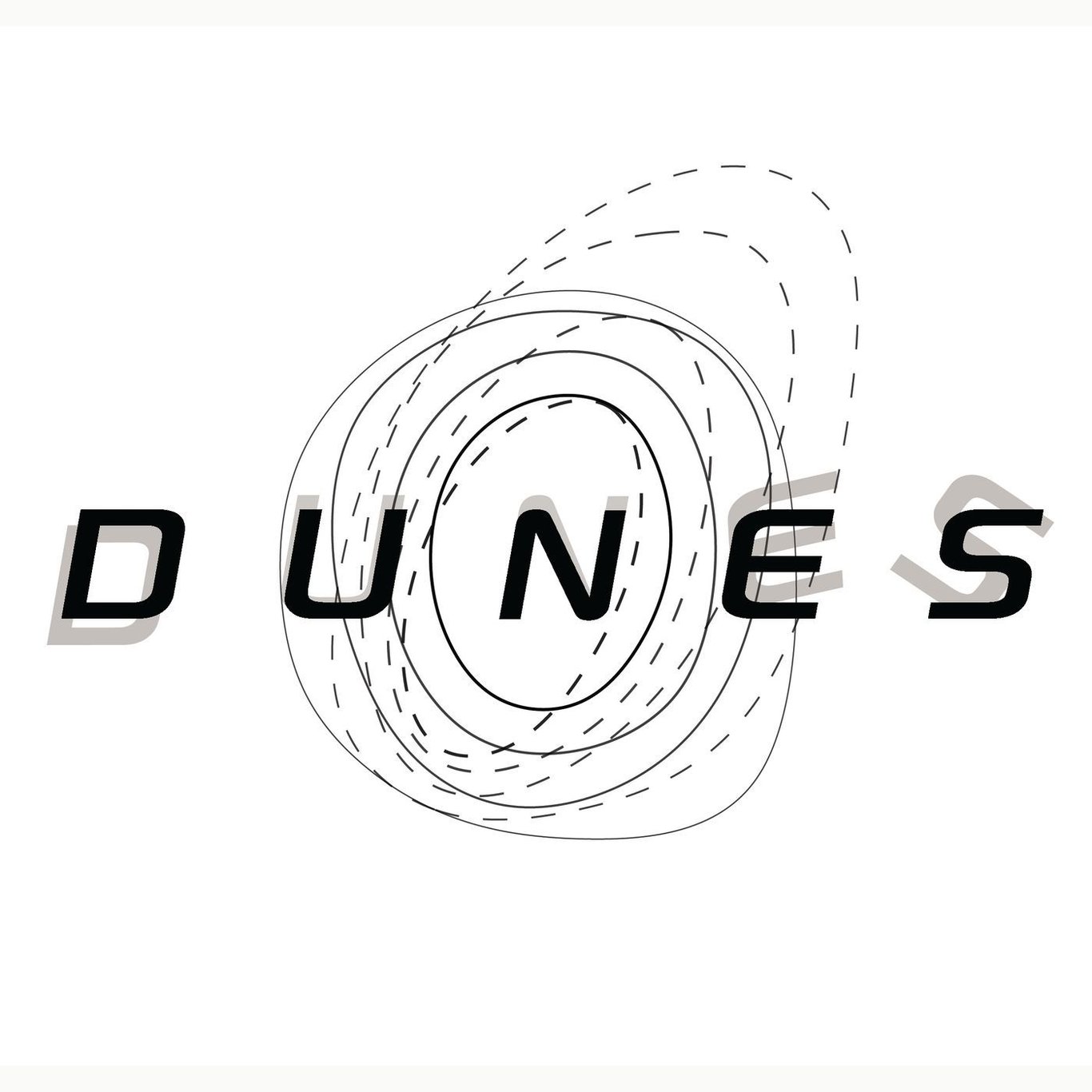阿伦特:彼此交谈,理解事物,爱具体的人
114年前的今天,汉娜·阿伦特出生。

01 公民的言说以及彼此交谈
(摘自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公共与私人领域”一章,中译:王寅丽)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动物”(zoon politikon)最早译作“社会动物”(animal socialis),特别是经由托马斯·阿奎那所采取的标准翻译:homo est naturaliter politicus, id est, socialis.(人在本性上是政治的,即社会的。)
“社会”对“政治”一词的无意识取代暴露了人们丧失了希腊原初对政治的理解,因为“社会”一词源于罗马,而它在希腊语言中却无所对应。
亚里士多德对人作为政治存在的定义与家庭生活中的自然联系相对立,因为人是“能言说的存在”(zoon logon ekhon)。该短语在拉丁文被译作“理性的动物”(animal rationale),同“社会动物”一样都基于根本的误解。
亚里士多德并非要表明人的最高能力,对他而言人的最高能力不是“逻各斯”(logos)即言说或理性,而是“奴斯”(nous)即沉思能力,而沉思恰恰其内容无法诉诸言辞。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两个关于人的定义,城邦之外的任何人——奴隶和野蛮人——都是无言的(aneulogou),他们并非丧失言说的机能,而是丧失了一种生活方式,在其中,言说具有了意义,并且唯有言说有意义,所有公民关心的是彼此交谈。
02 因理解而非影响去写作
(摘自1964年,汉娜·阿伦特与昆特·高斯(Gunter Gaus)的对谈题为What Remains? 中译:沙丘研究所)
-高斯:
在很大程度上,您的工作与了解政治行动发生的条件有关。您想通过这些作品获得广泛的影响吗?您是否相信,在这个时代不再可能产生这种影响了?又或者,这些影响力本来对您来说就仅仅是次要的?
-阿伦特: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不过说实话,在我工作的时候,我不在乎它会怎么样影响人们。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对事物进行理解,而写作是理解事物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高斯:
写作是否有助于您对事物进行进一步的觉察?
-阿伦特:
是的,因为在写作的过程中一些东西被建立了起来。如果我有很好的记忆力并且能够保留所有想法,那么我有可能什么也不会写下。我明白自己的懒惰。
-高斯:
如果有这样的记忆力?
-阿伦特:
是的。但是我没有。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思考过程本身。每当我设法充分想清了一些事物,我都会感到满足。如果我设法以书面形式充分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过程,那也会让我感到满足。
您问我的工作对他人的影响。如果我可以用带讽刺意味的措辞——这个问题本身是男性化的。男人想成为“有影响力的”。可以说,我作为旁观者做出这样的评判。至于说我认为自己有影响力吗?不,我想要做的是理解事物。如果其他人同样以我理解的方式理解世界,那将会给我一种满足,一种处于某种平等之中的满足。
03 爱具体的人而不是抽象的集体
(摘自1964年,汉娜·阿伦特与昆特·高斯(Gunter Gaus)的对谈题为What Remains? 中译:沙丘研究所)
-高斯:
您曾经说:"在我这一生中,我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一个民族或集体,无论是德意志、法兰西,或是美利坚,无论是工人阶级或是任何其他一切。事实上,我只爱我的朋友。我完全无法爱任何其他非具体的种类。特别是,对犹太人的爱,那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我自己就是犹太人。"
我能问点什么吗?尽管这种态度是正当并值得尊敬的,但人作为一种政治上的积极存在,难道不需要对某种集体进行承诺吗?这种承诺在一定程度上,不可以被扩展为“爱”吗?你不担心你的态度在政治上是非建设性的吗?
-阿伦特:
不,我想说反对的观点才是非建设性的。当然,对于这个话题我们或许可以有很长时间的探讨。
人属于某个群体,这首先是一种自然的境况。每个人总是天生就属于某个群体。但是现在我们所讨论的,在第二种意义上——属于一个集体——即一个被组织的群体,那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这种组织总是与人与世界的关系有关。也就是说,组织内的人有共同的,通常所谓的利益,所以,这里他们之间的利益真正涉及到与世界的关系。直接的个人关系,可以说是“爱”,它当然首先存在于实际的爱情中,在某种意义上也存在于友谊中——这里直接涉及一个人,与他们和世界的关系无关。所以我们可以说,来自完全不同组织的人仍然可以成为私人朋友。但如果一个人混淆了这些东西,如果一个人把“爱”的概念带到谈判桌上,说得比较直白一点,我觉得这绝对是致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