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哥城的陷落
这一篇文章的灵感来自于贝多芬第七交响曲。愿疫情可以早日被扼杀。 ——写在前面
十九世纪中页,一位法国生物学家深入中南半岛的热带雨林,发现了一座失落的城市。当他第一脚踏入城中时,便知道眼前这建筑群的伟大程度绝不输给任何一个世界奇迹。这个法国人的直觉是准确的,因为这便是高棉帝国的国都,陷落的吴哥城。它的陷落之谜,至今无人能解。
宣德五年,商人黄破武第二次到访了吴哥城。那时靖难之役已经过去三十年,大明经历了永乐年间的狂飙突进与仁宣初期的持续发展,已算得上是江山稳固,国泰民安。久居京城之人,时常可以目睹到万国来朝的繁荣景象。黄已经好多年没有回到故土了,所以这些消息在他看来似幻似真。他在日记里说,自己曾几次梦回应天,听到了花柳巷里隐隐约约的丝竹管弦,看到了远处庄严而亲切的宫殿庙宇,流下了梦中人的泪水。二十二岁的时候,他首次走出大明国境,见到了如画的吴哥城。当时他受到的震撼远甚于那位法国生物学家。黄破武从未想过在这疠瘴之地,在这丛林之中,竟有一座活力四射的大都市。城中矗立着星罗棋布的恢弘庙宇,庙宇里有盈千累万的令人叹为观止的浮雕,从内到外彰显着高棉帝国过去的富庶、辉煌与虔敬。不得不承认,比较起来,应天府的繁华气派也相形见绌。如今,黄经历了半生颠簸,已是老态龙钟。再回到吴哥城时,他惊人地发现,这座城也已经衰老得不成样子了。 更令他想不到的是,一场灭顶之灾即将降临。此刻他踏入吴哥城,便再也没有机会踏出了。
在吴哥城陷落六百多年后,波尔布特与他的革命军于高棉北部的丛林里站稳了脚跟。这六百年中,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地球上诞生了,也失去了很多优秀的城市,但没有一座出落得如此铅华不御,陷落得如此异想天开。当然,波尔布特不懂这一套。他看样子是一个心中有信仰的人,大概不会在乎一座老朽的都城。波年轻的时候,在铅华洗尽风韵犹存的巴黎呆过一段时间。他不曾被卢浮宫的精致感动,不曾对枫丹白露的典雅向往,只是偶尔会盯着巴黎女郎的双腿,想象她们在革命前线袒胸露乳的样子。这是艺术给他带来的唯一一点影响。后来他从艺术之都回到了雨林,准备展开一场翻天覆地的行动。每当他肩挎冲锋枪,带着几个灰头土脸贼眉鼠眼的兄弟走进葱郁的丛林,看到榕树的茎干从废弃庙宇的石雕中长出,把栩栩如生的毗湿奴大神挤得头骨崩裂时,都会觉得这是一个美好的隐喻,美好到远胜于巴黎画中的女郎。
黄破武的妻子很久以前就死了,他这些年一直孑然一身。破武长期在东南亚一带贩卖乱七八糟的东西,比如管制刀具、盗墓所得的文物、野生动物以及人口,每到一处就在日记里记录下当地的地形地貌和风土人情。如果这本日记可以流传到现在,那真能破解不少历史谜题。黄在第二次到达吴哥城的时候这样写道:“都城的墙老了,石像老了,庙宇也老了。难道是因为我已到迟暮之年,才会看一切都如此死气沉沉吗?不应该。城墙的表面朽坏出一条条裂纹,里面夹着将死的植物与昆虫。城东那供奉湿婆的神庙也显然是多年未经修缮了,远看那神就像阳痿了一般。你可以说那是庙,也可以说是塔,或是祭坛。想当年,猴子似的奴隶驱赶着拉着万吨重的巨石的大象,从西边奔袭而至。奴隶们把巨石切割成完美的立方体,一块一块堆砌起来,垒成了高耸入云的石塔。若是站在塔尖,你便可以望见同样雄伟的吴哥窟,望见厚实的城墙,生机勃勃的雨林,和城外军营里赤裸的兵士。匠人们开始日夜劳作,把湿婆的躯体印刻在这通天塔上。竣工那天,苏利耶跋摩大帝携文武百官来到祭坛附近,瞻仰这三目大睁,乳房浑圆,阴茎外露的无上圣主。皇帝把铜柱插进祭坛不远处的深井,接着就有一股乳白色的液体从井中喷出,慢慢流淌向石塔,顺着塔向上爬,最后钻进了浮雕额头上的第三只眼里。神庙泛出金光,湿婆的眼睛渐渐合上,生殖器却变得如那铜柱一样直挺挺的。百官伏地大拜,皇帝则顺着乳白色的小溪爬上了塔顶。他高举权杖,俯视着壮阔的吴哥城和塔下渺小的人,发出了震耳欲聋却有一点尴尬的笑声。他喊道,吴哥城是神灵聚集之地,是群英荟萃之城;它的蓬勃势不可挡,属于它的荣耀将与天地争辉。此刻,苏利耶跋摩便是神秘而狂妄的湿婆,是艺术之神,是情欲之神,是高棉帝国当之无愧的狄奥尼索斯。”
波尔布特第一次听说希腊酒神的时候,整个国家已经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癫狂状态。那时正处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后现代的理论变得枝繁叶茂,狄奥尼索斯早就被搬上了神坛,而革命浪潮却已成了强弩之末。站在残塔顶端的波尔布特手持望远镜,观察着远处巴戎寺上神灵的微笑。与此同时,革命军在城边磨刀霍霍,这让他感到了一阵意乱情迷,有些欲罢不能。在他看来,革命就像性爱:赤裸而冲动,神圣而下流;革命也像生殖:银瓶乍破水浆迸,一将功成万骨枯。想着想着,他的下体就胀了起来,骄傲地指向了身处堕落边缘的吴哥古城。他认为,此时此刻,他在做一辈子能做到的最具神性的事情。
黄破武写道:“如今的高棉早已没有了苏利耶跋摩时期的光芒万丈,跟三十年前也是没法比。有人把这归咎于与暹罗的连年战争。但凭这一周在吴哥的所见所闻,我可以断定古城的衰颓另有原因。政府对国家的实际控制力依然很强,可是城内的居民却变得越来越奇怪。首先,帝国元首已经在金边修建了新都,这让人们开始怀疑是不是吴哥被当局放弃了。同时,天竺传来的佛教在城中大行其道,大家只有行房之前,哦不,嫖妓前才会想起湿婆。此刻,满城的神庙显得多余而诡异,只有统治者才会偶来凭吊,顺便进行一下滑稽的祭祀。郑和的船队初次到访高棉以后,有不少信仰禅宗的,或者什么都不信的华人迁居吴哥城。到现在,城中走几步便可以看到大明子民的面孔。他们有时还会拿着一些纸,发给街上的人。这样一股不伦不类的势力也让整座城浮躁了起来。自大明汉王被宣德皇帝做成叫花鸡以后,这群人便失了魂似的。我很好奇他们到底怎么了,但是我与官府有仇,不敢与他们接近。这几天,我和两个随从住在一家客栈里,偶尔出去买点古玩,等屯够货物,就离开这迟暮之年的城市。”
法国探险家走进吴哥城之后,便拔不动腿了。被热带植物包裹的绝美神殿让他不由自主地开始颤抖,而更让他着迷的是这座陷落都城的身世。那个时候,没有人可以讲清伟大的石头城是怎么建起来的,以及又是如何消失在密林里的。待他回到欧陆,便开始组织人手前往吴哥寻宝。这陆陆续续的发掘过程持续了近一个世纪,高棉故都才重见天日,恢复了往日的人烟。然而,那个谜题却始终无人能解,直到人们发现了一具抱着精美盒子的枯骨。那盒子里有一本笔记,用汉语记录了吴哥城最后的日子。
“当那玩意儿刚开始在吴哥城蔓延的时候,并没有人在意。按照我们明人的说法,这叫邪气,但几百年后的人应该知道,这是一种强力病毒。我初次听说的时候也没当回事,还以为是某些寡廉鲜耻的狂徒在造谣,试图为平淡到颓圮的生活增添一丝情趣。没想到,在接下来的几天,告示上说吴哥城内居然死了近百人。他们先是双眼通红,头脑发热,接着歇斯底里,神情癫狂,最后口喷鲜血而亡。与病患有过接触的人也多半不会幸免,变成陪葬品。我没有目睹这种惨象,却也不方便怀疑官方是在胡扯,毕竟天底下的官府不都是一样的。整个吴哥从上到下变得人心惶惶,大家一边默念神佛保佑,一边把矛头指向了那些耗资巨大的神庙。我拾到了一张明人发的传单,上面说这叫做天谴。当局昏聩无能,天天想着鬼神与自己那荒唐的权杖,不顾天下苍生。值此危难之际,大家应该团结一心,推翻这苟延残喘的神王统治。一旦做到了,天谴便可结束,万事当回归原初的欣欣向荣。待到那时,高棉便可重振雄风,把那北边的大明也给比下去……”
黄破武在几天后的日记里写道:“我从每天更新的告示上知晓,高棉医学委员会派出了全国最顶尖的专家进行调查。他们白布遮面,身穿着象皮服,一具一具解剖病发者的尸体。专家发现,这种病毒具备了优秀病毒该具有的所有品质:潜伏期长,传染性强,致死率还奇高。官方给它起名为ZXWY病毒。从科学角度讲,它已经接近进化的极限;这最后的四个英文字母,便象征着病毒的终极形态。大概是一个月前,它首次出现在吴哥城。这一个月的潜伏期内,ZXWY可能已经感染了很多的人。其传染途径则更是稀奇。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它依靠眼睛传播。当然,它也有可能通过呼吸道,但是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这些结果一出,吴哥城中的男女老少更是纷纷怆天呼地,痛哭不止。我和随从也是惴惴不安,又无法可施,只能自认倒霉。皇帝在金边下达了最高指示,说病毒来势汹汹,请各位团结一心,服从安排,一起打赢这场决定着人类去留存亡的战争。当晚,吴哥封城,没有国王的文碟,任何人不准进出。诺大的吴哥变成了一座孤岛,岛上是一群惊弓之鸟,和暗礁一般的陈旧祭坛。”
波尔布特在围困吴哥城的时候,爱上了神庙里的湿婆大神。几年以来,他打着共产主义的大旗,凭借东方某大国的支持,在柬埔寨攻城伐寨,不亦乐乎。后世的不少人们无法相信他是拥有理智的,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充满了目的性极强的自我毁灭。纵观高棉的历史,我们也找不出第二个如此擅长减少人口的统治者。当然,他愚蠢里面的理想主义成分不容质疑;他对自己的信仰也是至死不渝。按照官方的说法,波尔布特觉得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需要依赖农业,所以城市的人口都应该前往农村进行生产。但是,此人真正的想法其实单纯到可怕:他觉得,这样美丽的城市拥有自己的生命。虽然它是人建的,但是作者已死。它本该空空如也。
“吴哥封城以后,街道就变成了我的肠子,总是空荡荡的。没病的人怕被传染缩在家里,有病的人应该都红着眼睛缩在床上。只有每天张贴告示的时候,才会看到陆陆续续的市民面用白布遮脸,上街打探消息。贴告示的士兵被各种动物的皮裹得像粽子一样,光看着就让人热得受不了。不幸中的万幸是,我们旅馆所在的区域还算安全,目前没有发现病例。高棉官府的人告诉我,不要走出这片区域,若是来了外人,也切勿让他进来。封城的日子难过的很,能买到的食材只有米粒,还昂贵至极。官府说,这种疾病乃是千年一遇的大灾难,封城的日子怕是不会短,建议我们做好心理准备。同时,政府已经派出了心理专家,可以做免费上门辅导,以解决因幽闭、沉默、压抑、饥俄而导致的想做爱和想杀人的冲动。那天,我想得厉害,就请了一个心理专家。他进门后,戴上了遮面布,说:“肏你妈的,你们这些死明人,活该。”说完,就跑走了。我并不知道这种人是干什么的,之前在大明也没听说过这个职业。被这么一骂,我一时间也没有什么想法了,看来这些人还是有些真本事的。”

吴哥陷落的六百年后,高棉修了第一条铁路。不少外国人来到暹粒瞻仰这伟大的都城,并在市中心建起了红灯区,取名为“红色高棉”。那时候正值可怖的经济大萧条,人们把这雨林深处的绝美古城看作是世外桃源。夜色降临,整条街都亮起了橘红色的灯。管弦乐从古色古香的酒吧中飘出来,男男女女在暖风和月色下跳起了似是而非的探戈。一位有法国血统的小妓女总是坐在一块雕刻着阿修罗的老石头上没心没肺地笑着。这是吴哥难得的回光返照。人们和这座城一起,忘记了山崩地裂般的灭顶之灾,忘记了镜花水月般的前世今生。
这样浪漫的时代,也曾出现在波尔布特的人生中。当他刚刚进入丛林,怀揣着伟大梦想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最浪漫的人。他和他的反抗军痛骂着心中那个懦弱、保守,没有生命力的政府,讨厌着身居高位、衣冠楚楚的国王。夜晚来临,他可能会拉着一个女人,或者男人,穿过虫声清脆的灌木丛,爬过大树的板状根,攀上废弃神庙的屋顶,然后在满世界的虫鸣鸟叫和星光烛影中脱掉衣服,把象征着破坏、进攻、摩擦、重生的革命进行到底。液体流入湿婆的第三只眼,一切在那原始而残忍的冲动中变得琢磨不透,而又美不胜收……
“我实在没办法只待在家里了。那天晚上,我和随从趁着夜色偷偷溜出去,打算看看瘟疫究竟有多严重,以及有没有可能逃出城去。当我们沿着空街走到路口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位肌肉结实,面无表情的士兵。他用低沉的嗓音喊道:’干嘛的?’ 我连忙解释:’水不够了,出来取一点。”他看我们是汉民,又穿着得体,不像是坏人,便又用那驯狗的语气说道:’为什么不戴遮面布?’’切,你为什么不戴?’我用蹩脚的高棉话回他。这下这家伙真急了,不过我根本不害怕。眼看他就要过来打我,我突然倒地,不停咳嗽,一边大喊’别过来,我有病!’ 想不到,这个士兵还是狠狠地打了我的头,还拎着我的辫子,把我和随从塞回了屋里。对这种不怕死的人,真没什么手段。第二天,我们从街头酒馆的后门绕了出去,省的被他找茬。现在处于特别时期,街上走动的有一半都是便衣士兵。我们老老实实戴着遮面布,慢慢走在空街上,并没有看到生病的人。民居都大门紧闭,每扇城门都有上百人把守,城内的居民真是插翅难飞。街上唯一热闹的地方便是公告栏。每两个时辰,疫情相关的消息就会在这里更新,现在那公告栏上已经贴了厚厚一层纸了。我仔细看了看最新的告示,吃惊地张大了嘴巴:ZXWY已经传染了整个高棉。现在,全国沦陷,大灾难彻底降临了。”
红色部队从雨林中冲出来的时候,已经变成了一支组织严谨,训练有素的铁军。尽管政府把他们说成恐怖组织严加防范,其势力还是在一步一步壮大。波尔布特告诉贫苦的农民,跟着红色部队一起干,就可以推翻人吃人的社会,然后每个人就都能像城中的国王那样吃上白米粒了。他手下的亡命徒就开始戴着遮面布,潜入了象征官僚与资本主义的都市。他们一开始只是围堵政府和商会的办公楼,后来有些人会砸大人物的车子,砸公共设施,最后大家开始攻击反对派市民。警察干预了一次又一次,可是戴面布的人越抓越多,而且只要他们摘下面布,就变成了普通人。待波尔布特兵临城下的时候,城市早已被白蚁一般的面罩们占领了。大家欢呼着,在残破神庙的注视下,期待着一个无私而神圣的新时代的到来。
新时代往往是复杂的,不论对一座城,还是一个国。当吴哥被法国人发现后,新时代就成了一位不速之客,闯入了原本静止的时空。重见天日的神庙被钢锯切成小块,装船运往了目不可及的远方。这种嘈杂原本不利于神灵清修,然而在新时代到来之际,世界一瞬间就被工业社会填满,神便没有了显灵的自由,更没有对革命进行病理学分析的权力。这样的新时代,只适合更加彻底的革命,与更加优雅的病毒。
“告示上说,ZXWY病毒造成的死亡人数持续上升,金边已经变成了一座废城。从这一天起,吴哥城内的所有人都只能呆在住处。每天会有士兵挨家挨户分发食物、水,传递与疫情相关的消息。我的随从由于发烧,必须自己被隔离在一个房间里。这样,旅社的这间屋子,就只有我一个人了。接下来的几天,更可能是几周,甚至几个月,我都要被困在这儿,一步也踏不出去。”
“高棉帝国极盛的时候,吴哥周围都是正在崛起的新神庙,城中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小贩。我为何不是在那时到的吴哥城呢?眼下,我就要被困死在这病怏怏的城里了,我的故土,我的皇城,我的一切,都要变成,都要变成他人的囊中之物了。都是些混蛋,都是大逆不道的病毒!王八蛋,狗皇帝!不配做人,愿你这一支全家短命,断子绝孙!肏,我推不开门了。他们把我的门给锁了。哈哈哈哈哈。狗皇帝!”
黄破武的笔记从此处开始,便时不时出现一些奇怪的歇斯底里。据最初发现这本笔记的人推测,写这篇的时候,黄身上病毒的潜伏期已经过了,等待他的是一场毒与人的大战。更准确地说,是一场简单生命对复杂有机体的残忍虐杀。
六百多年后,波尔布特下令,所有人都要从大城市迁出去,限时两天。此时他刚刚得了高棉的天下,正要用百万生民,去做一个石破天惊的试验。吴哥城在两天之内变成了空城,城内尚未散尽的烟火气和可怕的寂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们成群结队赶往农田,开始了没什么必要,却必须进行的劳作。整个国家在朴素而有生命力的思想的引导下,也进入了一种罕见的歇斯底里。
“早上,官兵通过门上的洞给我送来了一桶水、一碗米和一张纸。纸上写着瘟疫的最新情况。据悉,吴哥周围村子里的村民已经死亡殆尽了,金边也好不到哪里去。原先的病毒虽然可怕,但人们还不至于无能为力,结果这病毒现在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异。最新一批感染的人出现了骇人的症状。有男子在得病后浑身溃烂,烂的地方形成了条纹。死的时候,他像一匹斑马,只不过黑色的部分要涂成红色。另一个人被病毒引起的囊肿堵住了呼吸道。临死前,她痛苦地戳破了气管和鼻腔,却还是没能喘上气来。很多人被病毒一口一口吞食掉了肌肉,死的时候像一根一动不动的干柴。最令人胆寒的一例,发生在大金欧市的街上。据目击者称,那位患者在走路的时候耳朵掉了下来。他低头去看,结果鼻子也掉了。在他还没有反应过来之时,头就重重地摔在地上了。一团紫色的粘液从他的脖子里流出,向远处太阳升起的地方慢慢爬去……”
没人预料到,高棉病变的如此迅速。在郊外的田野上,人们顶着炙热的阳光,把种子洒进稻田里。除了劳作,生活便只有背诵语录,学习思想,在身心的疲惫中等着一波又一波的肃反。有着法国血统的偷懒者悄悄爬上了湿婆神庙,眺望远处的吴哥窟。 他看到了残破而诡异的都城全景。城市像母马的胎盘,孕育,爆发,干枯,最后消失在茫茫大地上,丧失了作为被寄生体的最后尊严。偷懒者被发现后,病入膏肓的人们用铁刷子刷掉了他一半的皮肤。死前,此人仿佛获得某种艺术味道浓厚的保护色。他激动万分,安心地睡去了。这样的事情就一直发生着,人们仿佛十年前雨林中那些未被发掘的神庙,在轰炸机的吼叫中互相削鼻割耳,然后干柴似的慢慢消失在烈焰中,逃出了反复陷落的轮回。一万,十万,百万……漫山遍野都是瘦的不成样子的尸体。大城市旁,残肢摞成了玉米堆,血液流得像高粱地,人头好似大黄豆。如果有人站在神庙顶端,也许会默默感叹,啊,今年真是个丰收年。
“为了处理成百上千的尸体,高棉政府组成了“围剿瘟疫临时小组”,由大丞相担任组长。围瘟小组在城郊挖出一个个大坑,把堆积如山的尸体丢进去。坑里的躯体千奇百怪,又互相缠绕,其所能带给人的震撼远胜于世间任何一座博物馆。士兵用白布遮面,日以继夜地劳作;石灰粉在湿热的季风里放肆地飞翔,遇到水,便化成一道热气,钻入 遥不可及的天空。”
“小屋内的灯油已经全都用完,我只能在白天借着门缝的光写下病城的最后手记。不知是因为心力交瘁还是食物匮乏,我感觉自己大限将至了。今天没有人给我送水。若是我死在吴哥,请发现这本笔记的人切勿忘了此刻我们的煎熬与勇敢。横祸从天而降,每个人都使尽了浑身解数,却还是难逃天命。入侵,复制,再入侵;病毒就是一个可怕的象征,隐喻着简单、恶劣、有极强传播性的一切。它们时刻准备着,向精致、美好、别具匠心的事物发起漫无目的的虐杀。只有彼此的崩颓,才能证明他们的存在。从北边长驱直入的那个老匹夫和那些随风倒的狗奴才就是这样的垃圾。不过现在还活着人,谁又不曾是病毒呢。天渐渐黑了,水还没有送来。但我相信会来的。我相信。只要我们有必胜的勇气,有对生的渴望,有不屈的灵魂,那便一定有人可以活下来。我们就一定可以战胜病魔……”在这些颤抖的字迹中,这本笔记来到了尾声。它身上有一股好闻的檀木香,让人读来神清气爽,不忍放下。
六百年后,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地球上失去了,也诞生了很多优秀的城市,但没有一座出落得如此天马行空,陷落得如此大开大阖。波尔布特站在祭坛上,禁不住想放火烧了这座独一无二的城市。此刻,他手持破武的笔记和一本六百年前金边皇宫的奏折,正看得入神。
折子上写道:“吴哥城最近出现大明皇族。据可靠情报,城内已布满探子。他们企图发动革命,颠覆国家。建议封闭吴哥城,永不续用,以绝后患。”
“准奏。”
波尔布特用手摸着神像巨大的阳具,哈哈大笑了起来。他觉得这世界荒谬得明目张胆,诗意得狗屁不通。他决定烧掉这些破纸,让这荒唐的陷落,陷落到永恒的荒唐中去。
那本笔记的最后一句话是:“今天还没有人来送水,也不知道疫情被消灭得怎么样了。”波瞥了一下,点燃了它,然后合上了双眼。笔记从头开始一页一页往后烧,每烧一页,波尔布特就会看到那页里记录的吴哥城。他目睹了伟大神殿的落成,看到了风光满面的湿婆,了解了封闭都城内犹斗的困兽,便觉得这一切都似曾相识。
新的万人坑还在远方修建着。同时,感染瘟疫的阎摩一个一个摔进早已挖好的坑中,好似堕入无间地狱的赤裸羔羊。
此刻,温暖的风吹拂过波尔布特的脸,让他澎湃的心渐渐平静了下来。他回味着笔记中那飘渺的过去,额头上慢慢长出了一只眼睛。这只眼睛里的世界一片红色,不分黑白;此眼之所见亦是一类事物的绝佳隐喻,它们宏大而精彩、混沌而澎湃,令人想入非非。
明日,波尔布特会如约占领吴哥城。在湿婆之眼的庇佑下,这座城将又一次走向命中注定的陷落。
“水还是没有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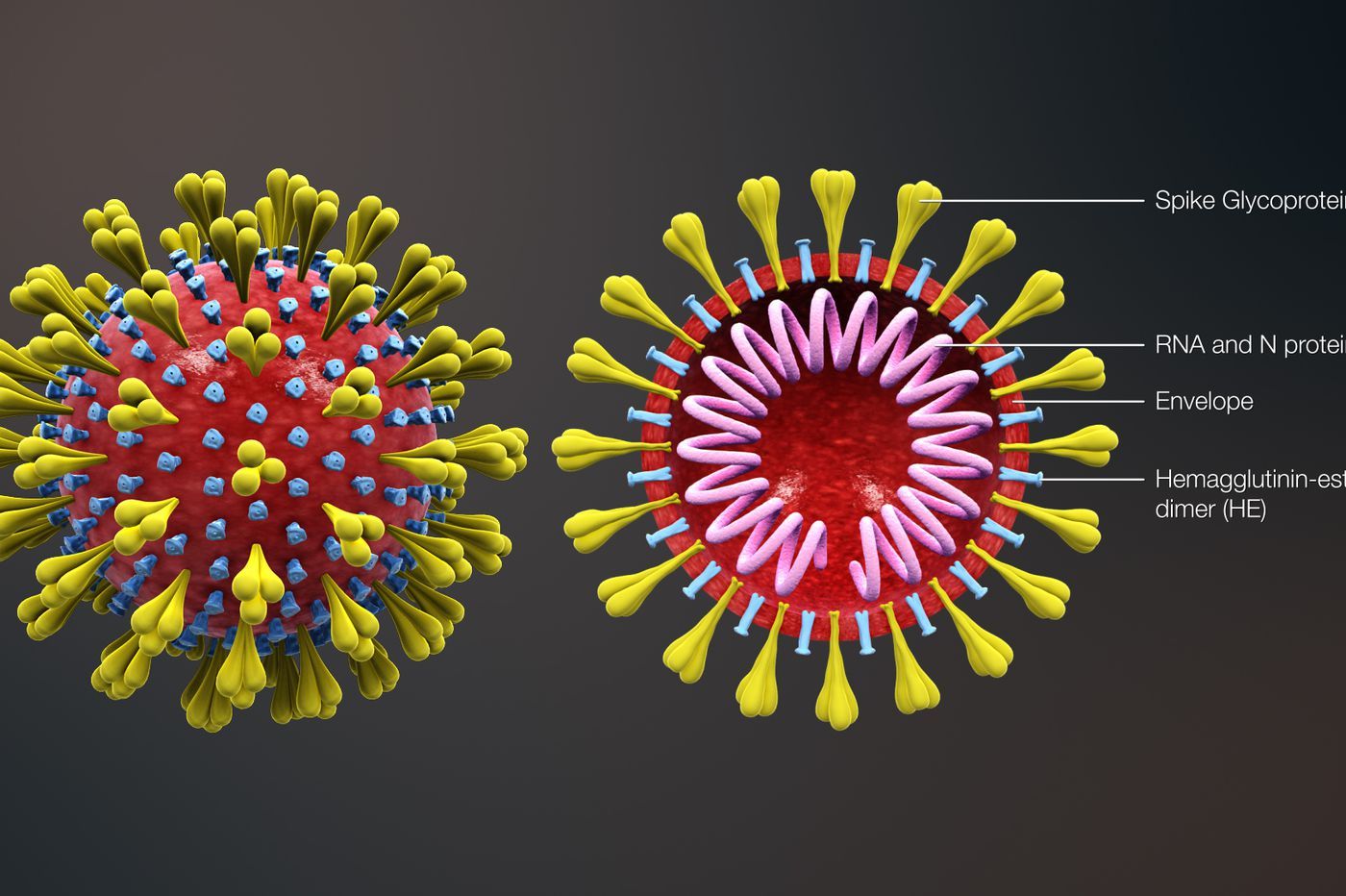
2020.2.10
李借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