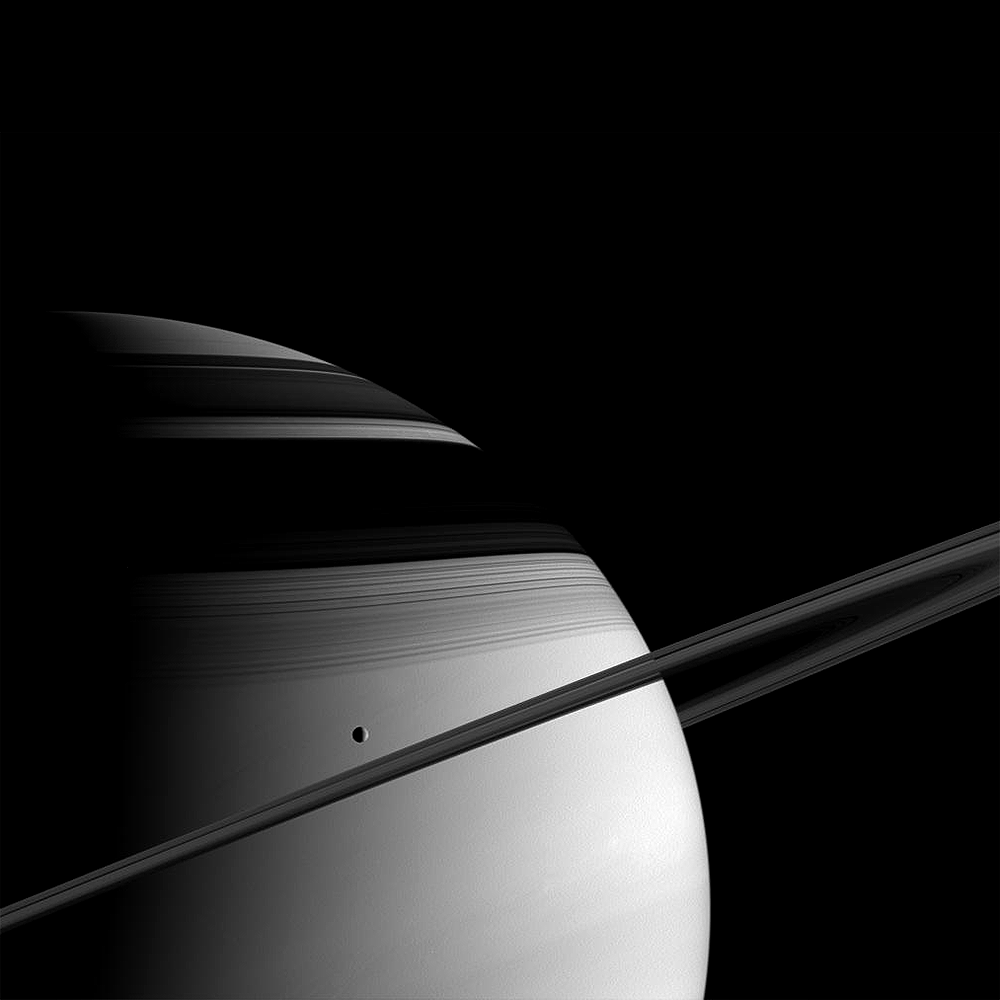秋衣
作者:越客,南浦村人,现居杉城,城外有湖,湖下有舟。
世上有那么多需要叹气的东西,速朽、恐惧,还有秋衣。从上海回到杉城后,我住到老房子,一个人做饭,一个人洗碗,一个人洗衣服,一个人到顶楼晒被子。
那是一件修长的灰色秋衣,不知洗过多少次,V领整个耷拉下来,已经成了O字,风一吹微微晃动,后背可以看见两三个小小破洞,秋裤同样如此,中间是洗到发白已然皱成一团的底裤,还有什么比天台晾晒着的内衣更能窥见中年男人的随便与窘迫呢?
他从事什么工作?我见过许多家境良好穿着随便的男子,更多时候,这是个资源分配问题,他们一方面不在意,一方面把钱用在显卡、手机与孩子身上,就在同一条天蓝色绳子上,在那件秋衣旁边,挂着好些亮丽光鲜的衣物表明他已经结婚,至少有个女孩,她在哪里上学?成绩好吗?他从事什么工作,是本地人吗?有没有离开过杉城,还是像我一样,去过哪里又回来了?
有年世界杯,我在外滩玩一种射门游戏,在你面前摆着无数小门,全部用贴满广告的纸罩着,你射上一脚,球把纸捅破,才能看到后面的奖品,有时你想射左上角,却射到旁边那个,如果你不确定是否想要,就收下吧,不然能怎么办呢,没人有机会把所有门打开,谁也不行。这样年复一年,你收到的东西越来越多,到一定时候,你不得不扔掉一些,我们每个人都听过芝麻与西瓜的故事,可你怎么知道什么是芝麻什么是西瓜?何况有人就是更喜欢芝麻只是他那时并不知道,等知道时又已经太晚了。
那以后一年过去了,我还是经常想起这件秋衣,每次我都庆幸那个人不是自己,但我清楚,那个人很可能是幸福的,家庭生活总有让他微笑的时候,当他为孩子,为妻子,为婚姻感到自豪的那个时候,他将带着只有他才能体会的欢乐看着那些尚未结婚没有孩子的人。
两年前,我们部门七八个人到萧山的联排别墅度假,我们这栋一看就是草草装修后用来出租的,一共四层,三层地上,一层地下,我听他们在客厅打了一晚上麻将,那天没有月亮,一阵又一阵呼啸的风被密闭着的窗挡在外面,室内弥漫着燥热空气,被子没有干透被灼热身体烘烤着发出既湿且霉的白雾。
一切都是缓慢而轻易不为人察觉的,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时间过着平淡、琐碎、重复的生活,如同一个向下的斜坡,当到达某个临界点,就不由自主滚落下去。最让人不安的并非幽暗潮湿的囚笼,而是在日复一日的对抗里,眼睁睁看着自己长出爪牙变成老虎。
我们这个国家,一旦有份足够稳定的工作,似乎就拿到一张通行证,可以对一切看不惯的事情提出批评,薪水越高,批评的人就越自信。我同样沾染这个毛病,在夜里,我说,这是另一个我,似乎这样就不必为白天做过的事说过的话负责,可以堂而皇之站在高处观察整个世界,这可真让人厌憎。
刚回来几周,看见许多惊讶的脸,连同许多疑问,每个人都希望从我的回答里验证自己某个看法,这是向过去告别不得不经历的一种仪式。并非他们在追问,是过去的凝望,一张苍白疲倦的脸。
你们见过凌晨四点的杉城吗?凌晨四点的杉城有两种模样,取决于你凌晨四点睡,还是凌晨四点醒。有段时间喜欢夜里漫游,四处看静寂的样子:漆黑的花坛、路灯下的桌椅、桌上轻舔舌头的猫,墙上画了一半没有上色的戏剧脸谱。在凌晨四点,他们样子是不同的:轻轻张开眼帘的花,不声不响的黑色藤椅,徒留痕迹的猫,以及笑着的脸。
当早上蒙蒙雾气升起,阳光已经穿透云层,我听到鸟儿的鸣叫。很快,天色放光,人们从一栋栋楼房走出来,走到街道上去,打着哈欠,半眯着眼睛,他们前天晚上太累了,工作、家庭、欲望,让他们疲倦。总有人被困在不合适的地方,他们一方面抱怨,一方面什么都不干。
多少人年轻时想要一个饶有诗意的生活,最后却只得到满满一盘又硬又酸的醋栗,有时甚至连醋栗也没有啊。让人难过的倒不是满满一盘又硬又酸的醋栗,而是他竟然为此满足。
对生活我没有太高欲望:主要穿衬衫、T恤和球裤;偶尔到楼下散步、吃夜宵;没有烟瘾,偶尔喝酒,主要啤酒——尽量不喝本地的,水质太差,按照经验,以武汉、厦门、重庆、青岛等地出产的口味为佳。有一个米白色直筒瓷制扎杯,冻好的罐装啤酒倒下去刚好八成满。一个樱桃红轴键盘,敲打起来像夏天落在地面的豆大雨点。一个蓝色圆口咖啡杯,早上下午各一杯浓咖啡,以及一张通体黑色的人体工学椅。总体来说,人体工学椅和机械键盘是我觉得性价比最高又不易为人察觉的两样东西,后来椅子塑胶把手慢慢剥落,露出好大一块铁片,将右边木制抽屉戳得坑坑洼洼。
我喜欢在这个熟悉的房子四处走动,从客厅一头到另一头需要十二步,客厅到卧室是十五步,绕卧室一圈是十步,这是我以前不知道的,中学六年我都住在几公里外的学校宿舍。或者做点不怎么吸引注意力的事:站到飘窗上贴近透明玻璃看楼下缓缓走动的黑色小点,看与昨天形状迥异的云朵,看对面高楼阳台上的脚手架、鱼缸、洗手池以及蔓延墙上的青藤。
有时我觉得疲倦,一般由于前天晚上没睡好,或被隔壁突如其来的吵闹声惊醒,头向后靠着,就这样睡过去,但外界一切,属于南方午后的阳光、空气、声音、味道,依然在耳旁飞舞。有好几次,当我醒来,觉得有朦朦胧胧的光,透过薄薄眼皮呈现出一层亮色,睁开双眼,依然身处密室,腿伸在桌子底下,屋子被一层暗色雾气笼罩着,一点光线从被风吹开的窗帘底下钻进来,无精打采接受自己黯淡的命运。
“我”之成为“我”的东西,沉在深处。过去有千百万种可能,所以通往今天,有其必然所在,解释过去不会让现在变得更好,或更坏,借由解释过去通往未来要冒着不断改变过去的危险,囚笼、铁屋子、老虎、沼泽、城堡……某种意义上,我们依靠想象活着,经由“现在”这片滤镜折射而成的朦朦胧胧的影像,倾向于呈现自己愿意看到的模样。
从老房子骑车到城外镜湖要一个多小时,据说镜湖底下有艘装满瓷器的船,谁也没有见过。我更愿意相信下面沉睡着一座古城,那是我在梦里见过的,那时我坐在湖边,头上是闪耀的群星,月光和湖水一起流向远方黑蓝色的天空,然后我看见水底许许多多人穿着古时衣裳走在青石板的街道上,耳边传来一阵阵寒暄叫卖声,尽是乡音。
几天前,在镜湖边上,我遇见了秋衣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