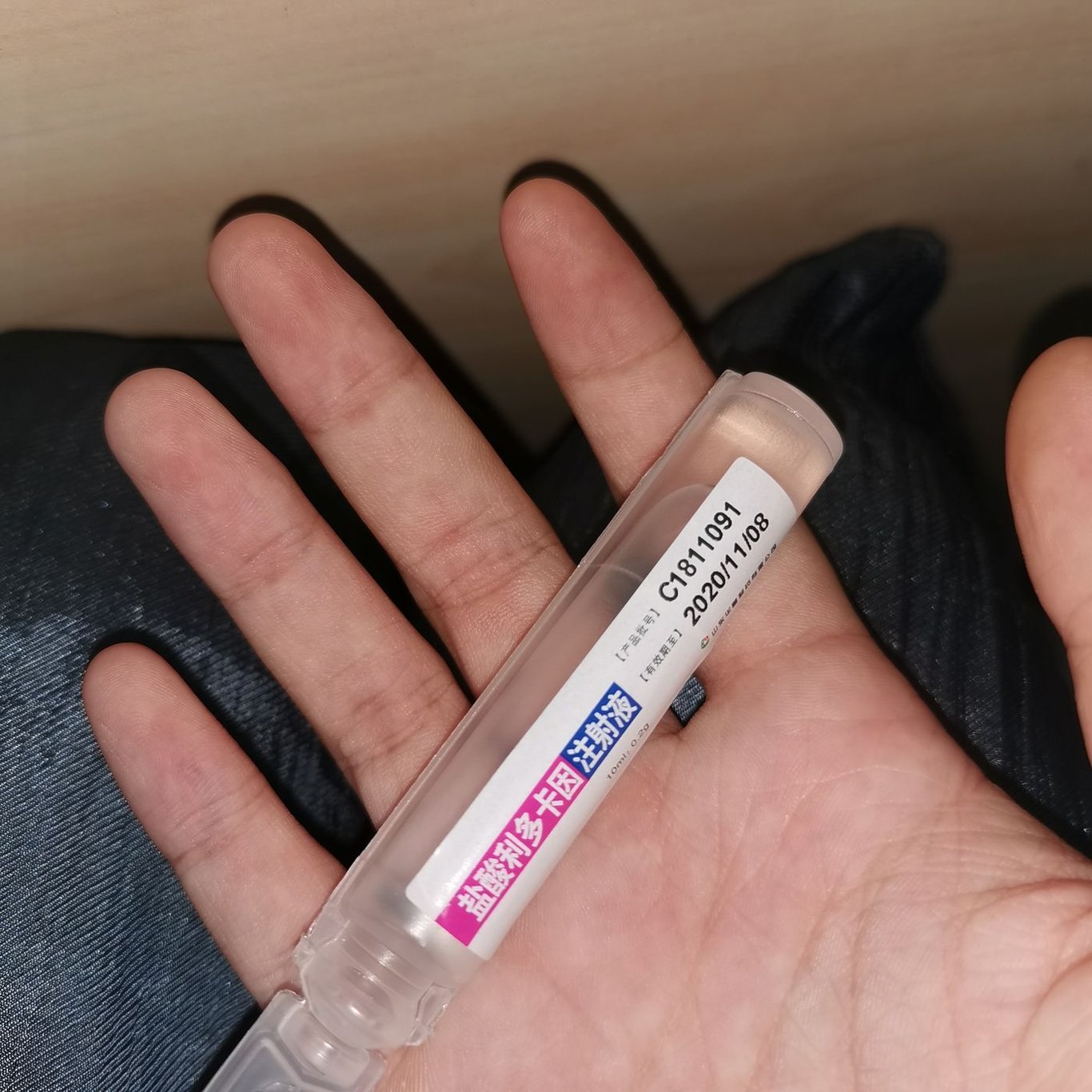对死亡的误读
01 小狗
听闻妈妈说小狗去世时,我正与约会的女孩在电影博物馆闲逛。临近闭馆,我们从四楼乘电梯向下的当口,看到那条微信时突然抑制不住情绪。
如果将礼貌和距离代入这个场景之中,那一位在我身边的人,是正应当“做点什么”来回馈我的“悲伤"。但事实是,我知晓我并不是一个可以为它的死去而理由充分地落泪的人。
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我不够爱它。这种“不够爱"非常庸常:我对它并没有投入深刻的情感,也并没有承担一个小狗主人应要做到的事;随着我长大,我越来越疲于与它玩耍,在它每一个长大的关口我又都并不在乎;在它的生活中,我充当一个突然出现而又突然消失的角色,即便它并不了解什么是“孤独”,但我却漠视它的孤独,并且将这种孤独放置。
十六年来,它的世界就是我家楼顶的花园。在我小学时,它是我的伙伴,我与发小每天会牵着各自家的小狗上街,然后到晚饭时间一同回家,我们带着它们出门,看它们打架,在它们狂吠的时侯生气,教导它们做一只“听话的狗”。它一直很笨,在我们对照着《狗迷》(一种以前可以买到的大开本杂志)里的方法训练它握手时,它怎么都学不会,每一次都是把狗粮吃掉然后以摇尾巴转圈结束。
后来姐姐把她的另一只小狗寄养在我家,我会因为它欺负那位新朋友而生气;后来我在家里小花园养彩色小鸭子,我也会因为它的霸道而跟它生气(当然现在来看,买卖这种彩色小鸭是很不道德的行为)……我对它的不满情绪,随着它的不听话和戾气上升,最后变成一种嫌弃。
我至今能够回想起来的它灵动的瞬间,是它在还是小小狗时,第一次学会爬家里的楼梯。从三楼向下的十几级,一直是它童年时的阴影,每次我们把它抱到楼上玩耍,它因为腿太短,总是不敢自己下楼梯。直到有一天它终于学会之后,开心得活蹦乱跳——那一年我念小学四年级,我会因为它的成长而雀跃。
但是回溯这些故事,并不是为了佐证我曾“陪伴”它。大概从进入初中开始,我的生活有了更多面,它越来越无足轻重。我可能情愿上网冲浪,也不愿意摸它一下。我的家人也并不会很经常地陪伴它,甚至属于它的那个花园,也在日渐因为不搭理而显得狼狈。我们家的房子,有许多个被荒废的空间:我小时的卧室、书房、花园、小浴室……对这些空间的漠然,和对它的漠然是同一种逻辑:它好或者不好,都并没有这样重要。
如果让我理清这一些,可能可以朴素地归结为对生活的不热爱。所以每每旁观周围朋友对小动物的欣喜时,强烈地抽离感总在提醒我。甚至与我亲近的大学同学,也只在最近才知晓它——我的小狗——的存在。她们或许惊讶为什么它这么隐形,因为它确实对我来说不再重要了。
年复一年,它每天在花园里看着对面楼顶中发小的狗,大概知道一些“孤独”的情绪吧。直到今年寒假回到家,听说发小家的狗离开时,我还在想“它去哪了?”。
所以与朋友谈起它的离开时,收获到的安慰,都是基于同样的饲养宠物经历起:“我也养狗,我知道你的难受”。但我无法去辩解和说明:我其实因为它的死并没有非常直观的难过,因我们之间的情感连结,随着我的成长和它的老去,已经逐渐成为权重最低的一项。我不会认为它是我的家人,我也没有对它有家人般的亲密……所以我无法向朋友解释这样的情绪,实际是非常不堪的。
但那一刻阅读信息带来的难过,只是对自己身上一个“道德污点”的消失的恐慌——当它离开,一个曾经能强有力地作证我作为一位并不负责任的、冷漠的人的原本富有生命力的“证据"真实地消失了。没有人会再知道我对它的不好、漠视和不关心了。而可怕的是,童年的回忆和面孔,也只是那一霎那的悲伤而已。当我哭泣结束,我还是会继续我的约会,或者下一个刺激的、有趣的事情。无法抑制自己面对现实世界的欲望,与无法抑制自己对大部分炙热的情绪的不感兴趣一样。它不会出现在我的生活中,也并不非常特别,当写完这篇文章,对它的记忆也会逐渐淡去。而这些都是我无法控制、也不想要控制的事。
02 死亡课
都说成年人最需要的是爱情课、友情课和死亡课,前两者我一直觉得我本人大可摸着石头过河,自成一派不用教化,最后一项其实近期才发现,自己有多么空白和无能。
前阵子有一次,在谈话间朋友说起ta亲人离世的信息时,我只是在大脑飞速旋转:我应该说什么?是表示安慰?还是安静聆听?
几秒钟前我们尚处一个调侃和发笑的语境,而后对方提起这件事时,我突然对我的玩笑话感到羞愧,“需要道歉吗”?我先想了一下这个,“道歉会给对方压力吧”,然后放弃这个想法;“需要说节哀吗?”,“好像是应该这样”,但是对方显然比我更会处理情绪得多——有一种恐惧在于,你发出得任何一句话,任何一种祝福/安慰/回馈/表达都是带有预设的,你恐惧这种预设与对方的立场相悖,正如同ta说“说难过肯定不会开心 但是也不至于到悲痛欲绝 虽然这样说让人感觉没心没肺”,一定有悖于我们面对死亡宣告时被欲加和被建构的“悲伤”情绪。
就好像当朋友对于我小狗离开的"共情",大概率也建立在我对小狗的爱、真诚和亲密之上。但事实是,无法预料我作为一个并不合格的主人,有多么糟糕的行为。
中学时,我第一次经历亲人离世这件事。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一点感觉也没有,姐姐在外地读大学,白事宴席上还听了她给这位舅爷爷写的文章:大抵是带有非常不舍的情绪。很多写作者“借由”死亡进行创作,而那天我其实也创作了,写在一个已经倒闭了的博客网站,但我着实没有什么情绪——如果悲伤是一种必须的共识,那显然我是不被允许的。而“没有什么情绪”这件事,说来非常上不得台面。再到第一次读大学时,春节期间自己爷爷过世,那才稍有一些清晰的对于死亡的认识——但是尴尬的是,爷爷在我们家也有一个较为尴尬的状态,亲人们会存有的共识,是死亡是对他(和对周围人)的解脱。但亲人们不会说的,显然是括号里的话。
而我对那天家里办白事的记忆,居然寡廉鲜耻地停留在我跟我姐偷偷抽烟这件事上。再把这件事讲出来,可能更是大逆不道。就好像我对小狗的离开并不合理的悲伤,而不悲伤,其实也好像不合理。
于是乎在很多年后的今天,我真实地对这些预设的悲伤手足无措。与第一次见面的朋友谈话时,十句话之间问“你从哪来”“从英国回来”“为什么回国呢”“因为我爸去世”,我又是一阵语塞,不知道表达什么。像当时的我,如果我说“我的舅爷爷死了/我的爷爷死了”,别人会说什么?他们如果说“节哀”,我会说“还好吧,没有特别哀”,然后对话就进行不下去了:是对方的尴尬,可能和对我冷漠的臆测(这无可厚非)。
后来,前年在电影院看了伊斯特伍德的《骡子》,看完真是一场奇妙的共情。主人公也是一位不受家人待见、古板、偏执、习惯“恶劣”的老头子,他老得快要死了,但还是跟家里人矛盾重重,最后好像他确实真的死了——突然一切旧的悲伤,才有了新的解释,尽管披上外衣,但是这不具备任何的可复制性。我还是没有习得死亡课,习得的只有艺术的调度。但社交啊,这是没法调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