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菠蘿披薩,就沒有意大利菜
我對自己的意大利人身份常感到心虛。我大體上不具備那些普遍被認為屬於意大利人的特征——我不太外向,不怎麽穿西裝,更不會做提拉米蘇。我有次在北京地鐵的站臺和剛一起喝過酒的女生揮揮手分別,上了車才收到她對那一幕有點不滿的消息:“其實你不太像是意大利人。”也許她期望的是我更激情一點,比如在站臺上拿出吉他即興表演一首晚安歌嗎?那樣是不是夠意大利了?下次再試試。
吃飯也一樣:我好像無法勝任原生文化給我立的標準。是,我能享受一頓好吃的,但我似乎也能將就一段時間?比如十年?一個人在外生活到現在,除了煮面之外,也就學會了拌拌沙拉,了不起烤個土豆?我是意大利文化的害群之馬,天生少了一些美食基因嗎?我怎麽對高級食材提不起興趣?我竟然對女生和黑松露都這麽冷淡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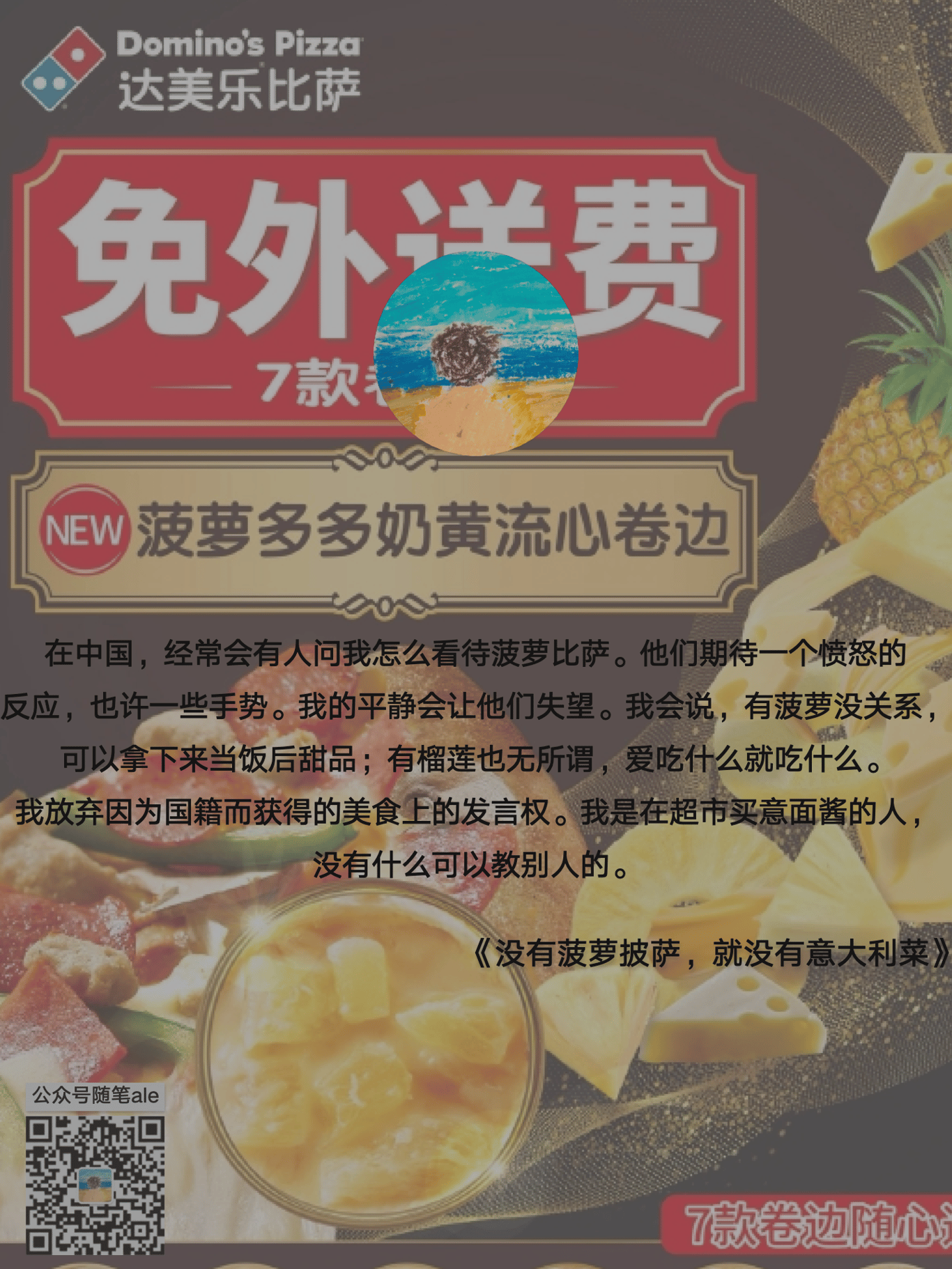
好在,這個世界上還是有相當合格的意大利人的。許久沒聯系的高中同學在巴黎開了自己的意面館。我在ins上刷到了他出演的宣傳視頻。他得意地坐在店裏面,雙眼被黑色發帶蒙住;兩個盤子從畫面左邊被端到他的桌子上。視頻的配音和字幕解釋,這兩道分別是剛加熱的速食面和店裏現做的意面。
兩道菜都是carbonara——在中文裏面,它多數情況下被翻譯成“奶油培根意面”,不過出於稍後大家會理解的原因,我這次想直譯它的意大利語原名:煤炭面。吃了兩口,同學連連點頭,豎起大拇指表示認可,贊不絕口。他接著盲品第二盤。面才入他嘴裏半秒鐘,同學像是中毒了一樣,身體忽然向前傾,將意面吐回盤子裏。“太惡心了。”同學搖搖頭說,笑著擺了個鬼臉。
眼睛終於被解放,速食品的包裝被放在第二個盤子的旁邊,輪到他發言,引向推銷的大結局:“我就知道。這個面煮得太熟了。它用的是培根和奶油,培根不能放在煤炭面裏,煤炭面是用面頰肉做的,培根是用來做別的的。真難吃。”他又指指第一個盤子幾乎感動地說:“這個就是,難以置信的好吃。”
他完美符合了網絡的期待,精準扮演了對正宗菜譜有執念的意大利人。2016年,一家法國媒體發布了某個改良版煤炭面的教程視頻。菜譜中犯的錯誤喚醒了部分意大利人的烹飪民族主義:用了平底鍋煮面,用了奶油,用了帕爾馬森而不是羊奶酪,用了培根而不是面頰肉,對法國人的辱罵迅速鋪天蓋地湧來。視頻中出現了百味來公司的意面;隨後,公司甚至出面聲明自己與這個菜譜無關。煤炭面仿佛和家人一樣重要——外人不許碰。它能如此成為全民的情感依托,是為什麽呢?
這道菜的名字比較有歷史感。它啟發了人們的想象力,直到編出了那種會寫在菜譜裏的故事。既然它叫煤炭面,那不就是煮來給十八世紀的礦工補充能量的午餐嗎?可惜歷史沒有那麽友好。要是能吃上營養如此豐富的菜,礦工肯定會開心上天了。我還敢說,如果用的是培根而不是面頰肉,他們大概率不會嫌不正宗。原因很簡單:當時,根本沒有這道菜。煤炭面的傳統,說輕點是虛假營銷,說重點是偽歷史。
它的菜譜更年輕,大概只有七八十歲。比起深厚的傳統,它的發明更多體現出歷史的偶然性。二戰期間,納粹支持的法西斯政府控制著意大利的北部,登陸西西裏島的美軍一路向北,陸續地解放著意大利。1944年9月,隨著一次戰場上的勝利,美軍在海邊小城市裏喬內舉辦了宴會。他們身上的食材有蛋黃粉,培根,奶酪,面條。那天的意大利廚師還記得美軍的“非常好的奶油”。他都用上了,且最後撒了點黑胡椒:給這道菜起的名字似乎是因為這一層看起來像煤炭粉末的香料。
煤炭面和意大利人的關系如此薄弱:它使用美國人的早餐材料——蛋黃粉和培根——給美國的將軍準備一個慶祝軍事勝利的晚餐;廚師還說過,菜譜的靈感部分源於他在南斯拉夫吃過的奶酪餡餃子。至於面頰肉,那天晚上是沒有的。五十年代的菜譜對這道菜給出了多種開放、包容的解釋:有用火腿的,用蘑菇的,瑞士奶酪的。六十年代起,面頰肉和培根通常是可以互換的,到了九十年代前者才成為了某種不可動搖的“新傳統”。因為覺得更好吃而堅持使用面頰肉是可以理解的。不過,要是認為煤炭面一直是這樣做的,等於是在美化自己的歷史,拿不存在的傳統來裝飾物質嚴重匱乏的、痛苦的時代。
在菜譜上死板、原教派的意大利人最近幾年成為了某種國際上的段子。在中國,經常會有人問我怎麽看待菠蘿披薩。他們期待一個憤怒的反應,也許一些手勢。我的平靜會讓他們失望。我會說,有菠蘿沒關系,可以拿下來當飯後甜品;有榴蓮也無所謂,愛吃什麽就吃什麽。我放棄因為國籍而獲得的美食上的發言權。我是在超市買意面醬的人,沒有什麽可以教別人的。我也不能算是傳統的背叛者。相反,信煤炭面的故事,堅定認為我們在美食上繼承了幾百年的權威,那才是違背歷史。我更傾向於維護姥姥姥爺那一代的真正的傳統:吃飽,雖然不容易,盡量地吃飽。
我老家在帕多瓦,意大利東北部。自十八世紀下半葉,帕多瓦所在的維內托大區糙皮病肆虐。它的癥狀是皮炎(因此被誤診為麻風)、腹瀉和癡呆。不及時治療,會要人的命。接下來的幾十年,意大利北部的精神病院擠滿了糙皮病患者。根據1878年的調查,意大利的患者數量多達十萬,幾乎全部是北方農民。那時有科學家認為這是玉米中存在的毒素導致的疾病。不過,真正的原因更簡單:那些農民每天消耗兩到三公斤的玉米糊,僅此而已,從而患上了這種維生素缺乏癥。今天的人吃飽了,也許飽到記性都變糊塗的程度,他們甚至將農村進行美化,懷念更純粹更自然的時代,還把大型超市說成惡魔,卻忘記了那對長輩的營養是一種救贖。
對於威尼托大區的農民來說,這場噩夢延續到了二戰以後,生活條件和營養有所改善後,他們才擺脫了糙皮病的折磨。只需要常識就能知道,那些人應該不會太在乎煤炭面是用培根還是面頰肉。我那個同學的家正好在帕多瓦曾經屬於農村的地區。僅僅七十來年後,創業的機遇代替了日常中的饑餓,讓同學有選擇能移民去法國,以捍衛抽象的傳統謀生,精神上和物理上都離開了那片土地。
2016年,我也成為了歷史上的意大利移民之一。和一百多年前的同胞來比,我逃離的不是不良的飲食條件,而是糟糕的就業市場。我很佩服他們:不識字就坐上船去美國打工,受欺負受歧視,就為了生存。想到他們的時候,我會感覺某種奇妙的連接。我們一樣為了尋找機會而離開了意大利;他們的孤獨、難過和委屈卻比我的要強一百倍。我隔著歷史材料觀察他們,試圖理解什麽叫意大利人。我找到了一些答案。大概,和正宗菜譜無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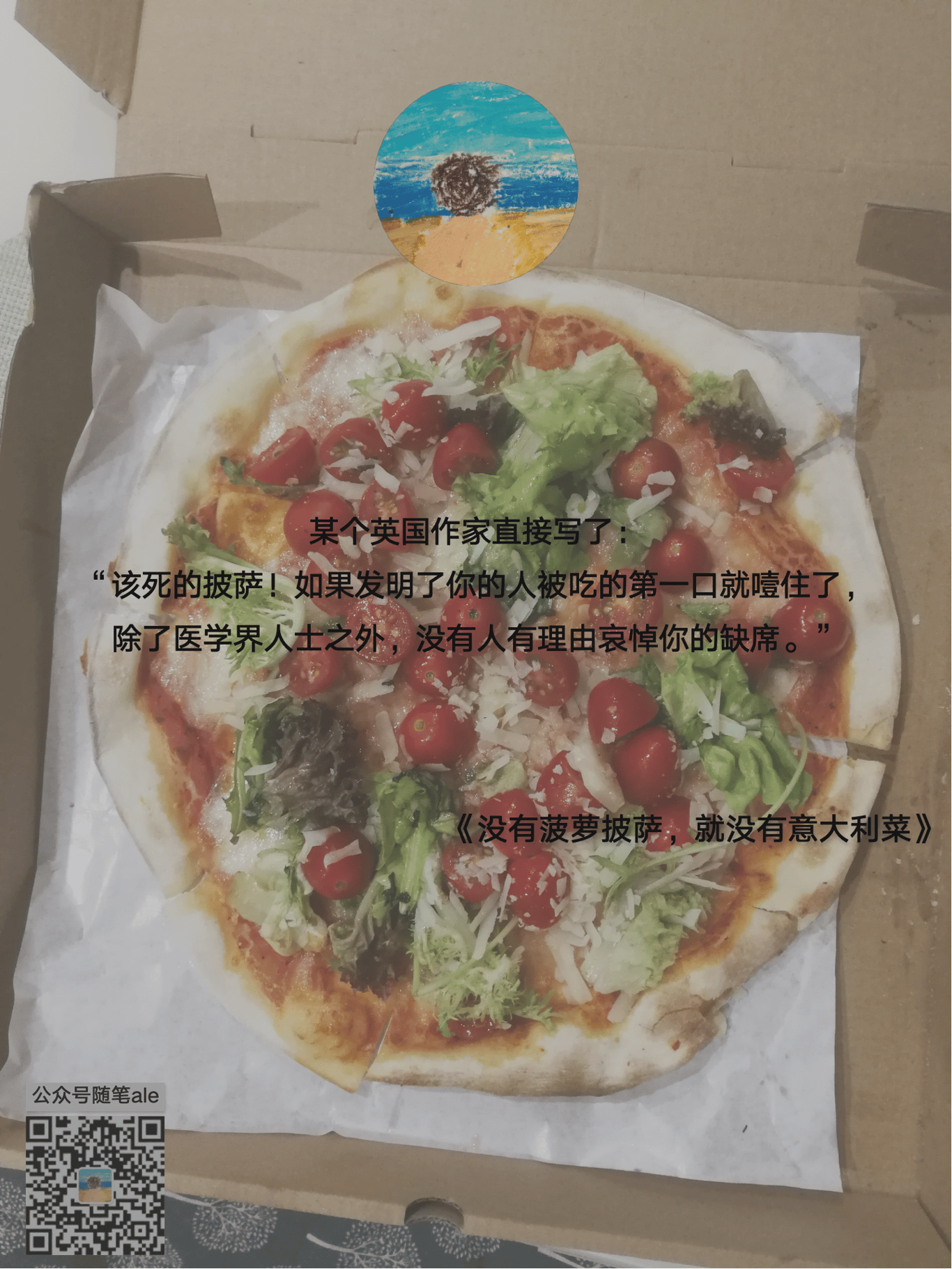
大家最熟悉的意大利菜有那些赴美的移民的關鍵貢獻在。他們會拿掙來的工資去買一些最為親切的食物。過節聚餐的時候,他們將鄉愁結合於美國超市的貨品,陰差陽錯做了一些會被列入歷史的嘗試。大概因為這樣的原因,有美食學者認為意大利菜源於二十世紀初的美國。我想補充一句:那些移民創造的不僅是我們如今了解的意大利菜,還有意大利人的身份。這就要說到披薩了。
早在十九世紀的那不勒斯,披薩確實已經是很常見、便宜的街頭食物。這是由來過意大利的各國作家用筆作過證的——有的還會毫無保留地吐槽它。除了披薩的存在,這些文字還記錄了另一個事實:那時候的披薩和現在的非常不一樣。
在1847年出的《帶新人逛那不勒斯》中,作者這樣寫過:“口味的確是無爭議的,但有些口味無論如何都不能成為嫉妒的對象。其中之一是披薩。 它是由不含酵母的面團制成的扁面包,因此極難消化。 這種披薩呈圓形展開,邊緣凸起,塗上橄欖油或豬油後再撒一些鹽。 有時他們將生西紅柿放在上面,有時放魚,有時放乳制品、大蒜,凡是你能想到的東西,都不需要經過精致的烹飪儀式,直接和披薩一起被放入烤箱。披薩主要被燒焦,而不是烤熟,再被取出食用。可憐! 算上這種難以消化的負擔,整整半天的時間裏,所有的消化力都處於糟糕的狀態。”某個英國作家直接寫了:“該死的披薩!如果發明了你的人被吃的第一口就噎死了,除了醫學界人士之外,沒有人有理由哀悼你的缺席。”
拋開作者們字裏行間的憤怒,有那麽幾點值得註意:披薩上有時會出現西紅柿,不過只是其中一個版本,並且是生食物而不是西紅柿醬。放上各種食材的“白披薩”才是常態。在1871年的一本烹飪手冊中,關於披薩的菜譜首次亮相了。手冊提供了三種菜譜:基礎款的白披薩餅,還有配鳀魚和配奶酪的兩個版本。沒有西紅柿。在1875 年的一首歌曲的歌詞裏,一位披薩師傅試圖通過四款披薩來吸引他喜歡的女孩婑婑拉,分別是:奶酪和豬油;馬蘇裏拉奶酪;大蒜、橄欖油和雜魚;新鮮的西紅柿。在那不勒斯,披薩餅和西紅柿偶爾會撞上,但並非是本地人最愛的搭配。
在美國,披薩變了。這是由現實條件決定的:紐約不是那不勒斯,買不到那些常放在披薩上的新鮮雜魚、西紅柿和奶酪。那不勒斯人會去超市找代替品。他們能找到意大利進口的番茄罐頭,還有橄欖油。至於奶酪——它容易變質,因此不適合跨海進口——那不勒斯人自己動手了:直接開店,拿家鄉的菜譜來做馬蘇裏拉和其他的奶酪。營業後,美國人也喜歡。很快,西紅柿和奶酪就在披薩上遇上了,並形成了被消費者默認的標準底料。
香腸和薩拉米被加上去了。這樣的披薩已經不是十八世紀外國作家怨恨的街頭窮食物。鳀魚也會出現,不過用的是罐頭的。只放豬油和奶酪的版本基本消失了。直觀上,披薩這才擁有了它典型的紅白顏色。初期的那不勒斯白披薩被淘汰了,而似乎沒有太多的人懷念它。也許,豐富好吃的食材能使人不那麽在乎傳統。
這個那不勒斯食物的美國化還帶來了另一個深遠的影響:讓世界看得起意大利菜了。在十八九世紀,來意大利探索藝術的歐洲貴族是真心厭惡意大利菜的。英國和德國人嫌菜做得太油,肉堅硬不熟,沒有黃油,還到處彌漫著蒜味。那時候,法國菜才算是高級。十九世紀末,面對意大利移民的美國人一樣不買單。美國那時用來定義健康飲食的指標是動物蛋白質,因此認為意大利菜太窮了。
不過,二十世紀初前後的研究陸續發現了卡路裏和維生素的概念。吃肉不再直接代表了健康,而是和代謝疾病聯系起來了。漸漸地,意大利移民的飲食吸引了美國人的興趣,意大利菜的欠缺變成了優點。1959年,美國生理學家安塞爾·基斯提出了“地中海飲食”的概念,碳水和植物成為了健康生活方式的標誌:沒錯,披薩的食材。西紅柿的種植隨之得以推廣了,意大利菜有了得體的名聲。披薩有市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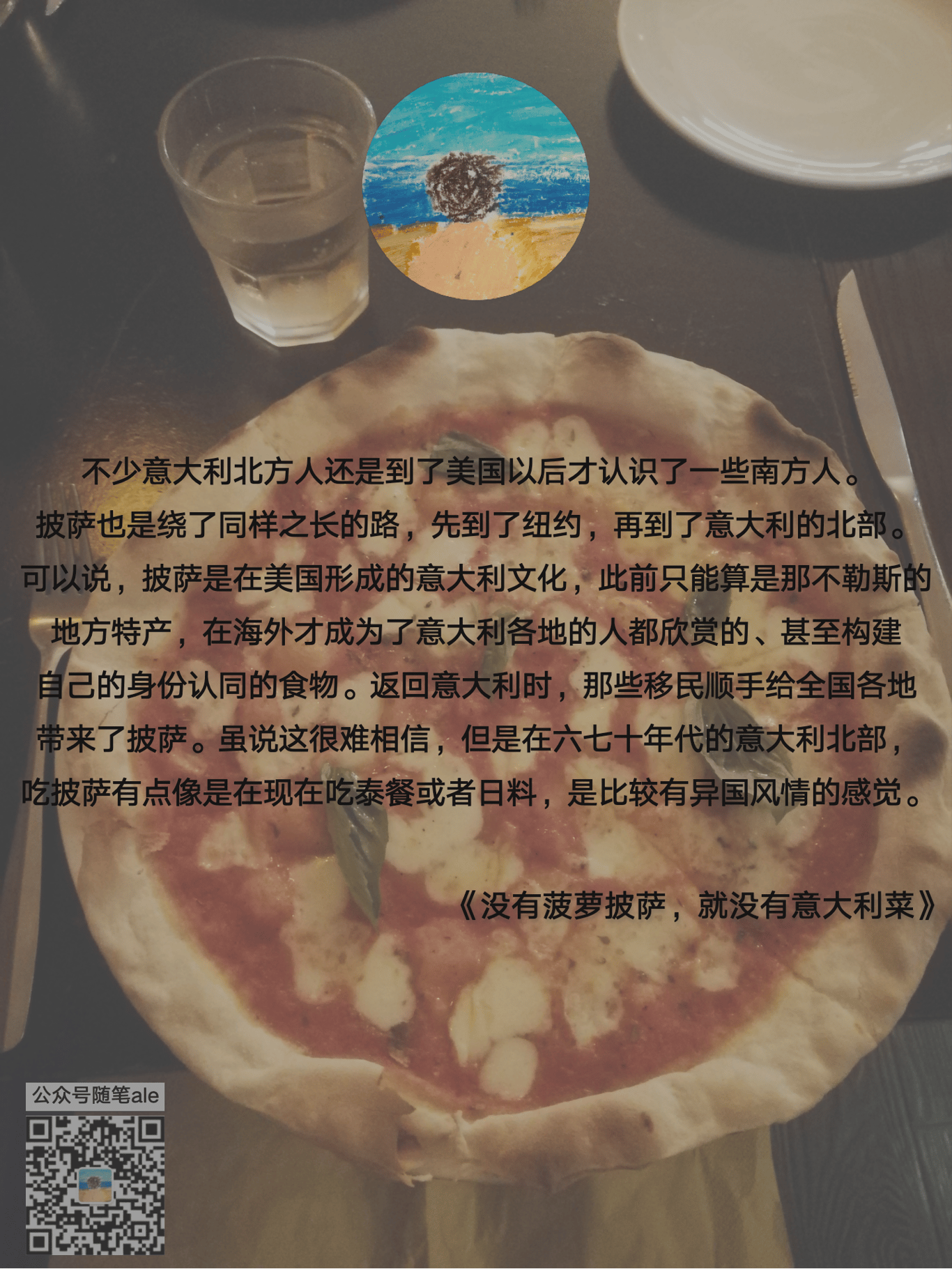
意大利於1861年統一建國。那時候,有政治人物說了一句至今仍在回響的話:“我們造了意大利,現在要造意大利人了。”也就是說,意大利從最開始就有身份認同的問題——生活在意大利的人不覺得自己是意大利人,而是那不勒斯人,米蘭人,佛羅倫薩人。兩千五百萬的人口,只有十分之一的人會講意大利語;剩下的講彼此不通的方言。
不少北方人還是到了美國以後才認識了一些意大利的南方人。披薩也是繞了同樣之長的路,先到了紐約,再到了意大利的北部。可以說,披薩是在美國形成的意大利文化,此前只能算是那不勒斯的地方特產,在海外才成為了意大利各地的人都欣賞的、甚至構建自己的身份認同的食物。返回意大利時,那些移民順手給全國各地帶來了披薩。雖說這很難相信,但是在六七十年代的意大利北部,吃披薩有點像是在現在吃泰餐或者日料,是比較有異國風情的感覺。面和披薩一樣,直到十九世紀末都主要是南方人的食物;北方人是在美國的意大利裔圈子才接觸到,再把它帶回家的。
距離意大利統一一百六十二年的時間,造意大利人的命題有推進,但不能算成功。有人說,只有國家足球隊踢比賽的時候大家才感覺自己是意大利人。考慮到它領土分裂的歷史,建立意大利這樣的想法還蠻樂觀——它要是失敗了,也不能說是在意料之外。先別說國家,相隔十幾公裏的城市都能為誰發明了餃子而陷入激烈的矛盾。也許,“意大利”是一個不太可能的概念,也許這就是它的浪漫。也許,這樣更能理解意大利菜的價值。從二戰後到現在的短短七十來年,圍繞著吃好喝好的幸福感塑造了意大利人的某種身份。這很了不起:對食物的熱愛讓五千多萬個陌生人成為了一個家庭,並把它變成了值得自豪的理由。
要知道,意大利人常感到自卑。和其他歐盟國家相比,我們的青年失業率、公共債務和逃稅總金額穩穩排名前三;反而,年輕人中本科生比例往往墊底,人均年收入和國家研發投資都低於平均水平。行政系統效率低,公共服務質量差,腐敗相當普遍。可以理解,生活在這樣的國家的人特別需要一些自我肯定。能夠在某個領域上擁有世界頂尖的地位,是對於社會中如此多的不足之處的一種安慰。食物告訴我們,不管經濟多差,生活多不便利,未來多不確定,到飯點的時候,我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所以意大利人很願意吐槽自己的一切,但不允許別人用培根做煤炭面,因為那是對我們本就不太穩固的身份致命的挑戰。
但仍然需要記得,意大利菜能做到如此極致的地步是通過創新、嘗試、甚至對傳統的冒犯的。在1860年的那不勒斯,有的店開始在披薩上放香腸和蘑菇,遭到早期原教派的反對。“跟著這些流行趨勢的食物配不上叫披薩。”他們會說。今天,那些卻是再正常不過的披薩料。在三百多年的歷史上,很難說有哪些食材沒有路過這個如今意味很深的烤餅。能確定的是,它的變化從未停止。能自由地嘗試不同食材,披薩才能做到各種令人有口福的版本——結果和過程在這裏一樣重要。換一句話說,沒有菠蘿披薩,就沒有意大利菜。
寫在後面
為這篇文章做的研究把我從傳統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了。在過去,自己對意大利菜的敬畏很大程度阻礙了我和它的互動。這很糟糕,因為會讓所有的可能性都滅在了起跑線。我唯一敢在廚房開火的時候,是在我能保證菜譜中每一個要求都被滿足了的情況下——我曾經為了找一塊面頰肉跑了半個北京,又在柬埔寨首都一家家店挨個找藏紅花,都是為了做面。自己設立的如此之高的門檻使我在做飯上變得僵硬,缺乏個性。在外漂泊時,吃意大利菜對我原本是一種心靈上的慰藉,我卻帶著沈重的不能犯錯誤的心態,把它看得很神聖,但其實是和它疏遠了,以至於它無法融入我的生活。這很可惜。
面對歷史上那些不斷在演變的菜譜,那些偶然形成的經典搭配,我放松了許多。我意識到,意大利菜不是一門擁有絕對規則的學科,而可以包容任何以好吃為目的的嘗試。寫到這裏我要承認,到底什麽是意大利菜的精髓,我無法為大家回答。不過,我還有一個好消息:我們都有回答的資格。今天做了一個豆瓣醬意面,感覺還不錯。

小小的移動編輯部包括
編輯:劉水
作者:ale
參考書目
DOI - Denominazione di Origine Inventata (Alberto Grandi, Daniele Soffiati)
Storia della pizza: Da Napoli a Hollywood (Luca Cesari)
閱讀我更多的文章,歡迎點擊鏈接,訂閱我的個人專欄!
專欄定價6刀/月,每月更新三塊篇 🍕🍕🍕
期待大家的評論互動!
a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