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加繆《鼠疫》:摘記、摘譯與雜感

蹉跎未幾,已然日午了。冬日的光陰,總是倏忽即逝。“蹉跎”——這個詞在腦海中出現的時候,我想起了《蹉跎歲月》這個電視劇。80以後的人們可能不知道。
這幾天,從早上十點左右到下午三點,空間中蕩漾着明麗的光。還有昨夜星辰,它們在天幕的位移,變化的顏色,都顯示冬去春來。季節轉換在星球、空間、光線、風、空氣的相互親愛中彰顯。
我想,或者說我認為我可以感受得到:很多人原先為自己設計的計劃,原定的日常,這些天都被干擾了。所有人都被感染了,從某一個方面,別的地方,從內裡。而這種異常的改變,也許不是臨時的、短暫的,而是一生或者整個世間和世界意義的。


31年前,我讀過加繆的《鼠疫》。31年前,是如飢似渴,極為空曠的一個世界。後來,我忘了這本書寫了什麼,只有結尾留下一點依稀的印象,就像在電影院,電影結束後,屏幕上的光靜止屏幕變成死寂的蒼白之前,最後一片光在抖動的白屏。而這留佇在記憶中光亮晃動的白屏,和它之前被遺忘難以觸及的歷史,就像我所經歷的時代的隱喻。
我重讀《鼠疫》,不是為了尋求共情或者感動,或者好奇人人傳抄的一句名言警句般的話到底怎麼說的,而是因為現實中一大塊無知而漠視了東西,需要去認識理解。我們都以為離災難太遠了,雖然世界上災難的信息鋪天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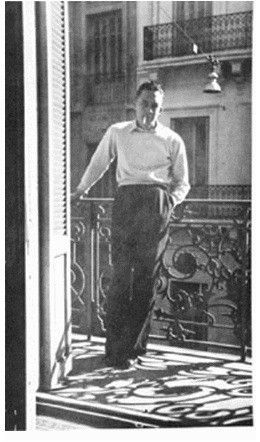
加繆的小說寫得實在太好看了。他知道怎麼寫,知道怎樣贏得讀者。譬如,《鼠疫》開始第一章,他講這是一個歷時事件的敘述,而這些事件迥異於平常,在當時當地是出格的、格格不入的。筆鋒一轉,他開始描寫奧蘭這個城市,這個自以為是、平和而景緻枯燥的地方。我不在這裡重複描述加繆所描寫的,權且隨便摘錄幾句:
季節只是在天空得以區別。告訴你春天來了的,只有空氣的感覺,或小販從市郊帶來的一筐筐鮮花;那是在市場高聲叫賣的春天。
事實是每個人都很無聊,就讓自己投入養成什麼習慣。
奧蘭,似乎是一個沒有親密感的城市;換言之,完全是現代的……男人女人迅速在所謂的“愛的行為”中消耗彼此,或者安然接受交合的溫和習慣。我們很少在這兩個極端之間找到一種中間道路……在奧蘭,就像在別的地方,因為缺少時間和思考,人們不得不彼此相愛,儘管並不覺知什麼。

最近一些年,我越來越喜歡一種特殊的寫作方式。它總是和閱讀密切相關的。往往,在讀到一段好文字的時候,我會不由得停下來,回味、沉吟;就像品嚐某種滋味美好的東西,聞道某種令人出神的香味,或者在某個無以言表的美景面前,人需要停下來,讓一切慢慢地在自己內裡醞釀、飄忽。期間,會有很多靈光驟現的思考和感受,有些是從以往的記憶倉庫中突然顯亮的,有些是猛不丁誕生的——它們和所閱讀的作品的作者親密觸摸、交流。這種情況下,如果你想記錄下這閱讀和感思的體驗,你不想從這種親密的生動的感思中脫離出來,寫作只能將兩者交織起來:閱讀的記錄和感受。甚至記錄本身,它的選擇,就已經是絕大部分的思考和感受,有時候不想再多餘說什麼。這種方式的寫作,我猜想,在羅蘭巴特、福柯、德里達等人打破作品、作者、讀者的邊界之前,在本雅明那裡已經開始了。本雅明和巴特都想寫只用“引用”寫成的書——一種親密之書。

回到加繆的《鼠疫》,跳過35頁,來摘錄一些里厄醫生和同事交談確認鼠疫之後,他的心理活動的描寫。就算他在朋友跟前承認了,城裡四處都有人死去,沒有鼠疫消息的警示,他也還是感覺危險“奇幻地不真實”(fantastically unreal)。很簡單,作為醫生,他對肉體受苦有自己的認識,比常人有更多想像。這時,醫生朝窗戶外面看去,城市從外表看沒有什麼改變,一如往常。醫生對未來僅有略微不詳的感覺,一種隱隱約約的不安。
他開始回想自己所讀過的有關瘟疫的書。首先他的腦海中出現的是數字,歷史記載的30多個著名瘟疫,造成了上億人死亡。他尋思,上億人死亡到底是什麼呢?要是一個人去打仗,過一段時間,對死人是什麼就沒感覺了。因為除非你親眼看着一個人死去,死人是沒有實質的。歷史中宣傳的上億人的死亡不過是想像的一縷輕煙而已。
里厄醫生思緒不斷。他想到,病人的生命命若懸絲。而三分之四的人都迫不及待動作,輕易便掐斷了那根懸絲。他看着窗外凜冷的春日下午寧靜的輝光,“瘟疫”這個詞在屋子裡在他頭腦中迴響。要是能像此刻這個城市一樣遲鈍而快樂就好了。

他回憶了歷史上記述的世界各地的各種瘟疫,甚至包括19世紀下半葉從雲南傳播到廣東再到香港的鼠疫,還有長城的修建也是為了阻擋疫戾之風南下。在這裡,略去不管是修昔底德、盧克萊修、黑死病期間帶着面具的狂歡、米蘭不管不顧的交歡、巴黎倫敦等等——所有這些歷史記載,日日夜夜,到處都迴盪着人的痛苦永恆的哭喊。然而所有這些恐怖,都不夠近,沒有近到讓這春日下午的平靜興起一絲波瀾。從窗邊駛過的街車哐當哐當,乾脆地拒斥殘忍和痛苦。只有大海,在骯髒的棋盤般的房舍後面,喃喃吐露這世間萬物的不安和岌岌可危。稍後,我會再回到里厄醫生的歷史追溯中提到的東羅馬帝國時期普罗科匹厄斯,被譽為古典時期最後一位偉大的歷史學家關於“查士丁尼大瘟疫”的記載。
醫生最終停止思索,“瘟疫”這個詞已經說出來了。那麼剩下的就是認識,就是行動,做該做的是。瘟疫會自然而然結束,因為它不可想像;或者說,因為人總在錯誤的路線上思考它。在日常循環中,有確定性。其餘的不過是掛在微不足道的偶然性之上。沒必要浪費時間,幹自己的活吧。這一章在這裡結束了。
為什麼我讀這本書會暫停在這一章,回頭去體會,又非要把它複述出來呢?因為即便是對里厄醫生這樣一個人,一個專業、正直、性情沉穩、極其聰明的人,瘟疫,或者說災難也是不可想像的。他的心裡過程的細膩描繪,或許對我們理解人在災難來臨之際的反應有所幫助。不需要我過多闡釋了,加繆的文字已經寫了所有改寫的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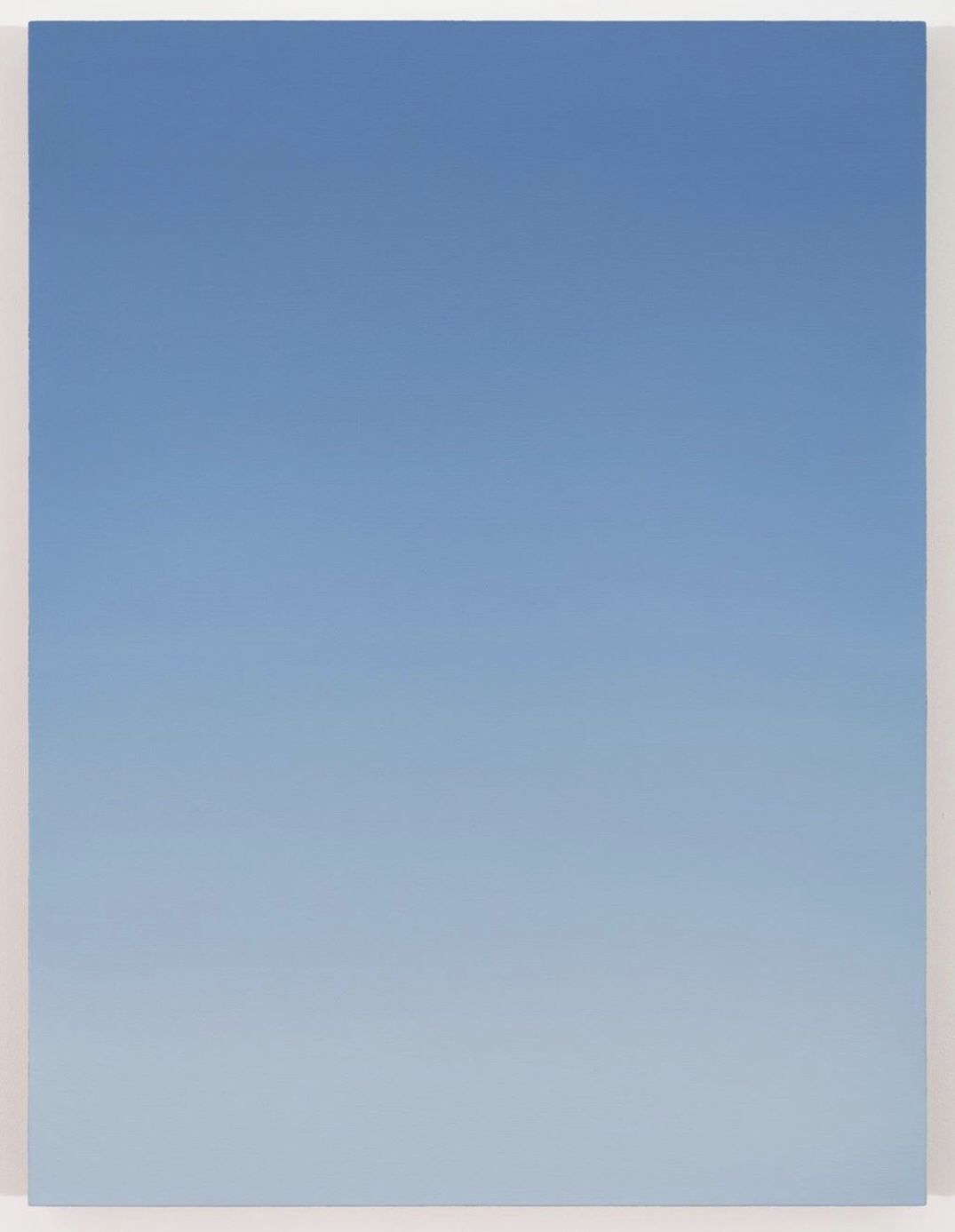
“查士丁尼大瘟疫”發生在542(541)至717年間,有說造成了2500萬人死亡,或者半數歐洲人的死亡。普罗科匹厄斯在拜占庭親歷了瘟疫,在他的兩本書中對這場瘟疫有記錄。在《戰爭史》第二部22-33節中,他詳細描繪了這場瘟疫的起源和在拜占庭的肆虐。在《秘史》這本吐槽查士丁尼皇帝的別史中,他將這場大瘟疫置於查士丁尼統治下羅馬帝國的一系列失範和災難之中。倘若說盧克萊修寫“雅典大瘟疫”的長詩淒厲之極,那麼普罗科匹厄斯的描述則冷靜、悲憫,堪稱優美。擇譯一些:
《戰爭史》——瘟疫,542
對這樣的大災禍來說,既不可能用言辭表達也不可能在思考中想出任何解釋,真的只能提及上帝。因為它不是只到世界上某個地方或者某些特定的人身上,也沒有局限在一年中哪個季節,它擁抱了整個世界,摧殘了所有人的生命,不管年齡和性別,雖然在不同的人那裡程度各自不同。
儘管人們因生活的地方、日常生活的準則、天性、或者積極的追求,等等,而各有不同,單獨在這種疾病面前,不同一無所用。
在第二年仲春時節這場瘟疫到達了拜占庭。很多人看到了偽裝成人的超自然幽靈之後瞬間就被疾病捕獲;有些人把拜訪的熟人當作鬼,在他們身上看到鬼顯示的幻象。有些人則無知無覺就病倒了。(各種情形的病痛和病苦造成的瘋狂描述這裡略去)
這種疾病中,沒有什麼是出自人的理智領域的;所有的情形中,事情都是不可描述的。治療方法對不同病人來說效果也不同。人們找不到任何可靠的方法拯救自己。所以要么小心預防;要么惡病來時設法儘自己所能所願而已;苦難不告而來;恢復也不來自外因。
有時候一天會死五千人,有時候又說一天死了一萬人甚至更多。開始每個人都盡量安排自己屋裡死者的葬禮,後來會把自己家人的屍體扔到別人的墓中。奴隸沒有了主人,曾經富有的人無人伺候,許多家再沒有活人,有些城裡最知名的貴族也死後多日無人埋葬。
皇帝派大將軍西奧多羅斯(Theodorus)為受苦的人採取撫慰措施。他的角色相當於羅馬人的“陳情官”——聽取百姓疾苦,反映給皇帝;再把皇帝的消息傳達給百姓。西奧多羅斯不但將皇帝給的錢用於濟難,還自己貼腰包。他不斷尋找無人料理的屍體,負責安排埋葬。
然而後來,挖溝埋人的人,已經無力掩埋過多的屍體。他們爬上加拉塔要塞的一座座塔樓,揭掉屋頂,把屍體亂扔進去,直到填滿了整座塔,然後再把屋頂安回去。這樣,塔樓中散發的屍臭瀰漫了整個城市。
這種時候,所有傳統的喪葬儀式都被無視了。沒有送喪行列,也沒有吟唱陪伴,能把屍體扛到肩上去到海邊就已經足夠了。在那裡屍體會被堆在舢板上,任其隨波逐流,飄到哪裡是哪裡。
也在這種時候,過去敵對的人們也放下彼此的敵意,共同照料死者的葬儀,親手搬運和自己沒有絲毫關係的人們的屍體去埋葬他們。
那些過去沉浸於追逐可恥卑劣生活的人,擺脫不當的日常行為,開始勤勉地踐行宗教職責。這倒並不是因為他們終於學到了智慧,也不是他們突然就開始熱愛美德了——因為當人出於天性或者長時間的訓練熏陶,品性固定下來,不可能他們這麼輕易就把既有的品性放下來;除非,某些向善的神性影響吹拂到他們身上。不管怎麼說,所經歷的事讓他們徹底驚恐,想想他們也馬上就會死去,自然而然,純粹出於必要,他們也暫時學會了何為可敬。而一旦他們擺脫了疾病得到拯救,並且以為自己安全了,那詛咒轉向別人了,他們立馬就回歸到以往的心靈的卑劣中了,有過之無不及。他們的行為越來越表現得不統一,惡行和無法無天遠遠超越了以往的自己。你可以萬無一失地著重強調,這疾病不管是出於偶然還是天意,精確地挑選出最壞的人,讓他們得以自由無咎。
最後,一言以概之,在拜占庭看不到一個穿短披肩(chlamys)的人,特別是在(查士丁尼)皇帝生病以後(因為他的腹股溝也有一個腫塊),在統治整個羅馬帝國的這個城市,每個人都穿著私人場合的衣服,悄悄呆在自己家裡。這就是蔓延羅馬帝國和拜占庭的瘟疫的過程,它也降臨到波斯和所有與其毗鄰的野蠻人的土地上。

以上出自《戰爭史》中的詳細記述。下面摘譯《秘史》中對瘟疫降臨康斯坦丁堡的描繪。
查士丁尼,雖然很年輕,卻是羅馬帝國的實際統治者。他對羅馬造成的大災禍比有史以來以往任何人都厲害。因為他無所顧忌,肆意謀殺或者掠奪別人的財產;滅絕無數人對他來說根本不是事。他不在意保存任何已有的習俗,總是急功近利,簡而言之,他是所有高貴傳統的最大破壞者。
儘管這場瘟疫襲擊了整個世界,逃脫的人不比死去的人少;因為有些人沒有染病,有些人在被疾病打擊後得以恢復。而這個人,沒有一個羅馬人可以躲得掉;好像他是老天派來的第二場瘟疫,他降臨這個國家,沒讓一個人逃過他的魔爪……這個查士丁尼是個魔鬼,不是人,是披著人形的魔鬼,想想他給人類帶來的巨大的惡,我所說的話就不言自明……他從不尊崇任何習俗常識,而是讓一切陷入混亂和騷動之中……他噬血而獨裁……正義和公正的懲罰很少針對施害者……地震、戰爭,無數居民喪生,然後瘟疫來了。這麼多人遭逢厄運,自從查士丁尼開始統治羅馬帝國並且後來篡取了獨裁暴政的王冠。

摘譯就到這裡。有沒有感覺,古代人觀察描述事物的心、眼、思、筆和我們現在的人很不一樣?我們很難貼得這麼近,進入得這麼深,而又有入情入理的一種籠罩的距離。【周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