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lking Talkers

今天四点多,JJ妈接我们回家。到小区她提议让我们出去跑跑。
今天早上挺冷的,和我妈爽约了,早上还是想多躺一会。
疫情的时候,有过一些焦虑,不过皆是间歇性的,大概也是闲出来去琐碎地阅读各种信息。已经会看到豆瓣,哇八十年代的同学录,留言都是那么有诗意;打开知乎,哇这ipad真香啊;打开ins,哇因为疫情又没有人发动态哎;打开steam,大家都在学习哎;打开油管,台湾的新闻节目就好像听段子听腻了东森的寳傑哥那声熟悉的“真的假的~”;打开直播,果然比赛是我最好的助眠剂,之前有一段时间,每次凌晨醒来发现灯没关,衣服没脱,解说还在熬夜;打开端媒体,刷下去就到了“加入端媒体会员”,过去是有去淘宝买,但感觉共享的挺捉鸡,定一个全年有感觉有点浪费。仿佛置身一条水道,流水裹挟着信息的泥沙冲向自己,即使自己有船可渡,也不知道该去往何处。
我们先(只)跑了五百米,沿着河。然后停下来,绕着小区走路,聊着各种问题。和别人说话最大的好处莫过于检视自己的想法观念。
以上是4月5日记录的。
过去有段时间很喜欢和其他的几个好友一起玩游戏,但似乎真正可以让我放下心思享受学习的时候,是有这样和你一起在努力的人。就觉得的确,日子可以过得很舒服,但荒废心智,于己还是有点自责。
就昨天JJ说到一个问题,简单来说就是说,卓越和平庸之间存在一些比较优秀但不算卓越的人。而这群人有些人企图达到卓越,但是最后没有达到,就会被别人同样认为“不过如此”。但常常觉得,的确,社会也好,具体到家人,朋友,周围每一个人都会有一种评价,从另一个角度看,也隐含着一种期望。所以关键是别人的期望合不合理,比如你平时每天早睡,你妈就有理由期望你早起;反过来看自己的期待也应该合理一些,你平时三餐丰盛,不愿运动,就别期望自己可以瘦。因此似乎问题需要被理性地看待,尤其是隐藏在评价之后那些期待和期望是不是合理,而不是去和这些评价本身辩论。
今天因为小组讨论是关于一些伦理道德和科学发展的问题。然后去TED重温了一个视频。演讲者Sam Harris觉得价值判断或多或少基于一些实证的经验。比如说,对于石头,你没有办法像你看到一只可爱的猫猫一样产生情感,因为我们不会认为石头会向我们一样觉得疼痛。
“Values are a certain kind of fact, they are facts about well-being of concious creatures.” ——Sam Harris
所以这里想将这样一种人的直接感触,感受作为最底层的依据。作者认为此处脑科学,神经科学可以逐渐阐释。其次,谈及宗教的一些价值观,这里举了天堂地狱之差别也来自人类对于幸福和痛苦的意识。总之,S将这些价值判断,亦或是文化给人类在观念上带来的变化都引向人的大脑,这些改变发生在大脑,然后再引入科学中的脑神经科学或者是心理学这些专业领域。

那么问题在于,不同的人对于同一件事有不同的value,比如说吧,我喜欢收集石头,去一个地方旅游会尽可能找一块当地的石头,我对某一块收集的石头的态度可能会相对于当地一个不具有相同癖好之人更为深刻。针对这样的现象又该如何解释?Sam Harris也绘制了一副Moral Landscape,想要说明这样一种相对性。道德景观中群峰象征着个体或者某群体所达到的独特体验。比如说一些宗教人士以通过spiritual or mystical的方式来达到一般人没有办法企及的道德/价值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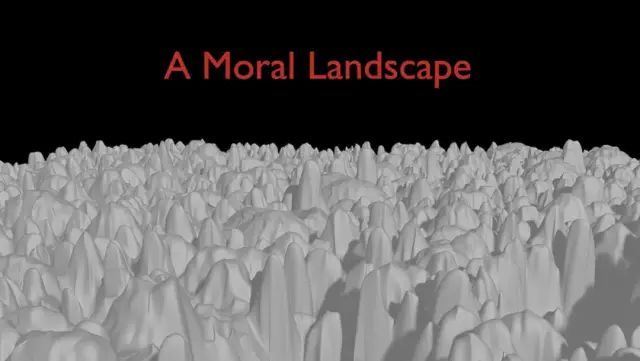
因为我们最近课上谈论的是医学的伦理,而Ethics(伦理)和Morality(道德)还是有很大的区别,ehtics是更加接近现实的东西,是在现实中具体的并且通常是严谨的规范准则,极端就是法律。Morality则更加倾向于一种价值观念,按Sam所说,也就是关于如何看待人类的well-being的一种判断。
emm,去查了下相关的一篇。画了这样一个图总结:

作者说了一堆,引用的是中国古代汉语和哲学的一些解释。但感觉有点拖沓。简单来说,伦理外显的具体准则,道德是人心中的价值判断。因此伦理必定相比Ted Talk更加具体。这也是为什么似乎感觉Sam可以在谈论科学与道德时候游刃有余,实际上很多时候,问题还没到伦理的难度而已。如果仅仅是关于道德,是否良善,可能的确科学正在企图解释。但是伦理学,就是一个很复杂的博弈,比如说基因编辑问题,除了立法问题,还有对于技术带来的风险和收益的讨论,这样的方法是实证的,但是科学由于技术所限,预测难免失准。
但之前JJ也说道,随着我们人类生产力水平提高,逐渐道德观念也在变化。就拿平等而言,本来可能在一群精英内实现,再扩展到国民,以及全人类。包括从性别,对于差异化的容忍度的角度看,生产技术发展,在一定程度以某一种新的方式去compensate for旧的某需求的缺失。但其实说了这么多,道德也好,伦理也好,科学也好,一个基本的命题就是,人会死。也正是因为会死,宣告了这种尘世的欢愉和痛苦都是有期限的,经济学里时间就有了机会成本。换句话说,之所以人类可以繁荣,不也是因为求生欲。假设我们的祖先,和其他的生物一样,在生态链中处在一个自然的位置,没有尝试去适应一些自然上的变化的话,比方说迁徙,是不是就失去了很多进化的机会,比如说从树上到地上的生理构造的演变,并且运用工具,形成分工。一方面自然迫使早期的人类进行改变自己的行为和生存模式,而在这一个过程中,我们充满脑洞的祖先从打造简单的石器开始,一直到现在,全世界建立的庞大的跨国公司,互联网,还有庞杂的知识体系。有人可能想说,动物也会求生,但我觉得他们的求生要么是停留在个体遭受的食物链危机,要么则难以抵御自然环境的巨变,假设人类在没有发明太空技术,同样遭受一次小行星撞击,那很可能也会因此灭绝。所以,这种进化的过程是需要微妙的平衡,而我们看到尤其是早期,这样的外部因素造成的自然风险是巨大的,而到了现代社会,整个社会因为人类密切的联系而导致局部性的因素将会被放大,从而危及全世界。尤其是制度性的风险,比如吉登斯提到的例子:
世界民族国家体系会带来极权主义;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会产生经济崩溃;国际劳动分工体系带来了生态恶化;世界军事秩序会诱发核大战的爆发。——安东尼·吉登斯
根源上看,制度性风险是现代性的发展带来的产物。一方面社会建立法律,伦理标准,一定程度是希望降低由于规则 颠覆者等一些小概率事件造成的风险,但是另一个角度,技术的逻辑在现代是一种趋向于独立和自发,新技术的的产生来带新问题,由此必然激励新的技术突破,在这个过程当中,必然会对现有的准则进行突破,并由此带来新的机遇和风险。并且,尽管是小概率,但由于这种密切的联系和复杂的结构往往引起巨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