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服务到启发大众——方可成的自媒体尝试

中国的时代进程对方可成选择成为一名媒体人有很大影响。2003年中国孙志刚事件发生、SARS疫情爆发时,调查新闻层出不穷,这些报导在揭露真相、推动社会对于公众事件的讨论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在新闻理想的感召下,2004年,方可成在入大学时选择新闻学作为自己的主修专业 。
2010年硕士毕业后,他进入了《南方周末》做一名记者,参与过不少深度新闻报道。2013年《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的事件发生,被不少人理解为中国言论自由收窄的标志。他认为当时《南方周末》这样的传统媒体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自己更愿意去寻找新平台做新的事情。
他选择同年年中到美国读传播学博士,一边运营自己的媒体平台。他观察,社交媒体的出现让媒体从以往的精英拣选读者可阅读的内容模式,转向至“服务业”模式——提供读者所需要的信息。现在方可成为人熟知的“政见CNPolitics”、“新闻实验室”两项自媒体项目,都有这一的特征,前者旨在将“社科学术研究进行通俗化传播”,后者既面向大众做传媒素养的普及,亦为媒体从业人士提供专业服务。
访问、整理:Niol Nagev (以下简称N)
《南方周末》时期:从“黄金年代”到“跪着造反”

N:您说2004年前后是新闻的黄金时代,您在大学毕业后也去南方周末工作了一段时间,期间也有很多调查新闻报道的产出,从现在这个时间点来看,好像2010年之前的新闻报道环境都是不错的。您在南方周末工作的时候感受如何呢?
方可成:我在《南方周末》工作的那3年,算是这份报纸的“强弩之末”吧,依然有优秀的报道产出,但明显在不断走下坡路。
虽然说那个时候大环境确实要比现在好很多,但我想说的是有时候我们回望从前,特别是回望所谓新闻业“黄金年代”,还是存在许多过度的美化的,他们其实也是有很多的问题的。比如南方系,对性别问题的认识就很浅,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那一代精英的媒体人和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不少所谓的“直男癌”。行业里很多厉害的记者都是男性,他们对女实习生也都会有很多不注意的言行,在报道的时候也很少去挖掘性别的不平等关系。而从时间的维度来看,年轻一代在性别意识这一块的进步就很明显。
N:现在年轻一代女权主义的崛起确实比当时要进步很多,但南方系媒体作为市场化改革的排头兵,在当时也是自由主义的践行者和先锋,在很多议题上也是促进了大陆自由主义的探讨启蒙,不可谓不进步。您会如何看待当时自由主义在新闻媒体中兴起的原因呢?
方可成:这学期我在港中大任教了一门中国大陆媒体发展的课程,当时回顾了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发展。在回顾的中间我发现,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当时基本寄希望于两点。第一点是在89年之后,因为你不能直接谈中国政治的话题,所以他们首先会希望于市场化改革,认为市场化改革、中产阶级的出现,会很自然的导致中国政治自由化会出现,很多外媒也是这个论调,大家会觉得需要时间,但需要的时间不会太多。可是经历了这些年环境的恶化大家才发现,市场化改革由于使得中共、包括许多中国中产在全球化过程中受益颇多,反而可能加剧了保守主义与威权统治的水平、规模。当然现在特朗普的对中态度与中美的贸易战又加多了很多不确定性,不过大方向上这种寄希望于市场化会带来民主化的想象可以说是一种事与愿违,也过于天真了。这当中还有一些个体的案例很有意思,比如连岳,他07年的时候是反px化工厂事件的领袖,也是当时公民社会的领袖,但他现在已经是川普的粉丝了(甚至可以说他法西斯主义者)。反讽的是,当他信奉市场的绝对自由,反对一切形式的再分配,就可能会走向认同严格的社会等级,甚至支持压迫。
第二点,其实就是对美国的期待,中国一旦发生不好的事情,媒体都要出“美国是怎么做得好”的文章,对标美国。然而现在来看这是非常天真的想法,因为美国在很多方面做得也是非常的差,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枪支暴力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等等。这一方面对中国没有什么启发,另一方面当美国内部出现很多问题的时候,给了中共的宣传机器非常多的口实——你看民主自由的灯塔国也这么的差,你还说什么自由民主呢?可以说,自由派媒体塑造了一种对美国的天真想象,将“民主自由”机械地与美国的治理方式捆绑,被动地将民主自由的内在价值忽视而直接将其等同于美国的所有情况,这是相当具有危害性的。
今年以来的疫情美国治理的失败、黑人平权运动美国政府的强硬处置,给了大陆宣传机器很多的空间去发挥,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案例。这里还有一个个案的例子就是乔木,他之前是一位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副教授,在国内的时候对党国的批评很厉害,之后去了美国,因为看到了美国具体治理方式上的一些问题就开始疯狂批评美国,认为中共的治理非常好,有一个大的转变在里面。
从这些人、个案的转变里面可以看出来上一代自由主义中间论述的矛盾还是非常多的。 到了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应当去开创新的论述,不再简单寄希望于市场化和美国化。
N:过度强调经济市场化改革的辐射作用、捆绑美国价值确实有点作茧自缚的意思,但是在当时也不好预料之后形势的发展,那在当时媒体人是如何看待自己能起到的推动社会变革的作用的呢?
方可成:在我去美国前半年,2013年1月的时候,发生了“《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这也是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媒体人的纠结和无奈。
这个事件当时有许多外媒报道,把我们南方系自由派的记者描述为一群奋起反抗中共的审查,然后罢工之类的异议者。但实际上作为内部的员工我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看到的情况是,打出了言论自由这样的旗号的都不是媒体的自己人,全是外面来支持我们的人。我们确实认为自己的新年献词被干涉了,出现了许多管理上的低级错误,但我们提出的最激进的要求就是希望他们能改善新闻媒体的管理方式。这里的前提是,我们完全接受中宣部来管我们,只是我们希望你们管得手段稍微松一点,多和我们沟通,是一种非常低姿态的反抗,都是外面支持我们的人打出了宪政民主、言论自由等等口号。我们当时反倒被要求不准与外界接触,以免被当局认为是我们南方周末的人在煽动外界打出这些口号。
当然内部也对如何处理这个事件有很多意见的分歧。
有一部分人会认为罢工是能够抗衡审查的出路,因为我们唯一的筹码就是不出报纸,但报社的很多中高层认为我们不能把地盘拱手相让给我们讨厌的人,当然这也是合理的,他们认为不能就这么白白让出阵地,让南方周末变成党报。最后事件的结果就是我们什么诉求也没有被满足,媒体的管理也没有任何松动的迹象,反倒是被进一步加强了。其实任何选择去南方周末工作的记者,心里都很清楚,自己最多能做到的就已经是“跪着造反”了,你必须完全接受在日常工作中受到的全方位监管,以此来交换一个记者证,和有新闻采编权资格的平台。
从现在来看,自由派记者们确实在特定的历史事件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也并没有实现当初一代媒体人想象中的愿景。
运营自媒体:媒体的“服务业”转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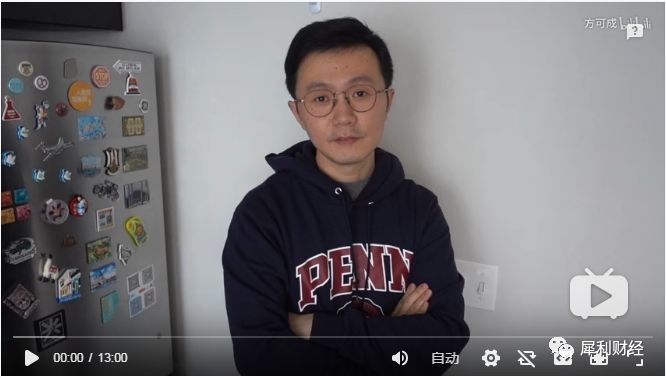
N:在离开南方周末之后您选择了去美国读博士,也一直保持在社交媒体上的很多内容产出,似乎是在尝试一种传统的媒体之外的一种介入式创作,对这方面的开拓您有什么见解呢?
方可成:对,虽然很多平台上的账号现在都消失了,但我确实做了不少的尝试。在当初传统媒体的年代里,新闻业是一个非常精英的生产方式,就是一群编辑记者聚在一起开一个会,决定什么东西放头版、什么东西应该给大家看——这当然有一定的好处在,但确实与大众相当脱节,因为大家只能去看去听第一线精英媒体人留下来的东西。但现在来说,这种模式已经过时了,大家也已经不爱看了,社交媒体的出现是对新闻媒体很大的一个冲击,也重新揭示了新闻业的本质是什么——去满足读者的需求,做一个服务业。我之前看到一篇文章,是尼曼实验室每年对新闻业的一个预测,其中有一篇文章是“all journalism is service journalism”(所有新闻都是服务性新闻),就是所有的新闻业都应该是服务性质的新闻业。这当中有三个需求比较突出。
一个是最基本的信息类的需求,特别是在当下这个年代,读者需要的已经不是媒体去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而是帮助他们“make sense of the world”(理解这个世界),帮助大家理解正在发生什么。
第二个就是对分析方法、获取信息方法的需求,其实就是告诉读者可以通过什么方式去了解、可以怎么去分析时事。这个是之前我在做新闻实验室的时候常做的:告诉大家可以去看什么样的媒体来获取信息,一个新闻热点发生之后我们应该如何来分析各个媒体的报道,我们如何在不同媒体的报道之间做一个评判和选择。一个分析的方法和框架是很有用的,例如如何和父母沟通,政见不同的朋友沟通,这都是这个时代相当突出的问题。
第三个需求其实是情感的需求,在这个政治抑郁、新闻焦虑的年代,大家很容易陷入很不好的情绪状态。我们之前对新闻业最硬核的理解就是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坏事我就去报道它。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也是这么说的,“所有的坏消息才是新闻,好消息都是公关”。这是一个很正统、原教旨的对新闻的理解,但其实我们应当可以去放宽这种对新闻的理解的。我们需要去正视大家很负面的情绪,因为消极的念头会让大家变得更加犬儒、更不愿去行动,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大家的情感需求,也是间接地去推动社会进步的途径。
N:可以看到方老师不仅仅做了“政见CNPolitics”、“新闻实验室”,也会在bilibili这个知名的年轻人弹幕社区发视频,和年轻人夜聊,您做这件事情的想法是什么呢?
方可成:因为这个平台对任何带有公共性质的议题的审核是极其严苛的,所以我也只能谈一些边缘性的话题。我因此在bilibili做了一些近似于“心灵鸡汤”类的视频,当时第一个火的就是“夜聊”系列,有人和我发私信诉说他的苦恼。
一个中学女生,说她自己长的很不好看,对自己的外貌非常没有信心,所以她从来都不敢在朋友圈发自己的照片,甚至发出来还会被人嘲笑。那个时候我就做了一期视频,名字就叫“给所有觉得自己不好看的女孩”,其实就是去打破这么一种外貌歧视,宣扬一种body positivity, 让很多人都有共鸣。有时候去做一个非常个人化的,服务到大家具体诉求的视频,也能带出公共性,背后的一个内核也可以很progressive。
其实我想说的是,媒体人,或者说具有公共性的知识分子在具体话题上的选择是可以非常多样的。有时候看网上的人架吵多了,往往可以根据一个人在民族主义话题上的意见去推断他们在女权话题上的意见,宗教话题上的意见等等。有时候每个人的意识形态是有很高的相关性,你对多元性别观的接纳程度与你对多元民族观的接纳程度是相通的,所以我会觉得说有时候曲线救国,需要在墙内讨论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的时候,可以从年轻人别的一些需求入手。
有时候我去大学去做讲座,会发现当代年轻人的困惑真的很多,无论是对知识选择的困惑,比如应当读什么书、大学应当读什么专业,还是价值观、意识形态的困惑,对国际大事、人生追求的诘问。能真正解决大家的困惑、做好服务的媒体现在是稀缺的,这里也有很多可以做的机会和空间。
N:您说的这个以私人话题来进行启蒙的途径很有意思,但是通过日常生活的介入来启发大众的可行性能有多高呢?比如当下很多年轻人可以在性别议题上非常进步,但是一旦涉及到一些宏大叙事,就很容易被民族主义话语收编,这些话题的相通度有那么高吗?
方可成:我的目的性没有那么强,其实我在青年系列论坛中提到过,归根结底来说我们需要去尊重不同的政治立场,就算他是个民族主义者这也没有什么,因为本来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大家就会居于不同的政治光谱上的位置,很多立场都是有自然分布的。
其实你是什么立场不是很重要,关键是你是不是认为真相、事实比立场更重要,就是说你是民族主义者没关系,但你应该是收集尽量真实的信息,体面地表达意见、参与讨论,而不是去举报人,不要在网络上组织各种攻击。
N:很可惜,您自己也因为这种举报而丧失了许多平台积累的账号,对此您有什么应对呢?
方可成:关于联结渠道的问题,我认为有时候可以选择一些去平台化的渠道与读者保持联系。回过头来看,一个思路就是邮件的形式,最古老的互联网技术实际上是现在来看最具有先进意义的,因为它是有跨平台功能的。Gmail的邮箱可以发给outlook,但微信上的消息是发不了给微博的。所以我觉得去把自己的核心受众的邮箱资料保持下来还是非常重要的。
编注:方可成的“新闻实验室”微信公众号于2020年2月29日因他人举报而被微信永久封禁。无奈之余,他又行动起来,将“新闻实验室会员计划”搬迁到Matters做介绍,继续连结自己的同路人。
关注我们:
Twitter:https://twitter.com/masses2020
Telegram:https://t.me/masses2020
Facebook:https://facebook.com/masses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