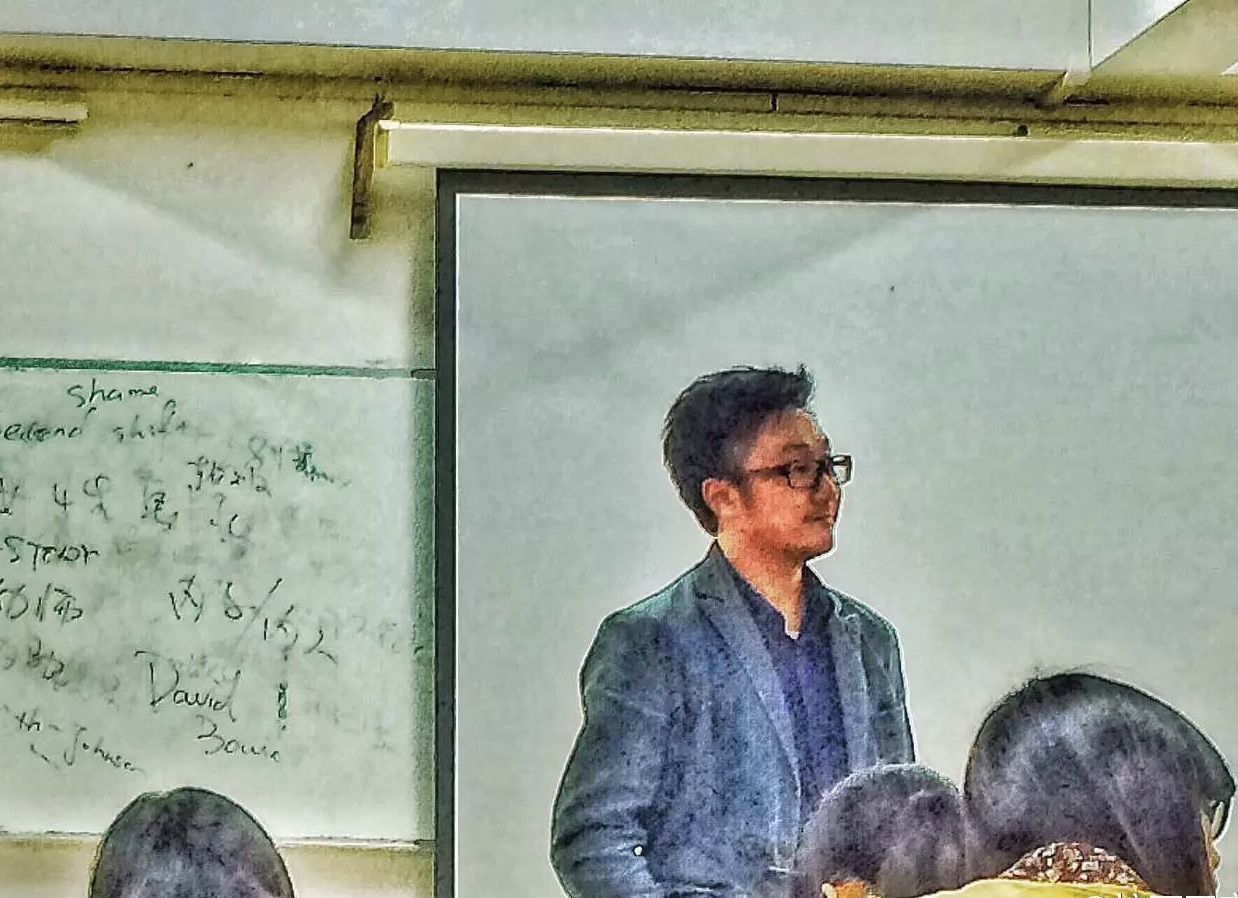“我不是女权主义者”:另类的女权宣言?
在2016年大选期间,仍是保守派电视台福克斯新闻台(Fox News)台柱之一的梅根·凯莉(Megyn Kelly)以令人惊讶的姿态成为反性别歧视的支持者之一。在她主持的《凯莉档案》(The Kelly File)节目中,她开始公开支持女性带薪产假(美国是目前发达唯一不要求企业给予女性产假的发达国家),反对媒体行业中普遍的性别歧视,支持举报性骚扰的受害者。而她最引人注目的举措,就是严厉批评当时仍是总统候选人的特朗普的厌女言论,最后导致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的强烈反扑和攻击。凯莉的形象似乎忽然之间与她所在的福克斯新闻台截然相反:她成为了一个进步派的成员,或者至少,她有此潜力。一时之间,不少女权主义者开始讨论,梅根·凯莉是否她们中的一员,尽管凯莉常常又是反女权的福克斯代表。她谴责过校园“性同意”运动为“反男人”,也宣称过性别间的收入差距不存在,更著名地宣布过自由派正在发起针对圣诞节的战争,耶稣绝对是白人等。这些都是典型福克斯宣言。
后来,凯莉离开了福克斯新闻台,高薪加入美国广播公司(NBC)主持新节目。如果凯莉身处保守派电视台让我们犹豫下判断,那么离开福克斯的凯莉,是否可以被称为“女权主义者”了呢?当然,她并不称呼自己“女权主义者”。
另一边,德国总理默克尔从公开言论到执政期间的政策都积极推地性别平等。作为世界上拥有最高权力的女性,默克尔自然被看作女权主义的代言人之一。然而,在2017年的一个活动中,当主持人问到“你是不是女权主义者?”时,默克尔犹豫过后表示,她并不想这样标识自己,尽管她并不害怕这个标签。随后引起的讨论围绕着默克尔是否女权主义者而热烈展开,其中大多都认为,默克尔就是女权主义者,她就该称呼自己为“女权主义者”。然而,为什么她没有这样做,是个问题呢?
女权主义者的标签
以上的这些例子,都会促使我们去思考那个熟悉的问题,什么是女权主义?这是一个足够有争议的问题,引起过无数的讨论。然而,这些例子同样促使我们去思考另一个问题,一个当下信息发达的、开放的社会才出现的问题:“女权主义者”的标签有什么意义?
即使现在女权主义者仍然被严重污名化,被指为只懂谩骂不懂风情的一群恶人,当下女权主义者的形象同时也在变化。越来越多来自不同社会领域的名人开始自称女权主义者。从艾玛·沃森(Emma Waston)在联合国的女权主义发言和“HeforShe”运动,到各路明星身穿“女权主义者长这样”的体恤,再到商界政界身处高位的女性为性别平等“打call”,女权主义者的形象在网络发达的今天开始改变。就算不是整个网络,至少在同温层中,贴上“女权主义者”的标签成为一种新的潮流。我们看到,甚至伊万卡·特朗普(Ivanka Trump)在默克尔同场活动中都自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她的父亲一贯支持女性平权运动。
不惜睁眼说瞎话来获得女权主义者的标签,可以想像这一标签的意义,或者说,好处。随着性别平等意识的传播,受我们赞美的女权主义代言人也越来越多。从《纸牌屋》中的克莱尔(Clair Underwood)到脸书首席运营官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不管是影视剧大女主抑或现实商界领袖,我们都乐意将她们看作女权主义者,因为她们打破玻璃天花占据强有力的位置本身就是女权主义的胜利。当桑德伯格的《向前一步》(Lean In)鼓励商界女性向前一步争取成功,我们庆祝新的女权主义代言人的出现,甚至还热烈讨论她是不是新的Gloria Steinam。然而我们却不去仔细考察向前一步背后到底做了什么,就如最近媒体报道发现那样,桑德伯格的成功背后往往是公司收益高于其他人的基本利益。
正如杰莎·克里斯宾(Jessa Crispin)所说,女权主义仿佛成为了强有力女性的挡箭牌。她们藏在女权主义者标签之后,大家就忘记她们的成功与性别平等有什么关系,她们的强大背后是否正义。仿佛女权主义就等同于个人争取获得力量,个人的胜利就等于女权主义的胜利。在克里斯宾看来,这样的女权主义标签,如果就是真正的女权主义,她并不想成为女权主义者。这也是为什么她写出《我不是女权主义者:一个女权主义宣言》(Why I Am Not a Feminist: A Feminist Manifesto)的原因。
女权主义:从运动到营销
杰莎·克里斯宾斯网上杂志Bookslut的创立者,同时也担任在线文学杂志Spolia的编辑。除此之外,克里斯宾还常常在各大报纸媒体发表评论文章,以尖锐的批评著名。正如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安吉雅·德沃金(Andrea Dworkin)等女权主义者一样,克里斯宾的文章关注性别平等的同时,也大胆对女权主义运动中的问题提出敏锐的批评。
在克里斯宾看来,当前的流行女权主义逐渐将关注的重点从整体的运动转变为个体的选择。她把这种主义称为“选择女权主义”(choice feminism):“只要是女性的选择,无论是关于生活方式、家庭关系抑或消费模式,她都是在做女权主义式的选择。”在流行女权主义者们看来,以往女性长期被剥脱自主选择的权利,被传统的性别规范安排好担当的角色,所以现在,女性能够作出选择本身,就已经是在反抗男性中心的压迫。换句话说,只要女性在做选择,她就是在做女权主义式的选择。
然而,这样的女权主义不过是一种自恋。通过将“我”定义为女权主义者,“我”所做的选择和行为就自然而然地是女权主义式的选择和行为,不管“我”的选择和行为是什么。即便随着性别平等的发展女性能够选择的领域得意扩大,选择女权主义反而使得女性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去争取的性别平等范围收缩。于是乎,在克里斯宾看来,只顾个人发展,美其名为“自我赋权”的主义,往往只是鼓励追求个人利益,无视个人的动机或成功所可能带来的影响,仿佛将“个人即正义”诠释为“个人的胜利即是政治的胜利”。
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流行女权主义这么重视“女权主义者”的标签。如果她相信男女同工同酬,相信女性应该得到平等对待,“为什么我们还要关心她是否自称女权主义者呢?”
克里斯宾认为,既然流行女权主义关注的不过是个人叙事,个人需要面对的权威只有个人自身,那么一套循环的逻辑(a feedback loop of logic)就会形成:所有行为和选择都是可证成可辩护的,所有行为和选择都可以描述称为女权主义式。于是乎,我们就需要将女权主义者、女权主义式的范围尽可能的放大,我们能够获得的辩护就更加轻易。女权主义者的标签可以成为“(避开)批评的防护盾”,而当越来越多人可以被放在这个标签之下,我们就更能感到安心:当身边尽是认同同一标签的人,我们不需要做更多的思考,不需要建构新的个人认同,不需要去质问自己的个人选择。
只要越来越多人可以挂上女权主义者的标签,女权主义就更少威胁更讨好。只要是你的选择,你已经是女权主义者了,不管你吃什么,穿什么,买什么,流行女权主义都可以将它们描述成女性的进步。换句话说,只要认同女权主义者的标签,我们就不需要再自我质问,吃什么穿什么买什么是否对性别平等有任何推进(或损害),因为我的选择就是女权主义者的选择。
所以流行女权主义十分重视女权主义者的标签,仿佛就像一种营销,让每个人看到自称女权主义者的好处,而不是一种会让个人不断反思生活而需要挣扎努力的哲学。正是这样一种流行女权主义使得克里斯宾宣布,她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
个人发展与身份认同
克里斯宾批评的流行女权主义,在争论女权主义者标签的背后往往是希望强调一种必须有的“团结”:“我们必须统一,我们必须掌控,我们不得批评运动。”在她看来,这不过是过分沉浸于当下的个人胜利而已。
克里斯宾的尖锐批评背后,是她不满当下流行女权主义对何为压迫的误解,或者说对如何追求正义的误解。在她看来,将问题简单化约为“我得不到我所欲”,对于揭露和修正女性在男性中心主义下所受的不正义毫无益处,甚至颇为有害。女权主义应当同时反思“我所欲”是否真的值得追求。如果“我所欲”不过是向前一步,在一套不公平的游戏规则中获得优势,这对真正的性别平等毫无实质贡献,好比Ayawawa式的教导。
在克里斯宾看来,真正的女权主义应该是建立更好的集体式合作,反思个人行动是否在规范意义上正当,改变作为整体文化的性别不平等。关于集体的行动和集体的想象是关键,而不是所谓的“个人赋权”。
克里斯宾对流行女权主义的批评十分精准,不过,强调女权主义的批评性以及集体行动的必要,并不等于需要否定个体作为女权运动目标。
的确,简单将女权运动的全部目标理解为“个人赋权”不过是某种利己主义的版本,但是让每个个体可以获得足够的能力和资源,去追求个人的生活理想,同样也是女权运动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评价女权主义是否正当的重要标准之一。为个体赋权,不仅仅需要个人的努力,更需要作为集体的社会去改变不公平的制度和规范,为个人培养追求美好生活所需的能力。这一点并不会与克里斯宾对集体的强调相矛盾。
另一方面,克里斯宾批评对“女权主义者”标签的重视似乎也不够准确。当然,仅仅将“女权主义者”当作营销式的品牌标签自然不恰当,但是“女权主义者”同样可以成为一种重要的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的女权运动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作为一种不依赖于具体经验性质的身份,认同“女权主义者”某种意义上更接近于给予一种承诺。对“女性”的身份认同,对“受害者“的身份认同,都依赖于某种过往的不可变的性质和经验,都不是女权主义运动团结的基础。胡克斯曾经批评过,将姐妹情谊(sisterhood)建立在这些身份认同之上,造成的结果会是继续顺从于性别主义对女性尽是柔弱受害者的形象塑造,同时也排斥不同的女性,遮盖女性之间的差异和分歧。
相反,“女权主义者”的身份认同展示出一种选择的承诺。这种承诺不需要通过抹除差异来获得女权主义者的团结。个人可以自愿投身都性别平等的运动中,认可这样目标,承担相关的责任。作为女权主义者,我应该怎样做,应该如何对待别人,我的某些言行是否正当;以女权主义者的标准看,梅根·凯莉的言论是否恰当,桑德伯格在脸书的行动是否正确,默克尔是否作为女权主义者楷模是否当之无愧。这些都可以通过女权主义者身份得到很好的回答,也是个人投身性别平等很好的标准和承诺目标。
同时,这种承诺带来的责任对于个人而言也十分重要。女权主义者会认为承诺的这种的身份认同而“懂得承担责任去反抗那些可能并不会直接影响到我们个人的其他压迫”。胡克斯认为这是女权主义运动关键的部分。我们不能仅仅关心自己的“向前一步”,更需要合作起来,“去指出,去检查,去消除我们之间的性别主义观念”。这些都是只认女权主义者的责任。这一点,相信克里斯宾宾不会反对。
克里斯宾的《我不是女权主义者:一个女权主义宣言》对当下的流行女权主义提出了相当尖锐的批评。这些批评点出了女权主义运动自身出现的关键问题。不过,克里斯宾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似乎也不够全面。发出“我不是女权主义者”的宣言,并不是修正这些问题的方案,反而未能看清楚“女权主义者”作为身份认同的意义。总的来说,克里斯宾的这本小书颇为有趣,略带刻薄的论述引出了许多值得反思的讨论。
本文修改版以标题《女权主义者的流行标签,已更像一场身份营销?》先发于新京报 书评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