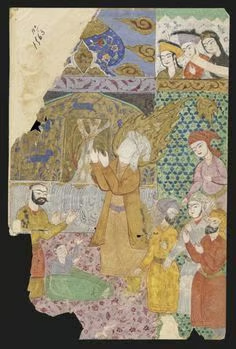鲍曼夫妇访谈
鲍曼夫妇访谈
齐格蒙特·鲍曼
雅妮娜·鲍曼
乌尔里希·比勒菲尔德/文
王立秋/译
Ulrich Bielefeld, “Conversation with Janina Bauman and Zygmunt Bauman”, Thesis Eleven, Number 70, August 2002: 113-117. 这个访谈原发表于Mittelweg36 (1993)译文仅供学术交流,请勿做其他用途。
齐格蒙特·鲍曼(1925-2017),波兰社会学家、哲学家。曾任英国利兹大学社会学教授。著有《现代性与大屠杀》(1989)等。
雅妮娜·鲍曼(1926-2009),波兰记者、作家。著有《晨冬》(1986)、《归属之梦》(1988)等。
乌尔里希·比勒菲尔德(1951- ),德国社会学家,曾任汉堡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社会学研究中心讲师。著有《自己人和外人:旧世界中的新种族主义?》(1998)。
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乌尔里希·比勒菲尔德:在纳粹恐怖统治结束、华沙解放后,和在1968年离开波兰后,你们两次被迫重新开始生活。你们对波兰解放的体验和别人很不一样。
齐格蒙特·鲍曼:1943年,18岁的我加入了在俄国组建的波兰军队。自1939年起,我就在俄国生活了,因此我对波兰被占领这件事情并没有什么个人的体验可言。身为犹太人,我父母担心纳粹会打过来,于是我们跑到了波兰东部的俄占区。接着我们越来越深地躲进农村。在回来后,我父母留在了俄国欧洲版图北部。我则入伍和部队一起回到了波兰。情况就是这样。在华沙起义期间,我们团在河的一遍,雅妮娜在河的另一边。
雅妮娜·鲍曼:当时我们还不认识。同时,我也在向他祈祷:请夺回华沙吧。我们初次见面是在1948年。我们在同一所大学,华沙社会科学学院学习。当时还没有社会学。我学的是社会科学和新闻。
齐格蒙特·鲍曼:我在华沙大学拿的哲学硕士学位,但我后来(博士和博士之后)学的是社会学。
乌尔里希·比勒菲尔德:你们都是活跃的党员。你们有一个具体的乌托邦理想,你们想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社会。
齐格蒙特·鲍曼:当然。在二战前,波兰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欠发达国家。当时有800万人处于失业状态,人们完全失去了希望,社会不平等也达到了不可想象的程度。我们都想全力创造一个新的波兰。
雅妮娜·鲍曼:我是到1951年才入的党,比齐格蒙特晚很多,他1946年就入了。在我开始学习、在我遇到鲍曼之前,我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我不是以犹太人的身份长大的。我家里没人信教,也没人信犹太复国主义那一套。是纳粹把我赶进犹太区,把我变成了“隔都里的犹太人”。我想去以色列,到沙漠里去工作。我都准备好要去了,只是因为碰巧才没有去成。然后我就遇到了齐格蒙特。他是我遇到的第一个诚实的党员。我对主义没什么想法。他是第一个我真正尊重的党员。
齐格蒙特·鲍曼:我做了一些反犹太复国主义宣传并说服她留了下来。我也不是以犹太人的身份长大的。我和犹太教生活没有任何联系。我也没去过犹太区。当时苏俄有很多问题,但民族问题还不是那么重要。我是犹太人,但没人关注这个。我加入波兰军队,回到波兰,并觉得自己是波兰人。我直到1967年才认识到自己的犹太身份。当时波兰不但反智,还反犹。
乌尔里希·比勒菲尔德:当时你退党了,身为波兰犹太人,你成了自己国家里的外人。是什么使你们离开了波兰?
齐格蒙特·鲍曼:一开始我们离开波兰的原因很简单。我们有3个女儿,并且我们都丢了工作。哪里都不要我们。1968年3月华沙爆发学生起义,6名教授被指控要为之负责。我们6个都是到1968年3月25日才在广播上听说自己被开除了。之前都没有任何风声。莱谢克·科瓦科夫斯基也是被开除的教授之一。我们中只有他留在了波兰,现在终于恢复了他的教授身份。他失业了好多年。
雅妮娜·鲍曼:从1967年起,我们就不断地被提醒,我们是犹太人或犹太复国主义者。但齐格蒙特从来都不属于后者。
齐格蒙特·鲍曼:当时的党报读起来就像是纳粹的激进反犹报纸《冲锋队员》(Der Stürmer),它们使用的是相同的语言。有人甚至发现党的领导班子发布的一个指示直接就是从《冲锋队员》翻译过来的。我没改过名。其他之前改过名——他们把自己的名字变成了波兰的——的人在报纸上遭到了“揭发”。当时的氛围真的很恐怖。大多数波兰犹太人都有相同的经历。他们不觉得自己是犹太人,而觉得自己是波兰人。突然他们被迫意识到,并不是这样。如果你问我,我是怎样成为犹太人的,那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
乌尔里希·比勒菲尔德:你的早期作品——我说的是《在阶级与精英之间》,《作为实践的文化》,我读不懂你的波兰语作品——中就有经典的社会学主题。
齐格蒙特·鲍曼:你说得对。我不认为所有这些经历影响了我的作品。我只是变得对犹太人问题和犹太人在现代文化中扮演的角色感兴趣了,必须承认,雅妮娜的《晨冬》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我突然意识到,我根本不理解这件事。和大多数社会学家一样,我压根没想过这件事情。当时,这只是一个边缘事件,是规则的例外。然后,我有了新的认识,得出了另外的结论。暧昧与纠结、关于纠结的恐怖和焦虑事实上不只是边缘现象,而是现代文明的核心主题。但我不是通过直接的个人经验,而是通过别人对我的智识影响才认识到这点的。我没有经历过我再《现代性与纠结》中描述的同化过程,我不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是我的祖先,替我经历了那个过程,我已经在另一边了,我不属于同化的那一代。
乌尔里希·比勒菲尔德:用你形容同化的那代人的意象来说,你并没有坐在湿滑的栅栏上,被拉朝两边,扯成两半。
齐格蒙特·鲍曼:也许,当时我的想法是,并没有栅栏。我没看到。问题是有的:身为波兰人,我不是苏联的波兰人而是在俄国的外国波兰人。但我是在俄国的波兰人,而不是犹太人。
乌尔里希·比勒菲尔德:1968年你们从波兰去了以色列。是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找到工作吗,还是说,以色列本身就是一个目标,一个属于你们的国家。
雅妮娜·鲍曼:就我而言,我的家人都在以色列。如果要离开波兰的话,那我想去找我的母亲和妹妹。我想去以色列。齐格蒙特从来都不想去。另一方面,我们也只能去以色列,我们被推朝那个方向。我们都被开除了。在为波兰电影工作20年后,我也被开除了。
齐格蒙特·鲍曼:为了离开波兰,我们必须申请入境签证。只有以色列能发这种签证。这是从波兰当局那里拿到一次性出境许可的唯一途径。不过,我们也不是非得去以色列。我们一开始在维也纳的一个难民营,罗伯克·麦肯锡(Robert McKenzie)邀请我去英国,也有人邀请我去蒙特利尔和维也纳。布拉格大学也愿意给我提供一个职位,当时捷克还没有被俄国人接管。只有以色列没给我邀约。我们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去了那里,我不会说希伯来语,因此只能用英语教学。我到处打听,但没人愿意给我工作。但我们不是为工作去以色列的,去那边是因为雅妮娜想去找她母亲和妹妹。
乌尔里希·比勒菲尔德:为什么在三年后,你们又离开了以色列。
齐格蒙特·鲍曼:才待了一年我就想走了。
雅妮娜·鲍曼:他从来都不想待在那边。
齐格蒙特·鲍曼:我在澳大利亚又找到了一个机会,直到现在我都还后悔没去那边,因为我非常喜欢澳大利亚。可雅妮娜不想去,那边太远了。然后我收到利兹大学发来的一封电报邀请我过去,我接受了。他们想找个人来担任空缺的社会学教席,于是我们就去了利兹。
乌尔里希·比勒菲尔德:在那很久之后,你才开始对纠结、对“反纠结的战争”和大屠杀感兴趣。这个兴趣的催化剂,是雅妮娜对她的“隔都”经历的描述。你在《立法者与诠释者》中第一次使用“作为园丁的国家”,即区分有意栽培的植物和杂草的国家这个隐喻。还是说,你在之前的作品中,就有这个想法了。
齐格蒙特·鲍曼:从那本很早的、60年代初在波兰出版的《文化与社会》开始,我的兴趣就从社会结构转向了文化,我在文化中看到了历史最强大的力量。现代性三部曲的第一部《立法者与诠释者》是对此的延续。我对现代文化的内部矛盾的兴趣持续了很多年,很难给出一个准确的日期。在《立法者与诠释者》之前,我还写过《阶级的记忆》。在这本书中,我告别了那种把历史当阶级史的解读。我批判地考察了各种从阶级冲突的角度提出的,对历史、对社会的动态变化的解释。也许,比大多数西方社会学家都要早一点。因此,我的处境和当下欧洲的处境相当,因为两个阵营之间冲突的消失留下了一片空白。但用什么来填补这个空白,现在的中心主题是什么,这是我当时正在寻找的东西,《立法者与诠释者》就是我的这番寻找的产物。我对这个问题框架的兴趣是从这本关于知识分子的书开始的。
乌尔里希·比勒菲尔德:从知识分子到外人还要等很久吗?
齐格蒙特·鲍曼:不。你会在《立法者与诠释者》中发现,有一个地方提到了知识分子自己的欠定(underdetermined)位置。知识分子本身就是外人。一个人如果不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外人,那他是不可能成为知识分子的。尼克拉斯·卢曼写过,我们都在某种程度上“离开了自己的位置(displaced)”,卡尔·曼海姆则干脆重复了舍斯托夫写过的话。我现在都还对这个主题,这个外人、异化和知识分子这个位置所特有的内在批判(inherent critique)的问题感兴趣。我想弄清楚它背后是什么经验,这个经验是怎样被反映出来的。
乌尔里希·比勒菲尔德:对作为“内敌”的“概念上的犹太人”的“发明”、生产是一种智识努力、一个智识传统的结果吗?
齐格蒙特·鲍曼:你应该记得,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有两个章节与反犹主义和对两种不同形式的比较相关。新旧反犹主义是截然不同的现象。新反犹主义以与后者截然不同的条件为基础。我在“黏滑的”、“液态的”的问题中发现了新反犹主义的基础。外人坐在栅栏上,他既不在这儿又不在那儿,他既不属于内部又不属于外部。这根插进现代社会身体的刺针对的是现代计划的核心:透明、清晰、理性。可这没用。
乌尔里希·比勒菲尔德:“作为园丁的国家”的意象给人统一的印象,让人觉得新兴的由民族国家组成的欧洲正在朝统一的方向发展。不过,现实中有不同的花园和不同的花园类型,比如说,英国的花园和法国的花园;有不同形式的对同化的渴望;也许,也有只适用于德国、使德国更可能走向大屠杀的历史条件。
齐格蒙特·鲍曼:也许我过度强调了大屠杀起源的非民族国家基础,也就是说,我过度强调了这点,即大屠杀不是一个德国问题。但我认为这是必要的,因为社会学中的整个论证就是做你刚才做的事情,也就是说,把这个事件和德国特有的问题联系起来。但我当时想说,现在也一有机会就说的是:别自满,这个事件的根源无处不在,它们只是有待施肥和结果而已。当然也有一些其他地方没有的、德国特有的条件。希特勒上台前,法国的反犹主义比德国还要猖獗。第一个真正反犹的小册子——它强烈影响了现代反犹主义的发展——是德吕蒙(Drumont)的《犹太人的法国》(La France Juive)。第一个写到应该用火炉烧死、用毒气毒死犹太人的人,是法国人赛利纳。在德国没人写要把犹太人烧成灰。最终他们确实这么做了,但也确实是没人这么写。材料、原材料就在那里,那么是什么让德国不一样呢?仅仅是因为它后来变成一个民族国家了,而且这个过程还没有结束,因为他们现在还有东德人的问题要解决。(德国的)民族国家是很年轻、很不安全的,此外,因为国家在1918年被毁,民族国家也就失去了它的连续性、它的传统合法性。于是又得从头开始了,慕尼黑发生了巴伐利亚起义,其他地方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所有这一切创造出一个特定的,比在其他所有早就建立的民族国家更致命的身份问题。
乌尔里希·比勒菲尔德:你是说国家对保护少数和外人来说非常重要?我们需要国家但同时,作为园丁,国家也要为对外人、对外人中的典范犹太人的暴行负责?
齐格蒙特·鲍曼:当代新自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个事实——传统民族国家的圣三位一体,即经济、政治和文化主权正在消解——的产物。经济主权正在向上转移到欧盟机构、跨国公司等实体手中。的确,现在国家只有有限的经济主权了。同时它也在丧失自己的文化主权,因为它不再对文化的同质性、对同化、对大一统感兴趣。这个主权被下放给了市场,下放给了各种群体、各种少数族群。剩下的,是没有经济或文化支撑的纯粹的政治主权。这就是今天的民族国家如此虚弱的原因。很可能没有权力能在组织一次像大屠杀那样的工业行动了。但另一方面,“部落”暴力也因此而有了充足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