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丨社交媒体神话与民粹主义


社交媒体神话与民粹主义
扬-维尔纳·米勒(Jan-Werner Müller)对世界而言,2024年是一个重要的选举之年: 预计将有五十多个国家举行全国性投票,其中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亚和美国之类体量庞大但已创伤累累的民主国家。人们普遍担心,被人工智能进一步武器化的社交媒体将在这些选举中扮演破坏性角色。
自特朗普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评论家就担心技术可能要毁掉民主。的确,社交媒体能有益于野心勃勃的独裁者。今天,民粹主义者尤其懂得社交媒体,以之作为与民众直接联系的一种方式,绕过了前互联网时代政党对他们的行动会有的限制。他们还能获益于回音室,这种效应强化了一种感觉,即:民众整体上一致支持某位民粹主义领导人。
但社交媒体并不天生就是民粹主义的。而且,假如民粹主义者今年表现良好,那不是因为没有阻止他们的工具或策略。
为对抗民粹主义,民主国家需要政治意愿。它们不只必须推动更优质的平台设计和监管,还必须行动起来,强化一些人认为完全过时的机构:有能力约束那些威胁民主的领导人的政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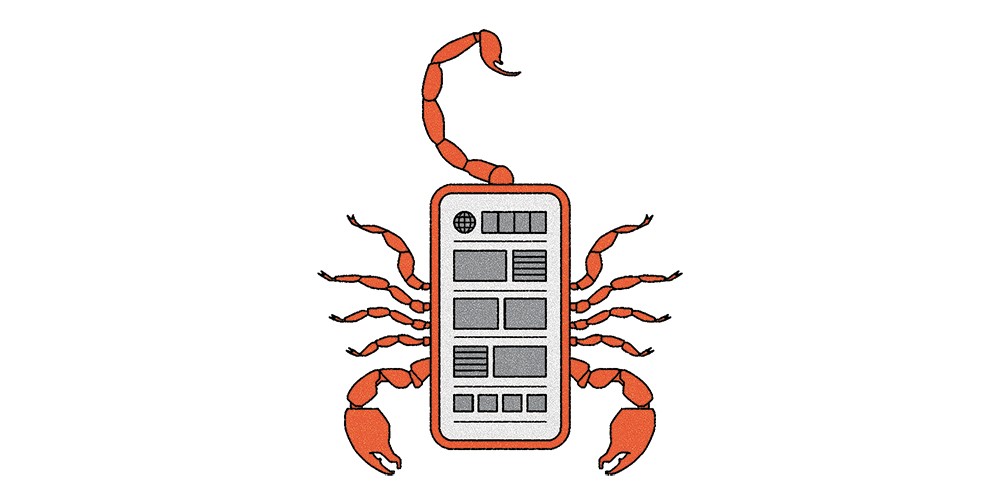
历史上的每一次媒体革命都导致了道德恐慌: 印刷媒体据说激发了宗教战争; 广播给世界贡献了阿道夫·希特勒; 电视成就了麦卡锡主义。今天精于世故的观察家们仍在反复念叨的这些看法,没有一个完全错误。但在每一个案例中,技术决定论都被证明是错误的,以下假设也是如此:新媒体将赋权于非理性的大众,他们心甘情愿被善于蛊惑民心的政客所诱惑。
最初,人们满怀乐观,欢呼社交媒体的到来。在那个人们现在觉得截然不同的时代,民主推广者转向Twitter (现在被称为X)和Facebook,视它们为助力世界各地民众反抗独裁者的工具。但正如“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那样,热情蜕变为了悲观。2016年,历经英国退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双重打击后,恐慌接踵而至。自由派评论员很快就找出了他们所认为的那两大全球民粹主义灾难的罪魁祸首:社交媒体和回音室,尤其是后者。自由派不只从欢呼转向嘲笑,还沉溺在了对记者负责任把关的所谓黄金时代的怀念之中。舆论的大幅波动和对过去的理想化,昭示着我们在理解新媒体时尚未找到方向。
今天的社会科学家比2016年的知道的多一些: 过滤气泡(即由算法构造的在线回音室)确实存在,但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普遍; 它们并不是极化的主因,尽管有助于更迅捷地散布虚假信息和宣传; 我们的线下生活在很多方面没有线上生活多样化。
社交媒体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使得政治领导人可以与潜在的拥趸发生看似直接的联系。这对民粹主义者尤其有用,他们声称只有他们才能代表他们通常所称的那些“真正的人民”。这暗示,所有其他权力竞争者都不代表人民,因为,正如人们惯常的指控所提到的那样,他们是腐败的。还暗示,一些公民根本不属于“真正的人民”。想想特朗普,他抱怨他的批评者不只在政策上错了,而且“不是美国人”,甚至——如他在去年退伍军人节集会上所说——是“害虫”。是故,民粹主义的要害不只在批评精英。毕竟,找有权势的人的麻烦往往合情合理。相反,问题的要害在于将一些人排除在人民之外: 政党政治层面的其他政治人物,以及公民层面的整个群体(通常是已经很脆弱的群体,如印度的穆斯林)。
这种看似直接的联系是政党衰落的成因之一。民粹主义关乎否认并最终摧毁多元主义; 运转良好的政党可以反击这一点,并约束民粹主义政治企业家。一些国家甚至通过法律要求政党拥有内部的民主架构。(在去年11月的选举中,荷兰激进的右翼民粹主义者海尔特·威尔德斯领导的自由党赢得了最多席位,但因威尔德斯是该党的唯一正式成员,自由党在那些国家就是不被允许的。)当然,政党团结了忠诚的党徒。但就他们共同接受的原则应当如何转化为政策,党徒之间往往意见不一。各政党内部形成对其领导层的合理反对,这没有丝毫不可理喻之处,而且事实证明,反对意见在遏制领导层方面往往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和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等民粹主义者以高度独裁的方式管理他们的政党,是有原因的。
可以肯定的是,社交媒体营造的直接感是一种幻觉。毕竟,社交媒体只是居间的媒介。但无论多么具有误导性,未经过滤的偶遇政治领导人的可能都承诺了真实性和一种联系感,这种联系感以往只有在比如党的会议或群众集会这样的特殊时刻才能获得。政治理论家娜迪亚·乌尔比纳蒂(Nadia Urbinati)为这一关系提出了一个听来自相矛盾的术语“直接代表”(direct representation): 站在公民和他们的代表之间的不论任何人,似乎都已消失了。
动员人们投票的工作过去是不同的。如政治学家保罗·肯尼(Paul D. Kenny)在其著作《为什么是民粹主义》(Why Populism?)中解释的那样,在社交媒体时代到来前,动员有赖于庇护主义(clientelism)或组织良好 (更直白地说: 高度科层制) 的政党。政党和候选人向支持者承诺了物质利益或行政职位方面的好处,以换取选票。这是昂贵的,而且假如政治竞争加剧或更多权力掮客加入竞争,代价将急剧上升。维持科层制的政党一样昂贵。必须为党的干部支付报酬,哪怕他们可以指望理想主义者的志愿工作,那些人会牺牲他们的周末去散发传单,或挨家挨户进行游说。
如肯尼指出的那样,社交媒体降低了动员成本,尤其是对特朗普这样的名流候选人来讲,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流行文化信誉。过去,当印刷媒体和电视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政党的战略家会花费巨大代价搭建好宣传反馈回路; 如今,反馈回路是由那些希望为了利润而最大限度参与的公司免费搭建的。
正如同打理网红,政治家的在线出场也有赖于持续进行管理,所以这并非完全没有成本。特朗普可能自己写下推文,犯下拼写错误,等等,但其他人必须付钱给精通技术的团队。社交媒体可能对那些已经将政党视作营销某种人设而非设计政策的工具的人最有效。以意大利前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为例,1990年代,他的公关专家为他创办了意大利力量党(Forza Italia) ,并像一家足球迷俱乐部和商业企业的融合体那样组织这个党。贝卢斯科尼在2022年意大利大选之前加入TikTok ,并非偶然(哪怕他试图吸引的年轻人或许已经发现,他的表现——正如年轻人会说的那样——令人难堪)。
最成功的政治家可以同时利用这两种支持形式。例如,坐享巨大个人崇拜的莫迪,已从一个拥有科层制机构、党员数量庞大的政党中脱颖而出,并可以依靠忠诚基层党工的免费劳动。不过,他一样拥有一批网络追随者,在网上,他可以作为一名超越党派政治的名流展示自己。
一旦民粹主义领导人建立了直接联系的假象,他们就会发现,声称职业记者之类传统媒介扭曲了政治家的信息,进而诋毁他们的声誉,要更容易一些。这可能转化为更少的多元辩论,并减少记者提出不方便问题的机会。莫迪和欧尔班已有多年没有举行过真正的新闻发布会,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都婉拒参加选举前的辩论。特朗普拒绝与目前的共和党候选人一起登台,看上去是一场冒险的赌博: 正如候选人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试图指出的那样,这位领跑者似乎惧怕与其他候选人对垒; 此外,他正在失去一个充分展示自己令人难忘的贬低技巧的机会。但特朗普正照搬独裁者的剧本: 置身选战之外,把自己描绘成民意的独特化身。假如你已经告诉你的支持者,其他每个人都是腐败的,或者至少,完全不代表他们的观点,为什么你还要下作到与他们同场竞争呢?
因之,过滤气泡可以帮助民粹主义者推销他们的核心产品: 团结在民粹主义领导人身后的同质民众之说。旨在增进与志同道合的用户接触的算法管理会放大这一动态。平台通常会建议用户观看或点击下一项内容。例如,任何在 X 上搜寻欧尔班的人都可能找到五花八门的极右内容。我最近查看他的账户时,X向我展示了来自俄罗斯外交部,和美国总统参选人、阴谋论理论家小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 Jr)的推文。
诚然,这些在线气泡并非在真空中形成。在美国,许多人确实生活在一个极右气泡中,哪怕是《华尔街日报》之类中间偏右的媒体也绝不接触。但这一气泡并非Facebook 或 X 导致的。正如哈佛大学社会科学家在2018年的一项研究中所表明的那样,1990年代,右翼有线电视新闻和电台谈话节目的巨大成功塑造了这一气泡的轮廓。社交媒体刚刚登上了那一基础设施的顶端而已。假如社交媒体自身成就了一个阴谋论和仇恨永远占主导地位的世界,那么我们在每个国家都会见证同样的结果,但我们没有。

民主国家必须彻底整饬平台的治理方式,使民粹主义者更难于以有利于他们自身的方式利用平台。当前形式的社交媒体存在的一大问题是,将太多力量赋予了太少人。平台力量,即对在线与他人联系方式的控制,是当今不受约束的巨大力量。如社会科学家迈克尔·西曼(Michael Seemann)所论,平台力量源自允许或拒绝用户访问平台的能力,而拒绝用户访问平台的实现,要么是通过彻底的禁令,要么是通过在线水军的侵扰。
正如埃隆·马斯克在Twitter上进行的改变所表明的那样,那些控制平台及其基础性机制的人可以操纵在线话语。自2022年接管该平台以来,马斯克不只武断地冻结了一些记者的账户,还弱化了内容审查方面的规则和人员配备。随着马斯克在X上恢复一些白人至上主义者和其他仇恨煽动人士的账号,变性人等少数群体受到的保护越来越少。
在半正常运转的民主国家,像马斯克这样反复无常的寡头几乎可以单枪匹马地治理平台。在走向独裁统治的国家,国家本身就可以成功地施压平台,要求其服从自己的命令,印度针对Twitter正是如此,该国迫令这家平台屏蔽了政界人士、活动人士甚至英国广播公司。在彻头彻尾的独裁国家,政府正在完善社会科学家玛格丽特·罗伯茨(Margaret Roberts)所称的摩擦和淹没技术。独裁政权不再像传统的专制统治那样,仅仅仰赖大规模镇压制造的恐惧感,而是用信息“淹没”互联网,以分散用户的注意力,并利用有意为之的技术故障(“摩擦”)使公民更难访问某些网站。这些政权知道,内容审查可以吸引人们关注丑闻内容; 真正有见地的人则会让这一类内容消失。这样的技术在中国随处可见,监视技术也是如此。野心勃勃的独裁者,包括在民主国家争夺权力的右翼民粹主义者,无疑会试图复制这一套技能。
诚然,你不能阻止民粹主义者在线建立他们自己的反公共力量,就像你不能也不应该妨碍政党召集它们自己的追随者。集会和结社自由意味着,志同道合的民众完全有权与有同样志趣的其他人携手并肩。比如,人们不会希望当局开始关闭致力于赋权少数族群的安全空间,仅仅因为他们碰巧不够多元化。通过在网络生活中注入观点的多样性对抗网络同质性,这一构想用意良善,但不切实际。例如,法学家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推荐了“意外收获按钮”,它大有可能是这样的: “既然你正在点阅女权主义的观点,那么点阅一下反女权主义的观点怎么样?”
对网络政治生活更细致入微的看法并不意味着民主国家必须宽容对仇恨的煽动。平台设计可以有不同: 正如政治学家詹妮弗·福雷斯塔尔(Jennifer Forestal)所展示的那样,比起 Facebook 群组,Reddit形成了更多样化的对话。Reddit 允许组建社区,但维持了其子板块(subreddits)之间边界的可渗透; 还赋权于版主和用户,都遵守在线社区商定的规则。
内容审查尤其应该是强制性的,就像在德国那样,而非像马斯克这样的平台控制者有权分配的一件奢侈品。内容审查可以被滥用,但任何控制媒体力量的企图都是如此。(诽谤法可以——而且正在——被不民主的行为者利用,但那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完全摒弃它们。)为预先组织这种情况发生,内容审查必须尽可能透明,并接受适当的监督; 算法的“黑匣子”理当至少向研究人员开放,以便它们能够帮助决策者理解社交媒体平台的管理方式。这听起来像是白日做梦,但通过最近的《数字服务法》(Digital Services Act)和《数字市场法》(Digital Markets Act),欧盟一直在追求这些目标。因Facebook未能遵守隐私法规,《数字市场法》迄今已阻止其在欧盟国家内发布模仿X的产品Threads。
立法和教育将是民主国家的重要工具。社交媒体商业模式基于通过提供越来越极端的内容将参与最大化,并不超出政治监管的范围。民主国家还应在讲授媒体素养方面投入大量资源,这种事情,许多领导人在抽象层面上加以肯定,但就像公民教育一样,最终总是被无视,因为对全球经济竞争而言,数学之类“硬”科目被认为更重要。尤其是,民主国家绝不能孤立对待社交媒体。假如它们通过重振地方新闻业、监管政党等方式,培育出一种更健康的媒体格局,那么民粹主义者将更难取得成功。
(作者是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近著为Democracy Rules。本文原题“The Myth of Social Media and Populism”,见于《外交政策》2024年冬季号,上线于2024年1月3日。超链接为原文所有。译者听桥,对机器初步形成的译文有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