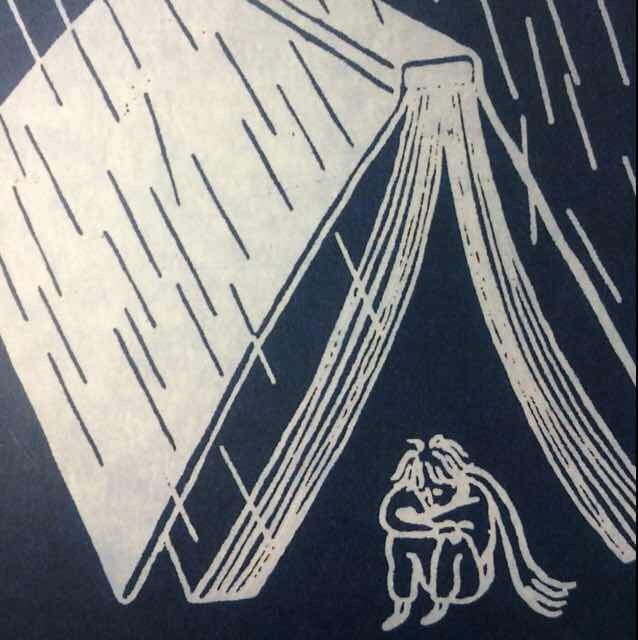MeToo#从法律规范中寻找性骚扰防治共识,而非滥用“舆论审判”“无罪推定”概念
1.不当类比,为讨论增添冗余信息
(1)不是“舆论审判”,而是“公众质疑”
“舆论审判”是对“司法审判”的类比用法。使用“舆论审判”描述公共讨论现象,可能从一开始就不恰当,导向了一些不必要的担忧。类比基于两个原因,认为舆论在为事件定性,并且对涉事人有不利影响。问题是,“司法审判”的定性具有终局意义,且直接威慑力(以刑事为例)来自对犯罪人人身自由、私有财产、政治权利的强制剥夺,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评价降低、日常生活不便(有“前科”多种职业业受限)。显然,“舆论审判”的效果远不及此。这种不准确的类比描述可能把焦点转向伪问题,比如是否应当纵容“舆论审判”,如何避免负面影响。或许用“公众质疑”描述比较合适,而由“舆论审判”引发的这个国度特有的“恐惧感”,可以轻减一些。
当我们担心“公众质疑”可能对被质疑者造成伤害时,止步于“运动是否造成误伤”的泛泛而论没有意义,应当以区分思维考察,对于哪些人、哪类群体,是否真的有伤害,以及可能造成何种伤害。知识分子、公益人这类群体,权力结构形成基于道德表率、执行力和信誉,一旦受到性方面的失德和违法检举,有可能导向对事业或大或小的威胁,这可能是他们恐惧的根源,尤其在社群其他成员认可检举为真时,不得不“退群”,另谋出路。而对领导干部群体来说又有不同,他们的权威来自职务,在其位有其权,与个人德行没有直接关联。舆论场的喧嚣难以远距离传导至体制内,成为启动违纪违法调查的契机,而一般性骚扰行为又难以认定为违反党政纪。
“公众质疑”投射在不同人群产生的效果不一,投向个体还是群体影响也有不同,我们不能只站在源头担忧它投射出去可能会伤到谁,不妨跑到它击中的靶子那里,细致观察一番。而且,这种观察应该是个案视角,关心个体而非群体。这场运动中,投向群体的质疑,很难说产生了什么实质伤害。在这种普通民事纠纷或一般治安违法中,若真误会了某个人,及时澄清基本可以避免实质损伤。面对不义事件,“公众质疑”是必然的,“误伤”是偶然,以“结果论”视角处理这种偶然事件,比在源头处就提出各种限制,更有可行性。
(2)“无罪推定”不是事实判断
“无罪推定”是制度设计,无关事实判断。在诉讼法领域,它关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程序性权利。简言之,在诉讼程序眼里,TA是“无罪”之人,有权为自己辩护、聘请律师、申请变更强制措施……至于执法者和公众内心如何看待TA,在所不问。在证据法领域,它关乎举证责任分配和证明标准设定,要求控诉方承担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并且,这种证明责任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之所以有这个制度设计,考虑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入诉讼程序后,要与国家机器对抗,若无“无罪推定”的制度保障,无异于砧板鱼肉。
而在法院宣判有罪之前,要求执法者和公众在事实层面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视作无罪,甚至不允许内心确信TA有罪——这是对“无罪推定”原则的误解,把“有罪推定”视为“无罪推定”的当然反面。“有罪推定”是事实判断,“无罪推定”是制度设计,二者不在一个层次,并非一体两面。
从无罪推定的内涵来看,它是对公权力的约束,并不适合进入舆论场,作为对公众的普遍要求。我们当然可以提醒参与者在事实判断时审慎一些,甚至要求在无充足证据前尚且信TA为无辜之人。这类提醒和要求无妨,但不叫“无罪推定”。
2.谨慎对言论提要求
法律和舆论在做同一件事:基于已有信息做判断。法律上,认定一人要承担何种责任,具有终局属性和强制力,必须慎之又慎,由此衍生出了必要的制度和理论,比如“无罪推定”这类制度设计。
但在舆论场这个复杂空间里,试图通过制度设计“规范”公众言论和思考的行为很难实现,有可能滑向消灭言论和压制思考的深渊。控制思维主导下的制度设计,在应对复杂场景方面历来不尽人意,计划经济如此,舆论场也不例外。
要求公权力慎用法律规则管制言论有共识。而对公共讨论参与者,有人建议是否可以借鉴法律规则倡导的证明理念来判断信息,比如避免“有罪推定”“类推解释”“自证其罪”(刑法领域),倡导“谁主张谁举证”“举证责任倒置”“盖然性证明标准”(民诉领域)等等。问题在于,这些规则本就总结自实践,源自人们诚实善良的信念和朴素的逻辑认知。实际上,公共讨论参与者一直在运用这些规则的基础版本进行判断。
比如,性骚扰事件中,检举人实名控诉,提供细节信息,友人为其信誉背书,同时,或有多人共同检举,或有关联证人证言……受害者已尽所能。常理来讲,加诸受害人的证明责任,到此足矣。而且,这些信息投进舆论场,并非不经受反驳,被质疑者提出有理据的辩解,若在证明力上有同等分量,则角力继续。看似纷乱,这条证明逻辑主线大体不乱。至于进一步的信息,比如更多的证人证言、物证、视听资料,受限于这类事件的特殊性,即便立法在设定规则时也考虑了减轻受害者的证明责任,并在取证过程中提供指引和协助,若在舆论场反倒如此苛求,不合常理,不近人情。其实,我更担心,性骚扰和性侵事件举证难问题,即便在有规则设计和特别协助的法律体系中尚难解决,更遑论纷乱的舆论场。对于受性骚扰性侵的同伴,我们不是过度保护了,我们是保护不足。
3.港台性骚扰防治立法的启发
那么,我们到底能从法律规范里获得哪些启发?立法在公共讨论中的意义,不只是“法律怎么判”,还表现在它能将一部分共识沉淀下来,为之后类似争议提供基础。有了共识基础,才有继续讨论、不断进步的可能,否则争论容易陷入低水平重复的境地。
比如,哪些行为属于“性骚扰”?如何认定某人遭到了“性骚扰”?受害者维权时应当给予哪些协助?……这类基础问题,法律条文沉淀下了一个时期社会的基本共识。我们不妨以此为基,展开更进一步的讨论。
香港《性别歧视条例》定义了涉嫌违法的“性骚扰”行为:任何人(不论如何描述其身分)(a)如(i)对一名女性提出不受欢迎的性要求,或提出不受欢迎的获取性方面的好处的要求;或(ii)就一名女性作出其他不受欢迎并涉及性的行径,而在有关情况下,一名合理的人在顾及所有情况后,应会预期该女性会感到受冒犯、侮辱或威吓;或(b)如自行或联同其他人作出涉及性的行径,而该行径造成对该名女性属有敌意或具威吓性的环境,该人即属对该女性作出性骚扰。所谓“涉及性的行径”:包括对一名女性或在其在场时作出涉及性的陈述,不论该陈述是以口头或书面作出。
《条例》规定,行为人作出“不受欢迎”的性要求和涉及性的行为即属性骚扰。“不受欢迎”应理解为被骚扰者的主观厌恶感——有别于违背女性意志,它还包含了不得已的“自愿”。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判断主观意愿?除了个人陈述,也设定了客观标准,即同样情形下,一般人(a reasonable person)是否认为该行为会令女性感到厌恶。比如,饭局上违背女性意愿摸大腿,故意触碰女性胸部、臀部等隐私部位,在诚实善良的公众看来,这当然是冒犯女性的行为。
《条例》同时产生执行机构“平等机会委员会”,履行条例赋予的职责,致力于消除歧视、消除性骚扰,促进男女之间的平等机会。该委员会颁行《性别歧视条例雇佣实务守则》列举了雇佣关系这一特定场景中的性骚扰行为,包括但不限于:(1)不受欢迎的性要求——例如挤眉弄眼、淫亵动作、触摸、抓弄或故意摩擦他人身体;(2)提出不受欢迎的要求以获取性方面的好处——例如向对方暗示在性方面予以合作或容忍其性要求会有助对方的事业发展;(3)不受欢迎的口头、非口头或身体上涉及性的行径——例如在性方面有贬抑成分或有成见的言论、不断追问某人的性生活;及(4)涉及性的行径,借此营造一个在性方面有敌意或具威吓性的工作环境——例如在工作场地高谈与性有关的淫亵笑话、展示有性别歧视成分或与性有关的不雅图片或海报。
台湾以《性骚扰防治法》及其施行细则与相关解释函、《性骚扰防治准则》、《性骚扰事件调解办法》、《性别工作平等法》及施行细则、《工作场所性骚扰防治措施申诉及惩罚办法订定标准》、《性别平等教育法》及施行细则、《校园性侵害性骚扰或性霸凌防治准则》等多部专门法律法规来规制各类场所的性骚扰问题。
《性骚扰防治法》规定,本法所称性骚扰,系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对他人实施违反其意愿而与性或性别有关之行为,且有下列情形之一:(1)以该他人顺服或拒绝该行为,作为其获得、丧失或减损与工作、教育、训练、服务、计划、活动有关权益之条件;(2)以展示或播送文字、图书、声音、影像或其他物品之方式,或以歧视、侮辱之言行,或以他法,而有损害他人人格尊严,或造成使人心生畏怖、感受敌意或冒犯之情境,或不当影响其工作、教育、训练、服务、计划、活动或正常生活之进行。
该法的施行细则对性骚扰认定提出原则要求,“应就个案审酌事件发生之背景、环境、当事人之关系、行为人之言词、行为及相对人之认知等具体事实”。
同时,《性别工作平等法》特别规制了雇佣关系中的性骚扰行为:(1)受雇者于执行职务时,任何人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别歧视之言词或行为,对其造成敌意性、胁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环境,致侵犯或干扰其人格尊严、人身自由或影像其工作表现。(2)雇主对受雇者祸求职者为明示或暗示之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别歧视之言词或行为,作为劳务契约成立、存续、变更或分发、配置、报酬、考绩、升迁、降调、奖惩等之交换条件。
台湾卫生福利部在网站上公布了113保护专线,24小时为被害人提供专业协助;制发性骚扰被害人权益说明手册、法规汇编、必要的法律文书、维权流程图,并且提供费用援助(心理评估、咨询及治疗费用;诉讼费用及律师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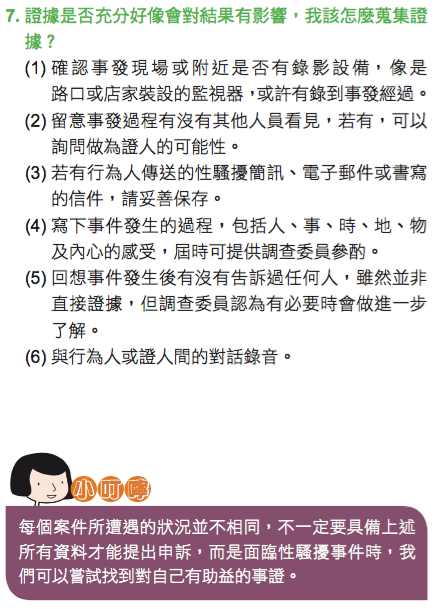
相比之下,大陆地区仅在《妇女权益保护法》中原则性阐述“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至于何为性骚扰?哪些部门承担保护或协助职责,工作如何开展?证明责任如何分配?追责措施有哪些?……原则规范多而实施细则少,距离通过法律手段实现对性骚扰受害者的妥善保护,仍任重道远。同属华人世界,分享文化共性,为何香港和台湾在规制性骚扰的法制体系建设却远远好与大陆地区?若无类似MeToo事件和民间组织的自下而上持续推动,仅凭公权力自省自觉,难见明显进展。
其实,除了这些制度规范,我还检索到了其他信息,比如性骚扰防治资料的公开、完整、可读、获取便捷。我若是性骚扰受害者,完全可以根据指引完成检举和告诉。且不说大陆的性骚扰防治领域,即便是讼争较多的家事纠纷领域,也做不到这样便民。再比如,《性骚扰被害人权益说明手册》中列明了由政府部门和民间组织构建起的明确而完备的保护体系,即便是像我这样第一次查阅手册的人,也倍感暖心踏实。

大陆地区的性骚扰防治,理当先解决有无的问题,而非担心矫枉过正。担忧MeToo运动“滥伤”无辜的人,当然可以建议检举者承担进一步的证明责任,并期待公众警惕运动可能造成的误伤。但也要认识到,历次造成扩大化伤害的运动,罪魁祸首恰恰是极为落后的法治环境,以及肆无忌惮的公权力,而非看似声势浩大的行动者。我们理应合力推动性骚扰防治体系健全并有效运行,为更多人勇敢站出来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免除TA的后顾之忧,也让涉事双方尽可能获得公平公正的对待。个案正义应当建立在整体正义的基础上。在污浊环境里追求个案正义,个体承担了太多额外的苦难和非议,遍体鳞伤。大多数旁观者,即便充分调动同理心,恐难体会深陷其中的挣扎和困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