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复社会行为,怎么防范?

“像这种报复社会的,还真没有办法防,什么严刑峻法也没用,因为人家已经想明白后果了那就是同归于尽……所以,只能看运气或者当时你的反应快不快了……”
在珠海冲撞路人事件发生后,这是网上相当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反应。毫无疑问,谁都不希望悲剧重演,可是要怎样才能预先阻止同类事件?一想到这里,人们的思路就卡壳了。
要预先防范暴力事件,是需要有信息的。这就像天气预报,哪怕云图瞬息万变,准确预测很难,但好歹通过复杂计算,我们可以大致有所判断。如果知道某人经常家暴妻子,最近还不断升级,那周围人和警方就可以提高警惕进而采取必要措施,因为潜在的加害者和受害者都可以提前锁定。
在这次事件后,很多人在震惊之下都认定,凶手内心肯定潜藏着“恶魔的种子”,仿佛他携带着原本就携带着某种病毒,只是一到特定条件之下就爆发出来,荼毒他人,谁沾上谁倒霉。
微博大V“荡科长”就认为:
能犯下这种恶性案件的人,我不信他在婚姻存续期间是个普通人和好人。案件的真相不是因“其对离婚后财产分割不满而引发”,而是“嫌疑人因其恶劣行为或性格导致离婚,进而恼羞成怒产生报复社会的念头并付诸执行”。
另一位就说得更明确:
我猜凶手肯定是从小或者一出生就是一个危害社会的孽种,他有预谋的选择地点,极其强悍的心理承受能力和极其残忍的杀人手段都昭示这凶手危害社会、杀人如麻的本性,只是他提前实施了。我认为下一步应该重点排查刑满释放人员,有暴力犯罪倾向人员,精神病居家患者等等这类不稳定社会人员。
这种思路实际上是推定:“正常人”干不出这种事,反过来,干出这种事必定是“天生坏种”,不可能没有迹象可寻,因此,把这些潜在的坏人搜寻出来,予以清除,我们的共同体就可以安全无虞了。
问题是,怎样才算“孽种”?如果真有所谓“犯罪基因”,那在人群中应该均态分布,坏人不会突然变多,那怎么解释此类事件增多?知道有些人有前科,就可以采取歧视性的预防打击了吗?不管设想多好,实践起来势必导致扩大化。

本来,这类事件的真正可怕之处,就在于其隐蔽性和突发性:行凶者可能没有前科,平日里看起来也都很正常,直到事件爆发,没人料到他会成为行凶,受害者也想不到自己会被害。这是霍布斯说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任何人都可能是潜在的加害者和受害者。
这就是应对无差别攻击普通人事件的棘手之处:加害者和受害者之间毫无关联,甚至没有征兆,哪怕你知道他对社会不满,但也想不到他会干出那样的事来。至于严刑峻法的威慑,对这些“自己不想活,拖几个人一起死”的人也不起作用。
由于警方通告中提到凶手樊某“62岁,离异”、“案件系樊某对其离婚后财产分割结果不满而引发”,公众在解读时也就更进一步滑向错误归因,并加剧了由此而来的无力感和宿命感。
不乏有人指责“凶手的前妻也应承担一部分责任”,仿佛是她躲避了攻击,这个残忍的懦夫才把气撒在无关的人头上。照这种想法,凶手的暴戾仿佛就像打雷下雨,是没奈何的事,也无法防范,谁轮上了只能算自己倒霉。
那还能怎么做?到这一步,中国式的管治思路很自然地就会滑向另一端:既然认定那种行为是无法预测的、难以锁定谁可能是潜在的加害者/受害者,那么还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管制凶器,但接下来难道要禁止开车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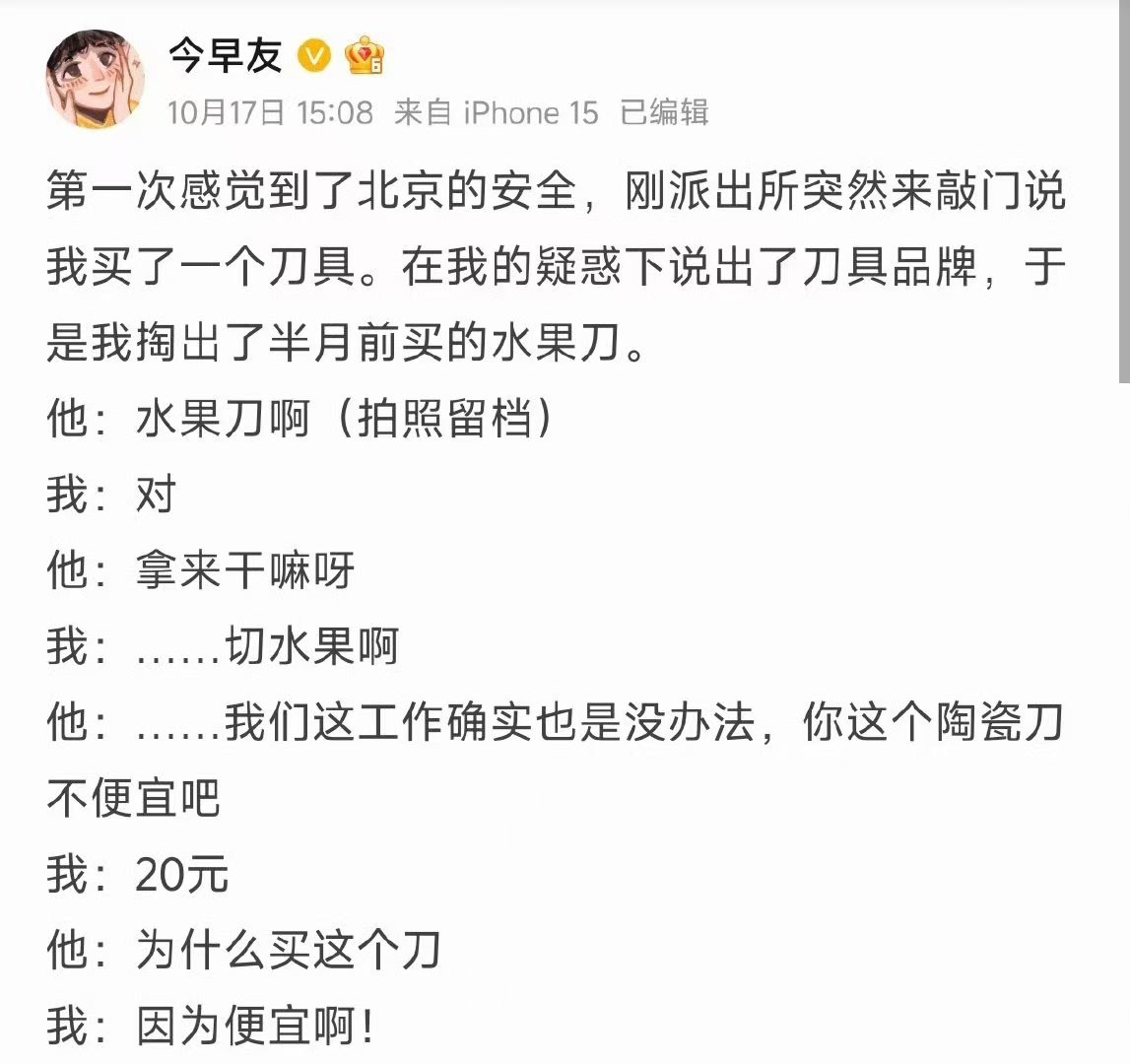
顺着这样想,很容易陷入死胡同,这表明,我们的问题本身可能就是错的。哲学家梁娥(Susanne Langer)曾指出:“问题的提法,不单规限且引导答案的答法。”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提问,就可能得到什么样的答案,因为问题本身就提供了一个架构,限制了我往什么方向去寻找答案。
张德胜在《儒家伦理与社会秩序:社会学的诠释》一书中对比了中西文化的差异,发现双方对社会秩序的根本设问就是不同的:
霍布斯提出的问题是:社会秩序为什么是可能的?孔子等人的问题则是:如何建立社会秩序?前者的问法是:“为什么?”是个智性问题(intellectual question);后者的问法是:“如何?”是个规范问题(normative question)。
在公众对这次事件的反应中,也能明显看出这一点:太多人关注的重点是“如何防范”(how),而不是追问、反思悲剧的根源(why)。
这种思路适合那种知根知底的小型熟人社会:每个人都生活在他人的眼皮底下,因而发生什么事都没什么复杂难解的(“早知道他会干出这种事”),也就不必问“为什么”了,之所以出现那些的行为失范,只是因为有些人没遵守正确的规范。至于什么才是正确的规范,那也是早就知道的,不必讨论,因而问题只是怎么去做——要么教导人照做,要么把无法改正的害群之马驱逐出去。
小时候看《包公案》,我就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包公断案,仿佛不需要复杂的推理过程,他总是一下子就能知道谜底,问题只是如何逼问罪犯承认,并予以公正地判决。
多年以后我才领会到,这就是中国文化思维的特点:受小农社会生活的影响,我们倾向于认为,原因是简单明了的,难的是怎么做——所谓“知易行难”。
但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到了庞大复杂的地步,像这样的思路已经无法指导、规范人们的行为了。像无差别攻击这样的事例频发,不仅是社会失范的征兆,也意味着凶手无法为自己的不满情绪找到明确的因果关系,不清楚自己的困境是谁造成的,因而才会把整个社会都怨恨上了。
要解决这样的问题,没有简单的办法。当一个社会出现全新的变动时,不了解清楚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就贸然应对,不但未必得当,有时甚至加剧了混乱——如果不知道“为什么”(why),又怎么知道怎么做(how)?
事实上,这就是我们当下的困境:问题不是一两个坏人制造了这样那样的悲剧,而是我们这个社会系统缺乏制度化的渠道,即便有什么不满情绪也是弥散的、无组织的,没有渠道可以释放和纾解,这看似低成本维护了稳定,因为每个人都自己消化了情绪,然而一旦爆发,这恰恰也是它难以对付的地方;与此同时,深入的调查和反思也随着调查记者的失势走向衰落,也就是说,制度化的信息渠道同样缺失。其结果,所有人就像在迷雾中兜圈子,当事人搞不清楚自己压力和痛苦的来源,出了事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也不去弄明白,就急于应对。
没有正确的问题,我们就找不到正确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