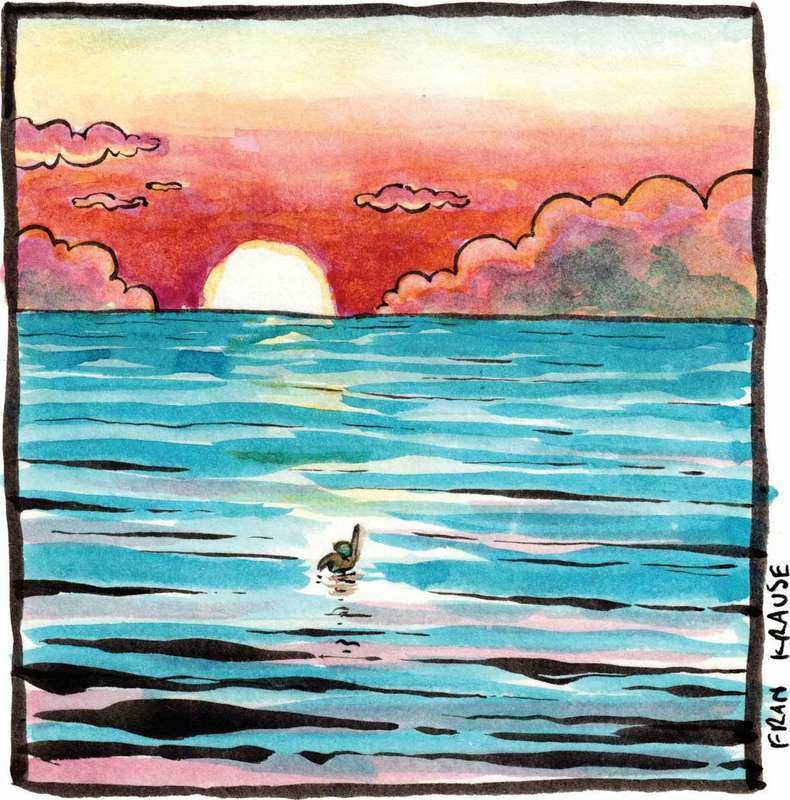女权主义一定是左派/右派吗——读《让女人自己说话:亲历战争》
不算书评,由本书引出的一些问题。
女共产党员的形象从20年代到现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一直在发生变化。
官方叙事中,她们是饱受剥削,站起来反抗的进步女性。不仅根正苗红而且品质纯洁,从容赴义。战争之后,她们积极参与到生产建设中,也同时证明无产阶级革命是如何让底层人民翻身做主,比如“三八红旗手”这样的荣誉,就是专门为女性设立。
但对女党员的积极进取精神,在80年代之后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原先引以为傲的品质,如今都成了被嘲讽揶揄的对象。
比如,搜索“刘胡兰”之后紧接着的联想词就是“刘胡兰发型”,用以指代土气的发型和外貌。改革开放后经济和消费主义的发展,让人们对“女性气质”更为看重。原本干练、中性化的女党员形象,在新时代变成了土气、老派的代名词。
但这并不是党内女性面临的首要问题。知识分子对共产党体制的反思,使得党内女性处在双重的弱势地位:
在党内,她们由于是女性,本身就处在比男性更弱势的地位。在知识分子的评价体系内,她们由于是党员,常常被自由主义者当做批判极权的靶子。
党内受歧视的问题,王政在《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中提到过一些。比如向警予本身能力极强,也希望参与到更多的革命运动中,但她最终只能负责妇女组织。
李小江的《让女人自己说话:亲历战争》更多地记录了作为女性,她们在战争中遇到的问题,同时也包括不平等的对待。比如在战争中,女兵或者女性护理人员,通常要担任掩护男伤员的任务,这种掩护甚至是以生命作为代价的,但她们在当时就会认为,因为男兵是去打仗的的,所以生命更珍贵。
而参与战争的女兵,不仅要承受战争中的伤亡,一旦被俘虏,就会面临大范围的性暴力,或者被强迫为人妻妾。如果说这些都是战争中两性都难以避免的伤痛的话,战后的资源分配再次体现了党内的结构性歧视。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50年代中期,军队实行“军衔制”,调整减员,大量女兵复员。这使得原本有机会获得军衔的女性,大范围被复员回家,失去了军内党内晋升的机会,而这些将直接影响她们今后的人生发展。
很多人看过一个纪录片,讲的是参加过战争的女性,一夜之间被告知自己的身份是“XXX太太”,并被告知这同样是国家需要,其实就是发生在50年代的军衔制和军队减员期间。
这些算作是女党员在体制内遭遇的性别不公的话,还有另一种性别歧视以更为隐蔽的方式投向她们,就是党外评价体系同样将女性作为了“象征”,用以批评。
比如电影《芙蓉镇》中,在文革期间利用政治斗争去举报、批斗普通人的“掌权者”,就是女科长李国香。当然,文革的头号坏蛋自然也要算到四人帮头像,尤其是江青头上。
当广泛意义上的自由派批判权力时,并且需要借助某个事件、群体去批判体制权力时,往往先批判的是为权力附庸的女性。比如朝阳大妈、比如女教导主任,比如女红卫兵。
这些批判有着更隐蔽的偏见,“女性原本应该是温柔善良的,极权体制让人失去了个性,也让女性失去了女性特质,所以反对极权的一种方式就是,反对这些权利欲极强的女性”。
阅读李小江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认识到党内女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尤其是推动性别平等过程中都曾经付出过很大的努力。
但很遗憾,这种努力在左派看来,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是党的恩赐。在右派看来,是虚假的平等,是为平等而放弃自由。
但如果从更现实的生存策略考虑,三四十年代女性当兵,与其说是“先进思想的感召”,不如说是她们没有活路,不然就不会有那么多底层女性参军。而六十年代很多女性或者黑五类的子女,义无反顾地上山下乡甚至在当地结婚,与其说是“思想幼稚”,倒不如说是为了求生存抓住的最后机会。你不能粗暴地说,她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感召或压迫,女性有她自己的主动性,有她自己为了改变命运所付出的努力。
但在评价时,不分左右,都可以只把女性当成他们进行意识形态批评的象征。
李小江还有另一本书记载了这种象征意义对女性的伤害——“强制裹脚时说不裹脚的都不是好女人,强制放脚时说不放脚的都死板封建不进步”。裹脚再放脚对女性身体的伤害,倒没有人提。
强调女权应该是“左派”或者“右派”,都忽略了女权主义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思潮,在它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中,本身就借鉴了诸多学说的观点,都是也是对既有学说的补充 。
而不分左右,都可能在他们的话语中有意或无意地进行性别歧视。无论左派右派,都不必然是女权的盟友,但无论左派右派,都可以成为女权的盟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