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紀快樂體驗券
第一幕 球場 近景
《新教要義》 3:2 真正的天國沒有國別、沒有種族、沒有性別,只有無窮盡的神性。
《新教要義》 3:19 俗世中沒有真正的國家、沒有真正的種族、沒有真正的性別,只有通往天國的大門,有德行的人才有資格進入大門,無論他是否相信神,無論神是否存在。
S與神父曾在籃球場有過一面之緣。那天上午,S打完籃球正坐在長椅上休息,躲在大樹後面的神父見到有亞洲面孔,便從樹蔭裡走出來,輕輕坐在S旁邊。
S向神父微笑致意,順便稍微打量了一下。神父的蒜頭鼻上架了一副平光眼鏡,眼睛細長,肚子搭在皮帶上,肚子下面勉強還能露出一半古馳的標誌,胸前掛著明顯生鏽的十字架,手裡提著附近超商的環保袋。
「你喜歡打籃球嗎?」神父微笑的程度很輕,讓人剛剛好覺得他不會對你圖謀不軌的程度。
「嗯,還好。」S不太願意跟陌生人講話,又不得不禮貌回應。
「你還在唸書嗎?是附近那所大學的學生嗎?」
「嗯。」
「那在念什麼科系?」
「哲學。」
「哎呀,不得了啊,哲學很難懂的。你家鄉在哪裡,那邊有什麼旅遊景點或者自然景觀什麼的嗎?」
「啊,哈哈,抱歉我忘記了。」S做過很多遍類似的結束語,有些無奈,又有些慶幸。但如此還能繼續下去的對話,至少對S來講算新奇。
「你知道喀爾文先生吧,我最近在讀他的書,你有興趣來我們的基督教聖堂參加讀書會嗎?」
S不太想順著神父的話往下說,畢竟有傳言說大學附近有不少藉宗教名義行騙的組織,就偏過頭來對神父說,「那你讀到過《基督教要義》第四卷第二章內容嗎?」
「啊哈哈,看來你真的對讀書有興趣,你對末世預言一樣感興趣嗎?要不要讀讀看我們今年自己出版的書?」隨即從環保袋裡摸出一本黑皮書,上面燙金字刻著「新教要義」,「這本送你的,回去讀一下吧,免費的。」
S身體稍稍往後傾,臉上的微笑略顯尷尬。但神父的書就快要戳到S的臉上了,S最後不得不接下來,收進書包裡。
「不然你週六過來吧,喔,就是明天,我們聖堂就在球場後面的超商旁邊,玻璃門上面有寫『基督聖堂』幾個中文字,讀書會下午兩點開始,結束後還會有免費的聖餐,有雞肉,很多很多雞肉,可以跟兄弟姊妹們一起吃。喔對了還有,讀書會的領讀員是一位漂亮妹妹,跟你一樣膚色,也是你們大學的學生,她平日還會在聖堂幫助新過來的學生學新語言、適應生活,是個心地善良的妹妹,到時候可以過來互相認識一下……」
「砰!」的一聲,突然飛過來的籃球砸在神父喋喋不休的嘴上,S藉機拿到籃球,回球場打球去了,自此,S與神父再沒見過面。
中午,教堂的鐘聲慢悠悠響起來,這對於神父的唯一意義是,午餐的時間到了。
第二幕 咖啡館 遠景
《新教要義》 2.4 說謊是為重罪。
《新教要義》 4.3 神在每一個人的心裡都留有神性,啟發這些神性的是信仰,而非教會;反對一切傳統教會形式,神不在教堂裡,神也不需要你的錢。
離開籃球場的S走向學校旁邊的咖啡館,咖啡館的位置其實並不適合開店,雖然距離學校不遠,但跟學校之間隔了一條充斥了尿騷味的小巷子。巷子裡經常整齊地蹲著幾個龐克少年,一邊談論不同醫療設備使用時的注意事項,一邊吸著手裡的大麻。偶爾會有年輕助教走進巷子跟他們搭話,但普通的學生,尤其一二年級的學弟學妹,連最初階的尿騷味都抗不住五秒鐘,更別說要在裡面張嘴講上幾句話了。
巷子最深處的牆上用漂亮的塗鴉字體噴著Orfeo ama Eury;左側牆面則用黃色油漆工工整整地刷著「公正、和平、民主、自由」幾個黃色中文字,底下歪歪扭扭刻著些「8964」的字樣,不知道誰那麼沒道德,居然敢在社會主義黃色笑話下面,對學生們開這種玩笑;右側牆面是學校的教學樓,那些街頭藝術家出於對知識的尊敬,並沒有往牆上噴塗什麼東西,反倒是這所學校裡的學生,在牆面上貼滿了小廣告:有代寫拉丁文論文的、有推交友軟體QR碼的、有賣二手書的、還有在Aula 27教室賣春的……S走進這條小巷,小巷最深處蹲著一位正在讀書的龐克青年,青年梳著雞冠頭,下嘴唇兩側打了唇釘,上身穿花襯衫,下身搭了一條橘黃色短褲。S走到他身前,拍了拍他的肩膀,等對方慢慢抬起頭,S指了指咖啡館的方向,青年隨即起身,跟S進去咖啡館。當天是他們小組織例行聚會的日子,有點像現代平民沙龍,成員裡面只有S還沒拿到博士文憑。他們八個男生坐在一起,偶而討論下學術,偶爾討論下宗教理念,但大多時候都在閒聊些有的沒的,在常人看起來,他們只是在講些違反世俗道德的宗教笑話而已。
這個自稱教會的組織很奇怪,成員們互相不知道姓名,更沒有彼此的聯絡方式,只有每週五下午定期在這個咖啡館聚會討論,他們有自己的一套神學價值觀,但即使是一套再革新過的價值觀,這個時代裡也多多少少顯得落後了。
S把書包扔在地上,點了一杯瑪奇朵咖啡,環顧了一遍四周的成員,低頭停頓了一下,說,「我們的教義被別人拿去利用了。」語氣很嚴肅,S從地上的書包裡翻出黑皮書,扔在面前的桌子上。「我中午吃飯的時候隨便翻了幾頁,他們的教義的體例是根據我去年起草那份改編的,內容也被改得面目全非。」其他成員不以為意,仍然輕聲繼續S進來前的話題,「他們有違反教義的聖堂,」剛剛蹲在巷子裡的組員跟服務生要來一盤餵鸚鵡的葵花子,自己低著頭慢慢剝,「他們還有女生領讀誦經會……」屋子裡的聲音突然降低了至少八十分貝,其他組員、除了雞冠頭的目光,都一齊投向S,表情變得跟S一樣嚴肅。雞冠頭還在剝葵花子,被旁邊了組員扇了一巴掌,目光裡好像透露出「沒出息」式的嫌棄。
仔細看書的內容,書頁左邊不知道是哪種文字,不是希伯來文也不是拉丁文,右邊則是繁簡混雜的中文,不過文法還算通順。除了S這個會講中文的,其他成員沒人讀得懂。沉默許久,一位穿白襯衫,看起來稍微年長的成員發話了,對S說,「你知道我們教團為什麼一直是地下組織嗎?」「知道,」S眼神直直地盯著地面回答道,「教團沒有女性成員,沒辦法申請成為合法組織。」「所以就像上週說的,你前任會加入我們組織嗎?」年長的成員用同樣直直的眼神盯著S。
S挪了挪屁股,兩隻手反覆搓了幾下臉,「她說開會的時候不讓滑手機她就永遠不會加入。」有幾位成員聽到這話,都瞬間癱在座位上,無助地望向天花板。「那你們呢?」S繼續說道,「還沒找到女朋友嗎?」「沒辦法,」來自東南亞的前輩插話道,「既有知識又沒錢的人,很難找女朋友的。」年長的成員翻了一個白眼,繼續說,「現在我們已經湊齊了黑人、東南亞人、亞洲人、同性戀、龐克族和腳氣病患者,只要再有一名女性成員加入就能申請合法了,但這都過去快一年了,還是沒找到。」「合法不合法的,有那麼重要嗎?」雞冠頭一邊插嘴,一邊還在低頭剝葵花子。「拿我來說吧,」年長成員嘆了口氣,「我去年原本想要出版博士論文賺點外快,但被一個有名的平權組織寄信說,她們有調查到我們的組織不合法,說如果不給她們七百萬『指導費』,出版的論文就會被她們組織公開評論為政治錯誤,一本都別想賣出去。」「那麼有影響力的組織怎麼會盯上我們這麼小的團體?」S顯得有些驚訝。
「你看到那邊的女店員了嗎?」年長成員指了指在旁邊桌偷閒、偷吃前一桌客人剩下蛋糕的女服務生,「她就是那個組織的眼線,她們的眼線到處都是,提供一則情報就能拿到十塊錢,說真的,她們要不是不收男眼線,我早就去應徵了。」
「跟你要七百萬這不是在勒索嗎?」黑人成員開口問道,據說他是法學博士。
「沒用的,她們傳過來的是合約,沒有寄信地址,連甲方乙方的部分也都是空白的,就是單純的威脅。」
「這我懂,小人物就算爆料也會被馬上刪帖,我也被威脅過,我自以為很勇敢地去網路上揭發他們,直到我媽媽的租屋被寄刀片。」那個有腳氣病的博士,講到這裡都快哭了。
「女性成員什麼的還是慢慢找吧,這也沒辦法,教義裡沒有給女性的特權,根本沒女生願意加入。」S把書塞進書包準備回家,起身的時候裝灑了雞冠頭的葵花子,害得他還要爬到地上繼續剝。話說他曾經還是這所學校最年輕的博士,後來因為檢舉自己教授學術不端,被副校長親自除名了。
第三幕 租屋 近景
被竄改過的《新教要義》 2.4 神在每一個人的心裡都留有神性,但發現這些神性的關鍵在於深刻理解教義的神職人員的引導與啟發。
《基督教要義》 3.3 悔改是信心的結果,悔改來自對神最誠懇的畏懼。
S晚上回到租屋,感覺身心俱疲,他的室友、同時也是他的前任,看到S回租屋,便問他,「你有吃晚餐嗎?」
「還沒。」S還拿對方當朋友,但就到普通朋友的程度,甚至可能只有到室友的程度,態度冷漠。
「要不要去海邊逛一下,順便晚上去外面吃,郵局附近那間你喜歡的披薩店。」
「不了,晚上還要讀書。」
「呵,笑死,你還真以為你能當成哲學家啊。」
「嗯,可以的。」S回答的時候頭也懶得抬,在餐桌上整理自己書包裡散落的筆記,好像順便還在想些其他事情。
「你以為社會還需要哲學家嗎?」很奇怪的是,S前任的語氣聽不出絲毫輕蔑的態度,反倒夾雜了不少違和的失落感。
「社會本來就不需要哲學家啊,歷史才需要哲學家。」
「所以認真做哲學的都窮光蛋根本就是活該囉?」
「嗯,既有知識又有錢,不會很不公平嗎?」
他前任對S的冥頑不靈顯得有些生氣,拿起餐桌上十幾年前流行過的Pinko果凍包,想要自己出門吃飯。出門前回頭對S說,「喔對了,你家寶貝貓中午又吐了,快去擦了吧。」
「呵,『我家』,當初是誰堅持要養?」
「笑死,我要養也不會養那麼醜的。」
S的前任摔門離開,S拿起餐桌上的廚房紙,去房間裡找貓的嘔吐物。打算等一下簡單煎幾片吐司吃。
他們養的是一隻深灰色的俄羅斯短毛貓,原本兩個人每天給貓梳毛,身上看起來沒現在那麼髒。但兩人分手後,只有S一個人打理貓的生活起居,灰貓的毛看起來很髒,還因為壓抑的氣氛時常嘔吐。S有時候會覺得,也許他前任當初每天抱著貓、親貓、叫貓「寶貝」的時候,只是把牠當作維繫兩人關係的工具而已。雖然所有棄養貓的人,嘴上都會說貓是無辜的,但當這些被稱為「寵物」的東西失去原本價值的時候,還有多少人願意不求回報地付出呢?一群連契約都懶得遵守的人,又怎麼會在意連承諾都沒有的責任?那麼其實對於S來說,他們的分手也同樣是注定的,沒什麼好可惜,只是原本的那些快樂,就好像是他自己沉浸在一齣戲劇裡想像出來的。S不得不承認在這齣戲劇裡得到的快樂,又不得不將自己從戲劇中剝離,站在觀眾席嘲笑自己的醜態,他從小到大一副無欲無求的撲克臉,並不是因為天生不懂快樂,只是湊巧看到了舞台上的自己而已。
S就坐在灰貓的嘔吐物旁,摸著紙箱裡的貓,想起這些好笑的事,假裝自己是海德格筆下非本真的存在,這樣一來,就能在安寧中享受當自己異化為自己觀眾時的樂趣。灰貓卻怕到不行,眼神就像一個舊傷尚未痊癒的奴隸,又怕被打,又怕被放棄。如果貓曾有一瞬間認同自己是這個家庭的成員,不知道此刻會不會對自己的政治身分產生些許懷疑。又或許是因為政府也從未關心過這些間接稅務貢獻者的身分,貓自己就更不需要關心了,或許牠們也在享受著觀看自己被當成「寵物」時的樣子。這恐怕是一則當代政治迷因:既然飼主並不是貓自己選擇的,那貓還有什麼理由關心自己的政治身分呢?
S站起身,最後還是忘記擦掉嘔吐物,也有可能是故意的,想讓貓像自己一樣,也沉浸在自己的角色中。
S在次走進廚房,在一個盤子裡打散兩顆雞蛋,在另一個盤子裡倒一點鮮牛奶,打開電磁爐,切一塊黃油跟一匙橄欖油一起在平底鍋裡燒熱,取出兩片吐司,兩片都只有一面蘸上牛奶,再把蘸有牛奶的一面疊到一起,最後把麵包外面沾滿蛋液放進鍋裡煎。才剛煎到第三片,S的前任開門進屋了。
「天吶,怎麼又弄這麼多煙,煩死了。我在你們學校旁邊的中餐館買了滷豬腳,要不要一起吃?」
S沒回答,繼續煎他的吐司,直到把所有蛋液用完,收起剩下的吐司,才在飯桌前坐下,此時他前任已經吃完一整隻豬腳了。
「你可不可以不要板著一張臭臉,我有做錯什麼惹你生氣了嗎?」前任似乎早已習慣、又不滿這張撲克臉了。
「妳沒做錯啊,我在想事情。」S也習慣這種回答了。
「你為什麼不讓我去你們教會的活動?」顯然,S在咖啡館說謊了。
「妳又不信。」
「你們不合法真的沒問題嗎?」
「合法後,我們討論的內容會改變嗎?」S對一切基於政治的合法,向來漠不關心。
「你真的相信神存在嗎?」前任並不擔心S會嫌她的問題俗氣。
「神存不存在跟我要不要信仰祂,兩件事沒關係。只有神能證明祂自己的存在。」
「你口中的『祂』,連快樂都忘記給你。你知道快樂是什麼嗎?」
這句話讓S愣住了一下,不知道是在努力回憶自己是否真正擁有過快樂,還是在懷疑神早就拋棄了自己。
「我問你,」前任打斷了S的思考,「你為什麼每天花這麼長時間讀書?會快樂嗎?能讓你賺到錢嗎?」
「都不會,我總覺得像是使命或者工作。不讀書就會變得不擅長思考,就會變得體會不到自己存在的意義。」S邊講話邊搓弄手中的面紙,直到面紙皺到沒辦法再拿來擦嘴。
「工作?呿,能賺錢的才叫工作吧?」
「那只是社會為了保證稅收才下的定義吧。」
「沒有錢你拿什麼吃飯?」
「重要嗎?」S重新展開手裡的面紙,好讓它繼續履行完自己的義務。
「不重要嗎?」
「妳每天花費的時間,只是想讓自己活得更好。」S也似乎早已習慣,又忍受已久。
「你以為我為了誰?除了我還有誰能接受你這種人?」
「一邊接納反時代的我,一邊又為這樣的時代焦慮。這樣的妳為我做的事情裡,會有我想要的嗎?反倒是妳,以『為了我』的名義塞給我我不需要的東西,妳快樂嗎?」
「呵,不然你要我做什麼?不然我還能做什麼?要是有下輩子,我不想再當人了,這樣的爛世界……」
「說真的,妳丟掉手機,妳眼裡的世界馬上會變美好,妳只是每天被埋沒在一大堆沒用的資訊裡才這樣。」
「丟掉手機那些事就不發生了嗎?是平民不會因為戰爭死掉?還是窮人不會因為分配不均挨餓?呵,這樣的世界還是快毀滅了吧。」前任的情緒開始變得愈發激動。
「毀滅的話,對那些覺得自己幸福的人不公平。」
「所以我才是想死掉的那個,不是你。」
「妳不是想死掉,妳只是想讓別人變得跟妳一樣不幸。」
「快樂原本就不屬於我,神給了我快樂,只是重新回收了,我還是賺到,從我的神那裡。」第二天中午,前任以為S一直躲在房間裡沒出來,但推門進房間,只看到這張只有三句話的字條。其中第二句是:「請幫我把藏書掛到二手書市上,這樣也方便妳找到跟我讀書品味相似的人。」
第四幕 聖堂 遠景—近景
《新教要義》 1.15 不可自殺,自殺是為對神的背棄。
《新教要義》 2.8 十誡是人心中律法的原則,以此約束自己,使自己配得上聖靈的恩典;但不可以此約束他人,因為每個人都有不信仰神的自由。
《基督教要義》 3.7 基督教自我否定之哲學:我們不屬於自己,乃屬神;我們屬於神,我們並不是自己的主人。
五年後的一個週六,聖堂的例行讀書會剛剛結束,距離聖餐還有一段時間,領讀的女同學因為下午要去便利店做兼職,讀書會一結束就離開了。能談心的人離開,讓百無聊賴的神父想給自己找點事情做,他先跑去禱告室坐下,過了十幾分鐘又跑去懺悔室坐下。「都什麼年代了,還哪有人要懺悔啊,人人都自由,人人都沒有自由,誰都覺得自己有能力主宰自己,結果到最後全都隨波逐流,被社會主宰,被政治主宰,被有錢人主宰。真的是,自由的人沒有罪,也沒有自由。」神父像是在對自己懺悔,又像是想起自己還有信奉的神,開始突然對神抱怨。「好在大家假裝行善的心還在,不然我連每個月的汽油錢都付不出來。」神父坐在懺悔室的小椅子上,瞪大雙眼苦笑,嘲笑自己反倒是那個最信仰神的人。「哎,我記得七八年前好像在倉庫大門旁邊釘了一個懺悔箱,這麼多年一直忘記打開,雖然說這個年代沒人會有心思懺悔,但總歸還是要去碰碰運氣吧,一旦蒙受聖靈的垂憐,讓我充實地度過這幾個小時呢!」神父一邊咕噥著「聖靈垂憐」,一邊朝倉庫方向走過去。倉庫在後門的巷子裡,神父要帶著自己一身贅肉穿過整個聖堂,可見神父想要讀到別人懺悔文章的意志有多堅定!
後門的巷子大約只有兩公尺寬,兩側堆了些垃圾,車子大概沒辦法通過。聖堂的後門,旁貼滿了傳教用的宣傳單。後門上面突出來大約半公尺左右的樣子,這樣好在下雨的時候提供一個能遮雨的去處,讓那些臨時過來避雨的路人,能順便多瞟上幾眼寫滿賣慘故事的傳單,也好給自己增加一點額外收入。
後門正對的才是倉庫門,兩扇棕紅色的木門,下半部分用鉚釘鑲上了兩塊鐵板,門檻的地方用厚鋼板墊高了十幾公分,防止下雨時積水流進倉庫。倉庫四周的窗都被鐵板封住,沒幾個人有幸見過裡面的樣子,甚至沒多少人見過這兩扇門打開的樣子,有傳言說木門後面還有兩扇防盜大門,也有人說倉庫有通往聖堂的地下入口,看起來神父根本就不擔心人們猜到這裡面放了什麼寶貝東西。
等到神父拖著比五年前更大的肚子,終於走到倉庫門前時,才想起來自己忘記七年前把懺悔箱的鑰匙隨手丟到哪裡了,可能扔在哪個保存機密文件的保險櫃裡、可能埋在哪個種罌粟的花盆裡、也可能是跟女同學談心的時候隨手扔進了地下室……這麼大一間聖堂,根本別想找到。但神父畢竟拖著大肚子走了這麼遠,不甘心就這樣空手回去,難道要他重新回去懺悔室,懺悔自己當初亂丟鑰匙的惡行嗎?「呵,以神的名義,我可不能因為一把鑰匙就辜負了這些向神真誠懺悔的兄弟姊妹!」神父在附近的垃圾裡找了一圈,找到一根受潮的厚木板,他本來想要用這些木板雕幾把日式打刀,但自從把買回來的木工工具丟進倉庫後,就再沒有過做刀的動力了。幸好當天沒找到鑰匙,否則這些木板永遠都沒辦法實現它們被砍下來的價值了!
神父把木板從懺悔箱的投遞口塞進去,用力一蹺就把鐵皮箱子蹺變形了,還好當初沒用什麼品質太好的材料。神父伸自己的胖手進去摸,蜘蛛網、嚼過的口香糖、破掉的避孕套、雜草、鴿子蛋……接連摸到這些東西的神父,絲毫沒有要放棄的意思,他不相信現代、或者說住在這附近的人類,全都已經失去自我否定的哲學能力了。終於,當他幾乎伸進去整個小臂後,終於在底下摸到幾張濕漉漉的影印紙,神父在那一瞬間,眼前像迸發出了聖光,讓他接下來兩個小時的人生充滿了希望,至少是作為一名神職人員的希望。
「嘖,這故事,通篇流水帳對話,沒什麼故事性,更別提文學性,有幾句哲學反思倒算是亮點。」神父把這一疊紙帶回辦公室讀了幾遍,但好像並沒有很喜歡上面的故事,「就是開頭寫的那個神父,怎麼好像在哪裡見過,應該是這附近的同行沒錯,哈哈,就只有這個人物個性還滿出彩的。」神父無意間作為自己的觀眾,誇獎了自己一番。「至於裡面引用的《新教要義》嘛,應該是按照我幾年前出版的那本《要義》改編的,看來是我忠實的讀者呢!」此刻神父的自豪感已經衝到他稀疏的頭髮上了!「但真要說情節嘛,最後S留下那麼短一張遺書雖然是挺有反差感的,但是S自殺的動機是什麼?沒活路了?分手?憂鬱症?嘖,動機不明確,雖然很像真的,但一點都不文學,不好不好。況且又是這類看起來是在做真實記錄的文章,如果沒有明確給說謊的地方留下標記,那它在符號學意義上的真實性就不成立。但怎麼說呢,像這樣在流水帳裡塞上一兩句有些許哲理的話,整篇丟掉也還是滿可惜的。唉……封皮上只寫了S,連標題都沒,更別提什麼地址了,連退稿都沒辦法退。」神父已經沉浸在一個專門做文學批評的編輯的角色中了,畢竟只是讀文章的話,僅僅只能打發掉半個小時的時間。「但反過來講,如果讓我寫這樣一篇故事,恐怕也要用上一個禮拜,這人文筆也還算通順,那倒不如……利用這幾頁紙做點善事吧,畢竟這世上窮苦的人那麼多,少了我一個也算是給世界慈善事業做一點小貢獻了。」
過了一週,神父把S的故事印在了一本紅色小冊子上,標題很俗套,叫《一名憂鬱症患者的自白》,當然,小冊子本身是免費的,但不能免俗的是,進入聖堂的長條桌子上,除了左邊擺放的小冊子,中間還擺了一隻紅色不透明的慈善箱,右邊則擺了一疊硬紙板,紙板上印有「二十一世紀快樂體驗券」的字樣。入口處的展示台上擺滿了關愛憂鬱症患者的宣傳單。這些傳單先拖住進入聖堂的人,要他們關注憂鬱症患者,再用左邊的小冊子告訴這個群體有多可憐,當人們發善心的時候,「恰好」又可以在桌子最醒目的地方,找到自己可以實踐善心的地方,至於快樂體驗券,只是一個恰到好處的補充,一邊可以讓真正患有憂鬱症的人,能帶走一個可以撫慰自己心靈的東西;一邊可以讓沒有憂鬱症的人意識到,這場活動完全沒有要騙信眾錢的意圖,而是實在地拿出了精神上的慰藉。在信徒們看來,這真的已經是世間最溫暖的印刷品了!
小冊子背面印著S字條上最後一句話:「我不知道快樂是什麼,但正因如此,我希望世人能得到它。」
很諷刺。
第五幕 讚美詩 近景—遠景
《基督教要義》 3.9 神藉磨難減少我們對現世過度的愛。
那個晚上,S在電腦上整理了自己最後一天發生的故事,留下了那張字條。把自己所有筆記、那些唯一有機會讓他成為哲學家的希望,像維根斯坦上戰場時一樣帶在身上,不同的是,S並沒有想要平安回來的願望。他背起自己滿書包筆記,把鑰匙、手機、錢夾全都扔在床上,把那本免費的黑皮書塞進書堆裡,給貓倒滿水、糧、貓砂,在凌晨悄悄出門。一直等到早上有影印店開門,進去在櫃檯上數出幾枚硬幣,把故事影印出來。到了中午教堂響鐘的時間,S則繞著聖堂徘徊了一圈又一圈,路人只以為他是想要數清地磚數目的奇怪遊客,沒人會放在心上,畢竟在這個時代,當看到一個我行我素的路人時,不會上前獻出多餘的關心,才是對那個獨立個性的最大尊重。
那天是週六,學校也幾乎沒課,不用擔心會碰到假期一定要遠離學校的同學。
S一直都在猶豫,但又實在想不出更值得信任的人,假使給了他那位前任,恐怕她連讀都不會讀就幫他全數燒掉了。願意花時間讀這種沒名氣作品的,很不幸,可能只有神父一人了。
至於為什麼最終選擇相信神父呢?儘管只有一面之緣,但神父可能是他所有見過的人裡面,最誠實的一個吧。
只是S不可能猜到,這份稿件直到五年後才會被讀到。
S背著重書包,自己往遠處的山里走,或許像臨死前的野貓一樣,躲到一處沒人能發現的地方;又或許扔下了背包,改名換姓用另一個身分在另一處很遠的地方活下去。但說到底,活在這座城市,或者無論哪座城市,城市都好像從未存在過一樣:不明所以的遊客對著沒有歷史的建築不斷拍照,在社交軟體上標記現代式的「到此一遊」;我們都有各式各樣政治上的身分認同,卻永遠缺失人本質上的認同;享受著各種自由,卻處處受到別人自由的壓迫。S接納了這個時代的浮躁,但時代卻很討厭他,讓他沒有身分、沒有標籤地在世界上遊蕩。或許是宿命使然,因為物慾與精神層面的需求一直難以相容;又或許是S自己無奈的選擇,因為精神需求原本就是對物慾不滿足的妥協。
一直到上週六我才讀到這個故事,花一週時間慢慢把故事梳理出來,雖然中間有加入我想像的部分。不過說真的,現代人講話我向來半信半疑,或著乾脆只信一半,畢竟說謊的成本太低,那好不容易留下的東西,會沒有一點「修飾」在嗎?人們更願意讓別人看到自己光鮮亮麗的一面、隱藏起自己見不得人的部分不是嗎?
拿到這本小冊子也是機緣巧合,本來聽學姊說,只要週六下午在這邊聽三個小時課,就會有一頓免費的雞肉晚餐可以吃。剛一走進聖堂玻璃大門的時候還沒有很適應,感覺自己好像為了幾顆免費雞蛋就去聽直銷講座的阿姨阿伯,但轉念又想,依照我的飯量,進去坐這三個小時也比在旁邊超商打工好賺,況且我這樣人生地不熟的,跟學姊打好關係也方便以後生活。
那天跟學姊一起走進大禱告室,剛進門左手邊的展示架上,歪歪斜斜擺了幾張皺掉的宣傳單,往前走一點,撲面而來的紅色大箱子著實有點嚇到我了,我向來排斥這些,好像他們把箱子放在你的鼻子前面,告訴你「應該」捐錢一樣。慈善箱左邊堆著幾本小冊子,右邊放的就是那一沓「快樂體驗券」,做工很精細,紙板四周描上了復古的中世紀花紋,上面印的十幾個中文字看起來也像是精心設計過的,並不是網路上隨便就能找到的尋常字體,仔細看發行單位一欄下面,還有小小的一行「唯獨因信稱義」,翻倒紙板背面則描畫著一個精美的棕紅色十字架,上面沒有耶穌的肖像,更沒有S的肖像。我本想拿一張回去當作藝術品擺設,但苦於沒有捐錢進去,想拿又不太好意思拿,畢竟還有不少比我更需要這張紙板的失樂者。
學姊似乎看出了我的尷尬,但或許是以為我忘記帶錢,就轉頭對我說,「哎呀,第一次來不用考慮捐款的事,這些都是自願的,這裡的兄弟姊妹都很隨和的,更何況你一個初來乍到的學生,也沒什麼錢。跟我進來吧,找一個前排的座位。」邊說著,隨手扔進箱子幾枚硬幣。「那……我能拿一本小冊子嗎?我還滿好奇裡面內容的,畢竟我過來念心理系……」
「哎呀,拿拿拿,」學姊自己拿起一本小冊子跟一張體驗券塞給我,「又不要錢,不拿白不拿。」
我們到場的時間有些提前,但教徒們已經整整齊齊坐好了,緊閉雙眼,兩隻手舉過頭頂,像是在對最前面黑板上的十字架祈禱著什麼。祈禱室四周乾乾淨淨,沒有肖像、掛軸之類的東西,前面也只有黑板跟黑板正上方的漆黑色十字架。
「喔對了,」學姊打斷了我的觀察,小聲跟我說,「今天誦經的那位姊姊可能沒辦法過來了,如果是那個胖神父的話,應該會帶大家唱讚美詩,你坐在旁邊聽就好,也不用張嘴。反正過三個小時就能填飽肚子了,也不虧。」
那個當下,我突然意識到學姊既世俗又脫離世俗的撕裂感,開始讓我有些反胃了。
過了不久,胖神父走到黑板前,環顧下四周,好像沒太注意到我這個生面孔,又或許所有人對他而言都算生面孔。他打開歌譜,領唱讚美詩,替死掉的S唱的那首、至少在名義上獻給神的讚美詩:
「前有一日,我意立定,靠託救主救我靈魂;
那時心中,實在高興,四方週圍,宣揚主恩。快樂日,快樂日,救主洗淨我眾罪孽!
心裡清亮,極大歡喜,這日永遠不能忘記;
快樂日,快樂日,救主洗淨我眾罪孽!」「如今離開世俗憂悶,救主教我出死入生;
天國榮耀,我有一分,這樣好處誰能講明!快樂日,快樂日,救主洗淨我眾罪孽!
心裡清亮,極大歡喜,這日永遠不能忘記;
快樂日,快樂日,救主洗淨我眾罪孽!」
—O happy day, that fixed my choice
Philip Doddridge (1755)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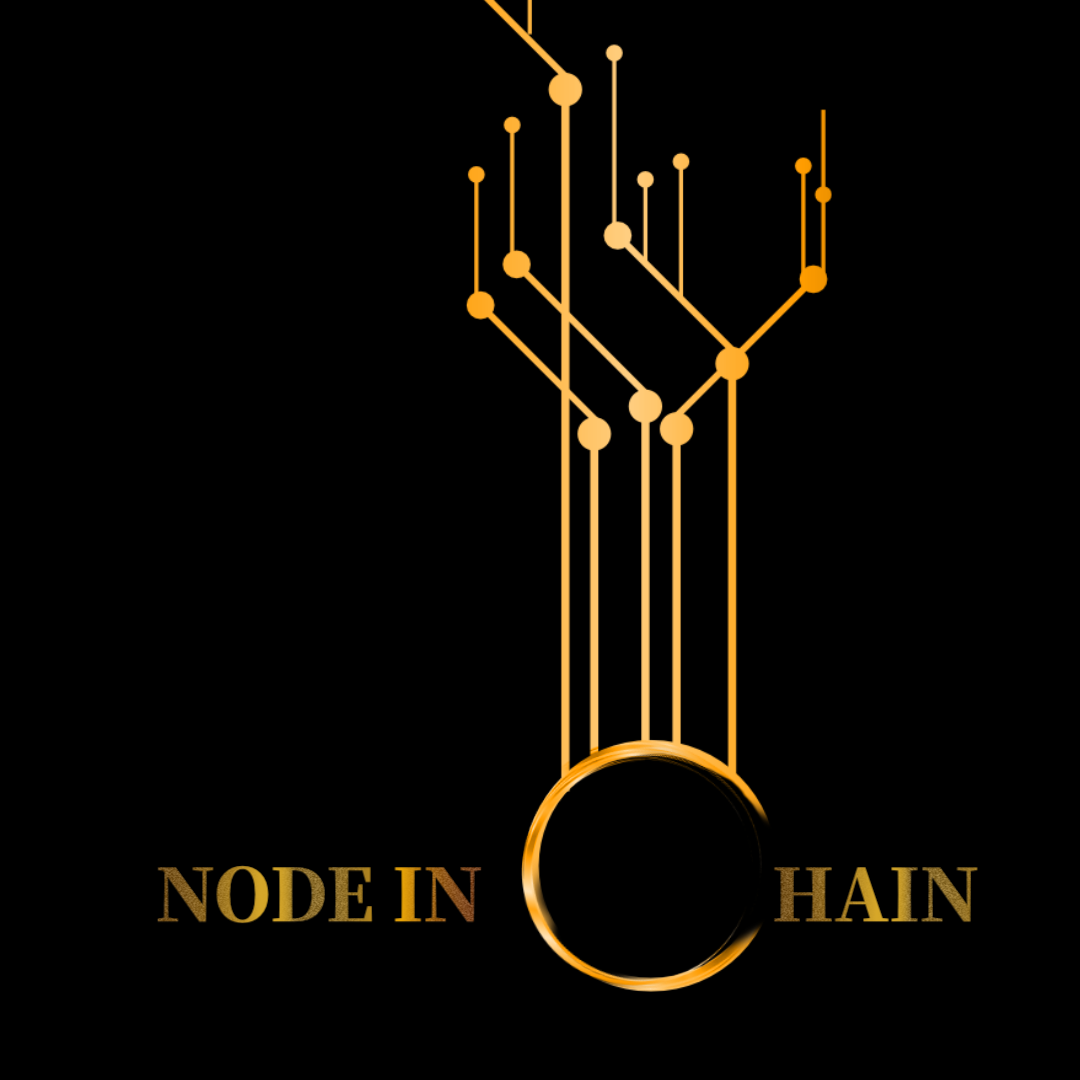
- 选集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