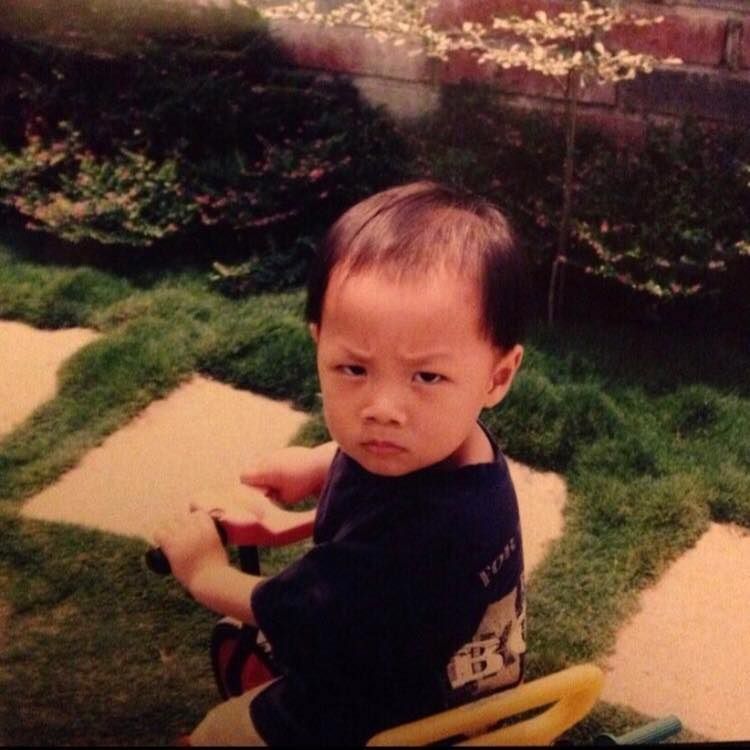洗衣店
「你們先去買早餐,25分鐘之後再回來⋯⋯」
一位父親對著兒女碎念,那是一對高挑的兄妹,掛著口罩,兩個都長髮,頹頹的。一個穿著花襯衫、花襯衫、黑長褲、老式金絲眼鏡,一頭捲髮。另一個走粉紅路線,放大片、波浪捲、方格長褲,和他的哥哥一樣不知道是不夠用心,還是約好一起穿了雙藍白拖。在洗衣店裡頭,他們把棉被丟進去後就站在洗衣機前頭低頭滑手機,在騎樓蔭下等著父親的下一步規劃。對面就是一間早餐店,看上去很熱鬧,他們的臉上總是掛著笑容,包含作客的與作東的,但是蛋餅的麵皮很厚,吐司的肉排很薄,醬油膏是還有甘甜,不過加了水。吉祥話遍佈、恭喜聲此起彼落,付帳時皮肉都笑,沈浸回網路世界或是踏入網路上量子力學的討論後,臉就垮了下來。
洗衣機持續地轉。人們的肌膚漸漸透紅,紅得幾乎要與牆上的片片朱紅融合在一起,使人分不清楚這裡到底是擁擠,還是寬敞。這裡的早晚溫差很大,過了早上十點之後街上盡是輕薄衣袖,而到了下午五點,大家的外套就從包包裡、臂彎裡、機車的置物箱裡被拿了出來,像是這裡四周不靠海,雨量不豐沛一樣,早有早的冷,午有午的熱——
幾乎家家戶戶都是這個樣子的,除了一些去吃早餐的家庭。這一天不需要上班,不需要上課,也不需要早起,幾乎不需要去想到底要忙什麼事情,趁著好天氣,趕快將家裡的被子、衣物、襪子內褲、胸罩、枕頭床單拿出來,找到附近一間洗衣店,盡可能塞進洗衣機,把洗衣粉窮一窮,從口袋裡掏出40塊,看了一看,餵進去。跟免費的陽光躲躲藏藏,呆滯的看著運轉的機器。
那種漩渦是吸引人的,雖然比不上人類圖,也不比對著鏡頭講話的人們,但大腦就是可以透過旋轉的東西迫使自己說服自己就是在轉動。他們可能在想著自己的人生,可能在想著自己的男女朋友,或者是某個AV女優⋯⋯也可能什麼都不想,就是看著鎖住軸心的螺絲釘。這樣很哲學對不對?藉由一些物件的轉動、輪流、遞迴,來幫助自己腦袋瓜裡沒想過的某一個小角落揚起一些灰塵,看了一看這些已經斑駁的物件,來體會人生。就像是佛家講的宗因喻:我有一個主張,我有一個理由,我有一個比喻,光是聽那個比喻彷彿就可以理解全部,並且好合理。從這裡到那裡,好順暢,無論是從鍵盤上的A到Z,還是從你的肛門到你的馬眼,更或者是從自然療法到西方醫學。他們就是盯著這個漩渦看,然後看看數字,累了就看看禁止帶寵物或禁止洗鞋這樣的告示,最後低頭滑手機,接著,又在某一個理性之光照進腦門的時候,抬頭看看洗衣機。
但有一個人的眼神更為無奈,看上去,對於那些轉動的東西一點興趣都沒有,他在想的可能比尼采更為深層,又或許比黑格爾更遠離絕對精神。雙手插口袋,身上有兩件大外套,鬆垮垮的長褲,破洞的布鞋,垂到幾乎鼻頭的眼鏡,幾天沒洗的頭,掛在脖子上的頭巾。他的衣物已經在烘衣機裡面,而且已經在烘衣機前足足站了20分鐘,沒有抓癢,沒有走動,沒有推眼鏡,就連店內人員要為桌椅消毒、掃拖地板時,他都無動於衷,當其他人被打斷關於人生的所有思考,並浮現一些故事的時候,他就是硬邦邦的站在那裡,盯著前面,不發一語。
「先生⋯⋯不好意思⋯⋯」
「⋯⋯」
「先生,先生?不好意思內讓我拖一下地板。」
「⋯⋯」
他斜眼看了店內人員,然後緩慢地將眼球移回原本的位置,沒有要讓步的意思。
「不好意思,可以讓我們拖一下地板嗎?移動一下就好了。」
「弟弟啊,你就讓一下嘛,往旁邊站個幾步而已,不要這樣歹逗陣。」
一個中年男子不耐煩的抬頭加入店內人員的行列,舉起右手指指點點加強語氣,左手上手機的皮套晃啊晃的。這個時候店裡的其他人也回頭看看這樣的對峙,有的人瀏海不整不齊,有的人穿著睡衣,有的人咋舌,有的人搖搖頭。
「⋯⋯」
這個人還是沒有什麼回應。甚至連眼睛都不眨一下。店內人員頗為無奈,只好拿著拖把一步一步逼近他的左右腳兩邊的空間,然後是盡可能地延伸到他前後的地面,最後在他面前彎下腰,拖了他雙腳中間的區域,店內就剩下這位年輕人鞋底下的地板還沒清潔。
「現在的年輕人就是這樣,家裡的長輩都沒教你是不是?」
中年男子逼近他,指著他的鼻子訓斥了起來。這一訓斥就是好幾分鐘。漸漸的,外頭是熱情的互相招呼與祝賀,店內是一股沈默對著一串數落,大部分的人還是回頭做著他們自己的事情,想著他們自己的人生,掛念自己在外頭沒有回來的家人,發著自己的呆。店內人員也就只是被長輩抓來幫忙的青少年而已,不太願意正面對決的,但也不想跟那位中年男子說好了好了,沒關係,等等他離開再拖就好,所幸放任不管,把拖把換了水,準備繼續處理店外的騎樓地面。
「⋯⋯」
被訓斥的年輕人看著中年男子的眼睛,把滑落鼻頭的眼鏡推上鼻樑。那名中年男子的眼睛混濁,眼角有顆痣,虎牙沒有矯正,牙齦帶點黑。橫條紋polo衫和休閒短褲,幾近小腿的灰色長襪與醜醜的涼鞋,還有爆著青筋的小腿肌,頭髮已經帶了不少白,戴的應該是接近二三十年前的老式方框眼鏡,肚子已經突出來,手機上的字被放大了不知道幾倍。他或許以自己的孩子為傲,並自豪自己的教育方式:孩子們在青少年時期碰上資訊爆炸,並存活了下來,唸到不錯的大學,用創業賺到錢,用股票滾到錢,規劃結婚,有房有車,小孩也在路上,包了大包給自己老爸老媽,就等著給他們抱孫。如此歷練讓將成阿公的中年男子滿意,以致在遇到不像樣的年輕人時,他能夠有一根又大又粗的棒子,當頭棒喝。
他移動了,看起來是中年男子贏得了這場對峙。中年男子扣上手機皮套的磁扣,並笑瞇瞇坐下,跟店內的妹妹說下次遇到這種客人就應該要硬起來才對,不要讓對方繼續可惡下去,如果沒辦法達成目的,下次就叫他來,讓他來教訓這些不知好歹的廢物,他就住在對面而已。店內人員微微笑笑跟中年男子點點頭,隨即舉起拖把往門外走去。店內恢復平靜,人們的鼻腔再度充滿柔軟精與靜電紙的馨香,太陽又更放艷了一些。因為太熱,店裡開了冷氣,把落地玻璃門關起來。那像一個巨大的螢幕,鏡頭固定,構圖清晰,有時還倒映後方車輛經過的畫面,角落有幾隻電風扇,還有向內收縮的一排洗衣機和一排烘衣機。那位年輕人想找個好位置坐下,一連移動了四、五台機車,把每一台都喬了個很奇怪的角度,然後把腳放在一台車的左手把和另一台車的右手把上,點起了一根菸,鞋底黏著一張爛掉的衛生紙,還有已經凝固、變成黑色的口香糖。這個場景就像是在致敬老美國的電影院,人人可以在院內叼著一根鴻運牌香菸,與香甜可口的女人並肩欣賞由愛迪生催生出的新藝術,煙霧瀰漫下可以找個氣氛對的機會,隔著白手套握住對方,並小聲地調著情,把眼神從欣賞新藝術轉到永遠不敗的酥胸小露,以及女人豐厚鮮紅的嘴唇、眼角的痣、四周昏暗仍然翠綠的眼神、向內彎的髮尾以及作為征服男人最後一根稻草的向著胸膛靠近的肩膀。然而這種迷濛,只要燈光一打開,留下的除了那些令人咬唇的氣味,就是散落一地的煙灰,塞在椅縫的煙蒂,被燙出好幾個洞的座椅,以及刺激人們口鼻與手指的二手菸臭。焦油很難清洗,天花板也會從潔白被熏出坑坑黃洞,活像個鐘乳石洞,不像文明的象徵。電影結束後人們湧去喝酒助興,徒留清潔人員,撿著一根一根的煙蒂,掃著一片一片的煙灰,久而久之痠痛、關節炎、駝背,還永遠無法躋身他們曾服務過並留下一堆爛攤子的上流社會。
那名年輕人看了看天花板,並把煙灰彈在騎樓的地板上。身旁沒有女人,電影也早就不是新藝術,反而常常被當作就是比較長的吉祥話的影音版;但是彎著腰打掃的人倒是沒變,他們還是天天到洗衣店報到,掃著被踩扁的煙蒂和影響美觀的煙灰。店內人員有點無奈,因為這個年輕人就是自顧自地一根一根的點,左邊彈完換右邊,前面彈完換後面,煙蒂就丟到地上,也不踩熄。在他周圍的騎樓地板大多已經掃拖過,但在辛勞與汗水之後,髒亂是不問過程的,他們就是這麼的以小博大,像是養一個人要幾十年,這個人要死掉並讓一切付諸流水可能只需要一瞬間,無論這個人的頭腦與心靈可能就是下一個改變歷史的孔恩。從移動機車造成的噪音開始,店內的中年男子又開始注意這名年輕人,一路看著他抬起腳,彈煙灰,丟煙蒂,並且同樣面無表情地盯著前方,並忽略在打掃的清潔人員,終於又再度受不了,燃起一把怒火,心裡想好了好幾套教訓的說詞與羞辱套式,拉開玻璃大門,走向那位年輕人。
「你他媽的到底是怎樣?牟操牟洨,幹你娘毋成囝!」
「⋯⋯」
「講話是不會應是不是?大過年的逼我這樣罵人,欠教訓,你家是在哪,叫你爸媽來!」
「⋯⋯」
跟上一次對峙的情況相同,年輕人沒有回應,只是緩緩地移動眼球,然後對前方吐菸。剩下的動作也沒有差別:彈煙灰,丟菸屁股,坐得東倒西歪,面無表情的聽中年男子問候祖宗十八代。中年男子見指著鼻頭罵也沒有用,便動手捏著年輕人的臉頰,逼他的正臉面向自己罵到口水都噴出來的嘴,甚至將手伸進口袋要找年輕人的手機,應該是要打電話給他的父母吧。
「幹你毋成囝,手機咧?手機咧?幹拿出來啊⋯⋯你娘級掰咧參手機仔都沒帶,幹身分證拿出來,恁爸看你住哪裡!」
「⋯⋯」
年輕人依然默不做聲。當然,中年男子翻遍了他的口袋也沒找到任何一張證件,這令他更惱怒了。這可能是頭一次遇到不吭一聲的毋成囝,越想越生氣,一巴掌就打在年輕人的臉上,應掌倒地,一屁股坐著的機車也遭受牽連,連帶的那些奇怪角度的其他機車也無一倖免。不過,沒有人去管那些機車,他把年輕人從機車夾縫中拽了出來,卻發現有些困難:也許是老了沒有力氣,又或許是年輕人的腳被死死壓在那幾台125的機車下。店內人員見狀放下拖把,連忙出來阻止繼續惡化的爭執。
「先生沒關係啦,我晚點再來拖地就好了,這樣其他人機車也倒光了,沒關係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你們這些妹妹不懂,這種人就是要痛打一頓,沒見過棺材不知道害怕!我幹恁娘,其他人都沒有教你是不是,我看你這種垃圾草應該要發的比我高了,幹!」
中年男子甩開上前阻止的店內人員,其他顧客也緩緩走出來看,接下來就是一頓拳打腳踢,甚至捲起袖子,跪在地上,手心、手臂、拳頭、手肘⋯⋯都打在年輕人的臉上。年輕人的眼角是泛起了淚,但是他絲毫沒有抵抗,只是摸著自己的右大腿。接著,中年男子抓緊年輕人的胳膊,使力一拉把它給拉了出來,結果那條鬆垮垮的長褲沒有跟著脫離機車堆,一起出來的只有半脫的內褲,受傷的右腿,還有一隻滿是污垢與爛瘡的腳。
「幹,不只沒受教育,還骯髒。這種人一輩子撿角,洗什麼衣服?幹!」
見狀,他也停止了拳腳相向。甩了甩手,表達了嫌惡與後悔,這麼髒的一副身體,自己甚至還跪下了、接觸了⋯⋯越想越是噁心,便吐了一口口水,走到樑柱旁叫店內人員拿出水龍頭的鎖讓自己洗手。那裡路面算是平坦,水在地上擴散,一波一波的幾乎要碰到那名年輕人。他臉上的眼鏡已經碎裂,臉頰也留下了一絲絲鮮血,但他是否疼痛沒有人知道,至少,他沒有任何反應。就在水將要碰到年輕人時,他坐了起來,摸了摸自己的下巴,放任內褲與外套的邊緣被水沾濕,然後機械式地移動視線,打量著自己身上的傷。
「先生,還好嗎?要不要幫你叫救護車?」一些顧客遠遠地問他。
「⋯⋯不用。」
「幹?關心仨小?應該死好,最好是去死一死。」
「先生,是你動手打人的欸,他再怎麼樣惡劣都不應該這樣子打他!快點幫他叫救護車,血越流越多了!」
「現在是怪我?恁爸在導正風氣!在教育這個失敗品!幹恁娘咧好心被雷親,一群垃圾。」
中年男子氣呼呼的走了,掉頭的路上,從腰間取出手機、打開皮套、對著電話碎念一些語句,抱怨著今天的事情,並帶著拜託的語法,似乎是要繼續處理這些事情。然而,年輕人除了剛剛開口說出今天的第一句話,動作也加快了(縱使還是極為緩慢):他一台一台的把機車扶正,立好中柱,嘗試某除車上的血跡,但是臉上和頭部的血液不斷滴落,他就一直擦、一直擦、一直擦⋯⋯但怎麼樣也都擦不掉,血跡反而越抹越暈開。那條破爛內褲在走動中從他雙腿滑落,顧客和店內人員也遮上眼睛,不願意看見接下來還會發生什麼事情。年輕人把外套脫下來,折好,放在店內的桌上,四周環視了一下,最後決定拿起其中一件已經折好的外套,拎著衣袖,外套的其他部分就拖在地板上,踏著蹣跚步伐走向那台血跡最多的車,然後擦了起來。接下來他花了整整十五分鐘,徹徹底底把血跡抹乾淨,一台接著一台。
「先生⋯⋯救護車等等就到了⋯⋯你先坐著休息一下⋯⋯」
一個男性用有點顫抖的語氣,拍了拍年輕人的肩膀,希望他先休息,再來處理其他事情。年輕人轉頭看了看他,渙散的眼神仍然,丟下那件沾著血跡的外套,用與幾十分鐘前相同的姿勢坐在那些機車上,點起一根菸,抽了兩口,就把煙熄在自己的大腿上。這股味道大家是沒有聞過的,所以,沒有人認得出來,因為他們大多還遮著眼睛。就那個釋出善意的男性呆傻站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
這部電影角色們的位置大風吹了。洗衣機還是奮力地轉,冷氣從門口滲出一片沁涼,遠方傳來警車與救護車的鳴笛聲音,越發靠近。年輕人將另一支菸熄在另一側的大腿上,倏地把玻璃踹破,拿著玻璃碎片割破每一台機車的座墊,與自己的衣物。他開始放聲大哭,邊哭,他邊發狂似的對機車施暴。其中一台機車的置物箱經受撞擊打開了,掉出兩頂安全帽,他便撿起來,朝往遠方而來的警車丟去;另外,後照鏡也被拆了下來,這個是朝那名回來處理的中年男子身上丟,但中年男子閃過了這條拋物線,往前擒抱住年輕人。警察趕緊下車制服住這個發瘋的年輕人,銬住他,他大吼大叫的聲音蓋過了警察宣讀可以保持緘默那些不是大家都理解的原則,留下汗水,滴在年輕人的頭頂上。
滿目瘡痍的洗衣店恢復安靜,鳴笛聲漸漸遠去。一包被踩爛的私菸被丟進垃圾桶,沒多少人看過這個牌子,估計是30-45塊買來的;早上去吃早餐的那個小家庭各個訝異,趕快拿出洗好的棉被與衣物就快步離開;店內人員無奈的坐在店裡,猶豫該不該清洗血跡與處理倒台的機車;一台一台的洗衣機相繼停止運轉,打開嘴巴,吐出衣物:他們不管這些衣物是誰的,有沒有來拿,就是暴力、粗獷、爆出血絲、口腔抽筋、肌肉痙攣、肛門破裂、骨骼變形的那副粗殘模樣,一口一口一口的把衣物嘔吐在洗衣店的地上,什麼洗衣粉、靜電紙、柔軟精⋯⋯別談馨香了,那股惡臭根本是難以想像。
怪異的年輕人、喋血鬥毆、破碎門窗、變成怪物的洗衣機、難以接受的惡臭⋯⋯人們逃命去了。這是個暖春,還有麻雀細語與幾片白雲,陽光斜斜地照進巷子,春聯通紅,但很純粹。不知道管線出了什麼問題,烘衣機關上自己的門,開始轉動;洗衣機的嘴巴還是張著,且他們沒有轉動,純淨、清澈的水源源不絕地流出,混著血、泡沫、玻璃⋯⋯往外流去。從陰影處流經騎樓,沖不動損壞的機車,成了略有高低、灣流的小川,流到光照的柏油路。黃黃的,紅紅的,白白的。接著是橘橘的,昏昏的,藍藍的,黑黑的⋯⋯白白的,閃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