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哥大抗议者的日记 | 草莓声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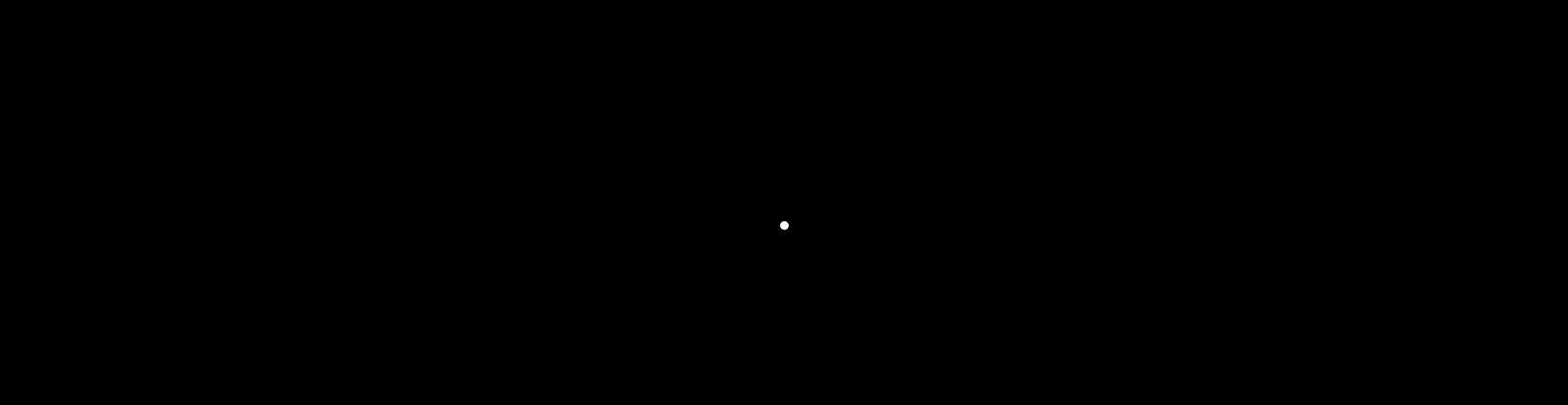
采编:芥芥子、虾
较对:芥芥子、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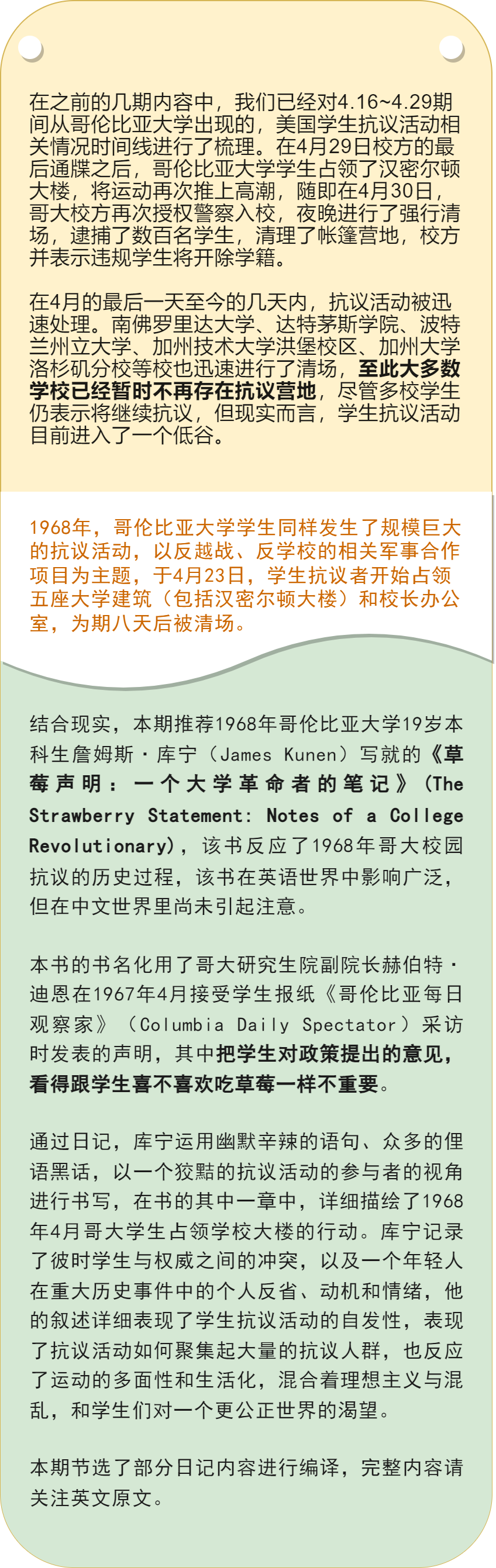

哥伦比亚大学曾被称为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他们在1784年改变了名字,因为他们想要爱国——哥伦比亚代表美国。本周让我们看看“美国”到底意味着什么。
现在每天早上醒来时,我都必须在脑海中回顾整个事情。我必须这样做,因为我在一个熟悉的地方醒来,但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我醒来,看到校园里到处都是蓝色外套和黄铜纽扣。(“黄铜纽扣,蓝色外套,抓不到母山羊”是哈莱姆俚语)(译注:大意为警察抓不到反叛者)。我开始离开校园,但后来记得转身走了两个街区,走到唯一扇开着的大门。在那里,我从警戒线上三英尺高的洞口挤了过去,摸了摸钱包,确定我有两张身份证件——这是回到我的大学所必需的。我盯着警察看——他们回头一看,将看到一个红色的臂章和一头长发,他们会用警棍敲路障。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激进的左翼分子——
我并不总是一个激进左派。直截了当地说,我也不是一个冲在前面的人,做的事情主要是十天前我给印第安纳州的参议员尤金·麦卡锡*写了封信;我与激进左派的主要联系是,我在船边缘搭把手。但后来我被卷入了这场运动,一件事接着另一件事发生。你知道,我不是领导人,但是光有领导人不能占领建筑物——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海量的人——我就是其中之一。接下来是一个革命数字的编年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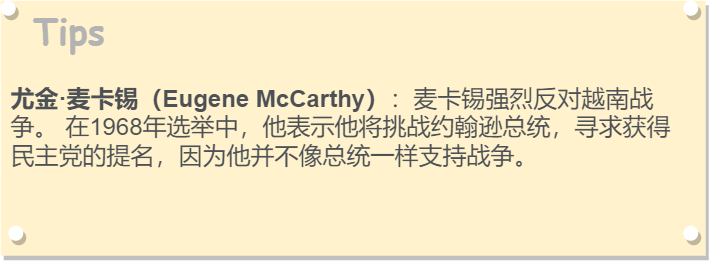
星期一,4月22日
校园周围出现了一张油印布告,指控SDS*使用胁迫手段达到政治目的;SDS被指控只是为了其自我的言论自由;SDS被指控威胁政府;SDS还被指控违规而不受惩罚。而我们——会因为把纸飞机扔出宿舍窗户而被开除。你是不是厌倦了、厌倦了、厌倦了?……做点什么吧。明天来参加SDS集会,做好准备——传单最初是匿名的,后来更新到第二版时,署名为“学生争取自由校园”。“运动员”们又来了,就像去年春天的反海军示威一样,来自右翼(运动员)的暴力威胁,使数百名秉持温和立场的人加入SDS的行列,只是为了联合起来反对“运动员暴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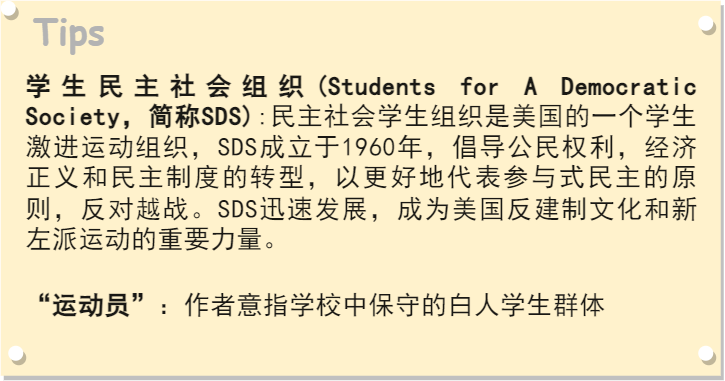
星期二,4月23日
日晷处有500人准备跟随马克·拉德进入劳纪念图书馆*,要求学校与国防分析研究所(IDA)*断绝关系,停止体育馆*建设,并反抗柯克*最近禁止室内示威的命令。大约有100名反示威者——他们是阿瑟·奥克斯·苏兹伯格信托基金报纸所称的“体格健壮的白人青年”或“具有相当运动成就的学生”——“运动员”。各位院长和其他人将两派分开。Low图书馆被锁上了。由于不知道去哪里好,我们决定去阳光普照的体育馆工地。我们高喊“体育馆必须走(Gym Crow must go)”。我不喜欢高喊口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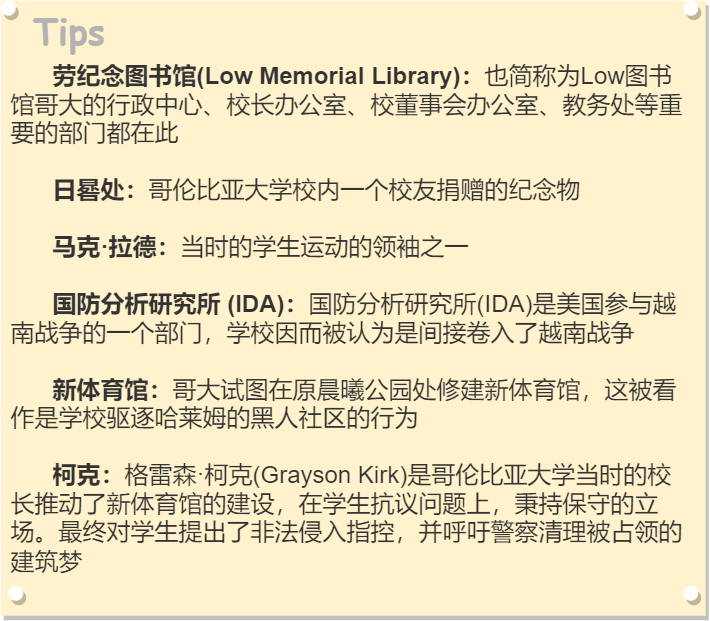
我对体育馆的态度一直不置可否,但现在我第一次看到了工地——那里有一个挖掘穿过整个公园的巨大空洞——真的很丑,而且周围有一个链条围栏——我不喜欢任何围栏,所以我是第一批跳上去摧毁它的人之一——随之而来的是纽约警察的介入。其中一个警察抓住围栏的门试图将其关闭,一些示威者抓住了他,我大喊“别去抓他”,部分是因为我为警察感到难过,部分是因为我知道接下来警棍会开始在我们头上挥舞——果不其然。我拉出了我的一个朋友,他现在high过头了,试图反击警察,但我拦住了他,因为我之前在Whitehall打过一个警察(之后很快就后悔了)。

……
有人建议我们去汉密尔顿,主要的大学教学楼坐一会儿,于是我们去了那里静坐。拉德说:“这是一场示威吗?”我们齐声答道:“是的!”“这次在室内吗?”我们又齐声答道:“是的!”
我们要求立即释放在公园被逮捕的学生迈克·史密斯——作为对迈克被拘留的回应,我们迅速采取行动扣留了柯尔曼院长。
……
晚上八点回到学校,准备在汉密尔顿过夜。
……
我上楼侦查一下,竟然看到和琳达·勒克莱尔暧昧的彼得·贝尔正在墙上涂鸦:“‘靠墙站着,混蛋……’——来自勒罗伊·琼斯的一首诗。”我也拿起粉笔,写道:“我很抱歉涂鸦了墙壁,但婴儿正在被烧死,人们正在死去,这所大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罪魁”。
星期三,4月24日
……
我们都走进柯克的办公室,分成三组,每组在一个房间。我们预计警察随时会来。一个小时的讨论后,我的房间以29票对16票的结果,决定拒绝离开,让警察来把我们抬出去。未选上的替代提议是通过窗户逃跑,然后去组织罢课——感觉是的,如果我们被逮捕了,那就有了组织罢课的理由。主持讨论的人站在一个小木桌上,我非常担心他会把它弄坏。我们用废纸篓收集水,以防催泪瓦斯。有些水洒出来了,我花时间擦干净。我不想把别人的办公室弄得一团糟。
……
就像蝙蝠侠一样从窗户爬进来的是奥雷斯特·拉努姆教授,一个自由派,他的学术长袍在风中飘扬。我们都笑了。他告诉我们,我们的行动可能引发教职工中的大规模右翼反应。他透露教职工一直在推动柯克辞职,但现在我们把一切都搞砸了;有的教职工也许会聚集起来支持校长。他说我们都会被逮捕,都会被开除。
他敦促我们离开。我们说不。我们中的一个人指出,索雷尔*说只有暴力行动才能改变事物。拉努姆教授说索雷尔已经死了。他给特鲁曼打电话,提出如果我们离开,他会给我们一个三方委员会审断的机会。我们讨论了一下,投票决定不接受。马克·拉德也从窗户爬进来。他说27个人施加不了压力,我们最好的做法是离开,加入汉密尔顿前的大型静坐。我们说不,我们不会离开,除非我们对体育馆停建、IDA停止,和豁免示威者的要求得到满足。拉德出去又回来,再次要求我们离开,我们再次拒绝。他便离开去找增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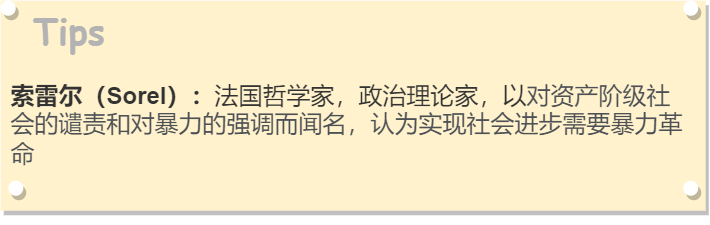
星期四,4月25日
由于看起来不会马上有警察突袭,我从窗户爬出去,四点去划艇训练。我和教练谈了谈,我们(小组)同意我晚上可以睡在楼里,如果我没被捕,第二天早上我会出现在来Low图书馆的校车上。

……
从划艇训练回来后,我必须穿过警察封锁线,跳到二楼的窗台上,这时,一个警察居然费心抓住我试图把我拉下来,但里面的一些人抓住我,将我拉了上去。
……
星期五,4月26日
我在8:55醒来,跑去乘坐开往划艇校队训练地的巴士。路上,我给马尔堡的家里打电话。我妈妈问我,“在这件事上,你是站在违法者那边的吗?”我们交换了十分钟的母亲式闲聊和革命言辞。她指出,甘地和梭罗都不会要求豁免权。我承认我没有读过他们的作品。但甘地没有(比他早的)甘地可读,梭罗也没有读过(比他早的另一个)梭罗的作品。他们不得不实践来到达自己的(新)结论,我也一样。
星期六,4月27日
……
我下午回来,站在窗台往下看。从市中心开始的和平示威活动中,人们把钱和食物放在绳子下面的桶里。每次我们拉上去再放下时,我们都会放上校卡,以便帮助那些想进入校园的人。许多车辆按喇叭表示支持,当一名巴士司机停下来向我们挥手示意胜利时,差点有十个人从窗台上掉下来。

……
随着夜幕降临,我感觉自己越来越无用,越来越疏离,所以我给自己分配了一个任务——确保蛋黄酱盖好。在盖了十二次后,我放弃了,决定写信回家。我想知道巴黎公社是否也这么无聊。
在信中,我试图证明用我父亲的钱来反叛是合理的。我指出,上大学的危险之一就是你会学到东西:我的当前行动很大程度上受到我所学《当代文明》课程的影响。密封信件后,我意识到我对法律哲学的看法不仅仅来自卢梭,更多的是来自费斯·帕克*扮演的大卫·克罗克特*。我记得他说过,你应该决定你认为什么是对的,然后继续做。华特·迪士尼*真的搞砸了,这个老法西斯无意中创造了一整代激进分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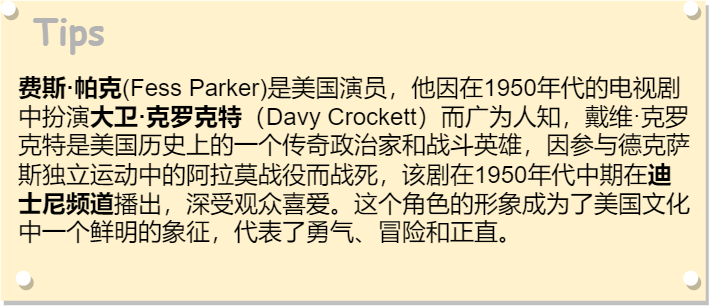
我发现一个没被切断的电话,于是给我哥哥打电话。当我说话时,旁边有人放了一张纸条写着“这...电话...正在...被监听。”我简短地向第三方问好,继续交谈。能和外面的人说话感觉很好,虽然发现外面的世界还在照常进行,这让人感到失望。
星期天,4月28日
……
我在窗台上晒太阳,读《吉姆老爷》。下午3点,四辆消防车急速驶来,消防员带着工具冲进校园。有些人以为这是突袭的开始。事实证明,这是个虚惊。
街坊的小孩们急切而能够通过栅栏缝隙钻进来。我和他们聊天,他们都了解情况,并站在我们这边。我举行了一个非正式的和平涂鸦课,分发粉笔。
……
我们的屋顶上飘扬着红旗。我向下面的人解释说,这些代表革命,不是共产主义。他说他记得读过有关的东西,我希望他指的不是《每日新闻》——《每日新闻》指责我们破坏和酗酒。(实际上我们投票决定禁止大麻和酒精,只有一个名叫梅尔文的人反对),报纸上一则漫画,标题为“跟着红色旋律跳舞”,展示了一个嬉皮士和女伴在乐队的伴奏下跳舞,乐队唱着“搞砸校园,耶,耶,耶”。
晚上,我走进一个正在进行诗歌朗读的房间。我不想显得无礼,所以我留了下来。一个看起来像基戴尔医生的医学生,朗读了一首题为《致米奇·曼特尔的第500个本垒打》的诗。
校园电台WKCR宣布,费尔韦瑟大楼*需要一位牧师;一对情侣想结婚。这并不让我感到惊讶。斯塔尔牧师主持了婚礼,并说:“我宣布你们是新时代的孩子。”不久后我们看到一队手持蜡烛的队伍走来。新娘拿着玫瑰,她递给我,我把它们传进去。当我触摸到玫瑰时,我因革命的热情而陶醉——我完全沉浸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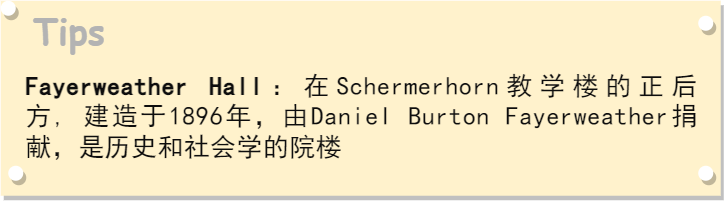
星期一,4月29日
“多数派联盟”(“运动员”们)已经封锁了Low图书馆,并试图让示威者饿退。我们决定突破封锁。我们在黑板上规划战术,然后去行动,(去之前)跟留下的人握手,仿佛我们可能不会回来似的。我们有30人,带着三箱食物。我们绕着Low图书馆走。突然,前面的黑人学生*跳进了“运动员”的队伍中。我拿着我的葡萄柚箱子冲过缺口,很快就被围在两层人中。我设法扔出三个葡萄柚,其中两个命中目标。退到数学楼,我们中的一些人说,他们打架的“运动员”腰带上有手铐(译注:大意指的是警察混进去扮演)。有创可贴的鼻子随处可见,成了一种荣誉的标志。我们讨论了给Low图书馆供应食物的替代计划,有人建议封锁“运动员”——“如果他们没有啤酒,他们就完蛋了”(译注:讽刺的说法,指白人保守派学生得不到他们喜欢的啤酒,他们就会失去继续他们当前阻拦抗议学生的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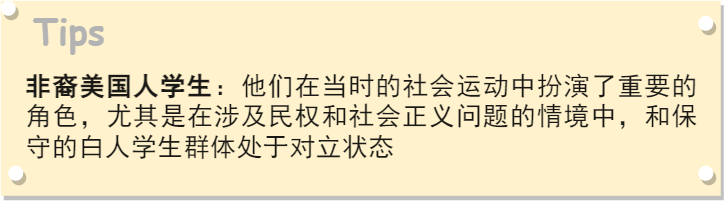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了数百个带着绿色臂章的援军向Low图书馆的窗户扔食物。我们决定用一根绳子和滑轮在一棵树和Low图书馆的窗户之间设置滑轮系统,但有人担心如何将绳子的一端送到Low图书馆的人手里而不被“运动员”抓住。当一个人建议把绳子一端系在扫帚柄上像鱼叉一样扔出去时,约翰建议我们还不如训练一只鸟。直升机已经被“罢课中心”考虑过,但联邦航空管理局肯定不允许。最后,我们同意用弓箭射出一根引线。
这一天我们大多数时间都在户外。有谣言说联邦调查局的人已经在校园里,这让我们有点紧张。我们在费尔韦瑟大楼的阵地又弄了点加固。据说,他们的大门已经有点松动了。
傍晚时分,我跟几个伙伴去了附近的一个地方。我们遇到了一位在牛津读过书的学生,他给我们讲了关于英国学生如何把牛津大学的赛艇船库变成了一个临时的革命指挥中心的故事。他的描述中充满了浪漫色彩,让我们都觉得自己是在参加一场大历史事件。
晚上回到大楼时,气氛有些紧张。我们听说警察可能在准备突袭,大家都有些不安。我们在大楼里走动,尽量保持警觉。
我们收到消息,学校又发了一个声明,警告说如果我们不撤离,他们将采取行动。这不是第一次我们收到这样的警告,但这次似乎更严肃一些。我们举行了一个紧急会议,讨论我们的反应。一些人主张硬抗到底,认为这是展示我们决心的时候了;而另一些人则担心事态升级后可能导致的后果。
我们决定派出一些人去和校方谈判,看看是否能找到一种和平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时,我们也准备好了应对可能的突袭。
就在我们讨论的时候,外面传来了嘈杂声。我们赶紧查看,原来是一些支持我们的学生在校园里集会,他们点燃了蜡烛,唱着歌声支持我们。这让我们感到不是孤军作战,精神上得到了极大的鼓舞。
夜深了,大家都在尽量放松,准备面对可能到来的长夜。我们知道,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可能会很关键,但我们也知道,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已经表达了我们的声音,做了我们认为正确的事。
……
星期二,4月30日
……
我们唱着“我们不会动摇”,意识到有些事正在结束。警察到了。警官用扩音器说:“我代表哥伦比亚大学的受托人,根据赋予我的权力……”他只说到这里,因为我们用我们组织的口号回应他和所有其他问题——“靠墙站好,混账们。”我们无法守住路障,因为门是向外开的,警察只是简单地把路障拉出去。
他们不得不切断(我们布置的)绳索和水管,花了十五分钟才能进来。他们离我不到三十英尺,我所能做的就是观察他们戴着绿色头盔在那忙。我用灯光照他们的眼睛,但汤姆告诉我不要这样做——他是“防御委员会”的头儿,所以我停了下来。
凌晨4点,警察进来了。我们八个在楼梯上(我们用肥皂和水让楼梯变得很滑),挽着手臂。大个子警察说:“别让事情难办,否则你们会受伤。”我们没动。我们想清楚地表明,警察想把我们的人带出去,必须跨过不止椅子那么简单。他们把我们分开,把我们抬出去,像堆柴火一样堆在树下。记者在场,所以我们没有被打。当我坐在树下时,我可以看到每个窗户里的学生们都在向我们看。我们交换了“V”手势。警察必须用斧头砍开每扇门,才能把学生们从办公室里带出来,他们这样做了。汤姆·海登现在出来了——他喊道:“保持收音机开着!北京会指示你们!”(译注:学生用来阴阳,暗示警察或其他当局怀疑学生运动背后有外国(尤其是共产党国家)的支持或指导),当他们把我们中60个人带出来后,他们把我们带到校园中央的囚车。我想让他们抬着我们走,但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段又长又暗的路,如果我们不配合,我们会被干掉,所以我还是走了。在囚车那里,至少有一千人为我们欢呼并高呼“罢工!罢工!罢工!”我们被装进车里,车门关上。约翰讲了一个故事,说一个警察抓住了抓他的那个警察,然后说“对不起。”(译注:警察在执行任务时误将同事当作示威者抓住。这种情况下,警察意识到自己抓错人了。反映了现场的混乱程度)。我们都放声大笑,显示出不屈的精神,并吓到了车外的警察。

……
我们的梳子和钥匙被没收了,这样我们就无法自杀。乘坐前往牢房的电梯时,一个白人警察告诉我们,我们看起来是一群“了不起”的人——我们应该被派往越南前线。有人说,越南现在就在这里。当我们走出来时,我看了看操作电梯的黑人警察,寻求他的反应。他说:“保持信念。”
他说“保持信念”,我重复了一遍,每个人都很高兴。我们经过五个空牢房,然后挤进了一个,我们34个人挤在一个12x15英尺的房间里。我们已经24小时没睡觉了,甚至没有足够的空间让我们都坐下来。
我们的一些同牢房的狱友来自艾弗里*。他们告诉我们,他们是如何被铐起来,然后被拖下楼梯的,肚子着地。他们的衬衫都是血迹斑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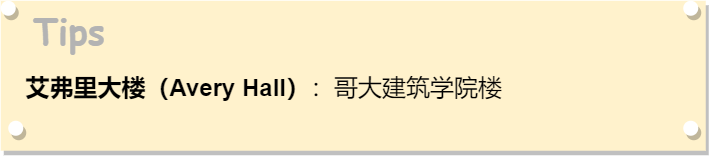
我们在法官面前受到传讯。局外人担心他们会被要求保释,但他们像我们其他人一样被直接释放了,只是他们被加上了一些指控:标准的二级刑事非法侵入罪。
回到学校后,我在一个满是警察的餐厅里吃饭。我尽可能大声地念诗,题为《向TPF的颂歌》。它歌颂了硬木警棍的美丽,手铐的光泽,以及靴子踩在你脸上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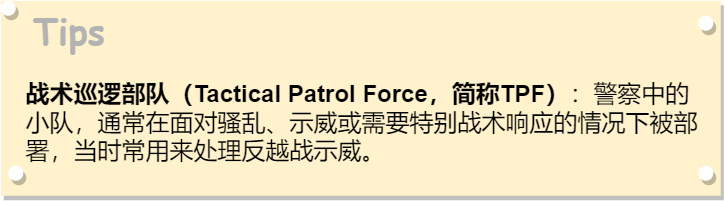
遇到了一个同牢房的人,我伸出手去,他拍了一下。我必须记住这一点——在革命中,是拍手,不是握手。
汤姆·海登现在在芝加哥。作为一个“外部煽动者”,他有很多外面的事要煽动。就像独行侠一样,他甚至没有挥手告别,就悄悄地走了,带着他的银色抗议徽章去了另一个困境重重的校园。
现在每个人都在组织——温和派,独立的激进分子,解放的艺术家,图书管理员。雅皮士派试图起诉大学,因为我们被赶出了我们所拥有的家。到处都是传单,巴纳德的女生们准备前往耶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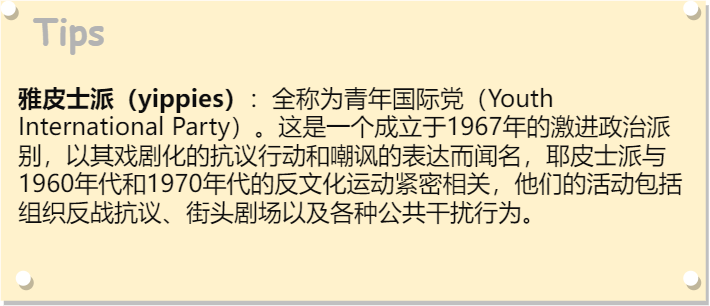
当然,我们在罢课。还有“解放课”,但是没有更多的铅笔、没有更多的书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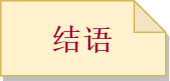
《草莓声明》勾勒出当时的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关心政治、关心世界的精神。彼时的大学抗议活动,让美国学校里的青年开始彰显其力量和影响力,今天来看,已经在美国的大学中扎根——1968年的抗议塑造了未来,也影响了美国政治和社会的轨迹,它仍然深刻地提醒人们,青年行动主义的力量和热情,及其塑造社会的潜力。在快60年之后的今天,故地抗议再起的时刻,重温1968年4月当年抗议的学生,在历史中的回音,再体察2024年4月学生新的占领大楼行动,形成穿越时空的共鸣,并将希望传向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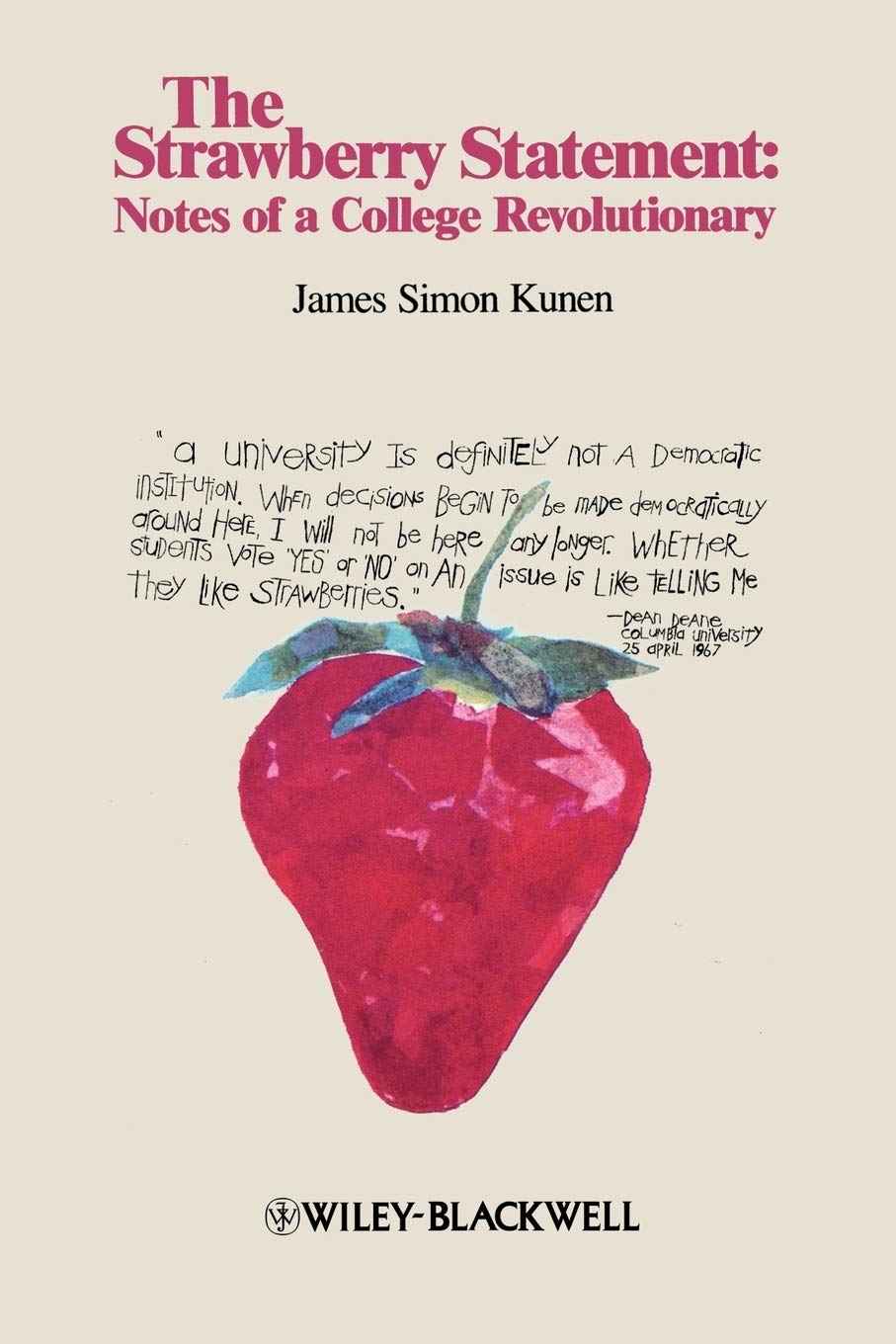

*地鸣是一个共创小组,如果你想加入我们,一起尝试聚焦一些议题,拓展写作的空间,欢迎私信我们
我们期待你的加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