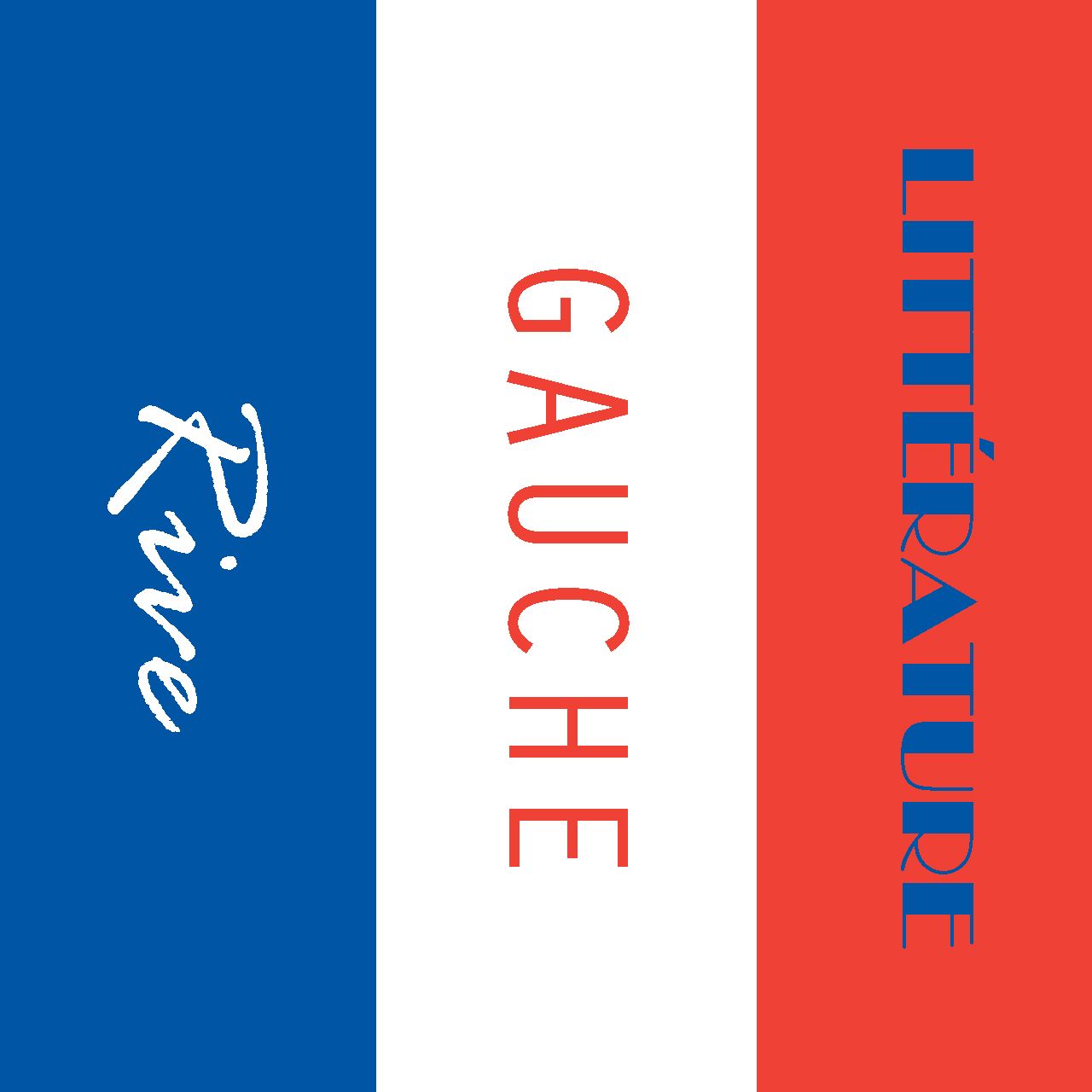短篇小说/川本大伯

《川本大伯》
文/林伯奇
图/山隼 from Pixiv
献给
为时代见证的石头的呼吸
「因为时代一点都不温柔,所以才反过来追求『温柔』。而『温柔』表现在现实中时,又只能采取头盔和棍棒这种粗暴的形式。在现实中的理念,暴力这东西成了非暴力,非暴力的东西却成了暴力,当下存在着『温柔』的悖论。」
——《我所爱的那个时代》
打开窗户,故乡的清新空气涌入房间。阳光照在挤在整个房间里已有一年之久的胶体灰尘上闪闪发亮。看到门前的故乡景色,自己才感受到离开东京后神经才有的放松状态。家乡的空气也比东京清新很多,少了那些资本主义的大气粉尘,自己的心情也自然比在东京时放松很多。
我房间的日历上画的叉到了1969年8月18号便截止了。我把日历摘了下来,准备换上新的日历。日历旁边装裱着一张大江健三郎的签名。拿起鸡毛掸子随便在房间里挥了挥,随便拿起一张唱片放上唱机就躺到在床上。那是一首爵士改编版的《到蒂柏雷利的漫漫长路》。
没过一会我便又站起来出了门,要去给今天晚上庆祝我从大学毕业买点啤酒和汽水。走在故乡小镇的街道上,仿佛四周都充满了快活的气息——这大概就是回到故乡的感觉吧。
“哟,A君,你回来啦。”我走到川本大伯的杂货店前,大伯看着了我,对我说道。“是啊,刚刚毕业了,回来休息几天。过阵再回东京。”
川本大伯的店里也放着音乐。是《步兵的本领》。我皱了皱眉头,不过我也能理解他。
川本大伯出生于明治四十五年(1912)。他出生后没几天,便传来了明治天皇驾崩的消息,所以他是大正浪漫的同龄人。他是这座小镇上的第一个大学生。27岁时,他应征入伍,参加了驻守在朝鲜的宪兵警察。5年后被调入了日本陆军部队被送往太平洋战场,在菲律宾险些被美军俘虏,非常好运地度过了将近一年多的军旅生涯,在冲绳被解除武装,后来回国。回国后在名古屋钢铁厂里干过活,昭和三十四年时,又回到了这座小镇,与他夫人开起了一家杂货店谋生。而我——则是战后新体制的同龄人。在我仍生活在这座小镇里的年少时光里,我常常来帮衬他的生意,也会跟他聊天,听他讲那些“过去的故事”。
“当时我入伍的时候,东京的代表说什么,我们的舰队已经开进澳洲的雪梨湾啦,什么旗帜飘扬在达尔文港的上空啦,军舰开进密西西比河完全不是问题……哪有这回事!我还在韩国的时候就知道这都是蒙骗乡下人的说辞,等我到了菲律宾的时候才知道这确实是骗人的说辞……”他过去经常这样说道。
“回到东京后,想做什么呢?”大伯问我说。
“去杂志社里做点事情吧,我想。”我说,“大不了还能坐办公室当文员呢。”
“哈哈,是这样的,”大伯笑了,说着,“现在哪里的工作不好找……过去我们要靠打仗去战胜美国,现在我们都可以用钱把整个美国买下来啦,只是买不买的问题。”紧接着他又说,“现在,东京还好吧?”
“总算是毕业了。”我说,“毕业仪式上还有人喊口号,诸如什么‘GM无罪,造反有理’。学校里还有些设施没恢复起来,几个讲堂去年直接给废掉了。”
“真不知道你们这代年轻人怎么回事,没过过过去的苦日子。”大伯说着,也皱起了他的眉头。“要不是我们这代人努力打拼,会有你们这些臭小子臭丫头的好日子吗?”
“大概是因为过去苦日子过太多了,所以今后就不想再过苦日子了吧。”我说,接过川本大伯递给我的可口可乐,喝了一口。
“可乐好喝吗?”大伯问我,我说好喝。“我第一次喝到可口可乐,也是在菲律宾。从没喝过这么新奇的饮料。你看这可口可乐,虽然也是美国产的……但不也是你们年轻人最讨厌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吗?”我苦笑着,不知该如何回答他。
1960年代的东京并不太平——不,应该说1960年代的世界都是如此。
北京,东京,巴黎,罗马,西柏林……甚至是华盛顿。1968年年底的三亿元事件还没完,1969年年初就发生了东京大学安田讲堂事件。这样的论调在整个东京都文京区都很常见——跟大布尔乔亚财阀的剥削掠夺比起来,三亿元又值多少钱呢?跟美军在冲绳,在越南杀人比起来,把大学讲堂放火烧掉又何妨?希腊戏剧,有讨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重要吗?诸如此类。
在我于东京度过的岁月里,“会不会哪天被挂上电线杆当成counter-revolutionary给吊死”,这种话已经成玩笑话了。
“大伯,你有认真思考过自己从军的那段经历吗?”我问大伯。
“认真思考这种事情嘛……倒也就那么回事,需要认真思考吗?”大伯说着,很是兴奋,“虽然我已经老了,但想想还是感觉热血澎湃啊。啊,菲律宾的丛林……”
“难道你不曾觉得那场战争是对其他国家的民众的伤害吗?不曾觉得自己被人给欺骗了吗?过着不知什么时候就死掉的生活,而整场战争下来什么都没有得到?”
“你这说的都是什么胡话?”大伯不高兴的对我说道。“我们那个时候都把能够战死沙场作为荣耀……想必你也是知道的。是啊,那时候征兵官骗了我们,告诉我们什么全面占领澳洲指日可待……但我不曾后悔效忠于祖国的那些岁月……”
接着,轮到我沉默了。我不知道我与这个固执的老男人究竟还有什么可以讲的;我并没有以“顽固的老东西”而是以“顽固的老男人”来形容他,因为他明明身上还闪着光芒!那是我们这一代人所没有的光芒。那份光芒体现在这个男人的目光里,体现在他的谈吐里,即使战争结束了这么多年,那一份所谓男儿的风貌依然没有被洗却;而这一种风貌却是在可口可乐,披头士音乐,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中成长起来的我们一代所没有的。
我内心里的一个小小声音说,那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那种蠢货一样的风貌有什么值得赞叹的?我的心情五味杂陈;心中既有一种赞叹,又有一种不屑一顾。又或者是,这是当代的不幸者对过去的不幸者的怜悯。
“其实,我们那个年代也不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见我沉默了,大伯又说道。
“小林多喜二。”我插了一句嘴。
“是啊,小林多喜二。我也不是没有听说过什么马克思恩格斯——把你们现在提出的那些东西放到过去,直接给特高科,给宪兵抓起来打!还崇拜什么M主席哩……”
我苦笑了两声,大伯继续说了下去。
“其实啊,照我看。你们这代人是教育出了问题。是教育出了问题。”他重复了两遍,“从来没有人,教过你们这代人爱国是怎么一回事。麦克阿瑟元帅制定的宪法已经写明白啦,禁止我们爱国。从来没有人教过你们忠诚是怎么一回事,高尚是怎么一回事,你们这代孩子啊,只是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长大的人罢了,武士精神也不过只是那么一回事……而你们连知耻的心都不曾有过……”
大伯笑呵呵地说出这些话来。我不知道他说这些话时是以怎样的心情说出来的。日本的精神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个问题恐怕没有任何人能给出答案。有的人认为日本的精神早已在明治维新西南战争的时候灭亡,又或者是明治天皇去世,又或者是大正民主的结束,又或者是原子弹在长崎爆炸的时候,又或者是裕仁接见麦克阿瑟将军的时候……大伯真的理解日本魂么?说不定在他之前的人也会觉得他这一代人是在普鲁士式军国主义里栽培出来的人——是他们把武士刀变成了仅仅放在博物馆里用以展出的饰品而非驰骋沙场、以无情答复强大敌人的武器!他们会说真正的勇士手里不会操纵加特林机枪,而是经过高温熔炼又放入冰水里凝结的刀剑!大伯他不懂日本魂。大江懂日本吗?三岛懂日本吗?我看都未必。
这个土地只是1960年代偌大的太平洋的西面的一串狭长的列岛,仅此而已。在1960年代,这个列岛上举办过东京奥运会和大阪世博会,年轻的白领挤在电车里即将要去为喂饱一家四口人的胃而奔走,有一群年轻人想要去呼唤新的未来而戴上蓝色红色白色绿色黄色的头盔去与东京警视厅机动队械斗,新宿涩谷的大道上除了呛人的催泪弹气味,还有被燃烧挥发的酒精味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烟尘味。没有人能够相信——仅仅是二十年前,这个国家看上去是那么野蛮而落后,人们吃不饱饭,为了生计必须要加入军队,以疯狂粗鲁的暴行来换取生存的资本,一切都显得那么萧条,并为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除了废墟以外什么都没有提供……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葛饰北斋在《神奈川冲浪》里所预言的我们的时代。大伯是过去的时代的人,我是当下的时代的人;大伯野蛮但有气魄,我斯文却又迷茫。
“那么,你在家乡停留多久?还去东京吧?”
“估计一个星期后我就回东京。”我对大伯说。
“多回来啊,看看老夫……唉,现在的孩子们啊……”我拿上买来的饮料酒水,跟大伯道别,就自己回家去了。
我是在一天夜里收拾行装回东京的。走前我想去跟大伯道个别,于是又走到他的杂货店前,敲了敲门。大伯不在,只有大婶。“大婶您好!我找一下大伯,我这要回东京,想跟他道个别,过去没少受他关照……”
“呵,那你来的不是时候!他跟阿健去城里进货去了,现在还没回。我替你转达吧。”
我不免有些失望,便请大婶替我转达。往车站的路是新修的柏油路,上面还有一股柏油的气味。惨白的路灯灯光有跟没有一样,那个我离开的晚上,能让我没一脚摔进沟里的只有满天的星光。就这样,在昏暗的星光的陪伴下,我与混沌回到了东京。
等我再回到家乡的时候,那已经是我大学毕业的三年后了。我在东京谋了一份好工作,这期间,尼克松访问了北京,跟毛主席握手了。
我轻松地走在车站到镇子中心的大路上。镇子的面积很明显地有所扩大。
我走到杂货店的门口,看见阿健站在门口喝汽水。“阿健!”我向他打招呼,“大伯呢?”
“大伯啊?一年前就走了!”阿健看着我,说道。
“哗!”我有些惊讶,“大伯……怎么就走了?他还不算太老吧,我记得我上次见着他还挺有精神的……”
“不知道他落了啥病,大婶说是过去打仗时落下的旧伤,医生说是突然中风了,于是就走了。”阿健说,“话说你这家伙,大伯走了也没见你回来见他最后一面……”
“抱歉,实在是不知道也没通知有这么回事……我可以进去吗?”
“当然,请便。”
我走进了杂货店,来到杂货店的二楼。二楼是过去大伯的起居室,现在起居室的柜子上摆了一张大伯的照片,那张照片用的是年轻时大伯参军拍的照片。
“老头子,你该休息了。”
我走近大伯的遗照,轻抚着大伯的相片。一种错愕感在我的脑海里久久回荡。
2020.1.16
编者注:本文由林伯奇先生完成于2020年1月16日,与原图文对比作出了一定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