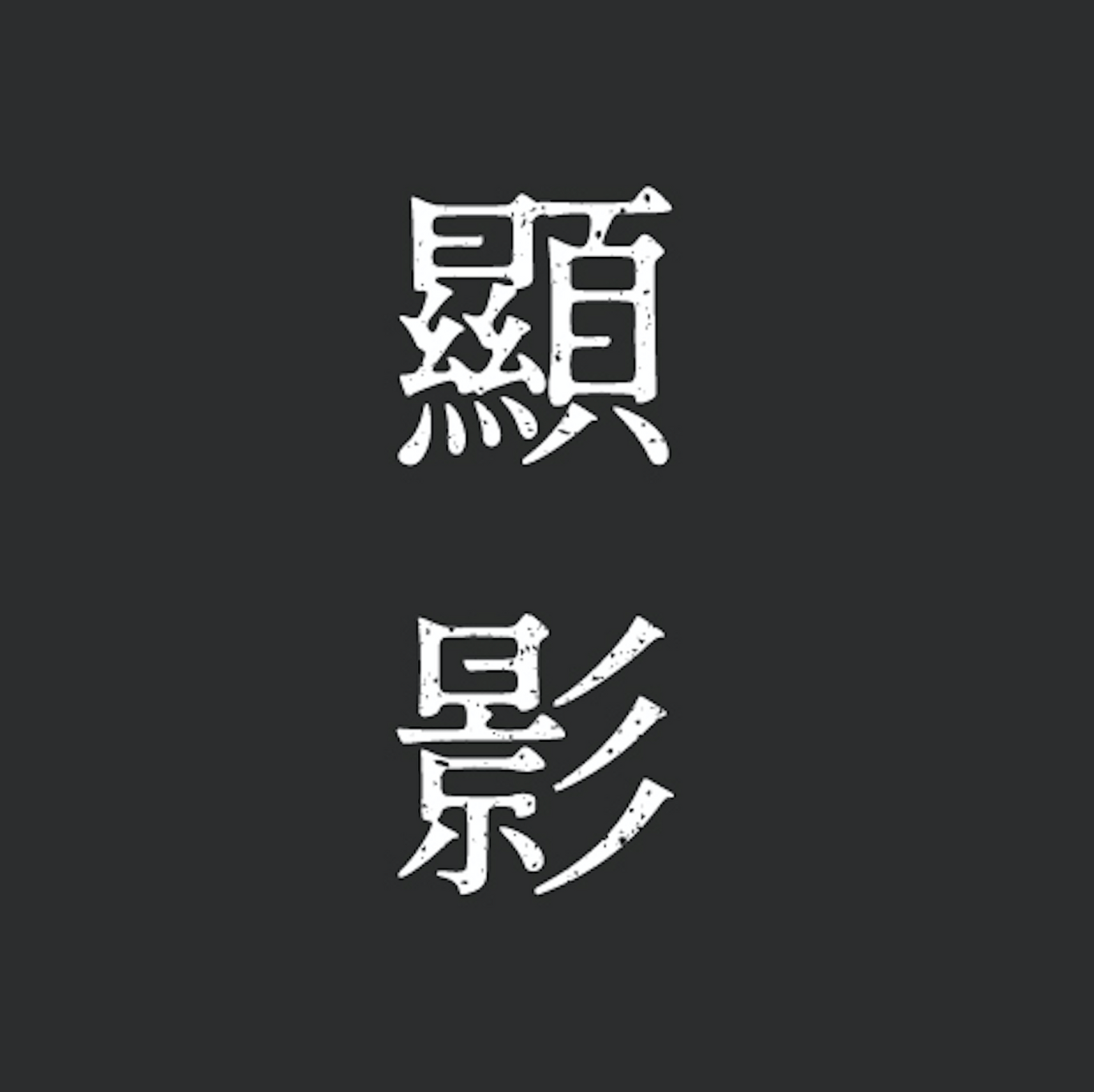廖偉棠 用詩意告別森山大道的影響
森山大道是當今日本最重要的攝影師之一,他的高反差、粗微粒、粗糙及模糊的攝影風格,挑釁着二戰後日本社會美學,也影響了無數後來者。詩人廖偉棠也曾迷戀過森山大道的作品,2004年發表的首本攝影集《孤獨的中國》,高對比黑白照片中的鬆矇,在作品中隨處可見。
十多年過去,如今的他已不再以攝影為生,與攝影的關係也變得更純粹,2018年初出版的攝影集《微暗行星》,收錄了過去多年在世界不同地方拍攝的彩色及黑白照片,前者稍顯黯淡、後者充滿詩意,「我想以此作為一個分界點,告別深森山大道對我的影響。」廖偉棠如此形容近年的作品。

大多數人認識廖偉棠,是其詩人及作家身份,他的評論文章,廣見於中港台報章雜誌。料想不到,他大學修讀的是攝影。「其實我有近十年時間都在從事攝影工作,幫時尚雜誌影相,連廣告攝影也有做過,但我始終不太鍾意。」1990年代末在文學界成名,廖偉棠曾放下攝影數年,做過書店店長。這位波希米亞主義的流浪詩人,回歸後從廣東來港後,輾轉又去了北京生活。2001年他在北京與陳冠中一齊做《視覺21》雜誌,原本他是圖片編輯,後來才重拾攝影。
那時的他是位超級文青,關注地下文化及次文化;喜歡西藏,也做過《西藏人文地理》的簽約攝影師;還與綠色和平、樂施會等機構合作,拍攝環境污染、塵肺病等社會議題。回港後他籌辦過攝影雜誌《CAN影像誌》,同樣關注低層人民的生活狀況,2011年也出版過攝影隨筆集《遊目記》。


調低飽和度 製造黯淡詩意
廖偉棠是為數不多遊走在攝影與詩之間又將兩者結合的人,從2005年的《巴黎無題劇照》到近年的《尋找倉央嘉措》、《傘托邦 — — 香港雨傘運動的日與夜》與《微暗行星》,無不如是。「我經常思考文字與攝影的關係,到底會互相激發還是產生矛盾呢?」在《巴黎無題劇照》作品集中,他以富士TX-1相機來拍攝,寬幅比例的照片看起來很有電影感,再配以沒有關聯的文字,文字與相片之間的貌合神離,故意製造出一種假寫實,頗具實驗性。
然而,他的根一直是紀實攝影,只是他不喜歡大多數的新聞紀實攝影。畢竟紀實攝影在二十世紀被塑造成一種權威,不是Robert Capa的那種生死攸關,就是布列松的決定性瞬間。廖偉棠偏愛在紀實攝影中保持距離感,也不介意構圖是否唯美,「我喜歡森山大道,就是欣賞他打破對美的固有想法。」正如《微暗行星》一樣,它不是傳統的旅遊攝影集,從城市A至Z的順序來排列照片,看似很有次序,其實跳脫得很,上一頁還是雅典,下一頁就去了巴塞隆拿;當你沉浸在京都時,下一瞬間又到了拉薩。
每座城市只挑選三數張甚至一張照片,沒有標誌性的景點,也沒有獵奇或風光旖旎的畫面,反而是平凡而隨性拍攝的瞬間。「我想在照片中找一個曖昧的時刻,很微暗很低調的,慢慢去感受畫面的內容。」在拉薩的博物館內,廖偉棠隔着花草拍攝了一張官方的宣傳相片,畫面中一位戴着紅領巾的西藏學生正開懷大笑,若隱若現笑容背後,代表他對西藏的又愛又恨。「我覺得很多事情都被歪曲了,西藏正被漢族文化改變。」
廖偉棠相信攝影能介入現實,但他不會像傳統的新聞攝影一樣,拍攝劍拔弩張的衝突場景,這在《傘托邦》一書裏可見一斑。他的照片沒有販賣苦難,也不會賺人熱淚,他覺得一位詩人或藝術家,面對這個世界應該是從容而淡定的,這樣才能更理解彼此。他故意將某些照片的飽和度調低,令其變得黯淡、平靜,彷彿很漫不經心的,有種淡然的詩意。


背後的這種細膩,自然與他寫詩的經歷有關。對廖偉棠而言,攝影及文字是對等的,所有影像都是經過思考之後才按下快門的,攝影並非只是文字的點綴。「當我拍攝一樣事情時,我就不會再寫。當我做回詩人時,會嘗試寫下無法拍攝的東西。」不過他也坦言,自己的攝影與詩是互相影響的,詩人的世界太文明,寫作時慢慢會規範了自己,「而拍攝時是很粗暴,是很亂的、不工整的。攝影令我保持創作的平衡與活力。」寫作時他往往不能自拔的,在文字間痛苦地糾纏許久,而攝影卻帶來歡樂,可以與世界很直接的交流、坦然相對,有時甚至是種休息。
·原文見於果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