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一生中,有许多次被人叫做叛徒
有些书跟人一样会一见钟情,《爱与黑暗的故事》就是这样一本书。不记得是在怎样的契机下去读这本书的了,但是我清楚地记得,当读完开篇第一段,我就知道会爱上这本书的。
“我在楼房最底层一套狭小低矮的居室里出生,长大。父母睡沙发床,晚上拉开的床从墙这头摊到墙那头,几乎占满了他们的整个房间。早上起来,他们总是把床上用品藏进下面床屉里,把床垫翻过来,折拢,用浅灰床罩罩得严严实实,上面放几个绣花靠垫,夜间睡觉得所有痕迹于是荡然无存。他们就是这样把自己的房间用作卧室、书房、阅读间、餐厅和客厅。”(钟志清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
这段平平常常的描写像狭缝中一道阳光,将我带回自己的童年:逼仄的空间,每到雨季便执拗的霉味,阴湿中挤在一起却无时无刻不在维护个体边界和尊严的人们。这些都在接下来的几段中有了印证。隔着时空,隔着语言和文化,奥兹唤醒了我心底那遥远、温存而感伤的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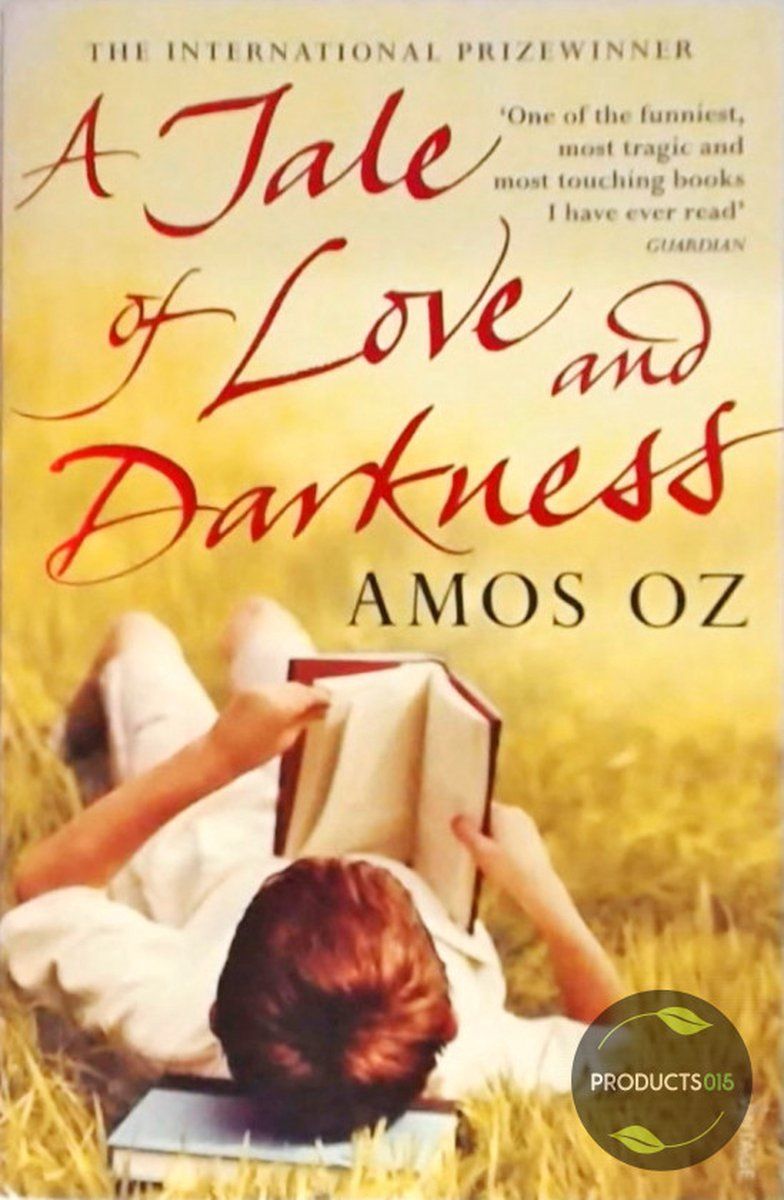
初识奥兹
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这并非我第一次“见到”奥兹。我兴奋地到书架上去搜寻一本口袋书,终于在一大堆书的缝隙中找到了它。这是奥兹的政论散文集《如何治愈一个狂热分子》。有一年我乘飞机忘带书了,正为如何消磨那几小时发愁,在前座插袋里摸到一本不知谁留下的口袋书,书名叫How to Cure a Fanatic。黑底封面上是个穿蓝色工装衬衫、古铜肤色、满脸褶子的老先生,想必就是印在封面顶端那硕大姓名的主人:Amos Oz。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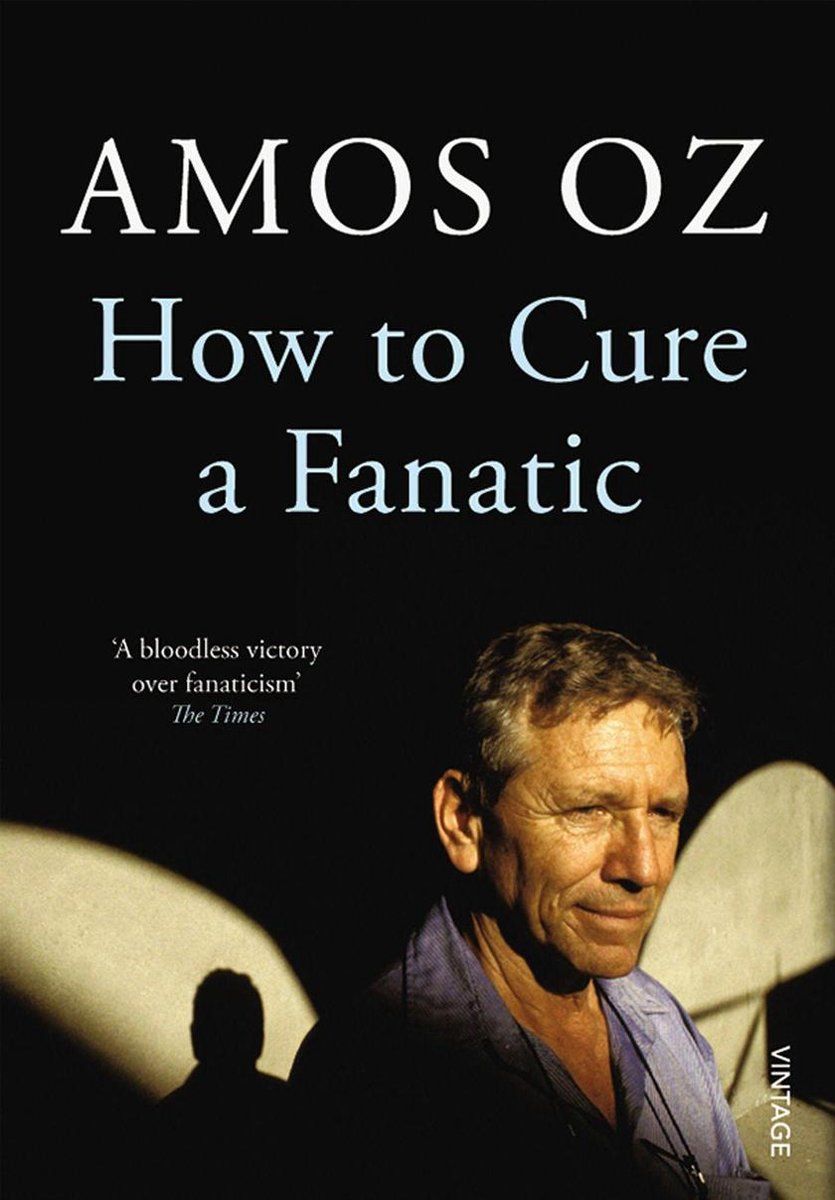
当时我从没听说过这个作者,翻了翻介绍,见是关于巴以冲突的,就全当学习来读,并准备乏了随时放下。然而,当飞机降落时我已读完了整本书。在那之前,巴以冲突在我的印象中一直是响亮但模糊的四个字——叫得出口,说不明白。读的过程中,我时不时感到醍醐灌顶,惊讶作者竟然能把一个复杂庞大的政治问题写得如此清晰生动,让我这么个小白不仅能够从理智上把握脉络,还能够从情绪上感同身受。
奥兹在以色列有小说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双重身份。他从不避讳政治辩论,是巴以“两国方案” (two-state solution) 的坚决拥护者,并且一生都在与狂热的民族主义做斗争。他的妥协常被看作软弱、耻辱、投降,他也因此在本国被有些人贴上“叛徒”的标签。尽管如此,他仍然坚信选择妥协就是选择生命,妥协的反面不是骄傲或刚直,而是狂热和死亡。他以“叛徒”为荣,称它为自己的军功章。了解奥兹的政治立场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母题——民族与命运、爱与背叛、亲密与隐痛,以及故乡耶路撒冷。
我是谁,我们是谁
《爱与黑暗的故事》是奥兹传播最广、最负声誉的作品。这是一本长篇自传体小说,从一个小男孩的视角讲述了个人的成长和家族的兴衰,从中牵出犹太民族百余年的历史。奥兹出生在巴勒斯坦,属于“本土以色列人”,他的父母辈是在英国托管时期 (一战后至1948年以色列建国) 迁徙至此的东欧人。书中他对父母这辈“旧希伯来人”、他自己代表的“新希伯来人”,以及两个群体之间的冲突有着贯穿始终的描写。
“旧希伯来人”被欧洲人驱逐屠杀,好不容易逃到了祖先所在的“应许之地”后,面对的却是炎热、贫瘠,还有与他们争抢土地的阿拉伯人。他们身在东方,心却在西方。他们的语言、教育、文化、情感都是欧洲的,对欧洲有着天然的认同和仰视。然而,“在那个大世界里,所有的墙壁爬满涂鸦:‘犹太佬,滚回你的巴勒斯坦去!’于是我们回到了巴勒斯坦,而现在整个大世界又朝我们嚷:‘犹太佬,滚出巴勒斯坦!’不光整个世界是那么的遥远,就连以色列土地也十分遥远。”(《爱与黑暗的故事》)一群流离失所、受尽迫害的人变得高度敏感和神经质。那个一辈子都在与细菌做斗争的施罗密特奶奶,那个总喜欢给儿子讲暗黑故事的母亲,都在预言悲剧的结局。奶奶荒诞地死于洗澡,妈妈严重抑郁,吃安眠药自杀。父亲似乎是唯一开朗的人,但他对生命的渴求让他疏远家庭,使他成为导致母亲自杀的罪魁之一。一群聪慧美好的人被连根拔起,放到一片他们根本就无法生长的土地上,陆续凋零腐败。
相较“旧希伯来人”,奥兹这批“新希伯来人”有着完全不同的本色。他们在以色列土生土长,以希伯语为母语,在文化和心理上跟欧洲没有天然的认同。反之,欧洲在他们的眼中代表着古老和腐朽。母亲自杀后两年,十四岁的奥兹选择离开父亲,去基布兹独立生活,并把姓氏从克劳斯纳改为奥兹(希伯来语意为“力量”)。他像当时许多以色列年轻人一样,受到犹太复国主义先驱和拓荒者们的鼓舞,上山下乡,用双手去创建属于自己的国家。在基布兹农场中,他把自己晒得黝黑,练就一身肌肉和好手艺,以此高调地与父辈割裂:他们才是新世界的人,未来属于他们。

何为英雄,何为叛徒
基布兹造就并成就了奥兹。他的很多小说是以基布兹生活为背景的,如《何去何从》、《沙海无澜》和短篇集《朋友之间》。基布兹文化阳刚、强悍、团结、共产,而这些恰恰是奥兹之后一直在质疑的。为了创造一个崭新而勇猛的国家,基布兹必须让英雄主义渗透进每个人的血液,将集体利益高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它不能通融个体差异,瞧不起大流散回来的欧洲人,甚至不同情集中营幸存者,认为代表“弱者”的过去是必须被彻底根除。一向具有人文关怀的奥兹在一次采访中说,“人不是神,人有其弱点。人性中与生俱来的自私与欲望拉开了理想与现实的距离。也正是在基布兹这样一个集体主义至上的地方,人的一切想法与行动均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人的隐私得不到保护,人性中的某些基本需求也遭到压抑。”(《朋友之间》译后记)。
奥兹关心个体经验。他在演讲时多次说到,人为什么要读小说是因为小说能够帮助我们走进陌生人的心灵世界,从而打破“我们”和“他们”的边界,促成理解与对话。这或许听起来老生常谈,但奥兹始终在坚持不懈地履行着。《爱与黑暗的故事》中,他多次提到阿拉伯人和阿拉伯社区。其中重笔墨描写的是他八岁时在一家阿拉伯富商家做客的经历:那里他遇到个美丽的阿拉伯小姑娘,在她面前以犹太民族代言人自居,甚至上树抡锤来展示英武风采,希望以此赢得女孩的好感。然而,结果却是误伤了树下的小弟,造成他终身残疾,这家阿拉伯人也因此与他们断交。他一辈子都无法放下这对姐弟,儿时的场景在他心中成为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日后的缩影,通过回忆童年他探讨着巴以关系,并挑战了以色列人的良知。

奥兹对巴勒斯坦人的同情为他招致了“叛徒”的罪名。作为一个哲思好辩的以色列人,他从九十年代起就一直在小说中与公众讨论何为背叛、何为爱与忠诚。他的小说《地下室里的黑豹》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在我的一生中,有许多次被人叫做叛徒。”这本书可以说是《爱与黑暗的故事》的预告片,《爱与黑暗的故事》有的元素,它基本都有,但是被浓缩进了一个相对简单的故事中。这也是一部个人记忆小说,从一个十二岁男孩的视角出发,讲述了以色列建国前夕,英军和犹太地下反抗军之间的关系紧张到顶点的时候,男孩和一个英国军官之间充满变数的友谊。
在这个阶段,他探讨的“背叛”仍聚焦于民族情感和人道主义之间的悖论。然而到了晚期,“背叛”这一主题则潜入了他书中的方方面。在他生前的最后一部小说《犹大》中,他将宗教的背叛(犹大究竟有没有出卖耶稣)与爱情的背叛(出轨、诱惑和不伦的爱情)和政治的背叛(犹太人是否应该跟阿拉伯人成为兄弟)交织在一起,三线并进,而所有这些都在一个冬天一座孤独的郊外房子里演绎出来。这是一部披着成长小说外衣的,富有挑衅意味的复杂作品。故事的时空虽然很窄,却将奥兹毕生的思考放了进去,可以说是《爱与黑暗的故事》的收尾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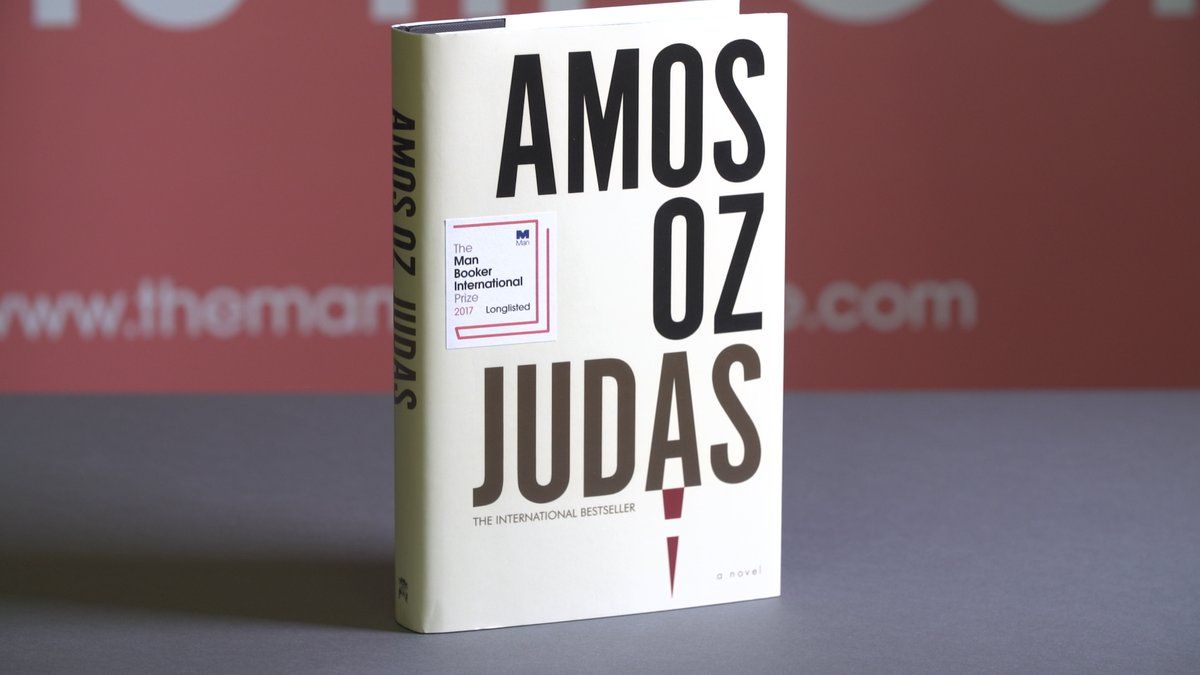
亲密隐痛
奥兹的许多作品读起来都像成长小说,因为他的主人公往往是早熟、敏感、困惑的少年或青年男性。他写了那么多男孩,每个都很相似,每个都是他自己。他到老似乎都未长大,似乎仍是那个失去母亲的十二岁孩子。这给他的作品一种柔软的特质。奥兹的笔法细腻诗意,安静醇厚,令人思绪驰骋。尽管有时会陷入琐碎平淡,却总在下一刻又有什么会戳中你最脆弱的地方。奥兹虽然忧伤,但他从不让自己沉溺于苦痛。相反,他的性格是幽默温暖的,在生活中以讲笑话出名,这在他的作品中也有着自然的流露。
奥兹还非常擅长写女性。他的小说大多以家庭为主题,经常附着一个不谙世事的主人公和一个令他神往的谜一样的成熟女性。这些女性身上都有他母亲的影子。可见,他一生都没有从失去母亲的阴影中走出来。他穷尽大半生去探索他的母亲是谁,为什么会自杀,并且将这些探索注入他的女主人公身上。除了母亲,另一位女性也对奥兹产生过深远的影响,那就是他青少年时期短暂的情人——基布兹中一位年长于他的女性。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中,他用波澜不惊的语气提到多年后与她相遇的过程:他在一次讲座结束后见到那张熟悉的脸,面容未变,只是老了一些。他拨开人群走向她,拥抱她,亲吻她,却得知那人是她的女儿,而坐在旁边轮椅中神情木然、无法言语的老人才是她。这个信手拈来的细节写尽了人生无常和隐痛,倒出一声奥兹式的唏嘘。

永远的耶路撒冷
如果说成熟女性是奥兹的迷恋对象,耶路撒冷则是让他爱恨交织的情人。奥兹出生成长于耶路撒冷,对这座城市有着复杂的感情。他笔下的耶路撒冷“是位性爱成瘾的老妪,不断压榨一位又一位情人,至死方休,而后一个哈欠便将对方从自己身上抖落;耶路撒冷是黑寡妇,趁着交欢之际将伴侣一一吞噬。”这段话曾被蒙蒂菲奥里引用,作为《耶路撒冷三千年》的引言来描述这座城市所历经的沧桑和轮回。“征服者前仆后继而来,称霸些许时日之后,徒留几座墙与塔、几道石上的裂缝、少许陶器碎片与文件,就如丘陵间的晨雾般,消散无踪。”(《爱与黑暗的故事》)
2019年疫情之前,我到耶路撒冷走了一趟,下榻的旅店正巧离《爱与黑暗的故事》中奥兹童年的家不远。在赶回程飞机之前的一小时空闲里,我拿着谷歌地图寻到那里。那是一个周六微雨的早晨,街道上只有零星的人,无一例外全是戴着黑毡帽、穿着黑大衣的男人和男孩。路边一个窗户内传出祷颂声,望进去,一群同样服饰的老少男性面对大册经书摇头晃头。终于找到了阿莫斯街18号,成了宗教服饰店,铁门紧闭,外墙上贴着逝者纪念会的通知。奥兹曾在采访中惋惜道,这个曾经多元的移民社区如今变成了极端正统犹太教徒的领地。这些年耶路撒冷的正统犹太教徒数量激增,世俗社会被挤压出去,就连世俗学校也所剩无几了。多年来在右翼政府执政下,奥兹这种反极端的温和派在以色列沦为边缘,甚至被左右共同夹击:左派认为他不够激进,右派认为他是叛徒。他成了一个过时的名字,同耶路撒冷一样掉入历史的尘埃。

1966年,刚出道的奥兹写下:现实会时不时地回到它的来由——黑暗的欲念、恐惧与梦境。此后,他一直在书写黑暗、恐惧与梦境,以此为镜照亮现实。38年后,当他终于鼓起勇气直面黑暗的根源后,他写下了《爱与黑暗的故事》。奥兹用他温润如水的笔在黑暗中拨开光明。当我们将手触进水,摸到的是一块光滑的磐石。无论现实如何变迁,他都在反复书写同样的主题,用水滴穿石一样的毅力与狂热作战。今天,远不止耶路撒冷,世界的角角落落、方方面面都在加速狂热与极化。读奥兹或许显得不合时宜,却是恰到时候的,因为他帮助我们回归理性,回归让生命锚定的本质:爱、幽默、宽容,以及正面黑暗的勇气。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