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5 完美主义是邪恶的教育|我的封城十日志
野兽按:今天在【心灵自由·不知所云】我们又聊到了“完美主义是邪恶的教育”这个主题,于是又想起了吴迪写于2017年的文章。再次分享,配上陈琪莹的《完美主义》一文。
特意在文末加上江雪的《我的封城十日志》和江雪专访,竟然在公号推送成功了。但不知道能够活多久,在这里也备份一下。

篇名:完美主义是邪恶的教育
撰文:吴迪(2017年10月胡因梦身心灵整合工作坊苏州站学员)
从小到大我幸运的遇到过过很多有缘分的老师和爱人,他们都在潜移默化中把我往身心灵的路上引。那些因缘都十分奇妙,我们相遇的地点和方式都一次次的提醒我,这一切绝非巧合。但是我最大的障碍就是我的自以为的聪明。有好几个我特别尊敬的不同宗教的老师,都告诉我。你不要闹了,你太骄傲了,你太聪明了,你要臣服。
睿智如我,谦虚的点头说:是是。但内心的独白是:聪明不好吗?盲目的追随那么腐朽,我才不会去做。臣服?臣服什么?臣服于谁?上帝吗?它才懒得管你臣服不臣服,它不是充满爱的全知全能的吗?它没有那么自我还需要人家臣服于它。
这些善良的师长看在眼里也不多说, 而我对他们的观察和批判让我无法全信他们所代表的派系和理论。他们在我眼里就是一群人格里有灵性特质但是自我矛盾和自我欺骗占很大成分的世俗好人。
后来看了很多胡因梦老师翻译的和自己写的书,理性被说服,感性层面上一总觉得怎么少了一点奇迹的意味(我希望感受到某种超越我认知的神迹,来彻底降服我过度intellectual的头脑), 另一方面觉得这些道理我都懂了,可是对“臣服”这概念还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直到上个月我参加了胡因梦老师的工作坊。
我写出这篇分享的东西, 除了寿文的一再提醒之外(我真的很懒),还有我内心无限的感激和触动,如果不表达出来是一定会憋死的。
如果你和我一样是一个分析狂人,科学思想观深入骨髓,并且傲慢的认为自己看东西很深很有洞见,那你真的需要来这个工作坊。
我去工作坊的心境十分的难易描述,里面夹杂着 1. 逃离自己的婚姻,需要找个借口出来独自待一周,2. 好像是某种自暴自弃的对赌:我想亲自“鉴定”一下胡老师,如果她都是假的(或者我觉得不符合我对完美高人的期望),那我就放弃了身心灵这条路。

工作坊在苏州一个美丽安静的山上举行,我到的时候已经是深夜,山里面有一种鬼魅的气氛,对应着我要踏入未知的烟雾濛濛的既视感。我似乎知道我的人生要被改变了,所以兴奋并害怕着。睡觉的时候有微微颤抖的感觉。
第一天早上,先做瑜伽, 胡老师的爱人长得很混血,他有一种天然的真诚感,朴实而可爱,作为瑜伽老师这种感觉很对,我非常爱观察一个人的另一半,(因为我就是一个分析+批判狂人),通过一个人的爱人,你可以看到很多他/她的内在。我仔细的听着金铭老师的讲解,感受着这个人的可爱之处和简单,我想胡老师会是怎么样的呢?
快到中午的时候,胡老师来了,大家鼓掌,一个纤瘦的轻盈的身躯,少女般的雀跃跑跳到讲台的椅子上。我的心完全被这个美丽的女孩子打动,她坐在那里,美美的,一点没有什么虚张声势的废话,静静的讲了一段很简单的开场白,然后说,我们来确认一下大家的出生时间。如此深的舒服和熟悉感在一屋子人里面蔓延开来。
我们开始自我介绍。现场的能量非常的亲密和放松,我昨晚的微微颤抖完全被抚平,我想好了一套说辞和嘴脸,突然完全忘了,我立刻全然的相信了现场的每个人,不打算说谎或者掩盖什么,我有一种把自己交出去的感觉,很脆弱,但是很安全。
下午开始做拙火的启动,我们跟着胡老师的节奏快速的呼吸。很快我整个人要麻死了,手脚胳膊都感觉有一股热流要冲出但被憋着的感觉, 这时候一个助教老师过来开始“折磨”我, 他按了我胸口正中心的一个穴位, 立刻把我疼死了。我想忍一忍就过去了,他还要去折磨别人呢,不会在我这里太久,我坚强的意志力开始作用。。。
谁知道他完全没有要走的意思, 我也停止了跟随老师律动的呼吸。因为你在忍受疼痛的时候不得不停止呼吸。紧接着他的折磨越来越大力,特别怕丢脸的我决定喊一嗓子,表达疼痛。
我长啸一声:啊~~~~~,声音震耳欲聋,那种洪亮是我不熟悉的。
这一声“啊~”的同时,胸中有一股很大的气鼓鼓的轰隆隆的能量蹿通了, 那种感觉好像是很长时间便秘然后突然把一辈子的屎都拉出来的感觉。那个折磨我的助理继续用力,我就继续大叫,现在想起来还不可思议。每次的大叫都伴随三个阶段, 最初是某种“不好意思打扰到别人,很丢脸”,进而转换成“顾不了了,要死了”, 然后转换成“豁然开朗好爽”的历程。直到最后几次,我毫不胆怯的直接大叫,完全没有了最开始的自我审查和生怕给别人添麻烦的压抑感。
这个还真是我人生的写照, 我的好几个事业和感情的历程都基本会经历这三个阶段。
这里要感谢折磨我的助教老师,我其实都不知道是男是女,在我混沌的当时,您的形象是雷公电母版半人半神的大力士,哈哈
然后据说拙火就被启动了。我还傻傻的问胡老师:我们都启动了吗?她说:是的。我说:你怎么看出来的呢?她说:因为我知道。
好霸气!她当时说,”因为我知道的“时候, 我被深深的震撼。说来也奇怪,一般要是有人这么回答,我的内心一定会觉得:“故弄玄虚,没逻辑。什么叫“你知道的”, 你怎么知道啊, 问你你还不好好回答。”
但是胡老师这句”因为我知道“给我无限的安定感和扎实感。没有任何的Drama和权威或者炫耀,就事论事的那种感觉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这个是胡老师给我最多的感觉,那就是她在说一个具体的事儿,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管内容有多么玄妙(比如她讲了一个人的神通,可以用手指一动群山,事后我觉得哇塞这么不靠谱儿的事儿,当下的感觉是如此的真实可信),她都是以一种最真实和不自我的方式来告诉你。 她的这种当下的真和没有造作的状态, 打消了我多年来的每秒钟以光速分析每一件事物的能力(恶习),我常常在上课的过程中发现, 我的脑子没有在飞速运作了,我好像被她的安住当下的强有力电波罩住,从而屏蔽掉了我的一些神经质习惯。
有两个时刻我想给大家讲一下。
第一个发生在我个案的时候:
到了我的个案的时候,我差点要紧张死了, 我进入了一种懵逼的状态。如果之前是老师的presence让我感觉到了头脑没有意思念头的清明感。那我自己做个案的时候就是也没有念头的完全懵逼感。
一方面我怕家排,因为我内心深处觉得我可能会家排出来很多特别狗血的家族秘密(虽然我的恐惧没有事实基础),另一方面我怕胡老师不喜欢我, 我所有的自信都没了。我觉得一个这么可爱的少女+高人老师要是不喜欢我真的可以去死了。
神经病如我,提前准备了17个问题。
胡老师看了看我的星盘,直接说:你不要这么紧张, 你现在要紧死了,咱们班的人都很紧,但你是冠军。
我微笑着,内心有种不安:完蛋了!胡老师不喜欢我,啊我那么喜欢她她却不喜欢我, OH NO!
胡老师紧接着说了一句话,吓死我了:没有人在批判你,我没有在批判你,你放松。你虽然听起来很温柔还面带微笑但是你紧缩的要把我脑袋弄破了。
天啊,胡老师真的是有神通,我一闪而过的念头,我多年奥斯卡级别的演技,完全没有唬住她。她直接跟我的头脑里面的真实状况对话。
反正我是服气了,我马上进入打坐的状态, 深怕自己的紧张把胡老师心脏弄坏。
胡老师说:你太完美主义了。斯科特·派克的著作《邪恶心理学》(people of the lie)里面说了一句话:完美主义是邪恶的种子,你得知道自己是凡人,不要把自己当神。
我问:这是我爸爸妈妈的问题吗?(因为我热爱责怪自己的原生家庭,觉得基本上都是他们的问题哈哈),她坚定的说:不是的, 你这辈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的, 你带着之前的习气,不是原生家庭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全国人民从上一代到这一带都有完美主义倾向,不光把自己当神,还期望自己的孩子是全能的,一味的责怪父母真的让我们变成跟父母一样面目可憎。
我有一些释然也有一些不甘,我责备了几十年的父母这么简单就理清关系了吗?这个念头产生的那一刻, 我突然看到自己的所有问题。不是脑子看到,脑子层面我早就分析了一百遍了, 而是一种从身体中心里面生出来的一种”哦~~~~~“ 的感觉, 层次很丰富,信息量很大,脑子根本来不及分析。那一刻包含了一种很深的对自己行为模式的洞察,一个巨大的结被看清楚,背后的不负责任和卑微、恐惧突然曝光,而头脑是没有一丝想法的,这种认知的方式我从来没有体验过,简直像做梦一样。
然后老师说:交托,那个能量大于你,你反正也达不到它的标准。不臣服于更高的力量,你想要达到一个比天还高的标准,你内在都不谦卑不臣服。你把标准放掉。发展处女座的正向特质:尽力而为,精益求精。(我北交双鱼南交处女)
这个时候,所有我之前遇到过的灵性的老师告诉我的,”你不臣服“突然就 make sense了, 我突然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了, 我从内心最深的地方看到自己在较劲儿,在跟宇宙较劲儿,一副”上帝您最好来我面前“是骡子是马溜一圈”的样子。包括来工作坊也是带着意思想要“鉴定”胡老师的靠谱程度的。
这种make sense的感受真的很爽。也让我前所未有的放松, 似乎之前我一直提着一口气,大气不敢喘的活着,但现在我感大大方方的呼吸了,我没有背景式的难以名状的焦虑了。这种感觉持续了很久,一个月后回到婚姻生活才又起了波动,婚姻真是照妖镜啊。
第二个时刻发生在结束的时候,7天下来大家都精疲力尽,(我们每天基本12个小时的纯课程,不包括吃饭休息上厕所的时间), 胡老师还是神采奕奕超级有爱的在那里,完全就是一个神奇的存在。在同学们跟她一一道别的时候,有一位同学(我给她起名叫神婆,因为她特别敏感而且总是出演大家族女性大咖的角色)给胡老师行了一个大礼,突然我内心的感激和爱如泉涌,我从来没有那样哭过,我一方面谢谢这位同学给胡老师行了一个我们都应该行的大礼,一方面觉被胡老师彻底打动,她真的没必要出来这么辛苦的做工作坊,她的爱心和慈悲把我的心脏锤的完全碎裂,在这种碎裂中我感受到了某种光一样的的柔软和力量, 我的眼泪完全是往外喷的,像消防栓被砸坏了那种喷射,这样持续了大概10分钟,我的衣服全部都湿了。我的语言如此的笨拙,不能表达当时内心获得的震撼和力量。我只能说,这一刻之后,我有了莫名的坚定和使命感。
其实还有好多精彩的内容,但是这已经写这么长了,下次更多内容的分享我换个方式。
这个工作坊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礼物,以我完全不了解的打开方式,展现给我。祝福每一个想要去参加的同学,向我一样有这么巨大的收获和感激之情,谢谢寿文帮我报名这个工作坊,也谢谢胡老师这么美丽的优雅的慈爱的聆听我们的苦,点化我们。

完美主义|陈琪莹
作者:陈琪莹
时间:2015年1月13日
完美主義(重貼補放)
「完美」,是不肯對自己鬆手,是不肯信任「等待」、不肯信任成長的步驟與過程--利用跳躍來一蹴可及。「完美」是頭腦的想像,頭腦中的「完美」屬於一種停止/靜止(有限),如此何以適用於無限﹖
「完美」,要因「完全」、「完整」而「美」,因此無法容忍缺憾,也看不到缺憾的美--事實上,「殘缺」才容許成長、修復、進步;「完美」等待著的就是之後的萎縮與凋零。生命是流變,不會允許停留/停滯在同一狀態下太久。
所以,「完美」實際上是「死亡」的同義字,只是名相上比較順口、好聽罷了!
那麼追求完美,其實是骨子裡相信自己無法「重生」、無法「再度擁有(任何或修正的)機會」,所以逼迫自己要在自己的「『有限』之內」完成,所以非常的物質,也非常地受限於物質。
完美主義之所以那麼為物質主義與工業主義所推崇,是因為它們也看不到未來、也相信不了未來,所以傾全力用人為的控制與作為來防範事物失控。但「瑕疵」之所以存在(如同「完美」)正是因為有個可堪檢定/檢視的標準在,因此被定義/歸類成「瑕疵」(或「完美」)。別忘了!「標準」本身就是限制;既有限制,就不可能完全、完整。所以「完美」真的是人類的異想/臆想:真正的完美必須無限,有限就無法完美。
那麼要求完美,就要看到自己的恐懼於「未知」與無法容忍「已知」。
完美也是因為你的焦點在外,你介意外在對你或事件的反應:你的「做」為著外在的成分遠大於為著你自己。因為外在因素強於內在因素,完美主義的你會完全無法忍受別人的愚弄與恥笑;也因為內在的高標,如果別人無法完成這樣的要求,你也會輕視、貶抑對方。抱持著「完美主義」也暗示著你欠缺著對別人的同理,甚至是你對自己的同理。
會完美主義,也是肇因於這是個太過強調智性的世界,因此你內在「思惟」的作用力大於「情感」太多,思惟的力量只能止於骨骼系統,無法進入肌肉,所以即使用了力,也無法讓四肢進入一種有彈性、和諧的精熟--智性元素只能驅動骨骼系統;然而骨骼系統的運作非常需要肌肉的支持,肌肉需要星芒體和自我體力量的灌注,可是這種灌注非有「景仰」(「向上仰望」的態度)的對象不可,無論是宇宙、宗教、或是人物典範,而且要活生生。這種景仰能讓肌肉與骨骼系統之間建立起正確的接觸與支持。標準再怎麼高,都是死亡的,所以無法讓自我體與星芒體灌注的力量真正進來或大量進來;完美主義者,實際上是用骨骼系統在對外作動,因此缺乏彈性與包容力。
思惟本身是外在乙太的反射,是世界乙太的一部分,所以你所認為的「自己的思惟」,不見得真的是你的(思惟),反而可能是環境/時代整體的(思惟);當你完全被思維主導了,你就不是自己身體真正的主人。
補充說明:很多想法、發明幾乎都是同時性也雷同的,這不是關係著誰抄襲誰,而是大環境/大時代的氛圍下,讓思惟性的乙太熟成到了相當地步,因此在時間點前後分別在不同地域萌生而已。所以世界上也沒有真正的「發明」,只有「發現」而已。
孩子的會完美主義,是因為著父母親(父母親是孩子最貼近的乙太環境)。父母親那雙無形的、監視著的眼睛,會讓孩子將完美主義的情結內化成自己。土相與火相的氣質比較會導致完美主義。
讓感覺出來!把焦點放在當下。沒有對錯、沒有優劣,就在事情裡。所有的注意力都在事情的「做」上。如果要幫助這樣的孩子,父母「全然的『在』」相當重要,你在對孩子的陪伴裡,沒有三心二意:你跟著孩子進入事件、進入事件的「做」,就只是「做」,沒有批判、指導與矯正。事物會帶你們進入感覺,情感就會出來,而情感就只純粹是情感,這會幫助你們放掉外在的尺規、放掉標準的高低--你們將知道:自己的感覺才應該是事情唯一的標準,而不是虛擬的目標。
山毛櫸(Beech)和岩泉水(Rock Water)花精能幫人釋放掉過於嚴苛的要求(對自己或對他人),也幫忙打開部分的自己、學習同理別人。
野兽按:2019年2月26日在我的简书上转载过一篇江雪的专访《江雪:自由是一种生活方式》,但几秒钟这篇文章就被简书给河蟹了。但从此我也记住了江雪,在网络上搜索过一些她的文章来阅读。
后来在朋友圈里分享她的文章时,有个朋友告诉我江雪是她的前同事,原来是《华商报》的首席记者。2020年4月5日晚上在听matters系列讲座的第二期郭晶的分享时,听一位matty提到当天端传媒发表的江雪文章相当好,于是立马找来阅读。并分享给诸位墙内的朋友们。
之后找来了江雪所有公开发表的文章细读,非常欣赏她。今天在宋石男的公号:默存格物 里读到了江雪的新文。才知道她在西安,并写下了封城十日的所见所闻。之后在朋友圈看见宋石男附上的江雪打赏二维码,立即打赏。

我的封城十日志
文 | 江雪
小区里的大喇叭又响了起来,一遍遍重复着,喊人们下楼做核酸。队排了很长。测核酸的女生,每做完一个,都使劲地用消毒水拍打着自己的塑料手套。我闻着那冰凉的气味,想象着她的手已冻成青紫。
这是2021年12月31日。旧年的最后一个黄昏,暮色即将降临。从阳台上看出去,大街上空寂无人。这城市不再有车水马龙的傍晚,死一般的寂静让人感到荒谬而又有一丝恐惧。
1 封城当日
12月22日下午,西安封城令宣布当天。我闷着头在南郊的家里编稿子,隐约感觉到疫情变得严重。家门口的一些餐馆几天前就被贴了封条,门口的便利店前一天已不再接快递,生活开始不方便。三点多,朋友随喜微信留言,说还是去买些菜吧,储备一些食物,马上超市都要关门了。我相信她,她是资深的公益人,有多次远程救灾的经验。于是立马出门。
到超市就发现情形不对。虽然当天的新闻发布会还没召开,傍晚的大抢购还没开始,但人们的购物车都塞得满满当当。我决定多买一些,共享单车是驮不回去了,最后还是用车载了回去。
果然五点多的新闻发布会上,下了“封城令”,虽然政府说“物资供应充分”,但人们已开始抢购。我因已买好东西,心里比较笃定。忙完了,出去转转。路上看到,高新区的沙井村村口,聚集了一大堆人。整个村子外面,沿路边有两三百米,都已被绿色的板子隔了起来。
从天桥走到路对面想看看详情,这才发现,有一家正在营业的商店,也被隔在了挡板里边,暂时还灯火通明。我站在天桥的台阶上,和老板打招呼。他告诉我,下午紧急封村,商店过一会儿就得关门了。
村口聚集了上百人,人们都戴了口罩,摩肩接踵,没有其它防护。路边,有一辆警车,闪着灯,车上没人。
一个年轻女人,买了一堆东西,塑料袋胡乱放在地上,正蹲着给家人打视频。一个中年男子,靠着自行车,发愁地看着人群。他告诉我,早上他出去干活时还好好的,晚上八点下班回来,就发现村子封了,进不去了。他告诉我,一个月的房租是500元。
我知道那种房子。20年前刚毕业,我就住城中村,大约10多平米,没有卫生间,在楼道里做饭,采光不好,黑咕隆咚的。
两位清洁工,手里拎着塑料袋,大约也是买了点生活用品,站在人群里,黄色的保洁服很显眼。问他们,说是下午四五点出去干活的时候,还能出来,晚上干完活回来,就进不去了。
很多年前我做过保洁员的报道,知道他们租房,只能在城中村,因为他们有推车、扫把等工具,就算租得起楼房,也没法住。当年报社附近的黄雁村,就是保洁员们的一个聚集地。后来那里整体拆迁,盖起了楼,他们也就失去了一个落脚的地方。
我陪他们站在路边,感受着他们的无奈。年龄大的一位很胆小,生怕说错了什么。年轻的那位,却始终笑着,对我不时点着头。口罩后是黝黑的面庞,我能感受到他笑容的温暖。
一忽儿,隔离板接口的地方,人群一阵骚动,似乎开了一条缝。听人们说,现在村里的领导正开会,还在等说法。两名保洁员也赶紧凑了过去,一会儿又失望地散开。看看手机,已将近晚上十点。人们聚在这里,在寒风里至少已等了两个小时。
几天后,看到网上说,住在城中村的一个年轻男人因封城吃不上饭,饿得大哭。我就想起这个封城夜。不知道这个男人是否也住在有几万人的沙井村,也曾在那一晚被堵在村外、一脸茫然。
又去了几个地方,然后回家,此时大街上已空荡荡。吉祥路上,俗艳的红灯笼挂满了路边的梧桐树。有人站在路边,拎着大包小包。高新路上,骑摩托的外卖小哥小吴正赶着送零点前最后的餐。他说,虽然封了城,人总要吃饭,商场里的一些餐馆应该会开门,会有单子跑。说话时他还笑嘻嘻的。
那时候,我们还没想到,这场“封城”,会如此仓促不堪,朝着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这个夜晚,那些被堵在家门口的人,超市里抢购的人,孕妇、病人、考研学生、建筑工人、城市流浪汉、路过西安的旅游者……可能都低估了这场“封城”将为他们带来的灾难。
而那些为这座城市按下“暂停键”的人,那些手握权力的人,他们又可曾想到,他们将怎样影响居住在这城市的1300万人的命运?如果这不是比天还大的事情,那还有什么是呢?
2 残存的市场
至少在封城之初,一切似乎还说得过去。很多社区门口的超市、蔬果店,遮遮掩掩都还在经营。虽然人们的流动已停止,但基本的生活供应还在运转,不过慢了许多。
我所在的小区,院子里每两天做一次核酸。大门虽不能自由进出,但物业开个“出门证”,也就是一张小纸条,就能出门。据说隔离政策是“每一户两天可以有一人出去买菜”。
我并不需要外出去买菜。一来还有储备,二来小区旁的便利店还开着,勤快的老板娘隔着栅栏记下大家的需要,不管是蔬菜米面油,还是生活用品,配好货,再递进来。12月25日,下雪了,有蔬菜车停在了小区门外,菜很新鲜,还有鲜肉,邻居们自觉地排队去买。一位女士在人们羡慕的目光中,抱走了自己订的一大束鲜花。
没有人能预料到,仅仅过了两天,全西安人都开始在网上找菜,全民买菜难。在这样一个物质过剩、人人都要减肥的年代,吃饭会突然成为一件难事。
12月26日,封城后第四天。在网上看到消息,说大家最近都在关注的湘西田田老师回家了。为田田老师高兴的同时,我想起了一位年轻的律师朋友,他的妻子,此时也在网上呼喊,盼着丈夫能回家。但她的声音实在是太微弱了。
心头憋闷。我决定以买菜之名出去转转。
拿“路条”出了门,在积雪未融的街道上扫了辆共享单车,享受这难得的自由。大马路上,公交车还在跑,但并没有人坐。某个站台的躺椅上,躺着一位流浪者。大街上,不时掠过外卖小哥、快递员的身影。
路上警车不少。出来十分钟,大约看到四五辆警车。
平日经常去买菜的甘家寨村口,用挡板遮住了。板上贴了好几张纸,歪歪扭扭写着“调料”、“辣椒”、“榆林豆腐”、“土猪肉”字样,都留了电话。有两个男子,就隔着挡板,一手交货,一手扫码付账。
这是一个庞大的城中村安置区,也是周遭一个著名的集市。每到傍晚,村里灯火通明,红尘万丈。好几个快递公司的服务站都设在这里。和周边社区相比,这里衣食住行,自成一统。虽然封城,但村里的好多小餐馆还开着。此时,社区的围墙外站着一溜儿外卖员。不一会儿,就有餐馆的小老板匆匆跑过来,隔着栅栏把待送的餐递给他们。
一位外卖小哥正坐在摩托车上玩手机。我和他聊了一会儿。
小哥姓刘,今年29岁。老家在宝鸡。他说,22号那天听到要封城,想赶紧回老家,结果一问,回老家就要集中隔离,隔离费还得自己掏,一天得210元。太贵了,他决定还是留下来。但他租住在沙井村,村子已封了,他也回不去。
没办法,他就住酒店,因为这样可以自由进出,还能继续跑单。而大街上的酒店,最便宜的是每天150元,他和人分担。这些天,开门的餐馆少了,单子少了,但外卖员也少了,所以他每天还能跑三、四百元,甚至超过了他此前的日平均收入。
几天后,看到新闻,老家在咸阳淳化县的一个男人,封城后,为了从西安回家,蹬了一辆共享单车,在零下六七度的关中原野,从晚上8点骑到早上6点,将近90公里,在接近老家时被防疫人员“抓住”了,罚款200元。还有一个年轻小伙,为了回家,从咸阳机场走到秦岭,又在山里走了八天八夜,一直到了分水岭附近的广货街,被人发现。
我又想起了小刘。不知道后来“管控升级”,他还能出来吗?即使能出来,又有单可跑吗?一天150元的住宿费,他又怎么承受?后悔那天没有留下他的电话。
3 管控升级
12月27日,突然听说全西安“管控升级”了。小区保安说,原本执行的“两天出门买一次菜”,已经作废。从今天开始,任何人都不能进出小区。
28日,全网都在呼吁“买菜难”。我所在小区门口,大门紧锁,物业的人不再让大家在门口停留,在栅栏内登记买东西。我扫码加了门口便利店的群,这才发现,这可能是我接下来唯一可依靠的生活补给渠道。
后来想想,道理其实很简单,如果所有的人都不能出门,那外面物资再丰富,宣传再好,其实也和普通人没了关系。
便利店的群里一片混乱,已有400多个人。人们都在找吃的,抢吃的。老板娘规定,每天“接龙”只能限于早上一个小时,但每个刚进来的人,都要先抢接龙一番,自然被老板娘一顿训斥。
翻了翻群里信息,看到小区里有年轻人在求助:“谁能卖给我一幅碗筷?到处都买不到。”我留了话,让他十分钟后在楼下取,然后给他收拾了碗、碟、筷子等一套餐具,送了下去。
隔着绿化带,问了一下小伙子的情况。小伙说,家在附近,公司在这边,封了后回不去,但办公室从没有开过火,所以啥都没有。他好不容易弄到了一个炖锅,但又没有餐具,也没地方买……作为感谢,他带给我一点零食,包括一袋鸡肉肠,一小包士力架,还有一盒特仑苏奶。
第二天,情形更糟糕。看到群里有两个年轻人说,已经吃了一周泡面,嘴都烂了。一个说,她现在所有的库存,只有两包方便面。另一个说,自己已“弹尽粮绝”。
我留言给两位年轻人,说第二天中午,我给他们送一顿盒饭。一位谢绝了,另一位答应了。临睡前,我取出了冰箱里的一块牛肉,想着第二天给这位姑娘做西红柿炖牛腩。没想到,第二天她留言,说自己有吃的了,不用给她做了。再三邀请,她还是说算了。猜测她是因为自尊,或者还有一丝戒备,就没有再强求,只告诉她,有事可以和我联系。
我也开始数着自己的库存过日子。看到邻居说天天做油泼面,为了省菜。就送去了四朵香菇,两个西红柿,一个西葫芦。再加上一桶我封城前买的啤酒,挂在她家门口。她挺开心,回赠我几个甜脆的苹果,我求之不得。
此时,看到网上说很多小区,邻居之间开始“以物易物”,拿方便面换香烟,大蒜换土豆等,哑然失笑,但我相信,这当然是真的。
突然进入了物质匮乏的状态,人也开始对食物计较。我老想去厨房看看,清点一下冰箱里的存货。封城已近一周,提前采购的食物,也少了一大半。想着再补给一些,但在便利店的群里,根本接不上龙,很多人说自己已在饿肚子,等吃的,央求店家能早点配货。我决定不去凑热闹,另谋生路。
4 人们的自救
从12月28日到12月31日,至少这四天,关于怎么买到菜以及生活必须品,也就是如何能吃到饭,大部分西安人只能依靠自救。
有外地的朋友好奇,问快递能送到吗。事实上,在12月21日左右,西安的快递已停,人们无法从外地网上购物。封城后,微信群里流传着一些网购平台,称疫情期间可以送菜。但我下单才发现,只要住在西安,就无法配送。平时常用的“盒马”,永远是“快递小哥已约满”。好不容易找到一家“人人乐到家”,下单买了些菜,但付账后两天,还没有动静,也就退了。
12月29日政府新闻发布会的直播,评论区被“买菜难”攻陷,结果干脆关闭了评论。
我和几位朋友在一个志愿群里讨论。他们都参与过各种救灾,经验丰富,都不约而同地说,这次在西安,要做点事,实在太难了。封城之初,他们就组织了线上线下几千名志愿者,但却没法发挥作用。政府“一刀切”关闭了所有小区,通行证又非常难办,志愿者根本没法离开居住地,到一线服务。这也是他们多年来都没有遇到的情况。
其实很容易想到,我们这些小区居民还是幸运的,家里一般都会有点余粮,不至于马上挨饿。最悲惨的是老旧小区,城中村、建筑工地等一些“三不管”地带的人。难以想象的是,那些平日在公司上班的年轻人,封城后也成为吃饭最难的人群之一。他们平时不做饭,没炊具,有的就住办公室。此时外面餐馆关门,外卖停止,连大门都出不去,方便面都成了稀罕物。
12月30日晚,气温零下。在一个小群里,朋友留言,刚在街上给流浪者送完餐回来。这位朋友热心慈善公益,与人合作,十多年如一日,坚持为西安街头流浪的赤贫者提供食物。这几天,他在南郊的工厂为流浪者准备食物,然后送去城里,一晚上送了185份热饭菜。他因有通行证,倒没有什么阻碍。
封城前,我曾参加朋友的活动,给流浪者们送过一次棉衣。知道他们平时主要在市区的银行、ATM机下等地方避寒过夜。如今封城,他们一方面被驱赶,另外,因为街道上没人,不管乞讨还是拾破烂,都没了条件。对他们来说,这注定是一个极为艰难的冬天。
元旦这天,我和好不容易有点空闲的张姐聊了会儿天。她做公益机构已10多年,原来为残障者服务,近三四年投入社区工作。这次疫情,她一直在和社区合作,链接资源,参与了很多救助活动。
张姐告诉我,遇到封城这种极端情况,社区邻里自救非常重要,类似独居老人、孩子等人群的特殊需要,有人没吃没喝等,一些燃眉之急,邻里互助完全可解决。包括在一些重大危机发生的时候,社区内的自助自救都是不可缺少的。但目前的情况是,社区不做这些事,人和人相处如在孤岛。在这块儿,原本公益机构可以做很多事,在社区耕耘建设。但这一点,往往又被政府忌讳。
说到目前到处吃菜难的状况,她比喻,类似于把大家全圈起来,再由政府工作人员去“投喂”,试想在上千万的城市,怎么可能实现?一个社区有两万人左右,基层工作人员一般不超过十个,光各种行政指令都忙不完。她感叹说,认识到的社区工作者,以年轻女性为多,很多也都是母亲。这些天她们根本回不家,都是超负荷运转,很多人就打地铺睡在办公室,让她都觉得“心疼”。
“政府还是没有认识到,行政力量不能解决所有的事情。就像这次防疫,基层工作人员这样没日没夜地辛苦,效果又如何呢。”我们聊着,不知不觉过去了一个小时。
5 我们的建议
12月31日上午,我终于买到了疫情以来的第一箱菜。说起来还是通过邻里互助。我在小区微信群里看到卖家的海报,发现价位比较合适,108元一箱,一箱20斤。赶紧下单,第二天就送到了,还挺新鲜。
此前,网上已曝出不少新闻,政府的免费菜发到了一些小区,但网友追查,一些自称保障丰足的小区都和政府有关。与此同时,住在曲江的朋友开始收到“爱心菜”,不少人开始发“正能量”。但我的判断,即使政府送温暖,一时半会也到不了我们手里。道理很简单,市场停摆,全市日常的物流配送都停着,1300万人的大城市,靠基层工作人员、志愿者短期内送菜上门,可能吗?
取到菜,问了老板两句。老板说菜是从宁夏调来的,调了5000件。因为前些天办不下通行证,没法送。只要小区的需求在5件以上,他们都愿意配送。“市场永远比政府聪明”,这是句老话了,此时此地,我才能感同身受。
事实已经很明显,持续多天的“卖菜难”,本质还是人为灾难。在西安,并不存在物资匮乏,只是物资难以送到最需要它们的人手里。看到很多自媒体文章,有一篇,作者叫兽爷,一语中的:“我们有天猫、京东等那么强大的物流系统,政府为什么不用?非要自认为聪明地自己去送菜上门?”
天天看着朋友圈,微信群,内心被各种信息轰炸。随着管控升级,每天都有坏消息传来:高危孕妇无法去医院备产,肾移植后急需用药的病人无处买药,农民工在关门的建筑工地上无法吃饭,考研学生滞留街头挨饿……因防疫管控而引发的各种次生灾害频频发生,再下去,并非没有爆发人道主义灾难的可能。
12月31日,一早和朋友们聊,讨论该怎么办,和随喜等朋友形成了一些建议。我决定,以市民个人的身份,先把这些建议发出去。这份“西安一位市民关于解决吃菜难问题的紧急建议“中提到:必须逐步恢复市场秩序。首先恢复末端物流系统,让菜贩、果蔬店、超市等能进入小区供应,包括让各种救命药品进入居民手中等。并且鼓励社会力量进入救助系统,鼓励民间自救等……
最后,还是决定不署名,为的是不被贴上“标签”,只让市民的心声能表达出来。但天知道,我心里是没有恐惧吗?朋友敏涛前两天写了几篇日志,就是呼吁解决“卖菜难”的,文章发出两天,就找不到了。我熟悉的一家平台,已开始刪掉西安疫情的所有“负面“…
6 “西安只能胜利”
2022年的第一天到来了,一大早,拉开窗帘,晨光熹微,街道依然沉寂如荒原。
我拿起手机,本来是想写一点新年的心情,随手点开一个视频,却看到在距离我不远的南窑头社区,一个外出买馒头回来的小伙子,在社区门口被防疫人员围着殴打。
画面上,白花花的馒头洒了一地,我仿佛听到自己心碎的声音。打人的人,面对自己的同类,这寒风里买回一点食物的人,怎么能下得去手?是哪怕最微小的权力,也会让人变异吗?是在有权者眼里,暴力才是成本最小的解决方式吗?我默默关掉了手机,此时此刻,我只希望自己闭目塞听,能平静地度过这新年一天。
这城市表面的寂静掩盖不住它的兵荒马乱。从个体角度来看,从12月27日以来,几乎每一天,都有灾难发生着。最初是各种吃不到饭,后来更多的是关于治病就医的呼救。我过去呆过的报社,成立了一个“记者帮”的栏目,希望“帮一个算一个”,记者去帮市民买药送药,解决一些实在过不了的关口。每一天,收到的求助信息有上千条。
新年到了,我所在的小区内,家家户户门上都贴了封条。因为另外一栋楼上有两例确诊病例的人,听说按照最新的社会面“清零”政策,如果再有病例,我们小区的住户,就要全体被拉走集中隔离。
在小区单元群里,我简直能感受到大家都在瑟瑟发抖。12月31日半夜,被全体拉走集中隔离的糜家桥小区,就在我家附近。而明德门8英里小区被拉到灞桥公租房集中隔离的人,已在求助。我们至少还是在自己温暖的家里啊。此时,不再需要物业提醒,单元群里,大家都在加油鼓劲:先停止一切购物、下楼,一定确保安全,否则,全小区的人都要被拉走集中隔离啊。一位邻居最担心的是家里养的五只猫,其中三只,都是一线防疫人员寄养的啊……有朋友提醒我,还是简单准备一下,以免真的被突然拉去集中隔离。
1月3日,又一天过去了,群里有人说:“终于又保住了一天”。我们就这样活在“盛世”。
中午,看到网上流传着一个叫“太阳花花花”的女孩的消息:她的父亲心脏病发作,费劲周折出了小区送到医院,医院因为她所在的小区是“中风险”,先是不接受,后来勉强留下,拖了几小时,要做手术抢救,但终于没有抢救过来……
我通过小红书去找这个失去父亲的女孩,我想知道,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她到底遭遇了什么。如果有机会,我想抱抱她。也想告诉她,我们遭遇的苦难,应该被记录下来,也不应该白白承受。
我留言希望这个女孩能和我联系。但到傍晚时分,也没有消息,却发现她小红书上第一页关于父亲去世的内容,已被删除。好在我截了图,那上面显示,有很多人已关注她。评论中看到一条,大意是:在这荒谬的城市,只要不是死于病毒,就不算死亡。
1月3日的黄昏又降临了。这是封城后的第十天。我没有等来小红书上女孩的消息,却看到了一个曾经熟悉的朋友留言,一大段话,大抵是为“社会面清零”叫好。末尾有一句是:“西安只能胜利,别无选择,没有退路。”
我很无语。默默地把那个女孩讲述自己失去父亲的遭遇截图发给他。说真的,我不想和他产生任何的辩论。
但最后,我还是忍不住发去几段话。
“‘西安只能胜利’,这是正确的大话,套话,也是空话。与之类似的,还有‘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这句话是不错,但具体到每一个普通人,我们可能要想一想,在这里,我们是‘我们’,还是要必须被付出的‘代价’?”
“事件过后,如果没有反思,不吸取血泪教训,忙着立功摆奖,歌功颂德,那人们的苦难只能是白白承受。”
我不打算再见到他。但我想告诉他,这个城市,不管最终如何从宏大叙事去讲述这场苦难,在今晚,我只关心那个失去父亲的女孩;关心那个流着泪,去找一个陌生的防疫人员要卫生巾、一遍遍诉说的年轻母亲。以及那些被羞辱、被伤害、被忽略的人们。他们原本不需要遭受这样的痛苦。
我也想对他说:这世间,没有一个人是一座孤岛,每一个人的死亡就是所有人的死亡。病毒没有在这城市带走生命,但别的,却真有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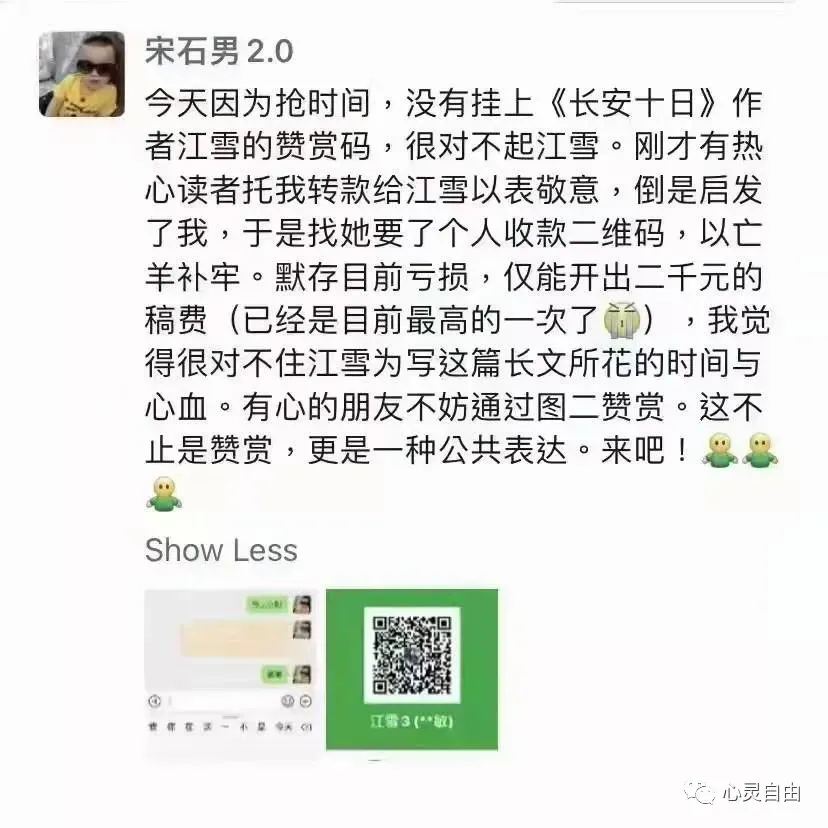

专访 | 江雪:自由是一种生活方式
采 | 王伊文 徐畅
编 | 张颖钰
编者按
这是一篇投稿。
江雪,原《华商报》首席记者、评论部主任,财新传媒调查记者,现为独立媒体人。代表作包括黄碟事件报道、“星火案”系列访谈、中国律师系列访谈等。
二十年前,出身法律专业的江雪想做关乎公共利益的工作。因偶然看到一句“我的透明的华商报”,她转行做了新闻,“做一份让民众喜欢的报纸”。
回忆起自己的记者生涯,江雪认为2003年具有启蒙意义。刚入行时,她对业务的理解还是“信息采集员”, 2003年的孙志刚案报道、SARS报道、“黄碟事件”报道重塑了她的认知,“做一个记者其实是可以和这个国家的脉搏同频共振的”。
2015年,江雪脱离机构,成为一名独立记录者。她开始关注自己真正感兴趣的议题,记录宏大事件中小人物的故事。在她看来,记者不仅是职业,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每个时代遇到很多的挫折,大家行动着会有一种无力感,但是对个体来说,对抗无力就是你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我的透明的华商报”
Q:你本科是学法律的,为什么后来去了《华商报》工作?
A:我毕业后本来是在国有企业做法务,当时我父亲希望我回到家乡,做一些更安稳的工作,但我希望做的事情是跟公共利益有关联的。那时候不得已去做法务,但是知道自己肯定不会在这个地方久留。
我想着不行就读一个中文研究生,因为喜欢写作,上大学之前就想读文学。读研究生需要报名嘛,我骑自行车路过,正好看到报社在招人。那时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他们的广告,他们做了一个街边广告,放在大的玻璃里面,叫“我的透明的华商报”。
我第一次意识到,噢,报纸可以是透明的。96年、97年那时,市场化媒体都在发展,他们都有这种意识,做一份让民众喜欢的报纸。那时候我对媒体的功能都没有什么认知,反正知道报纸上肯定可以写作啦,然后就去应聘,很顺利地就去那了。
Q:你不是科班出身的,当时转做媒体会不会有一些困难?
A:我倒觉得做记者不需要科班出身,学法律还挺好。其实我后来回望的时候,我觉得做记者最重要的素质还是问题意识。一开始当然没有那么多问题意识,只是记录事件和现场。但是慢慢地,当你想做一个好记者的时候,就要有问题意识。重要的是你在一个领域要建构起大体的框架。
我最开始是在社会新闻部,这种其实是最锻炼记者的,因为你要跑很多突发新闻的现场,这个过程也会锻炼写作,你要写消息,还要满足新闻五个w的要素。
Q:那时报纸的运作模式是怎样的?
A:这要讲到1990年代的中国报业市场化改革,一批报纸应运而生,发展到2000年,各地都有一份比较强势的都市报。国家不给它们拨款,报纸要自己养活自己,必须要有公信力,才会换来广告,换来订户。也是在那个时候,很多这样市场化的媒体发展起来,我所在的这份报纸是其中之一。
《华商报》很快成为当地最强势的报纸,一直占据后来十多年的市场。当时这份报纸的宗旨是,提供真实的新闻与信息,把普通人生活中的问题放在重点位置。
那时候的报纸都有跟读者互动,每一家报纸都设置热线电话,读者可以提供新闻信息,线索一经采用都有奖励,一条新闻线索最少奖励五十块钱,在当时还是比较多的嘛。如果有好的新闻线索,还有千元奖励。
所以我所在的报纸,大概一年多就发行到了四五十万的份额,成几何倍数增长。那一拨市场化媒体都有野蛮生长的经历,因为公众还是有信息的需求,只不过以前没有载体或管道,这种报纸出来以后很快形成比较暴利的盈利模式。有了钱以后他们慢慢建立记者队伍,也会投入到深度报道等给他们增加公信力的形式。
“记者可以和这个国家的脉搏同频共振”
Q:你之前说记者就是“信息采集员”,后来你对记者的职业认知发生了什么变化?
A:刚开始做记者,其实就是信息的采集员,但是天天去做信息的采集员,你会不满足嘛。见过那么多悲惨的事情,背后可能是社会机制的问题,当然这中间有个启蒙的过程。2003年对很多在今天还关注公民社会的人都是非常有转折意义的一年,比如说孙志刚事件的报道、SARS报道等等。
那时候我做了“黄碟事件”的报道,我是学法律的,我就从中发现公权和私权边界的问题。这个事情其实是警察权被滥用,警察权代表公权,个人权利其实是私权。从法学的高度就是法无明文授权不可为,行政机关要做什么事,必须要有法律的授权,要通过行政、立法相关的程序。对私权来说,就是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只要法律没有禁止我做的就有权利去做。
Q:说到“黄碟事件”,你后来做了《死囚枪决前4分钟 最高人民法院急令枪下救人》,这也是一篇和法律有关的报道。
A:这个事件也是有意义的,它涉及到死刑,后来从事件本身延伸到死刑复核权。死刑复核权有一个收回最高法院的过程,最初死刑的复核权下放到省一级法院,后来北大的陈兴良教授专门写过《中国死刑检讨》,就是用我那个案例做分析的。这些对我来说都是一些很早期的跟法律相关的一些新闻,我觉得还是起到了一定社会意义。它可能不是什么很成熟的新闻作品,也很粗糙,但还是起到了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
那是一个草莽的时代,我们都没有什么特别强的新闻专业主义的训练,是带一种朴素的人道主义思想。做记者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正义的角色,想让你的报道帮助别人解决问题,那时候有一段时间就会老被自己感动啊,认为自己做的事还蛮有意义的。那个阶段慢慢过去之后会冷静下来,有了问题的意识,你会更成熟一点。
Q:2008年汶川地震时你也去了灾区采访,做灾难报道和平时的常规操作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A:我是五月十七号去的。那个灾难太大了,十七号很多地方救援还是没有结束,还在找幸存者。我当时先到了青川、绵阳,然后又到了映秀那边。后来也有同行借这个机会,来写中国媒体记者应对灾难报道经验的缺乏,那么大灾难发生的时候,媒体人也是懵的。你到现场会发现到处都惨不忍睹,有的记者就直接说受不了,不能再做采访,会觉得你在采访是一件残忍的事情。
当时到了现场之后,我注意到一个志愿者的点,那一年也被称为志愿者元年,上百万志愿者从全国各地过去,这也是公民社会很重要的部分。我记得我当时看到了很多个这样的场景,每个地方都有全国各地的志愿者来帮着分发物资。
2014年鲁甸地震我也去了,发现跟之前就不太一样了,所有的志愿者都是安营扎寨在一个大院子里,会有为大家共同服务的NGO在现场工作。
有云南的公益人说,鲁甸地震的很多志愿者机构都是汶川地震之后成立的。汶川地震的时候志愿者都是自发的,很多人都是在飞机上发现彼此,大家比较随机地搭配。但鲁甸地震的时候,他们去之前就形成组织了,他们会在网上联络,彼此已经形成了一个志愿者的系统。这也是一个社会的进步,我们有了互联网,互联网帮助我们把群体连接起来,然后进行社会事务的建设。
Q:这些经历给你带来了什么改变?
A:不再像过去一样只是一个采集信息的人。你会慢慢地、隐约地感觉到,做一个记者其实是可以和这个国家的脉搏同频共振的,这个国家在进步,媒体人在中间扮演角色。作为一个记者,如果努力的话,你也可以发挥你的作用。那个时候慢慢会有一种自觉感,会有一种自豪感,觉得做这种事有更高的价值和意义。
转做独立记录者:自由是一种生活方式
Q:2015年你离开机构媒体,转做独立记录者,做出这样的选择会有什么顾虑吗?
A:其实当时我想着最多三年为期。我之前做媒体有点积蓄,其实也没有多少,只不过是说没有经费的支持,能暂时过渡一段时间。作为独立记录者,跟读者有比较密切的联系的话,还是会有读者愿意去为你打赏,支持你的。我觉得我就是一个独立记录者,来自民间,接受民间的支持是正常的。
Q:你的这种独立意识和小时候的经历有关吗?
A:可能有很小的影响。当我有独立思考的意识之后,我比较向往自由,对自己相信的东西就要去实践,我就会把它作为一个我的生活方式来实行,我可以让自己活得尽量像一个自由的人。
Q:如果受访者因为你不是机构媒体记者而对您缺乏信任,如何说服对方接受采访呢?
A:他们知道之前我写的一些东西,会对我有信任。他们知道我是关注他们这个故事,我也会写得很有人情,会有“人”,会尽量去记录下他们的故事。其实你之前写的东西都会成为你形象的一部分。
Q:成为独立记者前,做报道更关注事件本身?
A:之前还是关注故事本身,后来更多还是从故事的角度去讲。很多故事我还是从人物来切入,都是叙述人的。我觉得和大的历史的宏大叙事比起来,人的故事还是很让人印象深刻,能够引起人的共鸣。
Q:你写的《九一五西安之痛》,讲了重伤者李建利的故事,中间有很多他生活的细节,这些细节是怎么获取的?
A:主要就是跟他聊,他给我拿来一些照片,从中也可以推理出一些信息。因为细节就是作为一个有心人会去追问的。比如说我记得他弟弟说:“前几天有人要给我一个日本的什么东西,我都不敢用,不知道什么时候这帮人会冲进家里,说我用日本的一个什么东西。”
Q:您还关注了一些民间艺术家,为什么会关注到这个群体?
A:这些其实是他们有一帮艺术家到西安去折腾,有三百多个出租车司机在西安美术馆去看片子。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艺术家告诉我,他的作品并不是拍了这个片子,而是这三百多个出租车司机,第一次来到美术馆,实现了一次聚集。他们从来也没有见过面,从来没有进过美术馆。美术馆是一个公共空间。但公共空间没有发挥它的公共作用,艺术家为他们拍了一个纪录片,并把他们聚集到公共空间去记录,艺术家认为他作品最大的价值在这里。
我觉得这打破了我们观察的一些思维障碍,他会拐个弯,留一点东西在那里。艺术家们成了一个事实的挖掘者,但他们的方式会很含蓄,我觉得艺术的方式也可以是成为一种补充,在今天,各种领域方式方法的探索都挺可贵的,能够引导对公共领域的关注都挺重要的。
Q:看你三年来的新年献词,感觉你并不乐观?
A:我倒不觉得,我每次都是在悲观中还有一点点希望的。柔弱的生命的东西,慢慢它会长得像小草一样,不死的话它会长大。因为我觉得每个时代遇到很多的挫折,大家行动着会有一种无力感,但是对个体来说,对抗无力就是做你当下该做的事。
Q:如果要做一个独立记者,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基础?
A:我觉得还是要有非常丰富的非独立记者时候的经验:要有人脉,便于你找到你想要找的一些人;你要积累一定的口碑,别人会对你比较信任。比如说觉得我还是一个比较靠谱的人,可能我不是一个多么好的写作者,但同行也都知道我不是一个夸夸其谈的人,事实上我在转发朋友圈、转发消息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核查,这些东西是长期的积累,会让别人对你多一些信任吧。
直面最重要的问题
Q:你之前提到,新闻学院的教育其实是与现实脱节的,是什么时候有这种感觉?
A:我有一次到到高校跟学生交流,发现他们在讨论“异地监督”的问题,他们说异地监督是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其实哪有什么异地监督啊,媒体的报道也许只在本地发行,但当这个事件形成全国的影响的时候,读者也会关注外地事件,这里面也是有公共利益在的。
但那一次讨论这个事的时候,可能学院想当然地认为异地监督是不同省份权力之间的一种斗争。
新闻学院往往停留在概念,我们的问题是能不能报道出来,而新闻学院还在讨论得失的问题。当然不能说不讨论得失,只是当生产出的东西越来越稀缺的时候,你应该讨论的问题的本质,但他会去从一些细枝末节追问,这些可能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Q:谈到新闻学界与业界的问题,前不久,公众号“呦呦鹿鸣”发布了《甘柴劣火》一文,这篇文章使用的“综述”写稿方式引起争议,学界和业界都有讨论,不知你怎么看待这件事?
A:我觉得还是有洗稿的嫌疑,不管怎么样,你没有获得第一手采集的信息,你没有经过足够清晰地标注。当然他现在也迎合了网络阅读的口味,但是在这一篇文章引用的大量事实都是来自人家第一手的调查。如果援引得当的话,不至于被指责说有洗稿的嫌疑。
Q:这次争议也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传统的调查报道比较严谨,但可能在可读性上有所欠缺,这种矛盾怎么调和?
A:我不认为调查报道要写成“爆款”那样。调查报道还是要经过传统流程,信息核查,克制叙述,注定没法跟现在的新闻阅读习惯下那些爆款文章相比。搞成那样其实会损害调查报道的严肃性,对真正想获取信息的人,会影响他对信息的信任度,影响媒体的公信力。调查报道不会刻意迎合读者,但是今天的互联网时代,大众是喜欢那种加一些调侃式的,或者网络语言等等的东西。
Q:近年来非虚构写作比较流行,这类新闻作品通常比较注重可读性,想问一下你对非虚构写作是怎么看的?
A: 现在非虚构写作把玩文字搞得很精致,会自我感觉很良好。我是觉得不管怎么样,它的本质是你没有去关注最重要的问题。反正我没有那样对文字的迷恋。经过正统的新闻训练或者做调查报道出身的人其实不是很愿意做非虚构。现在很多人很迷恋非虚构写作那些东西,我觉得太矫情。之前《惊惶庞麦郎》那篇文章大家都很批评,它放大一些无意义的细节,带着一种恶意。你把一个小人物的那种尴尬的生活的情节放大,说他的头皮屑等等,有什么意义?那里面有很刻薄的东西,我不太喜欢那些东西。
Q:平常会看一些非虚构写作的作品吗?
A:其实是不太看的,当然有时候会觉得“哎呀有人写的特别好让我去看一下,看他的风格有没有可以借鉴的地方”,有的人确实文字是很精致啊。文字好了也是好事情,但是如果光去求文字就没什么意思。我还是觉得在这个时代就关注真问题吧,有更重要的东西在那里,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诚实一点,勇敢一点,直面这种最重要的问题。
我现在觉得非虚构写作是一把虚火,把它搞得很神秘很高大上一样,其实没有什么。可能非虚构写作更愿意关注人性的黑暗面。人性的黑暗面永恒存在,但这个时代的人性不一定就比别的时代黑暗很多。
(陈建佳、黄重重、边韵、江紫涵、沙莎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