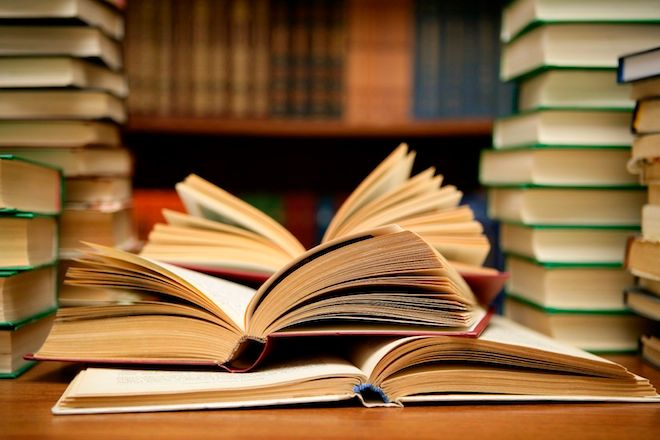張愛玲與張小嫺小說中的女性心理對比

張愛玲和張小嫺的作品中有着強烈的對女性自我意識的關注。由於兩人的時代背景、成長環境以及個人經歷的差異,她們筆下的女性角色在對待自我的情感問題、婚姻生活以及兩性關係等方面所表現出的女性自我意識雖有相似之處,但更多的是差異。
1、個體經歷影晌下自我意識的覺醒
作家的個體意識、思想和自我情感是作家個體經歷的集中反映,作家在進行創作的時候會不自覺地或多或少把個人的經歷隱射在作品中。女作家的個體經歷是創作主體意識的一種呈現,也可以說是創作的一種基礎,將創作者自身的經驗融人到作品中,依靠這種經驗使得文本更具有親和力和真實感,這是讀者與作家產生共鳴的一個重要原因。
張愛玲在《茉莉香片》中所描繪的聶家公館很明顯是來源於上海張愛玲與父親一起居住時的家,聶傳慶的父親和後母也是現實生活中張愛玲的父親與後母的寫照。散文《私語》用了大段的文字來回憶她被父親禁閉的黑暗時日,長篇愛情小說《十八春》則把這段經歷還原在了曼楨身上。她被父親禁閉時恨不得全家都死,她也願意賠進去:死了也許是埋在園子裏:睡夢裏都聽見鐵門打開聲:還有那條用煤屑鋪成的路⋯⋯這一切的一切都被她給了曼楨。
張小嫺的成名作《麪包樹上的女人》一直被讀者視作張小嫺的情感自訴。2011年10月張小嫺做客“楊瀾訪談錄”時說:“小說對我來說是一個虛構的創作,沒有完全一樣的故事,完全一樣的場景。但是裏面有一些情節,一些場面是我自己真的去經歷過。創作的時候,有時也可能已經分不清小說跟現實之間的分野。”小說裏面女主角程韻和林方文是大學同學,性格內向的林方文並沒引起程韻過多的關注,當她意外發現林方文竟然是自己喜歡已久的詞曲家林放,於是暗生情愫,兩人墜人愛河。但是林方文始終放不下前女友(畫家費安娜),這成了兩人關係中的一個隱患,最後林方文還是跟前女友重修於好。故事情節雖然比較老舊,但是這其中包含了張小嫺的朋友、同學以及她自己的親身經歷。1985年,張小嫺考入香港浸會學院傳理系,主修媒體學,不久便結識了同學王孜,而他正是歌曲《金背斑鴻》的作詞作曲人,張小嫺當時非常喜歡這首歌。從此,情竇初開的張小嫺對王孜多了一份仰慕之情,而王孜則被她的才女氣質所吸引,兩人很快墜入愛河。兩人戀愛後,王孜又認識了一個比他年長但是更具社會地位的女畫家,因此背叛了張小嫺。張小嫺將此真實的女性經驗創作爲小說,《麪包樹上的女人》這部言情小說因有了張小嫺的個體經歷而變得真實、感人。“女性作家是自己思維和行爲的主體。她有着獨特的自我意識和自省意識,同時由於女性觀照和介入,她們對自己筆下的人物形象往往表現出一種更爲女性化的同情、理解和寬容,更多一份女性的細緻和關懷”。
2、社會環境影響下的自我意識
社會環境是時代的大環境和大背景賦予作家的不同於其他時代作家的個性體驗。作家在進行文學創作時,無可避免地會在文本中反映出所處時代的特徵。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剖析女人的婚姻處境時,即認爲傳統女人除了婚姻之外,並沒有其他可以開展的空間。“在婚姻中的女性成了沒有自我意願、自我決策權和自我行爲體現的物化了的附屬,成了男人所欣賞、玩弄的被佔有的物,沒有獨立存在的權利和自覺,只能是攀附在男人這種大樹上的青藤”。
張愛玲的作品大多表現了時代更迭交替之際女性生存的困境。由於中國長久以來的宗法父權思想禁錮着女性的成長空間,加之在經濟上沒有獨立權,她們始終無法擺脫命運的枷鎖,想要獲得人格上的自主就註定要走一條艱難的道路。
張愛玲的作品中關於女人依附於男人的話題以各種各樣的模式在進行演繹。例如《等》中,奚太太不僅對丈夫在外養小老婆的事情只能忍氣吞聲。同時還要擔心自己年老色衰,最後只能在幽怨中等待丈夫回心轉意。在《紅玫瑰與白玫瑰》中,孟煙鸝在家庭中的地位本就卑微,還要容忍佟振保帶着妓女回家拿錢,但又對丈夫無可奈何。從《傾城之戀》中,可以看到,當時的社會環境下。女性想要佔得一席之位實在是可望不可及,這就讓“結婚”成爲了一種“比較有利的事業”。與此同時。在婚姻關係中。女性的自主權可以說是微乎其微。戰火紛飛的香港雖然成全了白流蘇,但張愛玲的筆下依然流露出對女性出走的諷刺,女性對於男性的依附仍舊沒有改變。
對於現代女性而言,當她們以“娜拉”的形象走出封建父權或夫權的控制之後,她們在現實社會中的進與退更多地表現出無力和絕望。“女性作家強烈的生命意識使她們在描述現代女性面對婚姻‘圍城’時很自然地構設出現代女性在事業與家庭、婚姻與愛情、自我與他人、靈與肉之間的心理困惑”。
張小嫺的作品中,大多是自我獨立意識較強的女性角色。她們具有不輸於男性的思考力和個人能力。但由於女人天性中對於愛和安全感的極度渴望,又很難擺脫對男性的依賴。《麪包樹三步曲》講訴的就是女性擺脫依附後自我意識逐步成長的過程。現代女性由於獲得了一定程度上的經濟獨立,她們不再像張愛玲筆下的女性那樣完全依附於男人與家庭,但對愛情的過度看重,致使“愛情”成了女性的精神依賴品。
《麪包樹上的女人》中女主角程韻把愛情視爲自己生活的全部意義,將一切都寄予男人和愛情之中。6年後,張小嫺創作了《麪包樹出走了》,小說裏男性的自私讓女性承受了愛情的沉痛,女主角開始思考自我存在的意義。到了《流浪的麪包樹》,程韻開始展現出女性的自我獨立意識,在事業上絲毫不遜於男性,而且更加懂得享受生活中除愛情以外的其它樂趣。當她發現林方文用“假死”來欺騙她時,她用寬容成全了對方。最後她選擇用“流浪”來療傷,這無疑是成長後的女性精神因愛受傷後的一種拒絕。
張愛玲的白流蘇依附於婚姻,張小嫺的程韻則依賴於愛情。然而,由於不同的時代背景,不同的經濟實力而有着不同的命運。這表明,隨着時代語境的不斷變化,女性的自我意識也在不斷進步和成長。
3、病態身體審視下的自我意識
一直以來女性的身體在男性作家的創作中作爲一種藝術空間想象下慾望化的存愛對象。而女性對自我身體的評價與言說,則是女性在精神和生命意識方面的雙重覺醒。如涉及女性身體的疾病,有論者指出這是“表達了一種人們對事物不滿的感覺”,“疾病是通過身體說話的個人意志的表現,它是展示內心世界的語言,是自我表現的形式。”
在張愛玲的作品中,爲了揭示女性精神上的焦慮與壓抑,表現女性受迫害的時代現狀,故多將女性身體進行醜怪化的描寫。在《花凋 》中,張愛玲着重突出了川嫦生前死後容貌、身體上的差異,以此反諷她“美麗的悲哀”:女兒的身體在死後變得真實美麗。川嫦生前臥病在牀,全家人以保護她爲藉口。剝奪她的自由,又不給她治療,她對這個世界感到深深的絕望,這充分反映出女性遭受迫害的社會現實。“對於整個的世界,她是一個拖累”,在自責的表象下,隱藏着女性的身體是父權文化壓抑的場所。當她拖着病軀走在大街上,從旁人異樣的眼光中,她窺探到了自己丑怪的身體——冷而白的大蜘蛛。這樣的醜怪經驗令她終於體會到了虛假的悲哀和真實的悲劇之間的真相。川嫦的醜怪反映出女性的焦慮、壓抑和受迫害的長期性與苦痛性。
半個世紀過去了,在不少作家筆下女性身體則成爲主體面對世界,以主體行動的力量表達生命本質的自由。身體不再是屏障,而是生命與靈魂的窗口。張小嫺《麪包樹出走了》的女主角葛米兒是一個很特別的女孩。即使她要忍受左腦裏惡性腫瘤對她的病痛折磨,但在生活中也依然保持樂觀、積極的狀態。“她站在那裏,戴着我(程韻)給她挑的那個齊肩彎曲假髮,身上衣服鬆鬆垮垮,看上去比從前小了一圈。她臉上塗了粉,除了有點蒼白,看來並不像病人。”同樣是面臨死亡的年輕女性,葛米兒與川嫦表現出不同的特點:川嫦由於長期處於一種壓抑的環境中,性格悲觀、焦慮,因而“醜怪”:而葛米兒一直是一個比較開朗、樂觀的形象,即使面臨死亡,她所想到的是極力維護自己的形象,繼續做好自己的事業。這樣的行爲和思想體現了現代女性強烈的生命意識和自我關懷:女性身體是女性生命個體的權利與快樂的來源,而不是自我的“怪物”和“禁忌”。
4、以“出走”爲抗爭的自我意識
1879年,挪威劇作家易卜生創作了其不朽名作《玩偶之家 》。1918年6月,《新青年》出版了“易卜生專號”,胡適與羅家倫合譯的《玩偶之家 》列於其中,娜拉形象迅速形成“娜拉熱”。《玩偶之家 》塑造了一位所謂追求個性解放的勇敢女性——娜拉。娜拉出走是《玩偶之家 》的高潮,也是一系列矛盾衝突發展的結果。娜拉之所以離家出走是因爲在這個家裏她與丈夫並沒有平等的地位和權利。劇中最後的關門聲震撼了19世紀的歐洲,其餘波也在20世紀引起了迴響,娜拉這一新女性形象也從此移植於東方土壤上,受其影響,一大批具有新的價值觀念、追求個性解放和精神自由的現代新女性,以全新的姿態紛紛從華文作家的筆下走出來,如胡適的《終身大事》、魯迅的《傷逝》等。
女性在愛情和婚姻中常處於兩難的境地,女性常常會因爲性別而遭遇困境,在與男性的競爭中處於劣勢,對此張愛玲選擇用出走作爲逃離困境的手段。
《傾城之戀》中白流蘇從活動場所到婚姻狀況,都處於“出走一回歸”的模式中。流蘇反覆往返上海與香港之間,出而復入的經歷中,每一次“出城”,都是又一次的“人城”,每一次的勝利(或失敗)都隱伏着下一次的失敗(或勝利)。出與人、成與敗、悲與喜,如此這般地既疊合又歧出、既對映又互涉。這就如同她原已離開了婚姻的牢籠,卻又再一次進入婚姻的“圍城”一樣。
張小嫺《麪包樹三步曲》中的程韻也有“出走”的經歷,卻有着與白流蘇完全不同的結局。第一部《麪包樹上的女人》中,程韻與林方文在一起之後發現林方文仍舊放不下前女友,一氣之下從他家搬了出來,那是她第一次出走。但友人的意外死亡使兩人都意識到生命的脆弱,都產生了要珍惜眼前人,珍惜愛情的念頭,於是女主角又回到了林身邊。第二部《出走的麪包樹》裏,理想化的愛情在現實中遭到考驗,第三者的插足讓程韻在愛情這條路上再次出走。第三部《流浪的麪包樹》中,女主角有了自己的事業,思想上也逐漸成長,最後用自己的遺憾成全了對方,至此,他們的愛情之路再也沒有迴歸了。女主角選擇用“流浪”來逃離眼前的困境,這是她能爲自己想到的唯一出路。從程韻反覆出走的過程中可以看到現代女性在精神上的成長,而這種成長往往伴隨着苦痛的生命體驗。
綜上所述,張愛玲作品中的女性總是一些被壓抑、受迫害的形象,她們都是一羣在男權宗法社會里依附於男人的女性,儘管有自我意識的甦醒,但因受制於主客觀條件,她們始終無法真正成爲擁有完全獨立自我意識的女性,依然擺脫不了附庸者的角色。而半個世紀之後的張小嫺用她獨特的女性話語,勾畫出從傳統父權或夫權社會中解放出來的、經濟獨立、事業成功、勇敢追求愛情權利的現代女性羣像。從她們的精神成長和自我意識的發展軌跡中,看到了女性在生存中的嬗變與成長。
轉載請註明出處,謝謝! https://bailushuyuan.org/novel/traditional/reviews/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