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听 | 乐夏后记
01
几年前宋冬野的董小姐,莉莉安;万青的杀死那个石家庄人传遍坊间,也在马来西亚年轻一代泛起传播涟漪。你未必真的记得哪个歌手或乐队,但忧郁寡欢的词曲收进了大部分人的深夜歌单,仿佛中国音乐以所谓“新民谣”曲风重新走进华人世界,那时我还没去北京,但是我看了中国好声音,认识了汪峰 杨坤,说他们撑起了中国摇滚半边天,可我只是当成了综艺选秀节目的噱头所需。
我更加不可能知道汪峰背后的鲍家街43号乐队,不知道晚安北京对哪个未眠孤独人唱。
昨夜<乐夏2>转播大家的热泪盈眶,我才意识自己局外人狂热的虚无。
02
重塑 RETROS 是我入门中国摇滚的第一支乐队,虽然他们总说自己属于小众音乐post punk, 在乐夏2得了冠军那刻也说不是我们赢了,而是欣赏小众音乐的人变多了,是小众音乐的胜利。想起很多年前苏打绿获最佳乐团,也发表了相似的言论:"作为一支独立乐队,不是我们从地下走到地上了,而是我们把更多人拉来地下了"

<pigs in the river> 戏谑看待13年上海松江漂浮数千只死猪,spotify 随机歌单 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首中国乐队的歌
"My right hand asked, should I raise for white? My left hand asked, should I raise for black? I really don't care which side you're raising for"
无论是坚持只唱英文的国际形象 或是 靠隐晦英文歌词映射社会现象,这都是我开始听进去,听更多的契机,因为好奇重塑的现场而去了草莓音乐节,因为好奇重塑的团员而看了乐夏 ,我这恐怕已经接近追星的举动,实际上真的是好奇心驱动,这样的音乐究竟从何诞生。也才有后来了解的为什么只唱英文 "因为摇滚源自欧美 想像上更容易捕捉 音乐上更容易进入"
其实我更喜欢某次访谈,华东提及,他们很少用什么奖项或音乐节去衡量自己的成就,觉得如果自己的胜利还能对他人有什么意义的话,就是大家可能因此被鼓舞去尝试实验音乐(或任何事),不需要混圈子,酒精社交(他们表演结束后从不出席任何聚会甚至不和歌迷互动)在舞台上不是只有煽情卖情怀,聚焦音乐的核心,专心做好自己。
从节目一开始重塑乐队就被定为音乐圈的精英份子,他们也不避讳承认他们的歌需要一定程度的门槛和审美观。然而,他补充,取决于你听得多少。也许在听歌的时候,你无法投射自己相关的情感经历,而且密集的鼓点,各种乐器的loop 已经让你耳朵忙碌得无法装下一点点小心思。这是一种纯左脑理性的慎密策划,来挑战右脑的音乐感知。有了建筑框架,才可以进行破坏,而且破坏也是经过设计的,他们的音乐不容许失误。
03
一个常被拿来对比的五条人乐队,反而因失误而增加学渣魅力的两个海丰人,几乎成了整个乐夏2的谈资,"你今天"捞"五条人了吗" "他们太好笑了!" 当然我理解这种好笑并非幽默,而是一种非现实感的滑稽,"你怎么穿拖鞋就来了","你怎么自己失误还安慰导演换工作",久了大家期待他们的不按理牌,即便短短5分钟的音乐演出,也更期待表演形式本身,甚至忽略了他们的音乐性。他们拿垃圾桶当鼓竹子当鼓棒,碎念听不懂的海丰话,这些看似非常"塑料感"的市井文化,其实是为了打破常规才进行的音乐实验,如果一个真的要展现海丰特色的音乐人,他们才不会写<城市找猪>这样的歌,不会有”想象中已经找到了三只 农村已经科学地长出了城市 “ 这样的歌词来戏弄马东。
他们不写县城,他们写县城和大城市的关系,他们不写阿珍和阿强的爱情故事,他们写生活无奈只好依赖爱情。其实他们真的很幽默,我在节目开播前,只见其歌不见其人的时候,就这么隐隐觉得。很久以前朋友推荐CD的时候拿过歌词本当微型科幻小说看过一遍,而且我会边看边联想起 my little airport (哈哈)
五条人有一首歌我很喜欢 叫<陈先生>,歌词很短只有三句:
"1878年伊生于海丰 1933年佢死于香港 1934年,其葬于惠州” (致敬陈炯明)
>推荐聆听:马世芳采访五条人 (音乐创作方面的东西谈了不少)
04
看了第二季再往回听第一季,印象较为深刻有海龟先生和新裤子乐队,在我还不知道后者是上届冠军,偶然看到合作赛 庞宽 与 Cindy 的表演那集,我第一个反应是“啊这主唱神经病”,第二个反应是“啊这妆容夸张扮丑的女生是谁啊”,”啊这鼓手干嘛躺在鼓上“,“啊还跑到嘉宾席去了" 我几乎下巴着地看完,然后再回放,至今还是会一直重看。那个女生叫Cindy,我很抱歉原来她并非刻意扮丑,而是她本来就是在一片审丑舆论中爆红的县城少女,她唱歌不行,长相不行,却想要成为女团。
新裤子为她量身打造的这首歌<everybody>,一开场就像大型舞厅 乐队肢体夸张地大吼 “everybody is here now ! everybody is here now ? ” 这时cindy 慢慢从舞台左边出现 "我来自一座小城的边缘,我没有一双漂亮的舞鞋” 仿照没有玻璃舞鞋就无法参加舞会的Cinderella.
他们夸张的对唱,转圈,唱不上高音,无所谓。我看到所有人脸上的不适感(犹如我的反应)却意外制造一种很爽的感觉,好像恶作剧成功了,挑畔了大众审美,& 最后终于所有人到齐了 everybody is here now.

05
这季看了另外一对神经病主唱,我慢慢接受了这种故意营造的"不适感",我说的是大波浪乐队,台下有忧郁症依然选择把钱砸去做一辈子音乐的李剑 和 台上把麦克风线缠绕在自己身上鬼喊鬼叫的邢星,即便是他俩私下的故事就足够说一整集,而他们的歌往往只有简单重复的歌词,以新浪潮电子舞曲为载体,再加入戏剧性的冲突,他们的双主唱模式并非一唱一和,而是制造对手,对立的立场,就像这首全场最高分的广场舞曲<爱情买卖>,原曲只有慕容晓晓的苦情吟唱,改编后拆解成两个角色,一个忿忿不平的当事者,和一个冷血无情机器的旁观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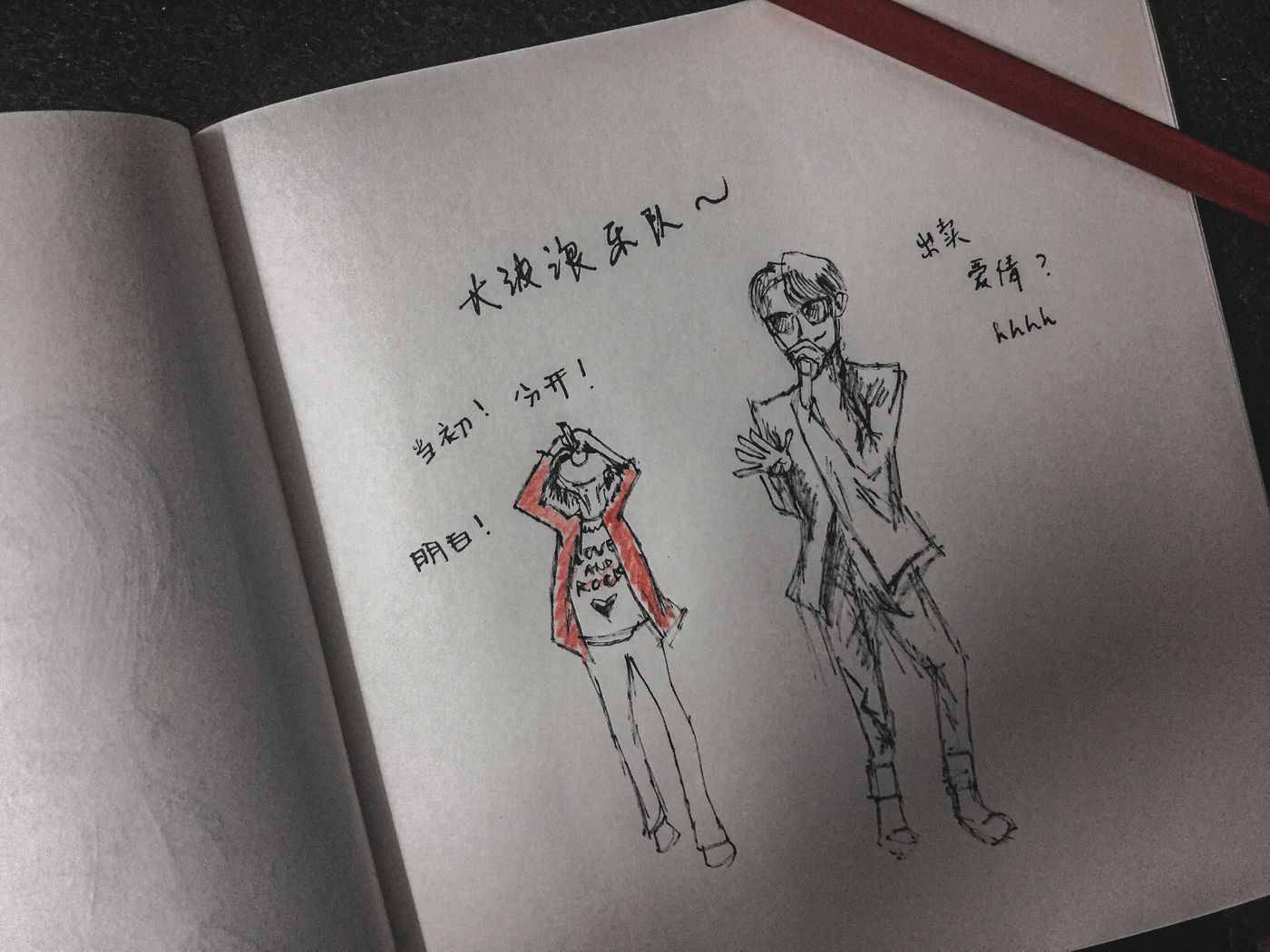
木马乐队可能是众多老牌乐队地下酒吧起家的一大票人当中我比较喜欢的(可能无法抵抗文艺青年),这种乐队的特征是往往当他们在唱几十年前的歌,我没有办法与这种情怀产生共鸣,我没有在离乡背井的时候听野孩子的<黄河谣>,听达达的<南方>,没有在青春迷惘的时候听后海的<猛犸>,或者人少叛逆的时候听joyside,我和大多数的中国青年的时代记忆割裂,仿佛我的狂热真的是一场虚无。
可是木马乐队第一场就唱了首新歌<旧城之王>,"大象没有眼泪可是却想要流泪" 的旋律烙印在我脑海,整整一周我带着这个记忆点,然后和下一场演出重合升温,他们选了芭拉情歌<后来> 进行改编,减去很多歌词,填了一首新诗。几个中年男子老气横秋地唱着"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颗心“ 唱的再也不是遗憾错过的爱情,而是更加坚定的赤子之心,即便那个生如夏花的时代已经过去,"错过不是失去" 主唱谢强独白。
演出永远画着性感的眼线和带着雅致的礼帽,这种精心准备不仅是体现在他个人的外型上,包括每一首歌的编曲,livehouse 有 livehouse的编法,放在乐夏的舞台,很多人说像是一种哥特式史诗级的舞台剧表演,即便不理解这种高级的词汇,你也知道他们的演出不能只是听,一定要看,看他张牙舞爪的儒雅。
他们因奇葩的规则而被淘汰后,写了首用摇滚乐消灭马东这个大坏蛋。"他涂黑了小白兔 他穿走蜈蚣的鞋 他洗掉斑马的斑" 为乐夏这个节目写了个寓言故事,我不能更喜欢他们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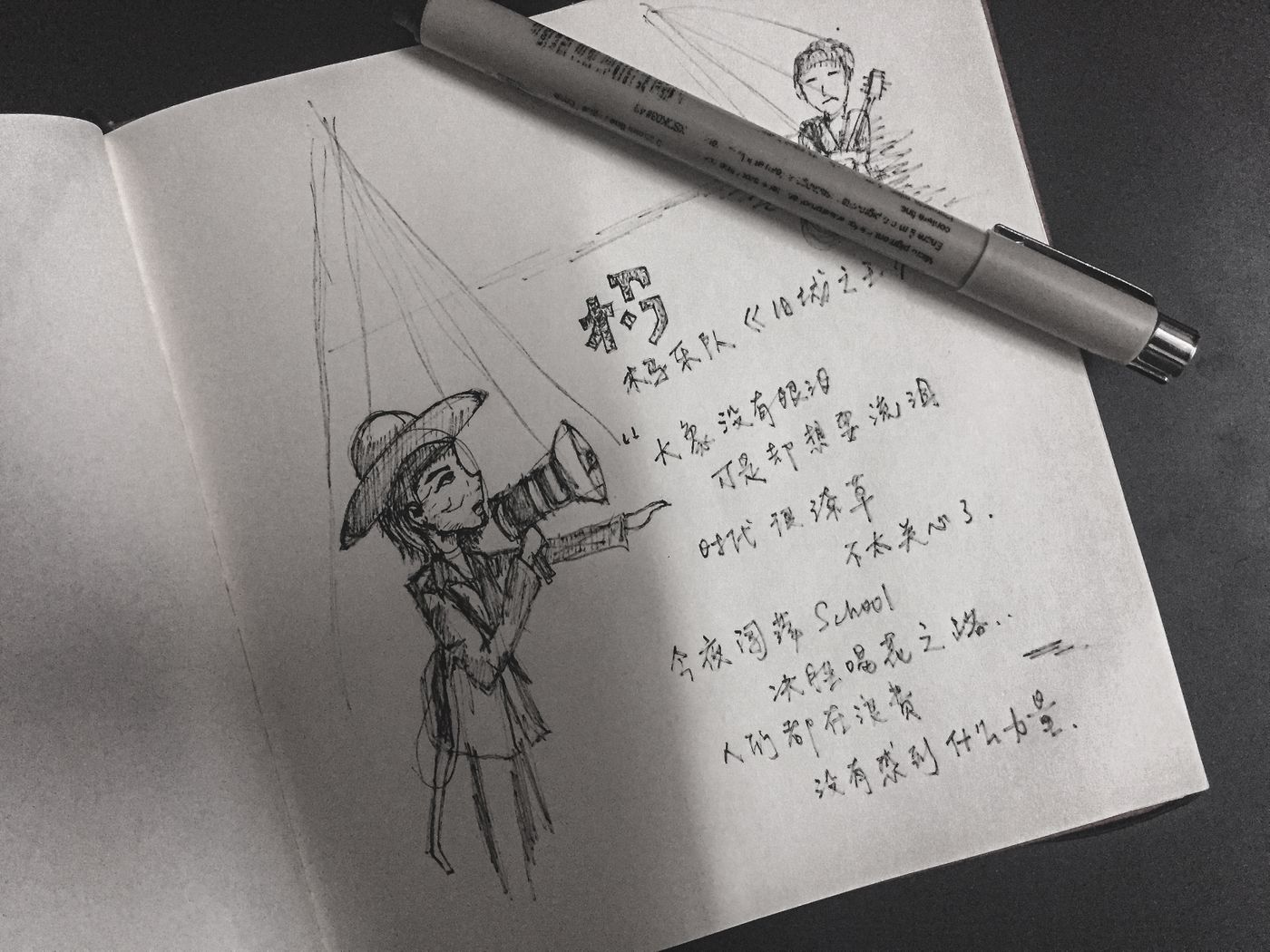
_
马来西亚疫情日趋严重,明天又开始封城,说实话呆在家这段时间并非不好,能平静无恙更好了。我的工作和生活时间交叠,但是每到周末晚上就会放自己假,全屏观赏<乐队的夏天>,不理会拼命闪烁的社交信息。
记在这样的日子里,我在中国乐队音乐的陪伴里,偶尔想起和北京那一丁点联系,还有远方夏天躁动的空气,隔着萤幕传递的人文关怀 情义 和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