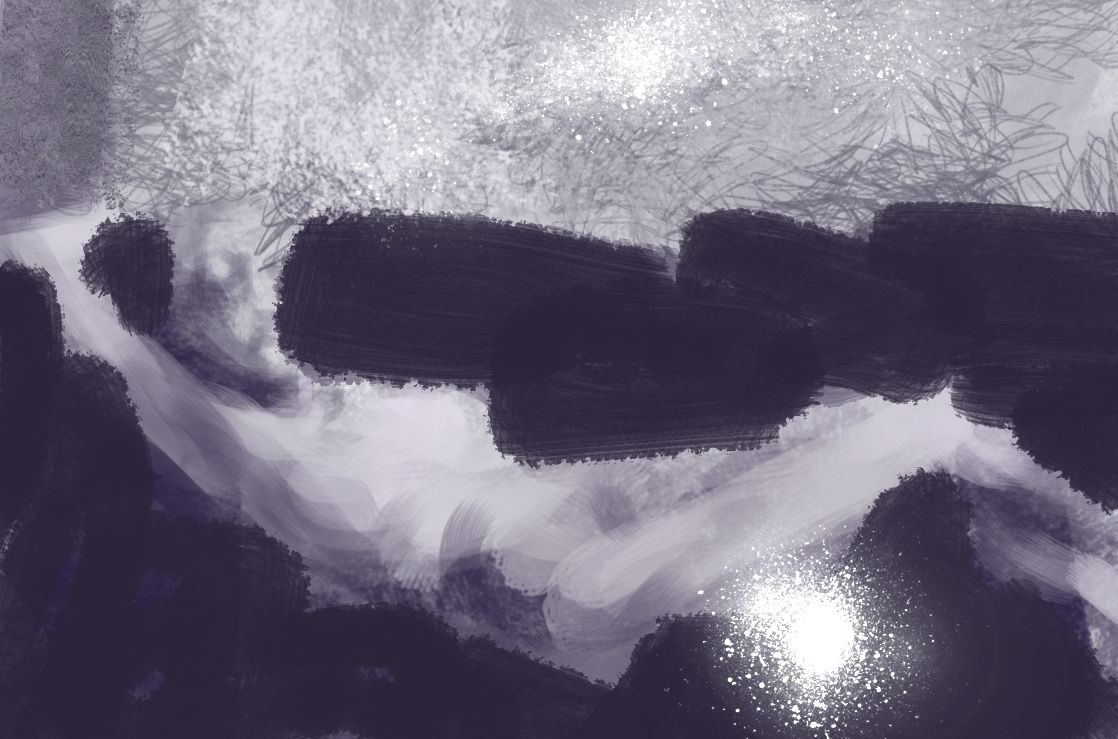給B的第二封回信| 男性需要自己的女性主義
B:
-3- 先大大地麽麽噠一下。MUA!(以及麽麽X)
也是很奇妙的,我看到你説覺得放鬆,就忍不住的也笑起來。也是放鬆的笑。多麽奇妙。合著現在晴又雨還有微風的雨季,多麽的美妙。以至於我,立刻馬上放下手裏在寫的東西,要給你回信了。這快馬加鞭,是因爲這舒適的好風不等人。
我要想想我上一封信説的這個「不妥當」還改不改了,也可以專門再寫一篇這個。實際上你説的哥哥的這個問題,難以表達、開口,以及不知覺間傷害另一半的問題,上野千鶴子在《厭女》中是説過的。我也知道,很多男性抑鬱、沉默都是相似的原因。就像女人不知道自己需要被肯定是一種廣汎的經驗一樣。男人也不知道自己抑鬱、沉默的大多數緣由,與其他男性是一樣的。都是被父權所結構的。
拉康、精神分析是極好的「男人學説」。它那一套,對男人太有用了,而我則聽到,好多女孩子說她們做過的精神分析不好。如今,我不覺得有什麽奇怪的了。
男性是執著於符號的,感官早已被符號所切割了的。從他們對女性的想象(大腿、屁股、乳房)就能看出來。上一封信講客體小a,只説了其中一面。另一面,客體小a,就是男性回不去的子宮,永遠吸吮不到的乳房。有些男的,你知道的,花心,喜歡的女人永遠18嵗、胸大。就是在這些可笑的偏見的符號裏尋找這個客體小a。不幸的是,男人掌權,女人就這樣被這些符號切割了,始終不知道怎樣與這樣的目光相處。而對男性而言,如果他爲此掙扎的話,那是好事,至少説明,他知道了「男性」的定義并不等於「人」本身。
我上封信講女人只是幽靈,不是人,但男性也一樣,他在父權機器之下,他也不是真正的人,只是他掌權、聲音能被聽見,因爲沒有存在危機,也就不善反思到這層罷了。
你一定是感受很深的。哥哥他也一樣被處在夾縫中:男人擁有話語,卻沒有語言去講述自己,尤其是自己的身體。
想想男性得的利益,他們能得到的尊敬、關愛、被聽見、被看見……更不用說其他的了,這些利益之下,他要怎樣才能堪破使他焦慮不已的哈哈鏡呢?那個壓在無意識之頂的男人父親的目光,在令他閉嘴,說你不如我;或者他每做一件事,總需要向男性集體證明自己,否則就要被除「男籍」了; 還有那些,我們常見的一些男性的自負自戀的時刻,似乎就是宇宙中心了。你想想小C,是不是這些問題的典型?他一跟哥哥説話,就要不斷地證明自己,只因爲哥哥在他心裏是「男人代表」,是話語權力,是他希望得到的目光。
其實功名利祿、爭奪女性之類的,不過是男人用以避免問「我究竟在哪裏」的小工具罷了。我們知道哥哥并不是典型的要去逐名追女的男人,或許,是因爲他對這一切有深深的懷疑。
但他也深深地陷入了沉默,除了沉默,這世界并沒有向他(也是其他男性)展現太多的路。或者,得去作爲一個(廣義的)女人來生活,就像澤那樣。徹底地對抗、反叛任何加諸于自己身上的話語、權力,成爲不受歡迎的人。
何況,對於大部分的男性來説,這樣做根本不值得。哥哥是很了不起的了,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背叛利益、拒絕自己所期待的目光(想想他和他老師的關係)。而可喜的是,還可以看到哥哥真正願意學習溝通,看到你的來信所説,我特別高興。
雖然很不幸的是,大多數的男性在親密關係裏,是聽不見另一半的聲音,也不知道要溝通的。也像你說的,他們有著受害者的「平庸的惡」。對男性來説,這會是比女性的女權主義還漫長的路,這是難以察覺的「既得利益的受害」。從前的佛教,似乎還有點用,勸(男)人放下執著、看破自己的閹割恐懼與自戀、無用的追逐與被深壓抑的欲望,重新做人。可佛教沒能阻止父權的無限擴張,沒能阻止它製造無數悲愴的母親、打了無數心結的孩子、極端功利、暴力的文化、體制的建立。
壓得哥哥難以言説的究竟是什麽呢?是什麽將他放入了那樣的夾縫,又將我們這些不服氣的女人驅趕了呢?是什麽使澤的父親在大街上看到兒子的長髮精神崩潰大駡他變態,是什麽使澤的母親狠狠地要控制一切又堅信自己是偉大的完美母親?是什麽讓你,永遠為自己被抛棄的可能而無法安寧?是什麽扼住了X的喉嚨,讓我認識了她有六七年了,才知道她的童年遭遇?
爲什麽、是什麽使我們離那自然的歡欣、放鬆、信任、暢談那麽遠呢?
我由衷地去思考、也要去行動,希望得到答案。也希望被定義成男性的人們,可以去爭取,像女人爭取女性主義 一樣,去爭取屬於他們「男性自己的女性主義」。
說到這兒,我忍不住地想念你們,我們有過那麽好的大笑大哭和舞蹈,想起我們在江邊聊天喝酒,那真是我做過的世上最浪漫的事了。多好呀,我們之間的愛,我們共同經歷的一切,是不需要語言也能感受的。
愛你們的,
Ia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