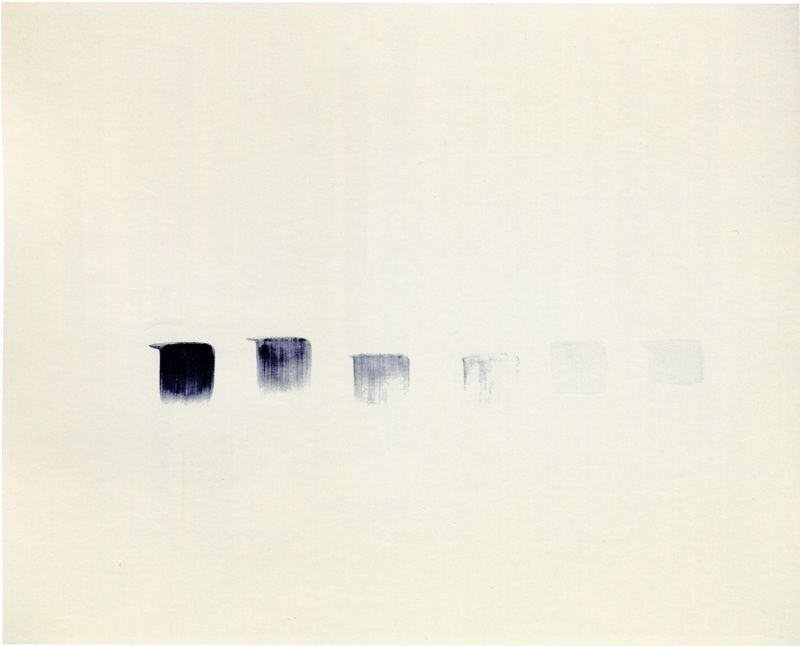城市旅劇──第十六屆澳門城市藝穗節觀察筆記(上)
文章刊出日期:2017年02月09日(週四)
文 — — 羅倩
本篇關於「澳門城市藝穗節」的駐節評論,勢必會是一篇不夠純粹的書寫。初次到澳門、看戲、參與座談,連續八天觀賞十場演出(是次藝穗節共有二十一個節目)。短暫逗留在城市的觀演經驗是否足以評品?自覺更像漫遊在城市的旅人。僅以此文記錄當下的澳門與觀演。
大致將觀賞的演出分為兩類,環境劇場的演出與黑盒子空間的展演。澳門資深劇評人、劇場編導及策展人莫兆忠曾在〈沒有空間,不是劇場──澳門「環境劇場」20年〉一文提到「就空間的特性做分類,澳門的『環境劇場』演出大致可分成『公共空間』、『閒置空間』、『文物建築』三大類。」[1]本文首先從環境劇場中的參與性談起,特別著重在觀眾參與的部分,也會提前將屬於黑盒劇場的《太平盛世裡的安全演習2017》加入討論。接著談在舊法院大樓[2]與曉角實驗室兩處黑盒劇場空間的展演。最後試圖跳脫演出之外,分享對澳門城市與座談參與的想法。
一、環境劇場中的參與性
I. 觸碰而形繪的《坐坐茶室》
不多不少,《坐坐茶室》用三首歌的時間,帶觀眾進入具有青樓歷史的福隆新街之劇場式空間情境。「明日和合製作所」希望透過「演出」給予觀眾真實戀愛的約會感,一對一的體驗式劇場。每場限定八位觀眾,進屋甫放下外套與背包,還來不及瀏覽演出空間,就依指示戴上眼罩,立即掉入了設定的圈套!眼前一片漆黑。音樂聲響起爵士歌手艾拉.費茲潔拉(Ella Fitzgerald)的〈Cry Me a River〉。感覺到有頭倚靠在妳的膝蓋上,牽起妳冰冷的手 — 輕輕撫摸,短髮 — 微微捲曲的觸感,妳的手感覺他左耳的輪廓。他起身滑過右邊,將妳的頭髮輕輕撥至耳後,皮膚感覺呼吸的靠近。沒有了視覺,只剩在黑暗的肢體想像,體溫與香味,雙手伸進肩膀按起因觸摸而緊繃的身體。最後演員回到妳的前方,彷彿這一切的互動還不足夠,再次牽起妳不知所措的手靠向他,觸摸到領帶後,才明白表演者是男性。
先觸摸形體,才看到視覺。拿下眼罩,甫響起伍佰〈一生最愛的人〉,八位扮演不同服裝角色的表演者,極盡賣弄風騷的舞動肢體,讓過於親密的互動一下子回到了帶有觀演距離的狀態。接著是抽紅線的配對,抽到了一位穿旗袍的女生,上樓時沒有刻意搭話,她幫我換上挑選的衣服,接著帶領我到搭起帳篷的空間跳舞。比起眼罩帶來想象的安全感,由於窘促,完全沒有聽到音樂聲(此段的音樂是安德烈.波伽利(Andrea Bocelli)的西班牙情歌〈Besame mucho〉),演員像是要逼迫面對她的目光似的,抬起我的下巴直直看向她,將手拉到她腰間,最後肩靠肩、彼此環抱而輕輕擺動,慶幸不用四目相交後稍稍沒這麼尷尬,一股溫暖的心情湧起,看向身邊其他觀眾,親密的身體彼此聚在一起,如此靠近,歌曲結束之後,幫我換下裝扮時她對我說「妳是不是很緊張?」我說「嗯,沒想到這麼靠近。」最後引導觀眾到隔壁間能看到天井的窗戶邊,樓下的表演者蘇品文和觀眾繼續扮演配對的戲碼,她親了觀眾的臉頰,一場即時戀愛演出。接著所有演員進入天井,將黑色與紅色氣球往上拋,入鏡與出鏡之間,以帶有舒緩與夢幻情境般的方式收尾。
對不擅長與人近距離身體接觸的觀眾(我),一開始的眼罩的確讓人順利的掉進被動與想像的姿態,也避免了與演員近距離對視的尷尬。在《坐坐茶室》感受到的身體與空間經驗私密且獨特。它首先不是依靠視覺,而是靠觸覺去描繪一個演員的形體,透過手來形塑表演者的形象,才回歸視覺的觀看。它和每個觀眾的身體與表演者的觸碰有關,甚至在演出過後還有點難以和他人分享自己的體驗,因為演出觸碰到了個人身體的敏感度,不論怎麼分享,好像都無法將自己的感受切分開來談。換句話說,在一定的演出時間與肢體動作設計的規範下,在表演者順著觀眾身體反應的即興互動之間,每一次都可說是全新的異質體驗。
如果劇場是一個允許觀眾想像的舞台空間,《坐坐茶室》結合展示的想像、觸碰的慾望、即興配對的逢場作戲感,的確將環境劇場中在特定空間的歷史演變具體感官化了。觀眾並不是真的在青樓消費,我們知道正在體驗一種想像的文化經驗,正是這種混雜著「真實的想像」與「想像的真實」的真假曖昧,《坐坐茶室》讓表演者與觀眾一起迴旋在奇異的、短暫的娛樂消費感之中。
標榜「體驗式劇場」的「明日和合製作所」給觀眾全黑的視覺,體驗青樓文化的身體感,用身體記憶演出,表演者作為一個想像的形體,帶觀眾進入異質的空間(不論是否過於表演或過於不真),你可能跟我一樣,不善於面對如此親密的陌生觸碰,而將身體感受無限放大了,以至於忘了觀看,在參與式劇場裡,畫面可以是什麼?而我用身體記得了這短暫三首歌的時間。

II. 不做表演的表演《生活藝術之流動廚房》
相對於《坐坐茶室》互動接觸的設計,《生活藝術之流動廚房》(以下簡稱《流動廚房》)給出另一種參與的體驗,從一月十三號到二十二號,一連九天十場,十位藝文人士做菜給你吃,每次限定十位觀眾參與。首先,一月十三號在台灣線上觀看了YouTube直播,看著主廚正在和觀眾用廣東話聊天。心裡納悶著誰是演員、誰是觀眾?如果沒話聊怎麼辦?如何延續話題?
我參與的場次為一月十六號[3],地點在望德堂區婆仔屋兩棵大樟樹下的中庭廣場,這裡過去曾上演過幾齣「澳門城市藝穗節」的戲,是次主廚是夏善生,料理為葡式及東南亞fusion(融合菜)。在特別訂製的餐座與料理台空間中,籌辦此節目的「點象藝術協會」策展人鄺華歡在活動一開始解釋為什麼要辦「流動廚房」的想法[4],接著介紹主廚的經歷[5],兩個小時的「演出」內容即是觀眾與主廚一起享用餐點與聊天。
在主廚夏善生的言談之中,可以感受到他對於澳門的身分認同,澳門是他身體的歸屬,也是心靈的歸屬,對於敏感的回歸中國的澳門,他倒是很自在地說「澳門還不是中國,澳門還是澳門,澳門也不同於香港的狀態,正因為澳門還是澳門,所以我以當澳門人為傲!」這倒讓我想起台灣,似乎沒有在演出場合聽過定居台灣的外國人如何聊台灣,特別談的還是身分認同的問題。澳門的四百多年的殖民史遠遠超過台灣的日治五十年,想像是什麼樣的文化與身分認同,可以讓一個不在澳門出生的葡人這樣認同一塊非出生地,是否也有因緣際會來到台灣,從此定居的「台灣人」呢?
主廚煮了兩道菜,綠酒搭配檸檬清酒蒸蛤蠣與紅酒搭配燉煮了四小時的澳門葡式家常菜燉羊排,此節目的策展人鄺華歡最後還煮了熱檸檬可樂薑茶。整個過程其實沒有感覺自己在看戲,意識到這還是一場演出,可能就是餐桌上那一顆即時傳輸到雲端網路的直播鏡頭了(360度全境串流直播),雖然不覺得有在「觀看」什麼,但《流動廚房》的劇場體驗設定非常有趣,這顆鏡頭記錄了整個晚餐的過程,就攝影機的紀錄性和節目的演出性來看,其實所有參與其中的人某種程度上都是演員,差別在於觀眾不但沒有排練,也不需要背台詞,就直接演出了!
原來在此次「澳門城市藝穗節」中,有一個不重視觀看,只是參與的節目,當日主廚的任務就是做菜,觀眾的角色即是食客。若《流動廚房》這樣體驗式的參與經驗能構成一個演出,還是在一定程度的規範之下,它依然是一個節目的概念,雖然在其中的觀眾會很容易忘記這一件事,尤其美食當前。首先,它安置了一個鏡頭做現場直播╱同時也作為演出的檔案紀錄與證明;其二,工作人員分佈在左右;其三,特定場域的空間;其四,特定時間與地點舉行;其五,對於人數的限定。
一開始也擔心是否需要和主廚有很多的對話,沒想到主廚說「他希望今天的活動是輕鬆自由的,就像在自己家庭的聚會一樣。很開心觀眾沒有打擾他做菜,專注在吃也就不用一直談話啦!我知道大家吃得很開心!」美食減低了觀眾對於和他人交流的恐懼與擔心,結束後觀眾還捨不得離開。《流動廚房》成功的創造了主廚、策展人與觀眾之間的互為平等的狀態,透過食物分解藝術、料理藝術,分享生活,再造一場自然的演出。
藝術家料理家常菜的過程,也可以是一種創作。換言之,策展人似乎想要挑戰一般節目演出的常規,藝術家在演出空間不做表演,我想起行為藝術家謝德慶,不做藝術,一位藝術家聲稱自己不再創作,不再發表。藝術與生活,生活與藝術之間的界線是什麼?或許在這裡不再是界定的問題,而是體驗與感受的問題。觀眾是否感受到何謂藝術與何謂生活?在主廚料理食物與分享的過程中,感受到了他對於澳門城市、身分認同與生活態度的思考。菜色可能是提前討論好的,《流動廚房》的概念也可能是策展人早已和各個邀請來的藝文工作者知曉的。但究竟在活動過程中,主廚和觀眾之間產生的化學變化是什麼?如何重新感受食物,或是說藝穗節與澳門城市的關係是什麼?透過食物的分享,某一方面來說,作為遊客的我也因緣際會透過主廚認識澳門,開啟對於澳門人的想像,以及它的文化混雜性。如何透過家常菜的「形式」感受到「藝術」,如果藝術是可以消化、具有形象與香味的食物呢?更何況蘊含著藝術家的情感。《流動廚房》轉化表演為食材的概念,是此表演最有特色的地方,論及題材的深度與廣度也同樣兼具,是令身心靈與胃一起滿足的特殊體驗。
如何談表演藝術的參與過程中,觀眾的準備狀態?在涉及到近距離觀眾接觸與互動的演出當中,對於容易緊張的觀眾來說,《坐坐茶室》極度親暱的身體性碰觸與視線對望,短短約二十五分鐘的演出,沒有一刻忘記「現在正在參與演出、觀看演出的狀態,也同時被注目與觀看」,全身僵硬與尷尬,不知道要往哪看才好;但是在《流動廚房》中完全相反,甚至在開始過後就漸漸忘記,這是一個表演節目,並沒有特定需要觀看的角度,也沒有必須面對與無法逃避的視線。當然以參與的程度來說,不得不提另一個在黑盒劇場裡的演出《太平盛世裡的安全演習2017》。

III. 參與式體驗──劇場中的後設建構與限制《太平盛世裡的安全演習2017》
若綜合從觀眾參與程度值來看,《坐坐茶室》設計了精巧簡潔的參與情境、《流動廚房》讓觀眾放鬆投入「演出」的程度最高,其中不做藝術的藝術、主廚身分的轉換、空間場域的置換、特定時間的直播、沒有演出的演出,藝術與生活的界線等令人玩味!
相比之下,《太平盛世裡的安全演習 2017》(以下簡稱《太平盛世》)強迫參與情境事件的力道最為強烈,演出要讓觀眾體驗參與抗爭事件──衝進立法院[6]後的情境模擬[7]。三位表演者不時滲入在觀眾中起鬨、發聲以推動事件與觀眾行為的做法,點出了在黑盒子劇場中,「模擬」真實現場與「再現」抗爭現場之間的操作與疑慮。何況團隊又必須「控制」觀眾的參與。
回歸到編導黃鼎云在演出文宣上提到的「劇場展演中觀眾的參與和介入的方式與程度」這個關鍵的想法。究竟《太平盛世》想要提出什麼樣的現場?觀眾又帶著什麼樣的心情與準備介入?
從衝入演出現場直到最後「自由地」(被迫地[8]、不知如何反應地[9]、搞不清楚狀況地[10])選擇繼續留下或是離場(演出比告知的八十分鐘還長,在裡頭待了兩個小時),在眾多拼貼的事件宣導與行動演說之間,在佔領現場中刻意安排許多社會事件的穿插,比如在演出發放紙條「裝飾我成為你心中的樣子直到你不再感到罪惡。」後,觀眾可以任意拿起手上道具裝飾演員。也模擬在社會運動現場的發言與談話,邀請觀眾發言。再現鄭捷[11]捷運上有計劃的無差別犯罪,重現在捷運上的攻擊。或是邀請觀眾上台唱歌等等。
演出過程中有兩點,讓我困惑劇團對於情節架構設定的嚴謹程度。第一是衝進場觀眾堆疊「椅子山」後,表演者直接稱呼這個「行動」叫做「作品」,並歡迎觀眾現場拍照。其實「椅子山」的爭議當時在台灣引起了不少的討論[12],在「太陽花運動抗爭現場的行動與作品之間」與在「此演出模擬的現場之間」,對於「椅子山」爭議(抗爭事件與作品概念的混淆),包含演員本身對於「椅子山」的詮釋,是否會誤導觀眾對於事件的理解?以致於太快下定論了呢。第二是演員穿超人裝上台演說,把歐美漫畫的「超人」與哲學家尼采的「超人」學說等同而語(超人說「我有被尼采拿來比喻『超人』」,究竟是戲虐手法或是對於「等同」的嘲弄?面對具有政治與抗爭性的時事議題,既使是劇場的模擬演練,也應審慎理解與考量。
關於加臉書的「互動」機制,在開演前工作人員說可以先加三位表演者臉書、瀏覽,因為演出會有一些互動,但短暫的開演前,實在無法好好滑手機(當天有些觀眾沒有加好友、有些觀眾其實也沒有網路)。在演出快結束時,收到張可揚的Messenger訊息:「你還在現場嗎?我們繼續堅持下去。」我回覆:「有,還在,畫國旗那位。」(他傳訊息之前曾過來和正在畫旗子的觀眾聊天,看我畫台灣國旗)下樓詢問其他觀眾收到的訊息,似乎還有其他演員和觀眾的對話版本。
以參與式的體驗來說,我不太確定這樣的互動與交流是否成立?或只是程式化的簡訊台詞而已。張可揚並沒有回覆,尤其觀眾數極多的時候,要如何確保每一位進場的觀眾都能感受到演出設定的用心?或只是「口號」?
究竟在什麼劇場現場?什麼抗爭?外頭的人又是誰?又要對誰說什麼話?參與是什麼?要讓觀眾主動參與?強迫式參與?或是不得不配合演出的參與?是觀看《太平盛世》跑出的許多疑問。
但反過來說有趣的是,如果跳脫出真實的抗爭事件與作品結構來看,把它當作藝穗節中一檔售票的節目,所謂的「觀眾參與」與「演出」之間的關係又會是什麼了呢?觀眾的「自主性」與「演出節目」之間的衝突於是產生。究竟是在看一場售票的「演出」(是抗議、演戲還是鬧劇)?還是一個參與式的「現場」(假裝在抗爭現場),觀眾的自主性、思辨性與能動性如果早已被框限在「演出空間」與「劇場消費」之間,如同在購票的情況下觀眾究竟是要「選擇」先行離開或是繼續留下?又要待到何時?對應到關於現實的抗爭議題,在演出中觀眾究竟能演練到多少成分?在層層後設結構下不斷消弱的,是關於嚴肅批判的街頭抗爭之省思。

IV. 無法介入的參與《生之葬禮》
大三巴牌坊是澳門的熱門觀光景點,《生之葬禮》選擇在具有特定歷史意義的戶外場地演出,演出內容與空間並無太多關聯,演出地點選擇在牌坊後方平台,購票的觀眾才能入場,已和周遭環境做了初步的區分,舞台背後的澳門博物館建築物本體也成為無關緊要的配角。
首先聽到雨聲,演員們的上衣是一套畫出來的西裝,一開始六位演員們撐著條紋傘從右方緩慢步行出場,伴隨著一只行李箱。B仔正要參加琦哥父親的喪禮,口白中細數著「太陽眼鏡、面紙、散銀是必備的」。從參加喪禮連結到B仔自己與聚少離多的父親的關係,中間串連喪禮現場與過去回憶的方式是B仔不小心在參加琦哥父親的喪禮時睡著了,以回顧的方式演出B仔和父親的故事,結尾要凸顯的是,如何在生前能好好把心裡的話傳達給重要的人,而不是在喪禮最後的場合說出口,對方已經聽不到了的遺憾。
所謂的「生之葬禮」,即是在生前舉辦的告別,團聚好友,互相傾訴真心話的寶貴時光,題材用意良好。但關於戲劇,不太能進入戲想要傳達的那份對於生的真摯情感交流。或許是日本演員的關係,必須在演員講述台詞時,頻頻轉向兩側的液晶螢幕看中文字幕(此中文其實是澳門慣用的中文),演員又有大量獨白時刻,且講話速度快,造成無法專心看演出的困擾。B仔的身分背景與時間交代不清,也造成看戲時的時空混淆(童年到求學期間B仔究竟是在澳門、愛爾蘭還是挪威長大?)父親為何要在其它國家工作,小時候又為何會在愛爾蘭被其他家庭收養後燙傷?是對於劇情較不能掌握的地方。
觀演場地的安排,也是無法進入劇情的原因,既使坐在第一排(共四排)還是覺得演員離觀眾太遠、打燈方式太分散與均勻化,無法清楚的對焦在特定演員上。多位演員輪流講父親與B仔的對話(同時快速帶過時間事件),無法把握目前究竟是誰在說話。在演員表演形式上,生動的肢體演出是很不錯,前段有點歌舞劇的歡樂味道,對於這樣沈重的議題,演員誇大的喜劇風格,無形中削弱了對於演員詮釋角色的入戲狀況,也讓後半段的抒情與情緒張力無法發酵出來,甚為可惜。

V. 香味與表演性《巴勒斯坦大飯店》
而「Dafa偶戲劇團」帶來的《巴勒斯坦大飯店》則是另一種在特定建築空間內的演出,故事是來自偶師胡辛.阿比(Husam Abed)在難民營的成長經歷,透過偶道具、各式物件的使用,如用米粒代表人、家人、家族離散、族群離散、國族離散等(他提到「巴勒斯坦人,就像一把散出去的米」),搭配其極具個人魅力的肢體表演,幽暗的室內空間中,用一盞紅燈營造說故事的氛圍,兩排觀眾約十五人圍繞在大圓桌旁。其實關於巴勒斯坦的一切我是暸解不深的,或許劇團考慮到了這點,演出一開始戲偶設計師Réka Deák播放了一段投影片,用歷史檔案、照片的方式(搭配中英文字幕),讓觀眾能有進入敘事的緩衝,在大概明白故事的梗概後,在操偶的演出中,既使大多時他說著自己的語言(同時搭配英語),但透過反覆的提示觀眾家族的人名、生動的肢體語彙,其實並沒有因為政治地理背景複雜而有難以理解的障礙,《巴勒斯坦大飯店》在考量不同文化轉譯與演出傳遞之間做了成功的配置。而演出不只是看,同時觀眾會聞到物件──米灑在空間的香味,同時一開始胡辛.阿比就告訴觀眾他會煮東西,一邊看演出,一邊享用熱茶,聞到米飯的香味,家鄉的料理成為劇場中可食的互動,異地的分享,「米」的多層次延展,成功地結合了演出物件、空間現場與觀眾參與的關係。

VI. 環境與行走《愛與死的證言》
如果說《巴勒斯坦大飯店》成功地運用了歷史建築何族崇義堂的空間。《愛與死的證言》則是此次環境劇場中面積涵蓋最大的戶外演出,地點位在澳門離島路環東北部九澳聖母村的九澳七苦聖母小堂(痛苦聖母堂),教堂附近曾經建有作為痲瘋病人的收容村,目前還保留多棟已荒廢葡式單層建築。演出從一開始教堂外的小花園一路往右進入到荒廢的建築群,再上山坡到九澳燈塔旁靠海的岩岸。
整個演出的參與後,其實並沒有感受到宣傳上所指「七」的靈性意涵。對我來說,同是編舞者與舞者的尼娜.蒂帕拉(Nina Dipla)在《愛與死的證言》中就像是一個領航員的角色,一個指引人或前行者。隱約感覺到尼娜.蒂帕拉在演出中對於聖母像,信仰的虔誠。在跟著演出移動的過程中,感受到舞者們試圖透過肢體與周遭環境做呼應的企圖,如對樹木的撫摸、廢棄建築物的召喚、對與陽光的感受與空氣的接納等等。現場的特殊打擊樂器與小提琴聲反覆的節奏有著迷人的哀傷與飄盪感。從舞者肢體中感覺到關於海浪、呼吸、船、移動的身體意象,也看到舞者們表現出個體與群體之間的猜忌與爭奪,也有個人表演出病痛、癢、躁鬱等症狀的身體,介於痛苦與和諧的掙扎。
在上坡行至燈塔的路上亦步亦趨,尼娜.蒂帕拉領先在觀眾與其他舞者前方,她先看到我們沒看到的,我們看不到她看到的,行走在未知道路的身體感,沿途思緒變得清晰,越往上走周邊環境越是映入眼簾,如最遠處的機場跑道、近處的澳門水泥廠與海。到了海的盡頭後,尼娜.蒂帕拉從胸口拉出了她先前在樹旁時藏入的那條紅絲巾,像是要極度貼近在岩石上傾聽周遭的一切,身體越來越沒有姿態,海聲、工業聲、風鈴與大自然的聲音。觀眾和演員一起看海、望海,寒冷的天氣中剛好有一艘船正劃過海面,望向沒有任何建築物的海,最後以步行回到九澳七苦聖母小堂做結束。
水泥廠代表著工業建設與都市更新,像是要把一切都凝固起來,舊的歷史建築正在凋零,飛機場起落的噪音,代表人的離去與歸來,在《愛與死的證言》中感受到九澳聖母村歷史與環境的變遷,自然環境與工業發展的衝突,正在新的進行式與舊的過去式之間並存。

[1] 莫兆忠,〈沒有空間,不是劇場──澳門「環境劇場」20年〉,莫兆忠編,《慢走,澳門──環境劇場二十年》,澳門劇場文化學會,2013,頁17。
[2] 「第二十二屆澳門藝術節」官網「演出場地」訊息中提到「法院大樓於1951年落成,原是澳門政府合署大廈,被評為“具建築藝術價值的建築物”受到保護。大樓已被選址為興建澳門新中央圖書館,即將成為澳門文化新地標。」http://www.icm.gov.mo/fam/22/cn/venues/,檢索日期:2017.01.26。但由於此計畫延宕多年,從去年「澳門現代日報」網路新聞〈重啟新中央圖書館 舊法院選址受質疑〉(2016.09.11)看來,似乎暫無定論。http://ppt.cc/Bk0D9,檢索日期:2017.01.26。雖然舊法院大樓建築物本身定位不明,照分類應該屬於環境劇場中的文物建築才是,是次的五個演出,幾乎都把舊法院當成黑盒子劇場來使用,和建築物的關係並無特別強調。
[3] 當日360 Live直播「Mobile Kitchen Jan 16」 https://youtu.be/B6–cDocSpc,檢索日期:2017.1.26。
[4] 他認為澳門現在的表演都太嚴肅了,不是用很多理論去討論演出就是演出過於商業與娛樂化。
[5] 主廚是葡萄牙人,在葡國當了十年的幼稚園老師,來到澳門十五年,娶了中國籍的太太,從此定居澳門,職業是幼稚園校長,一樣從事教育工作,白天教學,晚上則是投入在他喜愛的品酒世界,他曾經經營過兩間酒吧,亦是澳門藝文人士的聚集地。
[6] 台灣的「318學運」、「太陽花運動」,2014.3.18- 4.10期間佔領立法院。
[7] 酷卡文宣上的標語「劇場裡學會的一切就拿到街頭去活用」、「參與式劇場」、「現場的觀賞實驗與虛擬視角自我再製」。
[8] 表演者問有沒有人想離開,一位女生舉手,全體投票決定讓她能離開後,她被表演者說服又或有其他的原因留在場內,最後並沒有真的先離開。
[9] 指自己。
[10] 在演員與現場工作人員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有觀眾拉開椅子推開門。觀眾說:「要自己找出口這個意思吧?」演員:「自己選擇」。觀眾離場後,陸續有些觀眾離開,但其實演出還沒結束。
[11] 「2014年台北捷運隨機殺人事件」發生在2014年5月21日,約下午四點,台北捷運板南線,龍山寺到江子翠站,這是捷運沿途停靠距離最長的一段。
[12] 張小虹,《這不是藝術:提名太陽花運動的理由》,發表時間:2015.1.31。http://talks.taishinart.org.tw/juries/chh/2015013102,檢索日期:2017/1/27。
演出節目︰《坐坐茶室》|明日和合製作所(台灣)
觀演場次︰2017/01/14 17:30
演出場地︰澳門福隆新街福榮里9號
演出節目︰《生活藝術之流動廚房》|點象藝術協會
觀演場次︰2017/01/16 20:00
演出場地︰婆仔屋
演出節目︰《生之葬禮》|Theatre Moments(日本)
觀演場次︰2017/01/17 20:00
演出場地︰澳門大三巴牌坊後側
演出節目︰《太平盛世裡的安全演習 2017》|不畏虎劇團(台灣)
觀演場次︰2017/01/18 20:00
演出場地︰舊法院大樓黑盒劇場
演出節目︰《巴勒斯坦大飯店》|Dafa偶戲劇團、滾動傀儡另類劇場
觀演場次︰2017/01/20 20:00
演出場地︰何族崇義堂
演出節目︰《愛與死的證言》|梳打埠實驗工場藝術協會
觀演場次︰2017/01/21 15:00
演出場地︰九澳聖母村
2017–02–09首發於 評地Reviews(澳門劇場文化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