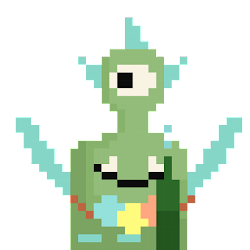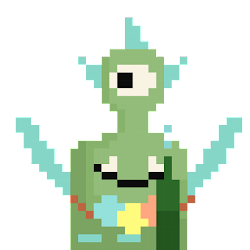驯服与被驯服的:在拉萨繁育藏獒【在场·非虚构写作奖学金】
作者:周雨霏
狐狸久久地凝望着小王子。
“请你……请你驯服我!”他说。
“没问题,”小王子回答说,“但我没有多少时间。我还有许多朋友要结识,还有很多事情要了解。”
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小王子》
不跟梅姐做爱,我就什么都没有了,我会失去一切所有的。我真不愿意丢掉这份工作。我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习惯了这样的享受,我不在乎做小藏獒。
陈冠中《裸命》
我将狗写作(dog writing)视为女性主义理论的一支,反之亦然。
唐娜·哈拉维《伴生物种宣言》
一
我在拉萨的藏獒老板有两辆车。一辆丰田陆地巡洋舰,白色,用来接人。一辆金杯皮卡,也是白色,用来拉狗。
暂且叫他李总吧。我在李总的藏獒养殖场里做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藏獒经济。待久了之后,每次一见他开哪辆车来,我和工人们大概就知道他今天要办什么事,至少知道是要办人的事,还是狗的事。
这天,狗场上午的工作结束之后,他从皮卡换到丰田,准备进城跟朋友吃个午饭。出发前,他用抹布擦车玻璃。拉萨西郊开发区的灰特别大,人要戴口罩,车要经常擦。
坐在副驾的嫂子回过头,问我:“小周,国外的街道肯定是一尘不染的吧?”
我说:“也不一定……”
嫂子和李总是四川同乡,小几岁,也是藏獒养殖方面的专家。李总说,她给藏獒配种的技术无人能比。别人配不上的,她能给配上。别人配上了怀不上的,她能让怀上。他负责推广销售,她负责饲养繁育。其实李总自己对饲养繁育也是亲力亲为,每天都到狗场检查工人工作,有时还亲自打扫狗圈,接生时整晚整晚地守在母狗身旁。因为夫妻俩的共同努力,他们的藏獒配成率、存活率和销量都很高。
那是2018年,十月,正值藏獒配种季。配种季持续整个秋季,不过每一条母狗能配种的时间就那么几天。纯种藏獒一年只发情一次,“不像人,随时都在发情,”李总说。一年就那么一次,一次就几天,错过就再等一年。所以拉萨周边尚且活跃的几十家藏獒养殖场,最近都在紧锣密鼓地部署今年的繁育计划,热火朝天地给藏獒配种。今天上午,李总和嫂子刚配了三对,下午还要配两对。他们狗场有一百来条成犬,加上别的狗场拉过来委托配种的狗,让他们每天都忙个不停。
嫂子换过了衣服。跟李总对车的选择一样,嫂子对服饰的选择透露出她每天要办的事。要下狗场干活时,她穿朴素的工装,沾染灰尘和狗的排泄物;要进城见人时,她穿整洁精致的时装,冬天多是貂皮大衣。十月的拉萨还不至于穿貂,今天她穿薄呢子大衣。
李总穿牛仔裤和皮夹克。擦完玻璃,他坐进车里,一边启动一边说:“拉萨必须要有灰。拉萨要是没得灰了,说明都开发完了,事情就不好做了。”
藏獒养殖只是李总在拉萨做的一件事情。另一件事情是房屋出租和拆迁。更准确地说,是等着他的出租屋拆迁。开车往返于机场、狗场和出租屋的路上,李总经常会大手一挥,向座上的客人们介绍:
“这个地方以前是我的狗场,拆了……那个地方以前是我的出租屋,拆了……这个地方,李克强来的时候,说要拆了修医院和学校……”
坐李总的车很有意思。你会发现,他脑中装载着一张独一无二的拉萨地图。他几乎不识字,所以不认普通路牌,而是把拉萨所有的路都记在脑中,并标上自己的路牌。这些路牌包括但不限于:买过他狗的地方、要拆迁的地方、他开过狗场的地方……
出租屋这片地,以前也是李总的狗场。那是2010年前后,拉萨藏獒的鼎盛时期,李总和嫂子一共有五家狗场,八千多个平方,一千多条狗。近两年藏獒走下坡路之后,狗场全拆了,修了出租屋,租给来拉萨打工的人,等着拆迁赔钱,据说是三年之内。现在这个狗场是去年重修的。
房子是临时的,布局潦草。人的生活也是临时的,房子里摆设粗略。大卡车一辆接一辆,从门前的318国道呼啸而过。流浪狗们在卷起的风沙里交头接耳。国道的另一侧,是光秃秃的拉萨河谷。河道裸露出河床。挖掘机一列又一列,开进河道,将河沙挖起,不知道要运去哪里,继续修什么房子。

车窗里,不时有人影往后闪过。是朝圣的人,骑行的人。他们用肉体抵御风沙,向拉萨的中心进发。同他们一样,要想进入拉萨,我们首先要穿过甚嚣尘上的开发区,然后经过空旷的“鬼城”柳梧新区,路过火车站、罗布林卡,然后终于进入拉萨更长久、更稳固的城关区。那里没有风沙,有很多绿化。但跟他们不同,我们的目的地不是石头做的布达拉宫或者大昭寺,而是天海路上的火锅店。
陆地巡洋舰驶上了车水马龙的天海路。天海路也属于老城区了,与布达拉宫直线距离一公里。这里跟开发区的氛围完全不同,但依然跟我以前想象的拉萨相距很远。要不是招牌上还写有藏文,你会以为自己回到了四川的某个汉地城市。天海路有很多火锅店,以及其他各种四川饭店、茶楼、棋牌室、洗脚房、美容院、按摩店、KTV。不止天海路,城关区的很多街道都是如此四川。每个在拉萨的四川人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告诉你,拉萨别称“小四川”,因为这里有很多很多四川人。来拉萨之前,我没想到自己的四川人身份会变得这么好用,让我在抵达两天后就结识了关键受访人李总,住进他的出租屋,然后住进他的狗场,成为他的藏獒养殖学徒。太方便了,可这毕竟跟我以前想象的拉萨相距很远。
这天中午,吃过汤锅肚包鸡,我忍不住告诉李总,下午我要放假半天。然后就奔去了八廓街,也就是围绕大昭寺的中转经道,拉萨最古老、最核心、游客最多的地段。
我融入转经的人群,悄悄地暂时忘记四川或者小四川这回事。逛小店,吃小吃,挑选佛珠和藏服,努力把自己打扮得更像、更像一个藏族人,仿佛这样才对得起我的专业——人类学!穿上一件刚入手的潮牌藏服,我接到了李总的电话。说他们在天海路吃晚饭,叫我也去。我已经吃过晚饭了,但必须要坐他的车跟他们一起回郊区,于是就坐公交车来到他们所在的一家涮羊肉店。
进入包间,李总和几个四川老板朋友已经吃得差不多了。他们看见我居然穿了个藏服,很是新奇,说还挺好看哈。我有点骄傲,又有点不好意思。他们说一会儿去唱歌,问我去不去。我不去也无处可去,就说好。他们便一边打电话叫别的朋友,一边开车来到附近的一家很大的KTV。是一栋几层高的、看起来很奢华、很“欧式”的楼,隐在一条小巷子的一个院子里。院墙上的霓虹灯,亮着五个红字:“西藏伊甸园”。
二
伊甸园门前很多车在排队,几个穿西装的男服务员迎来送往。我被其中一个领进一座很大很亮的豪华包间。不知为何,地上堆满了鼓鼓囊囊的彩色气球。我是第一个到的,找了个角落坐下。突然感觉藏服跟这个环境很不搭调,就脱掉了,露出里面灰色的套头毛衣。好像还是很不搭调。毛衣跟狗场,还有出租屋更搭调。没办法了,就这么穿着灰色毛衣,以及运动裤、运动鞋,坐在安静的大包间里。
老板们都去接朋友了。我起身去厕所。出了包间,在七拐八拐的过道里找厕所,发现来来往往好多人,好像都是在准备开展工作的服务员。进了女厕所,更是吓了一跳,挤满了人!全是在上厕所、排队、照镜子、叽叽喳喳讲四川话的女服务员。看她们那热火朝天的阵仗,仿佛这是今晚最后一次上厕所的机会。怎么会有这么多服务员?这里得有多大?她们几乎全都穿着高跟鞋、丝袜和紧绷的短裙。让我更加感觉穿毛衣、运动裤、运动鞋的自己很不得体,甚至幼稚。我费劲拨开人群,找坑位,然后又费劲地摸索回包间的路。

终于,包间里陆陆续续来了七八个人。不必说,都是四川人。把气球踩爆,热热闹闹地相互介绍。基本上都是男老板。嫂子没来,和其他老板的嫂子们一起打麻将去了。聊着聊着,一个特别活跃、嗓门特别大的大叔大手一挥,大声一喊:“上菜!”
老板们安静下来。门一开,走进来八个服务员。她们面向我们,整整齐齐、一动不动地站成一排,恬静地微笑,双手交握于身前。全都穿着白衬衣、紧身短裙、丝袜、高跟鞋,妆容精致。与其说服务员,似乎更像是办公室白领,或者空乘员。老板们嘻嘻哈哈地观察、评论、上前打量,开始挑选。挑出来一个留下了,其他的都出去了。又进来十个。这下我才有点明白她们提供什么服务。大嗓门大叔站在她们身边,手舞足蹈,像个活动司仪:“愿意结婚生子的,上前一步!”服务员们恬静地微笑,站着不动。
这时,大叔突然转向我大喊:“博士!你来选!”
我吓得赶紧摆手。
我其实是一个稍微有一点社恐的博士生,没有见过什么世面,突然置身此地,找不到恰当的体系来理解眼前的事。她们明明跟我一样,都是女性,都是二十多岁,甚至还都是四川人。可我坐在这里,她们站在那里。她们是我完全不理解的女性。
这么看了一会儿,竟突兀地想起我们狗场里有顾客来挑狗时的情景。不同的是,挑狗的客人比挑服务员的客人安静得多。他们在老板或工人的带领下,慢慢踱步于狗圈之间的通道中,用犀利的眼神打量每一条狗。喧哗的是被挑的狗。牠们在圈里上蹿下跳,或狂吠或低吼,有的扑到铁门上,把门震得咣咣响;有的用牙齿咬住栏杆撕扯;有的气急败坏地咬起了同圈的另一条狗。没经验的顾客(通常是游客),这时早就吓得魂飞魄散,逃跑时还不忘用手捂住口鼻,以遮蔽狗腿蹬起的漫天灰尘、地上溅起来的屎尿以及狗嘴里喷出的唾沫。而有经验的顾客,则依然保持着镇定,与狗圈隔开一两米的距离,继续沉静地检视每条狗最细微的品相和步态。这时李总一定会在一旁扯着嗓子推销:“这条铁锈红,骨量大,结构特别好!你看这个爪子,你看这个步态,这个神态……这个黑虎,爸爸是我们西藏有名的天龙,妈妈特别凶……这条铁包金,牧区刚拉过来的,正宗的原生版,短毛型虎头,现在正流行的版型,尾型也是标准的菊花尾……”顾客侧过头听着,不发表任何意见。
压抑着狂跳的心,我一动不动地坐着,模仿一个不露声色的藏獒顾客。
大嗓门大叔吓唬过我之后,又转过去面对服务员们,仰头大喊:“我选胸部比我大的!”
他的胸部一点也不大。服务员们继续微笑。
女服务员们接受挑选的过程中,来了一个男服务员。他谁也不看,以仪式般虔敬的态度,用开水把所有的杯子逐一涮了一遍。

二十分钟后,基本上每个男客人都挑了一位服务员,亲切地坐在一起。一位比较年轻的男客人没挑,他跟一位比较年轻的女客人组成了一对。还有一位比较年长的女领导没挑,但她热闹地起哄、开玩笑。令我舒了口气但也不理解的是,李总没挑。他一直抿嘴笑着坐在我旁边,看着整个过程,时不时拍手大笑。别人叫他挑,他就摆手。有人叫我坐到另一个地方去,他就赶紧叮嘱我别走,走的话他们就要给他挑人。我也觉得还是挨着他坐比较好,于是我俩就那么坐着,成为全场唯二没有组对的人。他见我紧张的样子,就问我:“你们同学一起出去是不是都唱素歌?”我没有听过“素歌”这个词,但听到就懂了:“你看我像唱荤歌的人吗……”
开始喝酒。我则开始一遍又一遍地拒绝劝酒。为了安全,不喝酒是我给自己的田野调查定下的纪律。最初他们都要怪我,做出生气的样子,我就更强硬地拒绝。果然几轮之后,他们不再理我,自己喝自己的。我终于放松下来,吃点瓜子和榨菜,观察四周,甚至开始在手机上写田野笔记。在逐渐高涨的气氛中,我获得了一种奇怪的自由。
一个看起来很和善的老板走过来,对我说:“你就充耳不闻,当没看见……但这也是你们人类学的实材……进入社会,就是要经历这些,你多学习。” 我说好的好的,把这番话记了下来。
李总也不喝酒。真不知道他来这里是干嘛,总不至于像我一样搞田野调查。他酒也不喝,也不组对,居然还掏出手机,在微信上卖起狗来。别的老板在大声地相互劝酒,跟自己的服务员搂抱、聊天;他在大声地回复顾客的问价,介绍狗的版型、谱系。我居然对他的工作热情产生了一丝共鸣。有时他收到文字信息,就伸过来叫我念给他听。我就努力洞穿喧哗,向他念出:“我很喜欢你的狗!能不能便宜一点?!”
喝了一会儿,十一点过了。终于开始唱歌了,我都快忘了这是一个KTV。灯光变暗,调出闪烁的效果。听老板们唱歌我才意识到,唱荤歌跟唱歌关系不大。他们乱唱一气,为的是与服务员打闹、跳舞,以及每首歌结束之后碰杯。碰杯时,我才发现包间里还有一个服务员,她没有跟任何人组对,但忙前忙后。主要是倒酒,以及每首歌唱完的时候,她要赶紧按暂停,以便大家起身碰杯。
而李总,真是来唱歌的。他叫我帮他点一首歌,是唯一一首他记得歌词的歌。从摇摇晃晃的人群里站出来,他清清嗓子,庄重地、抑扬顿挫地唱了一首陈星的《流浪歌》。
这首歌像一个咒语,在这个跟流浪沾不上什么边的场合,召唤出了我年幼时在大街上听到它的记忆——它是许多行乞、卖艺之人会用大喇叭播放的歌曲。李总为什么要唱这首歌?有那么多的歌,为什么他只记得这首歌的歌词?
唱完一遍之后,李总不满意,又点了一遍。这次他把手机塞给我,叫我帮他拍视频。我蹲在包间中央的地上给他拍。拍了一条他还不满意,唱第二段的时候让我再拍一条,并对我的拍摄手法做了一些指导。
专心致志地拍完之后,我环顾四周。一位穿西装、腰上别个对讲机的女士带着几位同样穿西装的男士推开门进来敬酒,然后出去了。一位老板把一位服务员抱起来,扔在了另一位老板身上。大嗓门大叔则骑到他的服务员身上去了。服务员们皱着眉头,继续微笑。
而这边,李总突然把手机伸到我眼前,叫我看他拍的藏獒配种视频,今天下午刚配的。他看上去严肃而热情,跟平时向我介绍养殖产业时的样子并无二致。明显是觉得我下午玩儿去了,没有认认真真搞研究,错过了重要的研究实材,所以现在要给我补上。
屏幕上,两条半人高的长毛狗臀部紧紧相对,静立在狗场中央的泥地上。毛太长,遮住了牠们的眼睛,但没遮住牠们一吐一吐的长舌头。脖子上都拴着铁链,末端由两个工人分别拉住。两个工人在上面交谈,两条狗在下面交配。李总的镜头上下左右挪动着,寻找最佳机位。我想象他蹲在两三米外,努力拍出两条狗宏伟的气势,就像他方才指导我蹲在两三米外拍他一样。
“拍照的时候,相机的位置一定要矮于公狗!才好看!”李总强调说。
三
藏獒是可以自己配种的。在藏族牧区,牧民们用来看护牲畜的护卫犬(འབྲོག་ཁྱི),也就是汉语说的“藏獒”,会在发情季满山跑,相互吸引、相互寻觅。有时,一条母狗发情之后,会有数条公狗们一起尾随她,都想与其配种。但并非所有公狗都能配上。这不仅是因为公狗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还因为母狗自身有很大的决定权。她只会在合适的时间跟她中意的公狗配种。当她不喜欢的公狗靠近她,往她背上爬时,她随时可以一屁股坐在地上,让公狗无能为力。
只有少数牧民主人替自家母狗选择配偶。大多数牧区护卫犬自行配种。可在藏獒养殖场中,自行配种是绝对不允许发生的。“乱配”有严重的后果,被视为工人的严重疏忽。每一年,每一条母狗要搭配哪一条公狗,都必须经过老板精心的设计和控制,为的是产生最优质的后代。
不仅控制谁配谁,还要控制怎么配。在养殖场给藏獒配种,至少是在李总的养殖场,需要四个人协同工作:
母狗被牵到空地中站好。两名工人扎稳马步,稳住母狗的上半身。李总走过来蹲下,稳住母狗的下半身,让她双腿分开,把她的尾巴偏向一边拉住,露出暗红色的外阴(称为“桃子”)。公狗从圈里放出来。通常牠会跑个一两圈,到处嗅一嗅,撒泡尿,然后直奔母狗冲过来,仔细嗅闻母狗的桃子,然后开始往母狗背上爬。爬的过程中,嫂子会迅速走过来蹲下,用鸡蛋清润滑公狗伸出的鲜红色阴茎(称为“雀雀儿”),并且帮扶其找准桃子的位置。雀雀儿进入桃子之后,她会紧紧抓住两条狗的臀部,让其紧扣在一起,这样可以保证公狗不管如何耸动,雀雀儿都不会掉出来。通常耸个十秒左右,公狗就会想要从母狗身上下来。这并不意味着配种结束了,因为公狗的雀雀儿在母狗的桃子中并不是一次性射精完成,而是首先会胀大,然后固定其中,接着再缓缓射精。这个固定的状态称为“连上了”或者“锁上了”。锁上之后,公狗的前腿会跨过母狗的一侧身体,落在地上,然后另一侧的后腿也随之跨过来。牠四脚着地、转过身去背对母狗,这样两条狗就可以反向站立,而臀部依然紧紧地扣在一起。公狗缓缓地持续射精,整个过程从几分钟到几十分钟不等。即便是锁上了,嫂子依然不能松懈,她继续紧紧抵住两条狗的臀部,让牠们保持紧扣姿势的时间长一点,等到她觉得把稳了,再放开。这是因为有时公狗没锁好就往下爬,雀雀儿就会掉出来。等到完全锁好、站好之后,就可以让两个工人一人牵一条狗的铁链,把牠们稳定在适合拍视频的站位。
在拉萨的养殖场里,成年藏獒的肩高几乎都不低于70公分,即便母狗也是。最高的公狗甚至逼近90公分。给这些巨兽配种会耗费相当的劳力。这还仅仅是在假设母狗都积极配合的条件下。很多时候,母狗不配合。虽然养殖户都会凭借经验,仔细地检查母狗发情的程度,估算母狗排卵的日期,只在最合适的那一两天安排配种,可很多母狗不愿意被安排。公狗往背上爬的时候,她们会试图挣脱,试图扭转头去咬公狗,甚至咬人,至少是夹住尾巴,往地上坐。工人的很多力气都被花在了稳定母狗上。在别的狗场,我见过一种比工人的蛮力更加便捷的“刑具”:养殖户们自制了配种架,把母狗绑在上面,任其如何挣扎都无法动弹。
即便如此,养殖户们依然称养殖场中的配种为“自然”的。视频中,李总对着两条相互锁住、同时也被铁链锁住的狗,向微信群友们宣告:“两条藏獒自然交配成功!”

所谓“自然”,是相对于人工授精而言的。獒圈(藏獒爱好者的圈子)中有小部分獒友(藏獒爱好者)认为,人工授精可以降低配种的劳动成本,同时提高怀孕的几率和效率。几年前藏獒热的巅峰时期,人工授精还可以为知名种公的主人牟取更多配种费,因为一精可以多用。同一条公狗一次射精产生的精液,可以分成多份,注入多条母狗。精液冷冻之后,还可以长期储存、长途运输。
我只看过一次人工授精,在别的狗场。那位老板先用类似“自然”配种的方法,让公狗爬一条母狗,但不允许牠插入。爬得差不多了,就把牠拖下来,给牠手淫,让牠射精在一根试管中。然后再把精液导入一根粗的注射器,用注射器把精液推入别的母狗的桃子。
李总给狗配种从来不采取人工授精,因为他不相信人工授精,只相信自己的技术,相信他八年来不断摸索、积累的经验。在他的狗场做田野调查,我想要学会并用人类学视角去理解的关键,就是这一套囊括配种、接生、养育、治疗在内的繁育技术。学习了几个月,几乎所有的步骤我都实践过了,但一直没有亲自尝试配种。李总不让,我也不敢,因为给藏獒配种实在是很累,技术难度很大,而且非常危险。被惹怒的公狗母狗可能会突然咬你一口。
所以在配种的场景中,我一直都只是一个旁观者,只在少数时候帮忙拉过一下狗链。其他时候我都站在两三米外观察,在手机上不停地记笔记,同今晚的工作方式一样。
在李总狗场里的十个月,我总共看过116次配种,视频更是不计其数。今天上午也刚看过。可是此时此刻,我不得不埋怨李总,为什么偏偏要在这个场合给我看配种视频?身边的人类肢体交错,与屏幕上的犬类肢体交错,交错在了一起。掩饰着窘迫,我不知道该看向哪里。
李总却熟视无睹,泰然自若。给我放完、讲解完视频之后,我们继续安静地坐了一会儿。突然他对我说:
“拉萨的小姐百分之八十是四川的。丢人得很。她们坐台六百,出台两千。一个月收入万把块钱的人,在歌舞厅玩一晚上就把钱花光了。社会复杂得很,乱得很。唱到四五点不会累。我以前也是开歌舞厅的,我和你嫂子九五年就开歌舞厅了。”
我震惊地看向他。
他继续若无其事地说:“一开始是素的。后来也有小姐。一共三年半。做这个生意倒霉得很,因为拿女人的身子卖钱。我再也不做这个了。所以现在嫂子也看我看得紧得很。老男人了,想法多得很。”
四
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亲爱的妈妈
流浪的脚步走遍天下,没有一个家
冬天的风啊夹着雪花,把我的泪吹下
走啊走,走啊走,走过了多少年华
身边的小草正在发芽,又是一个春夏
陈星《流浪歌》
“我和你嫂子在老家开歌舞厅,亏了二十几万。那时候,二十几万好吓人。乡下修房子又花了二十万,相当于现在的两百万。两口子拿着五千块,打算出门闯荡。
“有个朋友是工商局局长。他问我是不是不相信风水?我说不相信。局长说,那你这么勤快的人,怎么会找不到钱?就请人算了八字,给我改了名字,还叫我‘去西方’。
“‘去了西方,你这辈子大富大贵。’
“就去了缅甸。后来想起来,其实缅甸算是南方。你嫂子在百家乐当大堂经理,我做二手车。哪知道买了一辆从赌场偷出来的车。那时用掌中宝手机,一个老乡打来电话问,你是不是买了一辆车?很严重,赶快走,出问题了。
“我当时刚买了两个商铺,很大,还没有任何证件。还买了五辆车,桑塔纳时代超人。一接到这个电话,我手机卡都扔了,充电器都没带,就走了。结果边境证过期了,海关很严,出不去。幸好有个老乡在中国边境那边开餐饮,跟边境的人熟。他过桥送外卖过来,我们装成他的员工,这么回了国。
“然后跑到西双版纳,住了一个月。我从家里出去的时候,别人都说儿子不孝,没挣到钱就不要回去。就没面子回去。换了几张手机卡,那时候电视看得多,心想这样就不会被追踪。其实我们卖车完全是合法的!还想过去老挝,但宾馆里的老乡跟我说,老挝更吓人,杀人的事情更多,才没去。
“我们在缅甸的时候,看到过犯人游街。先把他们的耳朵割了,然后枪毙。那才叫残忍!刀太钝了,半天割不下来。你嫂子不敢看,我去看了的。
“后来就联系到了拉萨的老乡。他说快过来拉萨,这边发展可以。我们两口子就来了拉萨,到现在已经十一年了。一开始做家电,做了三年。有一天,我看到别人家一个小狗,黑不拉几的。一问价钱,一万多,心想怎么这么贵。戴了个红脖圈,说是藏獒。那时我听都没听说过藏獒。在我们老家,小狼狗卖三四百就很好了。过了几天,又遇到一个抱狗的人,也是藏獒,卖五六千。我觉得这条可以,就花四千买了。那是我买的第一条藏獒。
“然后就开始到别人的狗场打工,学养狗。积累到经验之后,就自己开狗场,开始到牧区去找狗,主要是措美、措那县(西藏山南地区)。古堆乡的狗是最好的。为了找狗,我们把那里牧区都翻遍了。
“拉萨才是西方。我一到拉萨,运气就变得非常好。任何狗都是一下就卖掉了。而且刚修狗场,就遇到拆迁赔钱。我的狗狗给我带来好多财富哦!去年我爸爸去世,一百多桌酒席都摆不够。我不是我们李氏家族最富的,但绝对可以写一本书。
“也遇到过困难。我们现在的这个村有个村霸,非要我买他的沙子,不买就要开十几辆大货车来揍我。我的警察朋友跟我说,只要他们一动你,就马上倒下,我们就马上来把他们踢走。后来他们真的开了挖挖机来挖我的房子,说我占了村委会的地。那地明明是我买的!他非说我多占了两三米,必须挖掉。当时我就拿个砖头,坐在那挖挖机上面。他没敢动我。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每天在我们家吃饭的那个,我的表弟,你知道吧,他其实是我的保镖。
“但我跟其他男的不一样。他们喜欢打来打去,我从小就喜欢小动物,就喜欢扯点草草喂兔子。十一二岁的时候,我就找小土狗来卖。结果晚上放在家里不停地叫,就被家人掏(骂)。第二天把狗卖了,一角钱一条,最贵的一条卖了两角。
“藏獒跟其他狗真的不一样。小周,这个你一定要写进去:我爱藏獒,不像有些人那样天天讲些大道理,我是通过实际行动。有时你嫂子不支持我买狗,我就偷着背着去买。我经常对我的朋友说:你们是闻了狗味吃不下饭,我是不闻狗味吃不下饭。
“三四年前,我是个很坏的人。每天睡到十一点自然醒,下午就到拉萨城里鬼混,凌晨三四点才回家。狗有工人和你嫂子管着,我完全不管。你嫂子抱怨得很多。现在我改邪归正了。
“然后藏獒就走下坡路了。我们把狗全都卖了,两年没养狗。每天就是闲到起,就是耍,又是睡到十一点自然醒。中午请客吃饭,晚上请客吃饭。下午一场牌,晚上一场牌。你嫂子喜欢这样的生活,可能也是年纪大了,累了。但是我不喜欢,我喜欢进取。所以去年我又开始养狗了。
“以后我打算在拉萨买两个商铺。现在狗场这个地方据说七年后要拆,到时候我把狗场往后移一点,路边上再修出租房。现在的奋斗,都是在为后代积累财富,让他们不用太担心钱的问题。
“等这些房子拆完,就回四川了。在老家养几条藏獒,养起耍。挖个鱼塘,再修个练歌房,朋友过来就一起钓鱼、唱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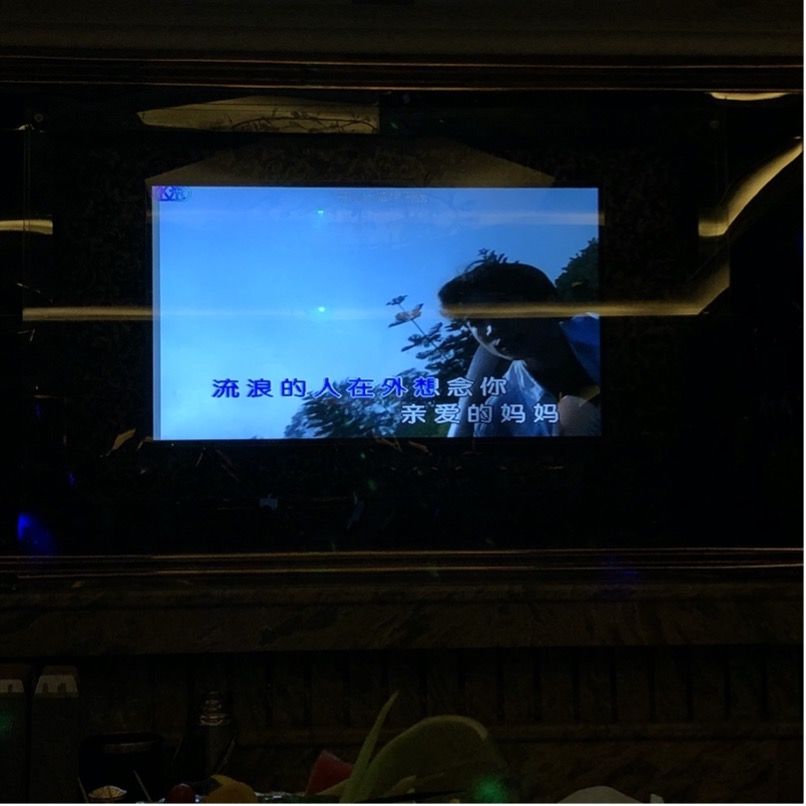
五
看来李总是真的很喜欢唱歌。但今晚他只唱了一首歌,然后一直跟我聊天。他的人生故事我前后听过多次。多次之后,逐渐拼凑出完整的形状。但这是我第一次听他讲歌舞厅的事。为什么拿“女人的身子”卖钱倒霉,而“狗狗”就带来好多财富?我沉浸其中,体会叙事的逻辑。周遭的喧哗短暂地退散了,直到大嗓门大叔拎着一个提包推门进来。
他从提包中取出一摞粉色钞票,递给一位服务员,让她分给其他人。服务员们簇拥上去。我看到一位服务员眉飞色舞地数她的那几张钞票,数完之后拉开前襟、塞进内衣,大张手臂跟她的老板抱在了一起。
我再次收回视线,移到一个空白的角落盯着看了会儿。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来这样的场合,没有相应的准备,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眼神去看她们,更想不到任何办法把看到的东西整合进我的论文。我只知道下一次唱歌,我肯定不会来了。我应该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少到拉萨来,在养殖场里好好学养狗。比如,我应该更勇敢一点,主动参与配种的工作。
其实有些时候,在养殖场里给藏獒配种,也不都是强迫、被动的,因为也存在非常积极的母狗。如果安排她们在最适合的时间,跟她们中意的公狗配种,她们一点都不会反抗,甚至不需要工人的强压,因为她们会自己大张开四条腿,坚定地、稳稳地站在地面上,尾巴偏向一边,露出桃子,等着公狗过来。有时,她们因为疼痛而嗷嗷大叫,甚至在地上打滚,但依然会坚持到最后。
甚至,有时公狗还没准备好、茫然四顾的时候,她们会转过身来吸引和引导公狗进入状态。
李总给一条叫天霸的公狗配种时,就出现过这种情况。天霸是我们狗场的明星种公,因为牠的体型非常大,毛很长,而且皮子非常吊。吊就是松弛而下垂的意思。獒圈讲究藏獒品相上的“三吊”:吊嘴、吊眼、吊脖束。天霸的三吊都很极致。李总非常重视天霸的配种,期待牠今年的后代能够在体型和品相上,继承、超越天霸。
李总已经把高大壮硕的天霸牵出了狗圈。为天霸选定的那条母狗也牵了过来。这是一条刚刚成年的红母狗,没有名字。这是她第一次配种。今天是她最容易怀孕的一天。李总用手把她双腿分开,尾巴偏开,轻轻抠她的桃子,工人在前面抵住母狗的头。母狗站立不动。天霸在空地里慢慢走了两圈,闻了闻母狗的桃子,然后竟趴在了地上。
“天霸!怎么睡瞌睡了,日你妈的。装什么斯文,快上来!给你说这个婆娘可以,你怎么不相信!”
天霸还是趴在地上。李总把母狗牵开,这时天霸突然站了起来。“是不是要爬了?”赶紧把母狗牵回来。结果天霸上前闻了闻母狗桃子,又坐下了。
等了几分钟,天霸还是不起来。李总想到个办法,和工人一起把母狗抱进了天霸的圈,果然天霸跟着我们进来了。
“你是不是在外面害怕嘛?一直装处,他妈的!”
回到圈里的天霸看起来状态积极一些了,又去闻母狗的桃子。
“你在这儿里头才愿意配呢?你才是喜剧!”
李总让工人给母狗拴上铁链。母狗不愿意,想挣脱。“你还怕链子吗?”李总正想给母狗取掉铁链,这时天霸又过来闻了起来。李总赶紧叫工人抵住母狗的头,他则蹲下扶住母狗的臀部。天霸抬起右上肢,又放下了。然后又抬起,准备往上爬。终于爬上去了。天霸开始耸,母狗嘘嘘地叫。李总叫两个工人一起用力把天霸往前提。
耸了两下,天霸不动了。李总纳闷了:“我咋觉得这公狗不耸呢?要配不配的。”
但母狗惨叫了两声,说明天霸确实有在耸。工人们于是慢慢把天霸前腿放到了地上。结果刚一放下,两条狗就分开了。
“怎么没锁上呢?”
“掉出来了。”
母狗还在继续挣扎,跳到了一边。李总摸摸她的头,牵住她对天霸说:“快来!你婆娘跑这里来了!”
虽然母狗刚才挣扎了一下,可是现在又乖乖地站稳了,回过头看天霸。天霸呆了一会儿,又走过来闻母狗。母狗挣扎,李总把她固定住,双腿分开。母狗又站定不动了。
天霸闻了闻,又坐下了。
“快点儿来。这个婆娘可以!小妹妹这是!”可天霸已经躺平在地上,好像完全失去了兴趣。
李总又气又想笑:“老子!”
公狗不愿意配种的情况少之又少,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冲上来就配了。母狗不愿意的话,可以强压。可如果公狗不愿意,又有什么办法呢?
李总抓起母狗的尾巴,去抚天霸的大吊脸。天霸还是躺着。即便躺着,天霸的品相都是那么好。李总由衷地赞叹:“今年天霸真大啊!”摸摸牠的大爪子,欣赏起来,好像暂时忘了是在配种。突然又反应起来,赶紧喊道:
“快过来!”
同时把母狗臀部推向天霸,抬头对嫂子说:“没问题吧?上回让天霸配另一个母狗,爬了三下就配起了。”
然而这回确实没那么顺利。天霸又起来闻了闻母狗,试着爬了爬,然后又躺下了,如此反复数次。我有点厌倦了,在手机上机械地标记着天霸躺下又站起来的次数。
母狗一直被工人们抓住,好像也有点厌倦,挣扎了一下。李总干脆叫工人把母狗放开,牵着铁链的末端,把她推到天霸面前。
母狗走向天霸之后,一个掉头,突然和天霸肩并肩站在了一起,还主动去闻天霸的头。李总顺势把天霸的耳朵翻起来,让母狗闻。
“快来呀天霸!哎就怕配不起,焦人得很。”
天霸也掉了个头,又闻了闻母狗桃子。嫂子也走过来戳戳母狗桃子,把尾巴偏开,腿分开。母狗很配合。天霸继续闻着。
李总又情不自禁地欣赏起来:“哎,放在六七年前,天霸好管钱哦!那么大的狗儿!那时候哪有这么大的狗?我都没见过。”再一次,天霸闻够了母狗,走到墙边上坐着,还回过头看这边厢的我们。
“哎呀!你这样子光看,是看不出儿来的。快爬!”
要是换成一条小一点的种公,工人还能把牠抱着放在母狗背上。可天霸实在太大了,根本抱不动。
李总再次把母狗推到公狗面前。“天霸你看!母狗来亲你了!快起来!”母狗和天霸又相互闻脸,但依然没有下一步动作。
“哎呀天霸!你丢不丢人嘛!”
李总走上前去,直接把母狗抱起来放到了天霸背上,开玩笑似地说:“来!你爬牠!”
天霸回头看看,还是坐着。李总干脆把母狗的铁链完全取下来,让她在圈里自由走动。天霸一见母狗朝自己走过来了,赶紧站起来,和母狗转着圈地相互闻臀部。两条狗都摇着尾巴,都比刚才兴奋了许多。天霸走开,母狗就跟在后面闻。她还去闻了闻公狗撒在地上的尿,然后自己在那里也撒了尿。
李总掏出手机开始拍视频:“(普通话)各位朋友好,今天是X月X号,你看我们这只红色的丫头,这只天霸,准备自然交配。(四川话)天霸!”
两狗又相互闻了闻。这时,令我、工人们和李总都很惊奇的一幕发生了:母狗上半身直立了起来,主动把前肢搭在了天霸背上。
李总像给母狗配音似地说:“(四川话)来嘛!你不来的话,我来了哟!你妈的哟,好气哟!天霸!你真是,让美女来爬,太丢狗了!不是丢人,是丢狗!哈哈哈……天霸!你看这个美女要爬你!你还是要主动一点嘛!
“(普通话)各位朋友好,这是我们十个月的母犬,两百四十斤的天霸,准备自然交配。今天是X月X号上午十一点。
“(四川话)天霸!(转过来对我们说)你看这个母狗都晓得爬了!”
试了一次没用,母狗落回地面上,走了两圈。然后她又站了起来,上半身再次搭在天霸背上。
狗没有表情,或者说没有人的那种面部表情。母狗的面部没有任何变化。可我发现,就连我也在情不自禁地给她填充内心独白,体会着她的主动,感应着她想对这条疲软的公狗传递的信息。
六
在汉语、英语和藏语中,“母狗”都是一个骂人的词。“Bitch”自是不必说。小时候学英语时,最早接触到这个词,就是在电影中经常出现的“son of a bitch”(狗娘养的)这个固定搭配。“Bitch”所指的对象其实很难总结出共同点,但似乎抛出一句“bitch”,就足以透露所指的败坏程度。这让我在很长时间里,对这个词都难以启齿,甚至是在开始做这个人狗关系的研究之后。我的导师喜欢养狗,有时会跟我聊到繁育的事情。他居然可以对“bitch”这个词直言不讳,这让我很震惊。然后我才意识到,“bitch”本来就只是母狗的意思。母狗就是母的狗而已。母狗有各式各样的,就像女人有各式各样的。
然而藏獒养殖场里的母狗几乎只有一种样式。她们都是被安排的母狗,不同的只是被安排的程度。我没想过,若是将一条母狗完全放开,她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或选择,就仿佛她还在草原。原来母狗也可以把前肢搭在公狗背上,母狗也可以去爬公狗。或许,这才是“自然”,这才叫交配。而交配,首先是一种交流。交流可能是复杂的,曲折的,徒劳无功的。没有什么是确定的。这是多么明显的事情,而我居然从来没想到过,而一直将配种默认为一套人施加于狗的、志在必得的技术。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身边突然多出来一个女生。她看起来非常年轻,最多二十岁的样子。开始我以为她是晚到的客人,后来意识到她也是服务员,因为她跟一位老板组成了一对。她也漂亮,也是四川人,但跟其它服务员的气质完全不同。她没有化妆,甚至皮肤有一点黑。也没有穿白衬衣,而是着一袭淡蓝白花的吊带长裤连体服。脚上是简朴的平底凉鞋。及肩的、没有烫染过的头发随意地披着,没有修过的眉毛粗犷地飞着。就像一个在海边玩儿的文青。她如此特别。我被她吸引了,忍不住一直瞄她。
她和老板喝酒、聊天,也迎合。但她的迎合有些心不在焉,大多数时候弓着背、撑着下巴坐在那里,嘻嘻哈哈地四处打量。一股天真烂漫的劲儿。突然,她摸了一下我的腿:“姐,我可以抽烟不?”被她摸到的地方像触了电,给我一个激灵。赶紧说可以可以。她便抽起烟来。老板敬酒,她就碰一下干掉,继续抽烟。
我对整个世界的兴趣都集中到了她身上。她还上学吗?是四川哪里人?来拉萨多久了?是不是新来的,所以穿着自己的衣服?是自愿来的吗?等一下,什么叫自愿?看起来自愿就是自愿吗?
还有关键是,为什么她看起来并不“职业”,跟其他服务员那么不一样?为什么她看起来那么……清纯?等一下,我为什么会想到“清纯”这样的词?我对她们原本的想象,就应该是“职业”吗?她们只应该有一种形象吗?那我应该想象什么?我还可以想象什么?
但或许,她也并非看上去那般清纯。面对眼前的一切,她好像显得有些过于淡然了,甚至淡漠,一种因熟悉而生的厌倦。相比之下,比她大好几岁的我,可能都要比她更“清纯”一些?对书呆子来说,田野调查可能是人生中最激烈的一次社会化体验。我诚惶诚恐地模仿,小心翼翼地自保,努力做一只静止在墙上的苍蝇。而她,同样是置身其中,又抽身其外,却似乎毫不费力,甚至完全无所谓。
然而,真的可以无所谓吗?会不会只是因为她的老板对她比较客气,她才有了无所谓的资格。跟旁边所有人都不同,他们俩虽然并排坐在一起,却隔开一点距离,只是相敬如宾地碰着杯。这也是我一开始没认出她是服务员的原因。她之所以看起来比其他服务员都要淡然,可能只是因为没有遇到大嗓门老板那样的顾客?她的不同,是否依然只是被安排程度的不同?如果没有任何的安排,她会是个怎样的人呢?
由于害羞,我没有跟她搭话,只是坐在她身旁激烈地揣测着她的身世。
有一点我是明确的,那就是我的“身世”跟她以及她们所有人都明显不同。并不在于成长背景,或受教育程度,而在于我自始至终的观察姿态。人类学的方法是参与观察,是参与+观察。可我好像从未百分之百地参与到我所观察的场景中去。不论是在狗场,还是在这里,我都最终变回一个安全的旁观者。田野调查是危险的,跟着一群中年男性老板做田野是危险的,可这终究只是对危险生活的一次模仿。无论如何,我不会被绑在配种架上,不会被扔来扔去。
我随时可以离开,代价不过是一篇论文。身为一个旁观者,我也随时可以扭过头去,只看我想看的东西。她们呢?

七
天霸和小母狗的那次配种,到最后也没有成功。母狗被牵回她的狗圈。天霸继续趴着。李总很沮丧,但也没有办法,只能庆幸前几天天霸已经跟另一条母狗配过了。狗场里还有很多种公,都等着要配种。配种季的安排,一天也不能乱。
“母狗”这个词给人一种下贱败坏的感觉;而“公狗”这个词,则给人一种强壮勇猛的感觉。尤其是“种公”,仿佛有取之不尽、贪得无厌的精力,仿佛专为配种而生。然而实际上,有很多种公并不符合这种想象。天霸就明显不是那样的种公。会有配不上种的种公吗?这么窝囊的种公,不是该被淘汰吗?
其实恰恰是天霸的“窝囊”,或者说温顺,才使牠成为了明星般的藏獒。跟母狗一样,公狗也有各式各样的。可就藏獒来说,公狗的多样性,似乎比母狗获得了多一点点的承认。
绝大部分情况下,獒友们偏爱凶猛的藏獒,尤其是公狗,因为牠们看起来更大、更威猛、更有震慑力。凶猛的狗单独拍照、拍视频会特别好看,但是就没法随便与人合影了。天霸这样温顺的狗却特别适合与人合影。任何人都可以蹲在牠身边,牵着牠的铁链,掌着牠的皮毛,与一头身形两倍于自己的巨兽摆出亲密的姿态。所以每当有旅游团或领导来狗场参观,天霸是一定要牵出来展示的。
天霸为什么这么温顺?不知道是不是跟牠的体质本身有一定关联。牠庞大的体型,其实很大一部分属于肥胖。而肥胖,据说是小时候打错激素导致的。激素会不会也影响了性格呢?又或者,天霸的温顺,其实是懒,因为肥胖而导致的懒?
无论如何,天霸这样又大又温顺的狗最适合作为藏獒的代表,与普通人合影。尤其是在旅游景点,比如羊湖。羊湖(羊卓雍措)是拉萨附近的一个著名景点。出拉萨市向西,沿拉萨河谷行驶4小时,就可以在绵延的草山之间,抵达一片绿松石般璀璨的湖泊。而在通往羊湖的路上,在服务区和垭口,常有一群小贩牵着藏獒,邀请下车的游客来与牠们合影。张数不限,只收十元。
那些摊位上的藏獒全都很像天霸。虽然品相没有天霸那么完美,可也都三吊具齐,高大,长毛,威风凛凛。而且一个都不凶。任何游客都可以站在牠们旁边,戴上皮草帽,系上哈达,手揽藏獒,对着镜头比耶。仿佛拍了这张照片,就征服了这条狗,就坐拥身后的一整片河谷。
初次来西藏的人都会来拉萨,而羊湖又是离拉萨最近的知名景区。羊湖的藏獒展位,从而成为很多人一生中第一次,甚至是唯一一次与藏獒接触的场合。
人人都知道“藏獒凶猛”。可即便是不凶的公狗,依然可以被安排在合适的位置,成为藏獒的代表,成为西藏的名片。
第一次去羊湖旅游时,我没有仔细想过这些狗是从哪儿来的。牠们肯定就是这些摊主自己养的狗了。他们都是藏族人,理所当然就是他们的狗了。直到在养殖场里工作了半年,我才发现,这些狗其实都是他们买来的。
四月的一天,狗场里来了几个藏族男人买狗。他们每看见一条品相好的狗,就问我凶不凶。但与其他追求凶猛的主流顾客正好相反,他们想要的是完全不凶的狗。他们的要求太难满足,不仅要高大、长毛、品相好,还要不凶,而且还要便宜。嫂子不耐烦地打发他们走:“现在藏獒涨价了!不像以前了。几千的大狗买不到了!”
原来他们以前也来买过多次。原来羊湖的藏獒,有很多是我们狗场繁育出来的!羊湖的需求正好与獒圈的需求形成了互补,李总得以脱手一些由于不够凶而不被主流市场接受的狗。
但有时,与羊湖的合作也没那么顺利,也会出现纠纷,甚至退货,因为羊湖男人们对于不凶的要求,是不由分说的。一条藏獒得以留在羊湖的决定性条件,就是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凶猛,因为一旦咬到游客,就会有很大的麻烦。曾有一次,羊湖男人们买去了一条看似不凶的狗,结果带回去之后发现,这条狗凶到拒绝吃饭,就给送回来退掉了。
不仅不能凶,甚至都不可以活泼,因为这么大的狗哪怕做出稍微大一点点的动作,都会吓到游客,游客就不敢拍照了。这些狗必须要有足够的定力,在一平方米大的展台上,面向公路静坐一整天,迎接数以千计的游客。
可是狗怎么可能拥有这样的定力呢?无论是天性多么温顺的狗。没有定力,人可以将定力贯彻其上。不知道羊湖男人们使用什么方法调教他们买来的狗,让他们最终展出的每一条狗,都是如此地乖巧、静默。牠们与身后如画的静默风景,和谐地融为一体,布置出西藏自然与文化的景观。

八
已经十二点了,包间里突然走进来一个藏族男人。我很好奇,本以为今晚的这个场合不会有藏族人出现。
他三四十岁的样子,中等身材,半长的头发,戴个眼镜。一进来,就与那位年长的女领导组成了一对。两人还说起了藏语。我才意识到女领导竟然会说藏语。她向大家解释,自己“半藏半汉”,意思就是在藏区工作时间长了,必须会几句。她的藏语显然比我好多了。她说这个藏族男人是她的同事,歌唱得非常好。于是点了一首《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让他给大家表演。
藏族男人非常乐意地开始了演唱,真的唱得非常非常好,简直像专门请来的歌手。调是蒙古调,词是汉语词,唱的却是一种最原汁原味,或者说最刻板印象的藏式唱腔,温柔、悠扬、婉转——
父亲曾经形容草原的清香
让他在天涯海角也从不能相忘
母亲总爱描摹那大河浩荡
奔流在蒙古高原我遥远的家乡
如今终于见到这辽阔大地
站在芬芳的草原上我泪落如雨
河水在传唱着祖先的祝福
保佑漂泊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
啊 父亲的草原
啊 母亲的河
虽然己经不能用母语来诉说
请接纳我的悲伤我的欢乐
我也是高原的孩子啊
心里有一首歌
歌中有我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布仁巴雅尔《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他一边唱,一边还娴熟地挨个向客人们敬酒、致意。上身前倾,张开双臂,笑容洋溢,让我想起了朗玛厅(藏式歌舞厅)里的那些驻场歌手。女领导在身边一路领着他,手搂住他的腰。她看见我想拍照,伸出手呵斥:“不要拍!”
像揣测连体服女生那样,我揣测起了这个男人的身世。正当这时,那个和善的老板又走了过来。这一次他对我说:“你是来西藏写生的。让这个正宗的藏族给你唱一首藏语歌!”
“写生”这个词让我一下愣住了。很多年没听到“写生”这个词了。它也如《流浪歌》的旋律一样,神奇地召唤出小时候,我背着画板去公园画画的记忆。和善的老板是在给我安排一块“实材”,一个供我凝视、临摹和再现的客体,就像公园里的花是我素描的客体,藏獒经济是我博士研究的客体,羊湖的狗是游客消费的客体。他是好心的,却不经意点破了我在场的真实意图。我并不只是在旁观,而是在对田野调查中遭遇的一切进行凝视、临摹和再现。不论是纯种的藏獒,还是正宗的藏族,都会被写进我的笔记,写进我的论文。
藏族男人现在就是我的“实材”。所以他“理应”向我展示他的文化。这是一种“自然”的安排。
如今经过回溯和梳理,我才最终想明白自己当时愣住了的原因。可在当时,我只是感到了一阵强烈的尴尬,只能赶紧说:“不用不用!”
但藏族男人没有一丝犹豫,转身立即点了一首根噶的《下雪》,走到包间中央,面向观众,看向我,再次温柔地、顺从地或者说乖巧地唱了起来。当然还是唱得特别好,配以丰富的肢体动作和面部表情。一场专业、完美的表演:
ཁ་བ་མར་མར་འབབ་དུས།
ང་ཡི་འགྲོ་ལམ་བཀག་སོང་།
དྲིན་ཅན་ཕ་མ་གཉིས་ལ།
དྲན་པའི་ཚིག་གསུམ་བསྐུར་ཡོད།
ཁ་བ་མར་མར་འབབ་དུས།
ང་ཡི་མཐོང་ལམ་བཀག་སོང་།
བརྩེ་ལྡན་གྲོགས་པོ་ཁྱེད་ལ།
སྙན་པའི་གཞས་ཞིག་བཏང་ཡོད།
དགུན་གྱི་དུས་སུ་ཕེབས་པའི།
ཁྲུང་ཁྲུང་ལྷོ་ལ་འཕུར་སོང་།
ང་ཡི་ཆུང་འདྲིས་བྱམས་པ།
རྒྱང་རིང་ཕྱོགས་སུ་བཞུད་སོང་།
白雪纷纷下,挡住我的前路
只能给恩父恩母,捎去三句思念的话
白雪纷纷下,挡住我的视线
只能给挚友你,唱起一首动听的歌曲
寒冬来临时,鹤群飞去南方
我亲爱的结发妻子,去了遥远的地方
根呷《下雪》
我心虚而专注地听着,一句都听不懂。除我之外,也没人在听。老板们都忙着跟自己的服务员大声聊天。只是唱完之后,一个老板突然走上前去,举起双手迷迷糊糊地喊了一句:“唱得好!”其他老板听到之后,也欢呼起来。
各种强烈的想法,在这一刻一齐涌了上来,让我的心跳得很快。一整晚的紧张、冲击、错乱,堆叠至临界点,伴随欢呼声,雪崩一般,坍塌成一团不可名状的情绪。
不能只是这样,我应该做点什么。我也说不清为什么,但我必须做点什么。墙上的苍蝇飞了起来。我激动得有些结巴,小声对身边的李总说:“其实,其实我也会唱藏语歌……”
李总一听,赶紧跳起来大声说:“喂!博士也会唱!博士说她会唱藏语歌!”
老板们一听,纷纷起哄说:“唱唱唱!来一个!”
二十多个人的目光集中到我身上,包括所有的服务员。我晕乎乎走向点歌机,点了一首《罗布林卡》,这首我当时唯一会唱的藏语歌,唱给这个藏族男人听:
མི་ཡི་མི་སྣ་འཛོམས་ས་ལྷ་སའི་ནོར་བུ་གླིང་ག
ནོར་བུ་གླིང་ག་མེད་ན་མི་ཡི་མི་སྣ་འཛོམས་ས་མ་རེད།
ཤིང་གི་ཤིང་སྣ་འཛོམས་ས་ལྷ་སའི་ནོར་བུ་གླིང་ག
ནོར་བུ་གླིང་ག་མེད་ན་ཤིང་གི་ཤིང་སྣ་འཛོམས་ས་མ་རེད།
རི་དྭགས་སྣ་ཚོགས་འཛོམས་ས་ལྷ་སའི་ནོར་བུ་གླིང་ག
ནོར་བུ་གླིང་ག་མེད་ན་རི་དྭགས་སྣ་ཚོགས་འཛོམས་ས་མ་རེད།
人群聚集的地方是拉萨的罗布林卡
没有罗布林卡就没有人群聚集
树木成林的地方是拉萨的罗布林卡
没有罗布林卡就没有树木成林
动物栖息的地方是拉萨的罗布林卡
没有罗布林卡就没有动物栖息
罗布林卡位于拉萨西城,是历世达赖喇嘛的夏宫。里面有大片的树林,是当代拉萨人休憩野餐的公园,还有一个动物园。我去参观的时候,发现动物园有些凋敝,年久失修,还有鸡鸭在地上乱跑。展示的外地动物有鸵鸟、骆驼、孔雀,也有本地动物,比如白牦牛、棕熊。居然还有一个专门的藏獒展室,但只关了一条狗。那条狗无聊地趴着,个头很小。照藏獒市场的标准来看,顶多算“藏狗”。听拉萨的獒友们说,达赖喇嘛的宫殿门前曾有最上品的藏獒守卫,因为藏獒是“贵族身份的象征”。我没有看到。
由于紧张,我忘词了,只能专注地盯着屏幕,把歌词囫囵吞枣地念出来。唱得很差,扯着嗓子,还破音了。藏族男人救场一般,贴心地加入进来,与我同唱。唱完之后,老板们都很赞叹的样子,更加热烈地欢呼。女领导走过来对我说:“真没想到你还会藏文!我一个藏二代,藏语会说,但是不会文字。你真是厉害!”
我羞愧无比,只想瞅瞅藏族男人的反应。他被女领导搂着,继续敬酒去了。
终
只不过唱了一首歌,我却累得瘫在沙发上。难道是气息跟不上,高原反应了?
凌晨一点半了。女领导总结陈词,众人起身,最后一次碰杯。活动圆满结束。我打起精神,观察人们都往哪里去。白领服务员们全都消失了。藏族男人跟着女领导走了。
只有穿连体服的女生还跟着我们。她的老板把宽大的外套披在她身上。她脚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换成了一双白色球鞋。拉萨秋天的夜晚已经开始冷了。她光着脚踝,冻得直跳。
上车之后,老板们说有点饿,接上老婆们去吃宵夜。
那位和善的老板从前排探过身来,对我说:“这是我们拉萨的文化、风土人情。你可以稍微点一下。”另一个老板急了:“这些夜生活怎么可以写?!不要写!”
到了一家冷锅鱼,或许也是在天海路吧,不记得了。大堂里居然有一半的位置都坐了人。连体服女生吃了一会儿,就埋头在手机上打起了“吃鸡”。老板们叫她去买烟,她不耐烦地撒娇说:“我先吃鸡!等一会儿!”老板们就没逼她。
一个老板说:“你们年轻人就是喜欢耍手机。我老二也在打这个游戏。”他说的是他孙子。
两个老板一边吃,一边讨论起了商会的事情。说着说着,音量越来越大,居然吵起来了。还站起来,想打架的样子。本来没人理他们,一见真的要打起来了,大家才赶紧拉架。两人是真的动了情绪,继续指着鼻子破口大骂。其中一个说:“你们这些当官的!有权力就要负相应的责任。没有担当!对不起XX人!”
XX是这些人共同的四川老家。
只有连体服女生,还在全神贯注地“吃鸡”,但也不忘时不时夹口菜吃。她的老板吵得都要打起来了,她居然毫无反应,只抬头看了一眼。后来越吵越激烈,实在劝不住了,李总就开车先把另一位老板送走了。
吃完饭后,连体服女生一边继续“吃鸡”,一边站起身来,头也没抬,跟着她的老板上车走了。一位嫂子看着两人离开的背影,阴阳怪气地说:“三点过了,送到屋头去。”她的老公,也就是那位和善的老板,刚才也抱过服务员,此时在她身边不发一言。
李总回应说:“好丢人嘛,可能才十六七岁。”
回狗场的路上我睡着了。很快就到了。不知道是因为半夜的开发区空空荡荡、畅通无阻,还是因为我睡着了。
已经四点了。工人老表起床,来给我们开门。老表五六十岁,也是四川人,说是李总的亲戚,但不知道是什么亲戚,只知道李总叫他老表,我也跟着叫他老表。老表和另一个老乡一起来李总的狗场干了几个月了,一个月四千,包吃包住。坐飞机刚到拉萨那天,就被李总直接接到狗场,开始干活,一天也没有歇过。所以他们虽然来了拉萨,但却从来没有真正去过拉萨,最远只去过镇上洗澡。而我们之所以能够去拉萨,都是因为有他们守在狗场。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这是一间空出来的工人宿舍。从出租屋搬出来之后,李总同意我住在这里,方便每天参与狗场的工作。我倒在床上,准备直接睡了。可是太晚了,反而睡不着。心好像又沉重,又空洞,一下一下,呆滞地捶着。但也听不太见,淹没在四面八方喧哗的狗叫声中。
2022年5月 伦敦
此作品获第一季「在场・非虚构写作奖学金」资助,严禁未经授权之转载、复制、改作及衍生创作,引用请加注连结与注明作者与出处,授权相关事宜请洽周雨霏(y.zhou43@lse.ac.uk)。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