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绳丨1月:难以逃避的匮乏(2024年,总第19期)

闹钟大概响了两次吧。当我从迷糊中猛地醒来,瞟一眼手机屏幕,时间已是凌晨4点过几分。简单洗漱后,网约车司机打来电话,我套上羽绒服,肩挂背包,提起行李箱下楼。2024年的第一次出差,就在迟到10分钟的匆忙中启程。
部分出于歉意,刚坐上车便跟司机闲聊几句。可能听出寒暄背后的疲倦,对方并未主动挑起话题,我也没打算继续振奋精神,去张开一个写作者的感官。接下来的飞行期间或动车途中,也是如此。
瞬间,我意识到一种敏感性的退化。作为职场新人,跟同事清早5点半就往会场赶,却煞有介事地在社交平台分享兴奋,这好像才是前几年的事情。不免怀念起那种生猛。
生活也许是渐渐陷入庸常的。作为重新流动的一年,大家走出去的意愿,似乎前所未有地强烈。平日碰面的朋友,很可能在某个周末就到了遥远的城市,再下次假期,贴出的照片就显示在国外了。置入灵活就业等社会语境里,这更加是个值得注意的改变。
流行语曾说,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但我担心的是另一面:身体和灵魂,总得被拉着上路。我们看似拥有全世界,恐怕纯粹绕着被包装好的概念打转。
1月的“结绳”,就从哈尔滨旅游热的讨论开始。此外,本篇内容的关注点,还覆盖记忆的保存、苦难中的诗歌,以及项飙最新采访中谈及的丰富且充沛的爱。如果症结关联着内心的富足安定,那么深入这些话题,或许就是朝着答案靠近哪怕一点。
讨论
01丨旅行,看见更小的世界
仅用三天时间,哈尔滨就创造了该市游客接待量与旅游总收入的历史峰值——304.79万人次,59.14亿元。2024年元旦假期这一成就,来自哈尔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的测算。[1]
冬季冰雪游本属于常规项目,为什么今年却令哈尔滨格外受追捧?尤其考虑到2023年末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退票风波,如此转折,实在有不小解读空间。
当地从事文旅工作多年的业者向第一财经透露,退票事件发生后,政府部门给各个文旅企业开会,要求他们必须做好接待工作,遇到任何问题,不论游客或路人都可以举报,杜绝出现投诉和纠纷。报道还称,哈尔滨的友善甚至到了本地人给“小土豆”游客“让道”的程度。[2]
但是,随着媒体的反复强调,“南方小土豆”的指代逐渐变得不那么喜闻乐见,网上关于此类表达是否带有歧视等争论开始密集出现。
《中国新闻周刊》旗下账号壹读的一篇文章认定,“南方小土豆”确实是褒义,甚至带点喜气洋洋的意思。这是以“言语的感情色彩义”来论,具体指不能孤立地看待该词组,还要结合北方人的言语和行动,比如加上前缀“亲爱的”,语气宠爱。[3]
同样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还来自《大众日报》。报道提出一个可以深挖的问题,即“南方小土豆”体现了什么?然而,作者也没打算多费口舌,直言“南方小土豆”的走红,“本质上展现了南北方人和谐相处、共享欢乐的画面”。[4]
科普作家项栋梁不认可这套逻辑。在他看来,即使旅游过程中,人与人的边界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北方人杂糅宠溺与偏见的“南方小土豆”的表达,打破了这层关系,容易滑向冒犯而不自知。[5]
一些更加尖锐的批评,指向潮流的另一方,游客,特别是女性游客哲学层面的自我规训。
署名阿月的文章,把“小土豆”表现出的幼态,与身高上的自我矮化、精神上的自我贬低关联起来。因为“小土豆”对人格尊严被侵犯时的“奶凶”反抗,实际上是以“凶”的形式来表达“奶”,目的并非为了反抗,而是出于让自己可以被安抚和镇压,召唤他者(在这里是“高大的北方人”)强势的征服。[6]
此番推论并非没有质疑。刘之行写道,如果接受上述分析逻辑,就必须承认两个前提:首先,“小土豆”是南方女性的主动表达;其次,这种主动表达构成一种普遍而长久的事实。刘之行说,二者都是荒谬的,是旨在将“小土豆”与“受虐狂”相接而对客体的扭曲。[7]
需要注意,阿月与刘之行的论述各有侧重,不构成“针尖对麦芒”式的冲突。
刘之行忽略了某些案例——视频中,南方女性“奶凶”地表达“我不是小孩”的意见,但观众又能明显感知,这种言辞更像是取悦他者(包括视频观众)的表演。而另一边,阿月也跳过追问“南方小土豆”到底先出自哪里,直接进入对某段现象的演绎。
某种程度上,阿月的选择可以理解。繁杂的资讯,令“南方小土豆”的脉络,弥散在“南方人的自嘲”和“北方人的强调”里。(补充一句,按项栋梁所言,哪怕“自嘲在前”亦不构成“强调在后”的合理性。)
我无意、也无力就此细节考究,还是回到讨论的焦点:为什么一种低幼化的标签借代,会令部分人感到不适?
指责感觉被冒犯的群体太过敏感,这实在属于偷懒、简化的做法。不论是否包含使用者的故意,“南方小土豆”一词本身就带有刺激和放大社会身高焦虑的倾向。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闻系运营的平台RUC新闻坊,曾分析知乎10027条相关讨论、微博721个相关话题,并采访了多名曾受身高问题困扰的青年,探究身高如何被建构为一种“问题”和“病症”。南北方、男女性间的身高差异,是具备社会化向度的。受访者表示,中国劳动力市场存在“身高溢价”现象,一定的身高优势可以获得加薪的机会。[8]

即使是优势者对优势地位的客观陈述,也可能误伤弱势者,连带强化“南方”与“小”的关联成见,从而忽视“高大”的“南方人”。除此之外,另一些不快,源自“南方小土豆”这套逻辑背后的“精明”。
专栏作者李厚辰在《从“小土豆”谈到话语低幼化的问题》里提醒,通过将现实世界“童话化”,和把某些事物“崇高化”的效果类似,都能有效避免争议。迷恋低幼化表达,会冲淡言论的冒犯,本质上是用可爱掩盖伤害。[9]
还记得瘟疫初期的“呕泥酱”吗?2020年,近4万名工人只用了10天左右,在武汉建造起武汉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该过程被直播记录,而围观的网民将工地机器赋予某种生命形式。[10]
吊诡之处正在于此。一篇评论说,我们推崇的,应当是“为救助病人而开设的大型工程所体现出的怜悯心”,是那些辛苦劳作的人(甚至我们有义务关心如此工期和强度下的劳动者权益保障),但呈现的现实,却是过度关注作为媒介的无机物。
“机器凭借我们的情感才获得主体性,但我们却反而去崇拜它,多么荒谬。”作者波尼亚托夫斯基如是写道。[11]
使用“南方小土豆”这些词组,当然不能跟北方人对南方人的异化直接等同。但我们也得承认,与小孩相比,成人将低龄化的词汇挂在嘴边,更容易夹带跟幼年阶段相悖的心性与想法。
例如,面对来自台湾的游客,大陆一方心照不宣地冠之以“小当归”。当媒体报道说,台湾小朋友壹壹收到297只千纸鹤,代表着大陆297个城市欢迎她的到来,我们好像无法将这种“可爱”的表达视作儿童的“单纯”。[12]
我自是承认“计算”利弊也能通往“共赢”,也没有否定无数北方人对待游客的真心,可与此同时,我确实为二元简化的认知滑坡而焦虑。
不仅海峡两岸的漫长纠葛被压缩在“归与不归”的单选题里,关于人生阶段的体认,又何尝没有被固化?“南方小土豆”这类低幼化的用词风尚,折射出主流舆论对童年与成年好坏之别的想象:至少在中文语境里,夸人年轻属于一种“社交正确”。
参加新书《求剑》的宣传活动时,作家唐诺指出:“在文学史上,老人经常是被描述得最失败的东西,典型化了,常常是由年轻很多的书写者想象出来的,一种弯着腰、说话声音沙哑、很偏心的形象。”
年过耳顺的唐诺,却对自己当下的状态很满意。“很多年纪大的人总会想回到青春,我不会,我年轻二十岁、三十岁看哪本书看不懂,我还依稀记得,觉得我自己笨得可以。”唐诺解释说,“走到这里,我比以前聪明多了,我比以前看得到东西。到目前为止,我觉得非常好。”[13]
复杂的层次,也本该出现在旅行这项活动当中。
媒体人梁文道在一档节目介绍了迪恩·麦肯内尔(Dean McCannell)关于旅行的理论。这位美国社会学家认为,我们很多时候热衷“本真性(authenticity)”,希望看到所访问地点的真实和原始一面,觉得那才是生活。[14]
但是,今天的旅途充斥着太多的表演。在哈尔滨这轮铺天盖地的传播中,最具话题度的,是圣索菲亚大教堂上空的人造月亮,是松花江冰面升起的热气球,是哈尔滨中央大街的背包企鹅。[15]
随着哈尔滨的走红,其他地方政府也试图为自己造势。搜狐网的一篇文章发问,文旅局的职能,在监管市场,还是说之后要像营销公司那样活跃于一线?从喊麦、cosplay,到演员赤裸部分身体,这些——不客气地讲——多少带有扮丑、擦边意味的宣传,能否如愿转化成实际客流,增进外界对该地的了解?[16]
很遗憾,去年因烧烤而走红的淄博,如今人气大不如前。其中或有天气影响,但《楚天都市报》记者走访发现,一些门店的淡季从10月就已经开始。从业者坦言,就“赌”接下里的春天淄博能再度火起来。[17][18]
那么哈尔滨呢?大部分本地人似乎对这个城市更有信心,毕竟哈尔滨景点并不单一,文化底蕴深厚,夏天也能摇身一变成为避暑胜地。然而,面对“旅游热能否带来长远改变”的采访,有的年轻又陷入沉默,他们留在本地的朋友,每月工资还是三千元。
《人物》的文章呈现了更多细节,离开核心景区,街道仍然安静。这个城市像被分成泾渭分明的两个世界,而天南地北的游客目睹的,很可能是作为“概念”的、本就“熟悉”的哈尔滨。[19]
我甚至担心,如此“非正常”的旅行互动,靠着过度消耗维持的宠溺与感激,一方面并未促成旅游市场该有的公平秩序与规则,另一方面,也不会让各种复杂议题的冲突缓解,令文化多元价值真正受到尊重。
1月5日,晋中平遥文旅局发布《关于禁止古城内旅拍店上架非汉民族和不符合时代主旋律服饰的告知书》,要求相关商家清理下架“非汉民族和不符合时代主旋律”的服饰。不到三天,文件又在热议中被草草撤回。[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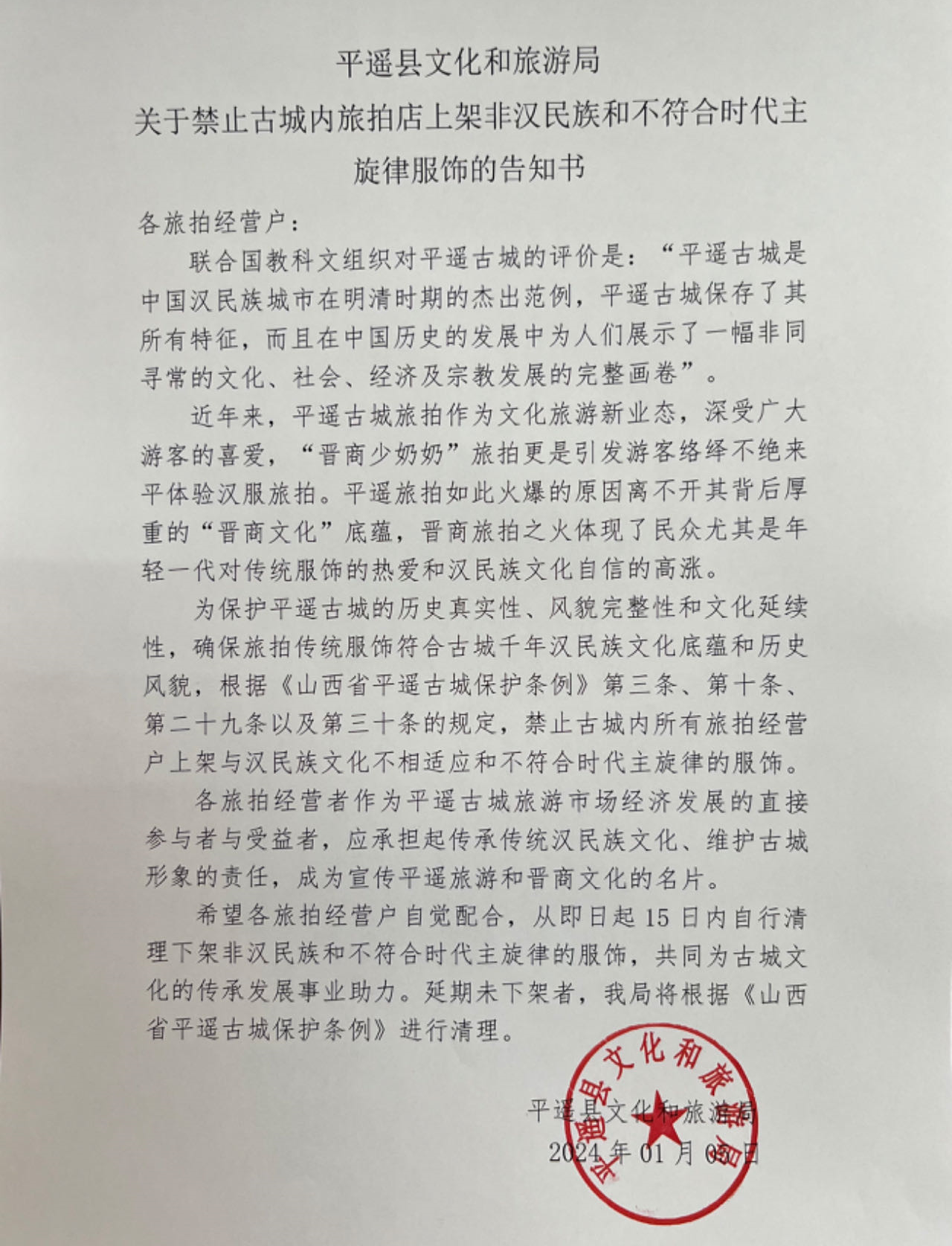
知乎的问题下,不少答主揶揄,一个县级地方政府将传统汉服的范围限制在清代,至于汉、唐、宋、明的汉服,连同其他少数民族的服饰,都被扣上“与主旋律相悖”的帽子。[21]
可就算东部沿海、经济更为发达的上海,包容度照样得打上问号。
1月里,一位身穿cosplay服饰的女性在上海乘坐地铁被拦下盘问的视频引起讨论。1月9日,《华商报》联系上海地铁,工作人员表示,上海地铁并未明文规定奇装异服者禁止乘坐地铁。然而,到了1月11日,《大河报》致电上海地铁,得到的答复却说,非日常服饰进站安检员会阻拦并报警。[22][23]
何谓“非日常服饰”?1月12日,上海地铁给潮新闻的说明是,地铁民警会作出判断。上海轨交警方则表示,规范以上海地铁发布的信息为准。[24]
如果加上国别,特别是“中国人”最熟悉的“美国”“日本”“韩国”,这类观念冲突恐怕只会愈演愈烈。
还是1月,有人发帖称,在南宁地铁通道内,看到一面广告墙上疑似出现“旭日旗”。一些评论认为,这是对将折扇扇骨的局部进行过度解读。极目新闻随后从南宁轨道交通相关部门获悉,该图案系传统元素组合装饰,目的是营造节日喜庆氛围。
尽管如此,争议画面最终被撤下。不过事情远没有画上句号。
针对极目新闻的报道,一条留言说:“一眼看出来就是半张旭日旗,撤是对的。”到1月下旬,“南京一商场被指贴旭日旗遭网友怒斥后撤下”的词条冒出,一张红色的圆形贴纸,也开始挑战人们的底线。[25][26]
我好像走得有点远了。这些跟旅行有什么关系?曾几何时,“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宣言大行其道,可这些年我们作为旅者,是否真的看到一个更大的世界?
末了,突然想起2023年被热议的“特种兵式旅游”——周末一天打卡6个景点,两天玩遍一座城市。他们的富足的,多闻的,我是如希望着。[27]
关注
01丨我们能留住时间吗?
科技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生活可以被记录和测量,比如,你今天走路的步数、这周屏幕的使用时长等。手机App往往也都设置了分享功能,方便用户将它们公之于众。但在20多年前,类似的做法只会令人诧异。
The Atlantic在一期播客中,讨论了写日记、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等方式对我们保留记忆的影响。不论采用什么媒介,记忆都是一种选择的结果。纵然有新技术,也只是增加我们保存素材的数量,并且,由于这个过程常常太随意,素材质量也不见得有多好,反倒令记忆难以把握。
参与交流的嘉宾认为,如果一次出游途中拍了太多照片,你很可能永远不会回头去欣赏。重要的并非囤积每一刻,而在于珍惜你所拥有的经历,这可以让你在人生的旅程中锚定你要去的地方。
另外,我们的记忆与外界交织,而交流这些经验会让我们更加深入了解自己。哪怕生活中的痛苦经历,如果我们认真记录,将会是一种以不同方式理解世界的机会。[28]
02丨诗歌在苦难中的价值
众所周知,诗歌无法阻挡子弹,诗歌也不会释放囚犯。但至少对于今天的巴勒斯坦,诗歌成为人们抵抗暴力的支柱。
自2023年10月以色列—哈马斯战争以来,加沙地区已有超过2万人被杀害,其中包括13名巴勒斯坦诗人和68名记者。TIME的采访中,巴勒斯坦人表示,占领军故意把作家作为攻击目标,扼杀那些讲述的人。
这是一个历史颇长的传统。20世纪30年代以来,巴勒斯坦诗歌一直在与殖民列强带来的苦难作斗争。某种程度上,诗歌是巴勒斯坦人“现实中乏力的补偿”。

那些散居海外的巴勒斯坦诗人,相对于战火下的同胞多了一种安全感。不过,这种距离使他们需要警惕对问题的失真想象,同时也有更多义务,帮助仍深陷苦难的群体。“如果我们无法用语言想象一个自由解放的世界,我们又怎么可能建立它?”[29]
03丨项飙:具体而直接的爱
面对《人物》的最新采访,人类学家项飙提到再次提到“附近”。这是他对世界的体感立足点。并且,他格外强调“附近”的异质性:并非要建立一个同人群体,而是怎么面对一个搬不走的邻居。
“一方面,你不能够把差异道德化,意识形态化。再一个,不能够把不同的观点和意识总体化。”项飙进一步解释。构建“附近”不是要把不愉快本身化解掉,而是将冲突放到关系中处理,看这个差异怎么形成,“你还是有你自己的原则,不轻易妥协,同时你又觉得维护这段关系也是你的责任”。
作为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当以色列—哈马斯战争爆发后,项飙提议把远方的政治、道德问题转化成“附近”来交流——不争对错,而是敞开去聊各自的感受和理解。虽然问题并未全部解决,但之后重点就不一样了。
2023年回国,项飙最大的感受是爱,它根植于日常,例如一次住宿经历,且跟思考相关联。爱还让项飙在动荡的世界里找到方向感:
真正失去方向的时候,往往是大的叙事盛行的时候。原因有两点,一,没有方向感的时候,大家才需要大的叙事。二,大的叙事本身很容易是空洞的,没有人能够预测历史。大的叙事会蒙蔽事实当中的很多矛盾和困难,因为话语中的方向叙述和个体生命当中的方向感是很不一样的。
……我觉得真正带给我们方向感的还是看到生命力的涌动,否则很容易就会落到抽象的好与坏的判断上,闯入具体的历史的感觉是出不来的。[30]
参考备注:
题图:Photo by Tanbir Mahmud on Unsplash
此前做过的一期旅行主题阅读:书单丨旅行的意义
战争频繁地出现在公众视野,我越发忧虑于一种血脉贲张的情绪的蔓延。关于战争的不同面向,“结绳”系列另有涉及:
> 7月:将法律当成一种思维(2022年,总第1期)
> 2月:ChatGPT回答不了“胡鑫宇”(2023年,总第8期)
> 3月:当我们在谈论公正时(2023年,总第9期)
> 10月:狗是人类的好朋友——吗?(2023年,总第16期)围绕项飙作品和观点的介绍,还可散见于既往的主题阅读、“结绳”系列:
> 书单丨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上)
> 8月:治愈自己,不必感谢苦难(2022年,总第2期)
> 11月: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附近”(2022年,总第5期)“结绳”系列邮件订阅及在Substack更新地址:https://yuliqing.substack.com
“结绳”系列在Matters更新地址:https://matters.town/@ysmwry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