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没有认清,爱也没有学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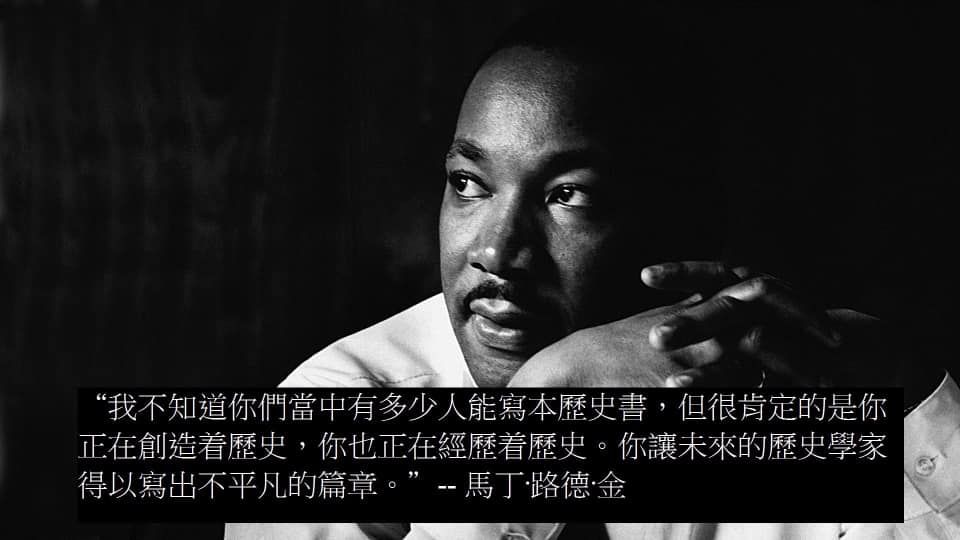
前言
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其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里,曾有这样一段描述:“我们离大革命(法国大革命)已相当远,使我们只轻微地感受那种令革命参与者目眩的激情;同时我们离大革命仍相当近,使我们能深入到指引大革命的精神中去加以理解”。法国大革命距离托克维尔出版≪旧制度与大革命≫,已然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可即使如此,在这位历史大家眼里,大革命仍距离自身所处的时代相当近。
而「国内疫情」才过去四分之一个年头。尽管还没有彻底结束,但重新深入到这段经历中去加以反思,对于我们每一个亲历者而言应该是责无旁贷的。诚如一位志愿者所言“这场灾难里,是医护人员的付出、普通人的彼此守望让我们的社会不至于信念崩塌、陷入黑暗。然而,这些荡气回肠、温暖感人的时刻,不该抵消我们对问题的深思”……
一,“中国历史不是一场能让舞台两边的人安然无恙、不受牵连的戏”——史景迁《天安门》
4月4日,一位微博博主写下了一连串没有名字的人:
“那个坐在阳台上敲锣鸣病的人。
那个深夜追着殡车凄厉地喊着“妈妈”的人。
那个在一千人共用一个卫生间的隔离所看《政治秩序的起源》的人。
那个……的人……“
3月5日,中央指导组在武汉青山区翠园社区开元公馆小区考察时,一个武汉大妈从自家的窗户向外高喊:“假的!假的!都是假的……”
3月2日,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的艾主任在接受《人物》专访时,数次提起「后悔」这个词。“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老子到处说,是不是?”
如果再把时间往前波一点,所谓的8名“造谣者”,他们到底是谁?他们有被平反吗?还有一位陈律师为了深入报道肺炎而孤身一人潜入武汉,他现在情况如何?还有人关心吗?
我相信大家都没有忘记这些人和事,只是我们不会花精力去刻意想它。因为比起钟南山、张文宏这样的大人物,以及后期集中力量办大事取得的成效,这些事实在太“小”了。还因为我们更笃信,“后期补救的成效证明了大局是在往好的方面发展”、“经过这次灾难后国家会变好的”……
真是这样吗?
我们是否有想过“今天集中力量办大事取得的成效,其实在它还是一个小事的时候是可以得到妥善解决的”?只要当初我们不那么轻易地把异见视为谣言……我们是否又想过“要完成宏大的理想,并不意味着要以让渡个人权利为代价”?如果我们知道导致很多历史悲剧的原因,并不仅仅只是“国家走了些弯路”那么简单……
我们总以为我们落后太多,总寄希望以一种最快捷的方式去完成远大的梦想。殊不知,梦魇其实来自美好的梦想。只因梦想太过高贵,使得一切恶的手段都被纵容。
我相信,待时间过的再久一些,我们再回过头看这段经历时,终究不会记住这样一个个“小人物”。毕竟,我们所受的历史观教会我们的,是去铭记那些“大人物”“大事件”。就像历史教科书上印的诸如“落后就要挨打”“弱国无外交”的总结性陈词,我们总是更习惯用这些宏大的历史观来回顾我们的历史。
只是,这对所有人公平吗?
二,“一个社会缺乏忠诚的反对者,只会增加不忠诚的赞同者”——堀田江理《日本大败局》
有一种声音说,疫情的扩散是无法避免的。「因为需要“在第一时间隔离最初病毒感染者”“要在第一时间让医生做好防护处理”“要在第一时间确定病毒的传染强度”……我们无法站在上帝视角要求当时的官员做到最好」。
很可惜,这样的观点并没有认清疫情扩散的根源。以上种种并不是处于“第一时间”的维度上。真正处于“第一时间”轴上的,是当武汉的一线医院已经有明显证据证明病毒出现了“人传人”,武汉政府仍选择压制这样的声音,并视其为谣言,进而再向上隐瞒新增病情。直到1月20日钟南山根据所掌握的情况,才做出了早已经被武汉的一线医院证明了的“人传人”的论断。3日后,武汉政府慌不择路的选择封城。然后便是殃及全国,蔓延全球……
试问:在“第一时间”尊重专业意见,不随意将异见视作谣言,将发生的情况一五一十的呈报上级,这些也需要“上帝视角”才能完成吗?如果一个不允许另一种声音存在的制度都叫没问题,那怎样才叫有问题?这和其他国家处理疫情的快慢好坏又有什么关系吗?而正当疫情肆虐,围绕冠状病毒的起源却又出现了类似当年SARS的阴谋论(2003年曾有传言非典是针对“黄种人的病毒”)。
我们真的有被针对吗?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自然地接受这种观点?
我们不妨先问问自己以下几个问题:
“对于国内某一问题的指摘,我们是否惯性地认为这是针对中国的偏见”?
“对于国内某一现象的批评,我们是否惯性地认为这是针对中国的批判”?
“当围绕同一事件出现多种观点时,我们是否惯性地更希望能有一种权威的声音来告诉我们事情的真假”?
我相信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就是阴谋论为什么可以大行其道的答案。阴谋论本质上不是关于阴谋的理论,而是断定事事背后总有阴谋的一种认知方式。提出和相信阴谋论的人,并没有深思熟虑后的见解,也非怀疑精神的表现,而是直接展现了其认知世界的直观感受。如此而已。
正常的逻辑,应该是用事实推导出观念。而不是用固定的观点重构事实,一种基于先入为主的想看到的所谓事实。而我们今天持有的观念,似乎更接近某个战争狂人所描述的情景“对批判国家,社会和指导者持有一种憎恶,并坚信那是少数派和异端者的罪恶。都抱有同样的想法,认为想法和大家不一样的人就是国家的敌人”。
当官方将不同声音定义为谣言的时候,我们扪心自问一下,我们那个时候更倾向于哪一边?我也相信没有人会质疑那位武汉大妈的控诉,但我更相信即便她喊出了那一嗓子,也不会有多少人关心这件事的后续发展。我还相信当那位博主写下那些个曾经鲜活的无名氏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无限感慨。但是,也只会停留在感慨而已。
公开的混乱或许不堪,但比公开的混乱更为恶劣的,便是假装一种秩序井然,却压抑正在挣扎中的真实秩序。
三,“一个没有英雄的国家是不幸的,但一个需要英雄的国家则更是不幸的”——贝尔托・布莱希特《伽利略传》
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全国的电视台全部统一播放汶川报道,没有任何其他节目可以观看。那时我正在读高三,默哀的那天没有多少人敢穿颜色鲜艳的衣服,老师们更是直接从他们的工资卡上被扣除100元人民币作为捐款。整个学校都弥漫着强迫悲伤的气氛。那时的我虽然不明所以,但总有一种“不自然”的感觉。后来,我明白了。这种“不自然”的感觉,叫做“不言论的自由”。我不想讲话,可以不讲,不想发表意见,就可以不发表,没有人可以强迫你。这其实很弥足珍贵。
12年后,又迎来了一个公祭日。
有人说,哪怕素不相识,为逝去的受害者和英雄默哀也是应该的。我无意贬低悲伤的表达,只要是真实的情感都值得尊重。但是,欢乐或悲伤应该是自发性的。任何一个人的情绪表达都不应该被禁锢。特定时刻的集体哀伤,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会铭记。抽身于集体悲伤的和鸣,也不代表无情和轻慢。被加工后的景观无论看起来多么美好,始终是不真实的。
也有人说,哪怕是形式,遵守一次又能怎样。我记得自己在念中小学的时候,有过这样的经历:“为了争取先进学校的名誉,学校会专门抽出一个周五的下午进行全校大扫除,为的就是几天后的领导检查。检查过后,清洁卫生还是回到老样子。或者,为了迎接教育局某领导的视察,学校会安排某个班级在一个叫做多媒体教室的大教室里举行一堂别开生面的公开课。哪一个老师授课,哪一个班级听讲,哪一个学生举手,哪一个学生发言,从指派到演习差不多会花一个月。视察结束,课程该怎么继续还是按老样子继续。再或者,当某个领导人提出了某个理念,学校也会组织相应的集体活动来响应号召。记得有一年是集体合唱,歌名叫八荣八耻歌……”。我是89年12月生的武汉人,和我同世代的人,我们应该都有共同的记忆。我们从小接受的「形式」,似乎并不止一次。今天,又要再加一次吗?只因为从来如此就应该习惯吗?从来如此,便对吗?
集体仪式的纪念,其实正是遗忘的开始。当个人的情绪被“上升”至国家大事的时候,属于个人的记忆和情感是会在不知不觉中被剥离掉的。因为“公祭”“烈士”“英雄”,这些并不属于个体的记忆或伤痛。纯粹的记忆和伤痛是脆弱、渺小的,而非坚韧、宏伟的。当数年甚至可能只是数月之后,我们再回想今天发生的事时,我们的个人感受就会变得无法体验。最终,我们只剩下在国家级的宏大叙事中追寻认同和慰藉。然后失忆、麻痹、戏谑……如同我本人已经无法感知08年发生的那些事了。
待我们的后人回顾我们这段历史时,也会像我们回顾前人的历史那样,“几个总结性陈词”“几个烈士或英雄标签”“又一条国家走过的弯路”……而所谓的真相、反思、追责,则早已被遗忘在今天的公祭之中。
汉学家费正清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中国新史》里,曾这样解剖中国的帝王政治:“君权无所不在,几乎凡事都要皇帝说了算。凡事因此而政治化,连穿衣、礼教、书籍、绘画都不例外。人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带上政治意味”。
有时候真的不得不感叹:“很多事一直在变,很多事从未改变……”
而比起美好的憧憬,我情愿相信一个“灾难过后擦干眼泪,埋完尸体,便重新回到鸵鸟式的岁月静好”的国家,哪怕地老天荒,它也是变不好的。
结语
2013年,中国政法大学的一位教授在毕业典礼上有过这样一段祝辞:
“面对滚滚而来的浊流,
如果你不能总是抗争,你是否可以选择偶尔抗争;
如果你不敢积极地抗争,你还可以选择消极地抗争;
如果你不能勇敢地表达,你可以选择含蓄地表达;
如果你也不敢含蓄地表达,你可以选择沉默。
如果你没有选择沉默而是选择了配合,但你还可以把调门放低一些。
在你主动的或被迫地干着坏事时,能不能内心里还残留一点不安和负罪感。这一点儿不安或负罪感,仍是人性未泯的标记。即使你不去抗争,但对其他抗争者,要怀着几分敬重,即使没有这份敬重,也不要在背后放冷箭,使绊子,助纣为虐。我希望,你们在大潮袭来时,选择站在理性和正义一边,文明与进步一边,选择站在人民一边”。
今天大潮袭来,我们都站在了哪一边呢?当我们做出选择的时候,我们是否又是一个明白人呢?龙应台在《大江大海1949》里,记录了无数人在那一刻的选择:“走还是不走?走,是一辈子;不走,也是一辈子”。一个人是如此,一个国家更是如此。国家走了一段弯路,对一个人来说,就是毁了一生。
4月8日,武汉终于宣告解封。早餐的热干面,豆皮,面窝……这是只属于武汉的记忆。再过些日子,户部巷,楚河汉街,汉口江滩也会恢复往日的热闹气息。76天后的重逢,武汉人会感慨,会惊叹,会激动……
此情此景,或许就像奥地利诗人里尔克晚年的一首诗所描绘的那样:“苦难没有认清,爱也没有学成。远远在死乡的事物,没有揭开了面幕。唯有大地上的歌声在颂扬,在庆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