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回来了,今夕是何年
周日进山的路上,手机里好友发消息说,柴静回来了。第一反应居然是不敢信,打了一个问号过去,她回复一个YouTube视频链接,《6集纪录片———对话圣战分子》。
还是不敢信,“是她做的吗”
-“对”
这才回过神来,天呢,真的是她,多少年没消息了。
白天攀岩的间歇,看到票圈里有人转发了预告片视频,来自一个叫“欧洲的陌生人”的视频号,十分钟就没了。接着她转了一个长图,柴静的发片语,点开来,多熟悉的文字啊,人性的温度和新闻调查的克制,“我想知道的真相我应该自己去找,因为我是那个受过训练的人。” 的使命感。天呢,真的是她。
傍晚回到家,打开视频,熟悉的声音,追问的视角。人不是非黑即白的,在欧洲长大,看起来像是普通大学生的人,被招募进圣战,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短短四分半,信息在头脑中爆炸,十年前在宿舍熄了灯等的一期期看见,上课考试间隙看的一篇篇博文,《看见》里面一遍一遍说的东西,“真实自有万钧之力” “我们终将难舍难分,像水溶于水中” “我关注新闻中的人” “不断犯错、不断推翻、不断疑问、不断重建” “人心人性中的种种枷锁,不是一挣一扎可以摆脱”
尘封多年的记忆开始复活,鲜活到能尝到那个味道,时间真的是线性的吗?
今夕是何年
鬼使神差的,前两周重新打开她的《穹顶之下》,看其中的逻辑一环一环相扣,惊叹于她的严谨,又在转折的时候,充满人的温度。看的时候其实有些惊讶,其中很多追问和事实,在八年后的今天,已经不可能在这片土地看到。会想她这些年在做什么,直觉里不相信她真的会像小报报道的那样,从此“回归家庭相夫教子”。她是多犀利有才华的一个人啊,12、13年,刚发了新书,卖了几百万册,几乎是在事业的巅峰,突然中断,销声匿迹。更相信只是蛰伏,在聚光灯之外做事情,在事情成熟、大环境变好之前,路人甲如我大概是不会知道的,直到今天……
恐怖主义、圣战、极右翼崛起、社会割裂、政治光谱极化,她选了这么难啃的一块骨头,因为“世界没有孤立的安宁”,因为三岁的哈维和女儿同岁,因为“我是那个受过训练的人” 像是逼到眼前骨子里叫你不得不做的事,像是15年“这是我和雾霾之间的一场私人恩怨”。起点似乎很personal,但是她一锹锹地挖下去,直到呈现足够多的真实,触碰到庞大机器运作的机理,摇撼人心。
还有一种神奇的感觉是,切入选题的方式如此柴静,就是那些年采访尘肺病、卢安克、兰考弃儿、汶川失独家庭的方式,但是她把视角扩展开来,投向世界,和新的生活相关、也是世界难解的问题。圣战分子几乎是最容易被概念化、被脸谱化的人,但她用人的视角去接近他们,带着《双城的创伤》那样的温度和追问,“一个国家由人构成,一个人也由无数他人构成”,这么多年,一直没变。
离开央视的平台,缺少资源,人在异乡,一个语言不通的陌生人,敏感艰深的选题,漫长的时间线,她一直没有放弃调查报道,直到它变成生活的一部分。仅仅这一点,就令人敬重。在文章的结尾,她写“很多夜晚,在离家万里的大陆上,从稿子中抬头,看到明月广照大地,我找到我的归属。” 读得很想落泪,一个新闻人用她的方式,不论境遇如何,坚持做报道,并把它们化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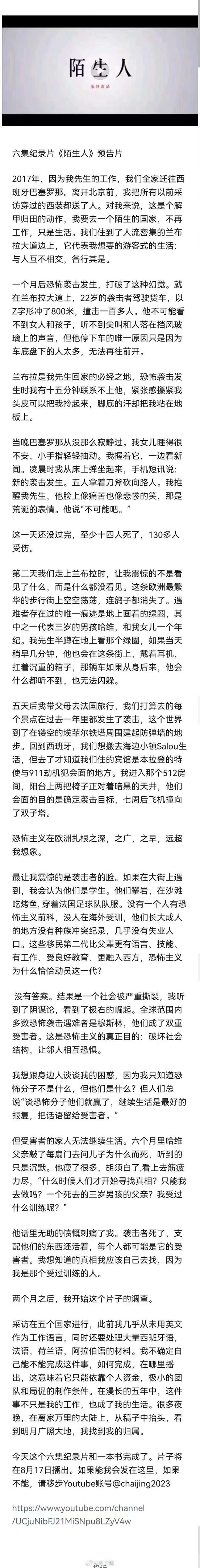
以下是一些矫情的私人体验
去年开始,在上海封城和此起彼伏的反乌托邦也写不出的荒谬之中,总想起13年春天柴静回湖南文广做的那期《夜色温柔》,在那期节目里,她念了一封读者来信,印象很深。
“(茨威格)说年轻的时候只是觉得蒙田好,不知道好在哪。直到他在大力摇撼人心人性中的种种枷锁,但他却以为,那些枷锁早已经被打碎。当时的茨威格只是把蒙田作为争取心灵自由而做的斗争,当作历史上的斗争,来给予尊重和崇敬。他根本没有意识到,那些枷锁当时正在被命运重新打造,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冷酷无情和残忍野蛮。”
“经历了二战,中年的茨威格才真正认识蒙田,将他当作’并肩作战的兄弟‘,他明白,要义不在于打碎枷锁与反抗权威,而在于不断地打碎,持续地反抗。不是一挣一扎,而是坚决地、永不妥协地保持住自我。
于是他说,谁描述了自己的一生,谁就是为所有的人而活着。谁把自己所处的时代表现出来,谁就是为了所有的时代。“
信在这里结尾,海浪声中现出胡德夫的《最最遥远的路》,我在熄了灯的宿舍,起了一身鸡皮疙瘩。那时候十几岁,觉得柴静好,把她的书、节目和广播都去考古了一遍,感激她带我进入新闻的世界,但好像一直隔着一层布,遥远和抽象。直到十年后,新闻自由被一步步蚕食到接近于无,人被以防疫为名关进大型数字牢笼,枷锁正在被重新打造。我才开始意识到,已从公众视野消失多年的她,当时想要说些什么。
十来年前她的博客里写过这么一段,大意是媒体圈的人和她聊天,说有一天,可能大家慢慢都做不下去新闻了,回家、隐退、忙别的事,一过就是很多年。直到有一天,发生了大事情,你坐着轮椅,被人推了出来。你准备播报,世界屏息聆听。
多年来,我一直在等着这一天
感谢她让这一天在这个夏天变成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