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8 悉达多·出人头地·文明的气氛|《野兽爱智慧》

01 悉达多
不许结伴而行,务必独自游历教化。以个体的自我面对向他一人展开的世界,体验、亲证、自律、实践。一个人,在路上。汝当自依。
佛陀的一生中,有过几次让后人颇费心思的转折:
为什么要抛弃他现成给定的富足生活与王位继承权而出家过流浪者的生活?
为什么在他的禅定修养已达到很高造诣而不得不令其师事的两位当时全国水平最高的禅定家惊讶并打算立他为思想继承人时,他却离开了他们?
为什么在他已与苦行对峙了长达六到十年而品尝了一般苦行者都未能做到的一切肉体磨难之苦并使得周遭人都满怀敬佩之情如圣人般看待他时,他却放弃了这甚至是唾手可得的名誉而离开了苦行林?
为什么在他于毕钵罗树下(这棵树后来被称为菩提)趺坐成道后实际已是全国最具境界的哲悟家而还要徒步跋涉到几百里外的异地去传教呢?
为什么在他已然拥有了近千名弟子后却不满足于平平静静做导师的生涯而还要坚持一个人独行游历教化呢?
为什么与婆罗门的对峙与征服,对提婆达多叛逆的粉碎,九横大难之后,在他八十岁高龄时,在释迦族灭亡后,他还会从婆吒百村渡恒河并选定他的故乡作为他最后传教的方向呢?
为什么,他能不顾恶疾缠身在弟子劝他休息时还要侧卧于沙罗双树间支撑着为前来寻访的沙门说法并以此作为自己临终的方式呢?
我总是怀着一种知识的渴望。一年又一年。发现在万事万物的本质中,有些东西不能称为“学习”。惟有一种知识,那是无所不在的,在你里面,在我里面,在一切生物里面······对这种知识而言,它的最大的敌人,莫过于有学问的人,莫过于学问。
从别人的讲道中是无法求得解脱的。远离所有的教条与导师――哪怕他是众望所归的救世者,哪怕他是另一个灵魂中的自我。像一个刚出世的婴儿,此外他什么也不是,此外,什么也没有。
再没有人像他那么孤独了。他不再是个贵族,不属于任何职工组织,不是个寻求职工保障而在其中享受其生命与语言的工匠,不是个婆罗门,不是个属于沙门社会的苦行僧,甚至连深山中最与世隔绝的隐士,也不是一个人孤孤独独的,他还是属于人类社会中的一个阶级。
迦文达做了和尚,于是成千个和尚都成了他的兄弟,他们穿着同样的僧袍,享受着同样的信仰,说着同样的话。而他,悉达多,他属于哪里?他分享谁的生命?他说谁的语言?
他一无所有,却得到了:悉达多,他自己。
当所有的语言已无法承载他的思想时,悉达多请求旧友吻他的额头,那一瞬间,迦文达在悉达多的面孔上看到的是一长串川流不息成百上千的面孔,出现、消失、更新。
一条濒死的鱼的面孔,一个初生婴儿的面孔,一个谋杀者杀人与被处决的两种面孔,男人与女人赤裸的身体,横卧的尸体和许多动物的头――全都纠缠在爱、恨、毁灭、再生的关系里,既静止又流动,铺开在一层玻璃般的薄冰或水的面具上面――那是悉达多的脸,那脸上是只有俯瞰与亲历了这一切的人才有的半优雅半嘲弄的微笑。

02 出人头地
中文中"出人头地"是一个难以用西方语言对译的一个词。与它比较接近的是ambition,即"野心"、"抱负",拥有ambition的人虽然不安分,但是他所要实现的是自己的某个目标,一旦自己的某个梦想成为现实,这个人就有成就感,就会感到满足,他以自己的尺度衡量自己的成功。
而对于想"出人头地"的人来说,其奋斗的目标在于获得一个"人上人"的身份,他需要在与别人相比当中,证明自己是与众不同的、出类拔萃的,他需要时时有人仰视他,有人艳羡他,承认他是如何了不起,如何能够超越许多人,一跃而成为众人仰慕的对象。
换句话说,"出人头地"需要有人围观,荣华富贵需要有人在场。这是一种奇特的精英意识,所依据的不是对于社会的责任感或者贡献,而是被他人知晓、自身出名的程度。所谓人和人之间的真正平等,这种平等的根据何在,对这样的精英来说,是完全陌生的。
除非出人头地,否则便一无是处;除了能够高居于他人之上,否则便一无可取。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是——若不流芳百世,便遗臭万年。
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很长时间的艰苦准备,寝食不安地苦读不已。读那些遥远的古代圣贤的书,四书五经,把它们读得滚瓜烂熟、倒背如流,以至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将它们信手拈来,脱口而出,博得众人的一片称赞。
在这里,知识不是作为对于世界、对于周围环境、对于人自身的某种了解,而是完全脱离了作为个人的经验环境,脱离了这个有血有肉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的经验事实。一头扎在圣贤的典籍之中,没有必要将某种现实,拿来作为一个人头脑中世界图景的类比或者参照物。
依拉康的现实界、想象界、象征界三重世界的划分,这样的人,他们仅仅面对想象界和象征界,而不用面对现实界,甚至根本就不存在这样一种现实世界。一个农民的儿子,如果他立志改变自己的命运,由"民"变为"官",那么他越是远离农事,农业方面的知识,他便越有可能获得成功。
在他的知识谱系上越少涉及他本人,越少有他个人的标志,他便越有希望达到目标。而说到底,"现实界"的被悬置,是处于这种现实中的个人被悬置起来的结果。
一个人无法经验这个世界,是因为他无法经验他自己。他的整个存在具有一种不及物的特点,既不触及这个世界也不触及自身。"读!读,读!书中自有黄金屋;读,读,读!书中自有千钟粟;读,读,读!书中自有颜如玉。"这么一个人,假如他的目光暂时离开书本,而抬眼看世界,会看到什么呢?一片朦胧和困惑而已。
早在客观上进入权力关系之前,他们在想象中已经把自己当作权力游戏中的一方,他们就生活在某种想象之中,把想象当作入口,而进入一个想象的世界。
他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满腹经纶,出口成章,和历史上的那些圣贤对话,替逝去的和当今皇上着想,头脑中考虑的都是国家社稷大事,为之夜不能寐、食不知味,"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心里唯独没有他自己(这好像是一句歌词,记不清什么歌了)。
借用马克思的表述,这种人把一些完全不属于他们自己的思想感情当作了自己"真实的出发点",而作为真实的个人、有血有肉的个人的存在,在一片云山雾罩的高词大语中,被一笔勾销了。而且这种勾销越彻底,将个人掩埋得越深,便仿佛离某个目标越近。
在这个意义上,某种屈辱不是实际上卑微的社会地位造成的,而是他对自己的如此惩罚,将自己放在一个需要自我隐匿的位置上,把自己当成了需要销毁的对象,如同罪犯一般。他脸上始终挂着的罪犯般的表情,时时在提醒人们,这个人还有尚未来得及藏起来的东西,他继续像耗子一样匆匆掠过人群,惊恐地寻找安身之所。
同时这种隐藏的行为,也是需要深深地隐匿起来的。最成功的隐匿是替换、置换。把各种各样遥不可及的、与自己没有切身关系的东西,说成恰好是自己所想的、所拥有的、所投入的,用普鲁斯特的《在斯万家那边》开头的话来说,即"凡不是我自身的东西,土地、事物,在我看来都更宝贵、更重要、具有更真实的生命。"

03 文明的气氛
今天重读《给胡萨克的公开信》,一字一字,念出声来。又一种新的阅读体验,同时还联想到了相关的论述,比如罗洛·梅《爱与意志》,徐贲的《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动》,崔卫平的《积极生活》,米奇尼克的《通往公民社会》乃至马斯洛的《动机与人格》等等。
它们似乎在对话,在呼应,而我是它们的媒介。这种感觉真是令人兴奋莫名.“办一座时空沙龙,用文字摆开厅堂,供古往今来各路名流穿梭往还,聚兴高谈。因为地域、年代不同而无法彼此相见的哲人诗人,围坐在自己提供的虚拟客厅里,切磋学问,碰撞观点,印证心得,交流情思。
自己时而像一位主持人,分置宾主,提供话题;时而像一位八面玲珑的贵妇人,怂恿阔论者,抚慰失意者;时而又像一位公正的仲裁者,比较优劣,评说短长。
随着文字的展开,又不断有生客破门而入,有熟人摔门而出,读者的耳边,门铃声和司仪的唱叫交错,每一次窗帘的颤动,都能闪进一缕别样的光线,抖落几枝别样的枝叶。在领教各路见识之余,甚至还能呼吸到风,感受到时间。”
2016年9月24日萨义德离开三年了,2016年10月5日哈维尔70岁了,2016年10月14日阿伦特100岁。得写点文字,怀念他们一下。他们是“文明的气氛”的创造者和呵护者。
一个人越是彻底放弃任何全面转变的希望,放弃任何超越个人的目标和价值,或任何对一种“外在”方面发挥影响的机会,他的能量就转向阻力最小的方面,即“内在”。今天的人们一心一意想着他们的家庭和房子,他们在那儿们找到安息,忘掉世界的愚蠢和自由地体验他们的创造性才华。
他们在自己的房子里布满各种用具和可爱的东西,他们试图改善他们的食宿,他们想为了使自己生活变得愉快,修建小别墅,照料自己的小汽车,将更多的兴趣放在食物、穿着和家庭舒适上。简言之,他们将兴趣转向他们私人生活的物质方面。
当权者欢迎和支持这种转向私人领域的能量的溢出。但这为什么?因为它刺激了经济的发展?当然,这是一个原因。另一方面,目前政治宣传的全部精神,都在平静而有系统地欢呼这种“内在化”倾向,将此当做世间人性满足最深刻最本质的东西。
这非常清楚地表明为什么当权者真的欢迎这种能量的转换。他们在其中看到心理学的意义:从社会领域的一种逃脱。为了正确地将这种剩余能量分流——如果导向“外界”将或早或迟转为反对他们,反对他们顽固依恋的权力的特殊形式——他们毫不犹豫地将实际上是绝望的生活代用品描述成一种人类生活。为了平稳地操纵社会,社会的注意力被故意转向自身,即脱离对社会的关怀。
通过将每一个人的注意力集中在他仅仅是消费品的兴趣上,是希望使他没有能力意识到在他精神上、政治上、道德上日益增长的被侵犯的程度。将他缩减成一个初级消费品社会的各种观念的简单容器,是打算将他变成复杂操纵的顺从的材料。
他或许抱有一个愿望,希望实现某些作为一个人类成员所拥有的巨大的和前所未有的潜能,这种危险通过将其禁闭在他作为一个消费品发挥作用的可怜领域,臣服于一个中央调控的市场限制而被掐死在污泥中。
一种杂志是社会有机体的微量元素。通过它,社会能够意识到它自身。权力对杂志粗暴的干涉,是对有机体内部进行的动力过程的一种打击,对所有它的许多功能平衡地相互作用的一种干扰。
正像长期缺少一种维生素(在数量上仅仅是人类食物中可以忽视的一小部分)可能使一个人生病,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失去这个刊物对社会有机体影响远甚于粗粗的一瞥。
在一个文明的社会有层次的世界中,很容易说明知识、思想、创造的真正重要性并不限于它们为一个特殊的小圈子的人们所拥有,这些人首先地、直接地、几乎是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不管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
总是有一个小圈子,尤其是在科学领域。但是正在被谈论的这种知识,通过不论多少中介和转换,最终可以深刻地影响社会,其最初的凝结和酝酿实际上仅仅由一个很小的和独立的圈子直接地和清晰地观察到。甚至接下来,这种行动继续存在于一般说来社会的知觉之外,但它仍然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因为我们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一些难以察觉的知识火花从少数人的脑细胞中擦出,这些人的头脑仿佛特别适合那个有机体的自我意识,这闪光将突然照亮整个社会的道路,社会甚至没有意识到它是怎样到来的。但是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
因为甚至那些其他的无数知识的闪光,它们从来没有在社会前头照亮其道路,从整体上看也有其深刻的社会重要性,仅仅通过它们发生这个事实,它们或许已经投射光芒,在它们特殊的闪现中。
它们实现了社会潜能的一个特定的领域——不仅是它的创造力量,或简单地说就是它的自由;它们也帮助和维护了一种文明的气氛。没有这种气氛,便没有更亮的闪光的东西出现。

04 伪士当去,迷信可存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因肺结核病而逝世。
1908年,鲁迅写了篇文章叫《破恶声论》。在这篇文章中,他说现在有两种“恶声”,一种说你现在要成为“世界人”,用现在的话说,都全球化了,还谈什么文化、民族或者其他的东西?另一种说你现在要成为“国民”,因为现在这个时代正是民族主义的时代。
鲁迅说这两者都是“恶声”,因为这些说法中没有人的自觉、没有人自身的独特性,无非是鹦鹉学舌而已。他说这是“万喙同鸣”,用他晚年的一篇文章的题目就是“无声的中国”。“无声”不是没有声音,而是吵吵嚷嚷,都说差不多的、自以为绝对正确的话。
这篇文章中有一个特别好的命题,叫做“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他说这是当务之急。“伪士”就是那些每天抱着自以为进步或先进的观念的人,办洋务、搞改良、谈民主、论立宪、搞共和,左的流行他就左,右的流行他便右,全球化来了他就成了“世界人”,在民族主义潮流中他成了“国民”。这些人是发不出自己声音的“伪士”。
他为什么又说“迷信可存”呢?迷信首先你要信,你不信不会迷,这里有一种对“真实感”的追求。没有这种真实感,一切都是虚无的。鲁迅批评名教,反对传统,但他竟然对“迷信”有这样的理解,他对“鬼”的世界有着隐秘的迷恋。
2016年10月19日 完毕于北京野兽爱智慧居
2020年4月5日修订于北京野兽爱智慧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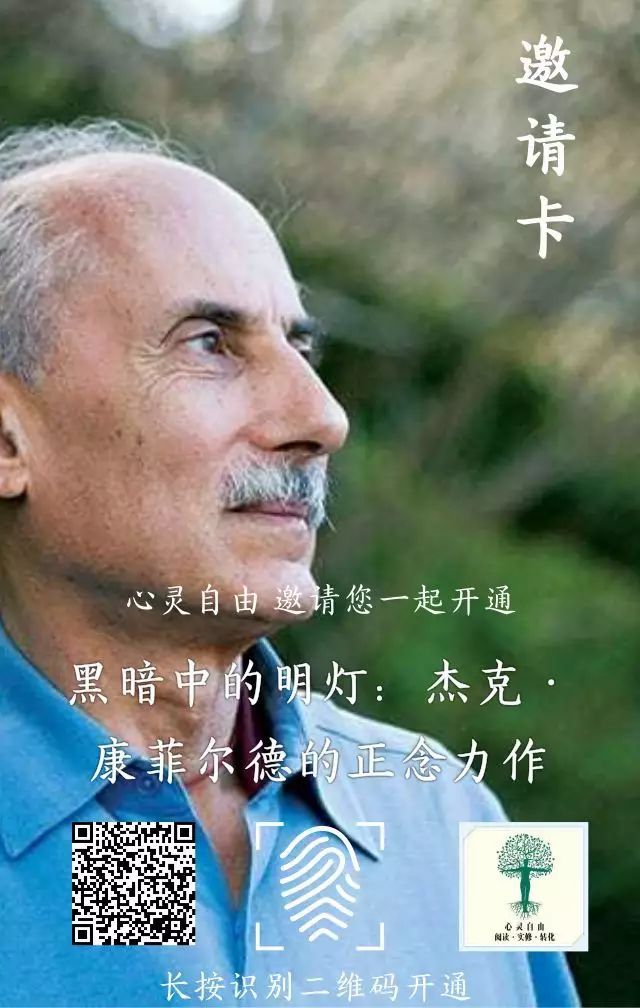
延伸阅读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