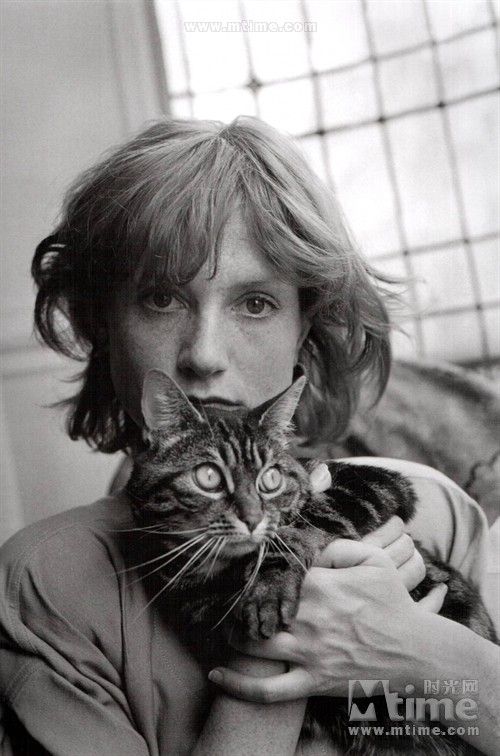如果我年紀輕輕地就死了,沒有出版過一本書
拉開地下室的門,黑漆漆的屋子裏擠滿了年輕人。女青年的烈焰紅唇,男青年的海軍帽,新潮的著裝打扮,與上海這座城市相得益彰。主持者手扶著直立話筒,介紹這次的活動。主持者站立的那壹小塊地方是唯壹有燈光的地方。朋友和我彎著腰,越過坐在地上的人群,擠到「舞臺」處。坐在冰涼的地墊上,我仰望著手臂上有紋身的主持者,還有他的光頭,轉過頭,左邊的地上有壹只點燃著的蠟燭,旁邊還有壹瓶可樂和壹只煙灰缸。
掌聲過後,壹個女生上去朗讀了《美麗新世界》中野蠻人與統治者的對話——
「我不需要舒服。我需要上帝,需要詩,需要真正的危險,需要自由,需要善,需要罪惡。」
有人拍照片,或許是此次活動的攝影師吧。閃光燈在黑暗的室內,每壹下的閃亮都讓人睜不開眼睛。詞語鉆進耳朵,詩意進入腦子裏。壹個高高瘦瘦的男生,戴著眼鏡,站在人群裏讀詩,他沒有用麥克風,在黑暗中吐出壹個個句子。有的朗讀者去到舞臺上,用麥克風,用投影儀,有的朗讀者在人群中,用他的人聲與在場的人連接。壹個身穿黑色裙子的女孩,將燭臺放在投影儀上,在地上鋪了壹塊紅布,而後,將鐵椅子立在紅布之上,主持者給她播放了背景音樂,她開始讀詩。讀完之後,她拿著燭臺走下臺來,用燭火點燃壹根煙。
倒數第二個朗讀者,讀了余秀華和聶魯達的詩,最後壹首《如果我年紀輕輕地死了》,我很喜歡。
壓軸的主持者朗讀了布考斯基的《苦水音樂》(以及《劊子手笑了》,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他說這首詩要送給他那些因為愛情受傷的兄弟們,引起大家壹陣哄笑。最後,他朗讀了李白的詩——眾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閑。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他幽默的腔調,換來的是大家的笑聲和喝彩聲。
第壹輪朗誦結束,差不多10點鐘了。我跟六尾打招呼說,我得走了,因為住處偏遠,得趕地鐵。他說最精彩的還在後面。在六尾籌備 「如妳所願」詩歌朗誦活動時,他在朋友的群裏問「群裏誰是詩人」。雖然我對活動感興趣,也偶爾寫詩,但我不並認為自己是「诗人」,所以我並沒有在群裏做任何回應。誰都可以寫詩,誰都可以寫作,詩意就在日常生活之中,就像賈木許的《帕特森》中的公交車司機壹樣,就像捷克詩人揚·斯卡采爾寫的「詩人並沒有創造詩歌/詩就藏在背後某個地方/它在那兒已經多年/詩人只是把它發現」。
屋裏響起壹個男聲的抗議——「妳們能不能不要在裏面抽煙?」
我想他們接下來應該會朗誦自己寫的詩吧,但是我不得不去趕地鐵了。
回去的路上,地下室裏壹群年輕人朗誦詩歌的場景在我的腦中揮散不去。似曾相識的感覺讓我想起《死亡詩社》裏的學生們在山洞裏講故事、演奏音樂、朗誦詩歌,壹張張面孔在手電筒光裏晃動,呈現出濃烈的生命質感和靈魂光環。這樣的詩歌朗誦活動,不也正如電影中所說:我們讀詩寫詩,非為它的靈巧。我們讀詩寫詩,因為我們是人類的壹員。而人類充滿了熱情。醫藥,法律,商業,工程,這些都是高貴的理想,並且是維生的必需條件。但是詩,美,浪漫,愛,這些才是我們生存的原因。
附:
如果我年紀輕輕地死了
佩索阿
如果我年紀輕輕地死了,
沒有出版過壹本書,
有看見過我印成鉛字的詩歌是什麽樣子,
我請求那些由於我的原因而拒絕的人
不要拒絕。
假如那種事情還是發生了,
那也是應該的。
即使我的詩歌永遠不會出版,
它們也有它們的美麗,
如果它們是美麗的。
可它們不可能既是美麗的而又不能夠出版,
因為根也許藏在地下
但它們的花朵會在敞開的空氣中開花 並讓所有的人看見。
那是必然的。沒有什麽能夠阻擋。
如果我年紀輕輕的死了,
請記下: 我永遠不會比壹個玩耍的孩子強多少。
我是像太陽和流水壹樣的異教徒,
帶著壹種唯獨人類沒有的普遍的信仰。
我是幸福的,因為我不要求任何東西,
我不試圖尋找什麽,
我不相信有任何的解釋超出了
徹底的虛無這個詞所解釋的意思。
我只是想要在陽光下或在雨水中——
在有陽光的日子在陽光中
下雨的時候在雨水裏
(永遠不會要求沒有的東西),
去感受溫暖、寒冷和風, 而不會有更多的要求。
壹旦我愛上了,
我想我會得到愛的回報,
可是沒有人回報。
我不被愛有壹個不可抗拒的原因:
我命該如此。
我會再壹次坐在我的屋門前,
在陽光和雨水裏獲得安慰。
畢竟,對於不被愛的人來說,
田野並不如在被愛者眼裏
那般翠綠。
去感覺便是去煩心。
《苦水音樂》節選
布考斯基
愛情是壹種偏見
妳愛妳需要的
妳愛使妳感覺好的
妳愛使妳感覺方便的
當妳知道只要有機會認識
世界上還有壹萬個人
可以讓妳更愛
怎麽能說妳只愛壹個人
只不過妳永遠都無法認識他們
我是個靠孤獨過活的人
孤獨與我
就像食物跟水
壹天不獨處我都會變得虛弱
我不以孤獨為榮
但以此為生
屋子裏的黑暗對於我來說
就像陽光壹樣
2019.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