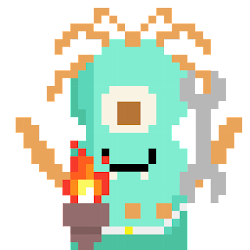以 公共空間 為 文化基礎建設(1)
一般我們提到 文化基礎建設 都會聯想到歌劇院或博物館那些大型建築。一直以來,文化建築都擁有一個很宏偉的形象,例如1960年代建成的紐約林肯中心,歌劇院和劇院像幾座宮殿一樣 坐落於高台之上。這項目是紐約上西區(upper west side)都市更新計劃的一部分,漂亮的文化建築取代了以前凌亂的舊社區,街區壓縮成新建的公共房屋高樓,也沒有和文化中心有什麼空間上或生活上關聯。從外區來的觀眾也就坐車直達平台上劇院的門口,中場時候留在各層的陽台上往下看。
可是這種“尊貴的文化” 和它所代表的文化建築在過去二三十年正在發生變化。而林肯中心的例子,正是通過公共空間的設計改造來達成。這個長達十年的設計案 由美國建築師團隊 Dillier Scofidio 主理。本來只是一個小型景觀設計案,可是在設計過程中也啟發了林肯中心管理層對於文化機構公共面向加強的想法,及後通過設計師,管理層和公眾持份者的持續討論,慢慢演變成整個公共領域的升級改造計畫。
其中一個設計策略是把平台上的私家車下客區引到下層,再將原本步行不友善的台階加寬延伸至人行道,讓大廣場與城市空間連接。再加上像戶外放映等大眾節目,把人和活動從封閉的地標建築帶到室外,也把林肯中心的公共空間與城市肌理連接,將孤島一樣的文化宮殿變成城市空間網路的一部分。
透過公共空間的改造配合加強公眾參與管理與策劃,這個案例把原本是孤立內向的文化中心改革成公共文化生活的場所,也展示了建築空間不只是被動的表述而能夠是具備主動性的agency(能動性)。
香港文化中心也是在6/70年代類似的社會背景下設計建造。那時候的香港經濟起飛,正好需要一個展示其國際城市形象的建築,也希望通過建造劇院和美術館將香港帶入世界文化舞台。 可是這個項目也面臨同樣的問題,推崇宏偉的地標建築而缺乏了對在地和人視點的關注,而這也似乎定義了香港的文化發展方向。香港文化中心成為了90年代旅遊明信片上尖沙嘴海傍的標誌,直到現在正在建設中的西九文化區,還是以類似的模式規劃,各個獨特型態的地標建築坐落在海港旁邊的填海地塊。
香港文化中心開幕已經超過三十年,而作為香港首席文化場館的地位接下來也將會由西九文化區取代,或許現在正好是一個從新審視這座文化中心的定位的時機。它會不會有機會像林肯中心那樣通過公共空間改造把文化中心面向公共生活?如果要展開這個討論我們又應該怎樣介入?
這幾年全球疫情讓關於公共空間的討論再次提升到一個 “基本生活需求” 的層面,而演藝場館的關閉和室內活動的限制也逼著文化從業者思考文化活動如何進行。如果不在劇場和美術館裡面,哪裡可以成為舞台/展廳?
除了線上,公共空間也是一個積極被利用的平台。藝文團體不單止把原本在場館內的作品搬到室外,更因而發展出許多利用公共場所在地性質的新作品(site-specific art)。這些本來是“迫不得已”的對應方案正好體現了一種創新實驗(prototyping)的機會,也回應了近年文化機構在積極探討加強公共面向的問題。那麼,我們應該如何建設文化空間而不只是地標或物件?
當我們把關注放在空間而不是物件的時候,人和體驗也就成為了主角,從而去討論公共性和參與性的議題。演藝廳的空間定義觀看和被觀看的這種二元關係,放在公共空間也變得不一樣。公眾能夠突破被動性“觀看者”的角色,而通過其位置/動作/反應等等成為主動的參與者。
雖然這不是本研究的主題,但在香港2019年的社會運動正好呈現了公共參與和文化空間的互動關係。當文化中心的公共空間變成了人群聚集的地方,它的空間設計和管理如何促進或妨礙公共參與就變成了很好的課題。與此同時,在香港後社會運動的現狀,幾乎所有聚集都有被打壓/管控的風險,依靠大型地標的公共聚集(包括文化活動)一下子變得沒有太多發展空間。因此,我們作為創意公民,需要思考一種新的模式去參與公共和文化活動。而接下來的研究試圖把香港文化中心從一個地標建築物轉換成一個人本空間(inhabited space)來討論文化發展與參與性的議題,更重要的是探討“空間”作為動能(space as agency)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