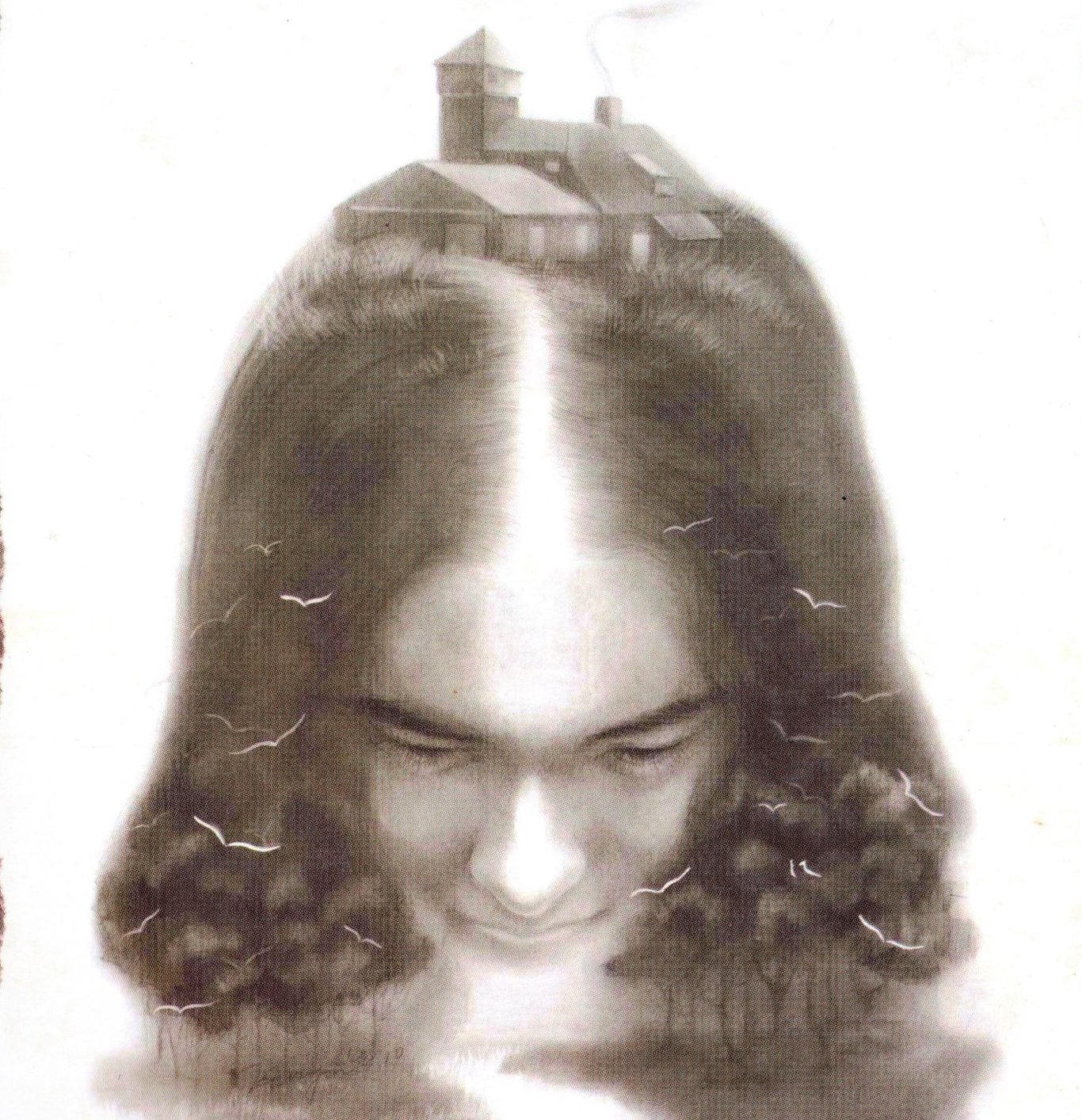未完成的完成:大江健三郎的《晚年樣式集》
大江健三郎的最後小說《晚年樣式集》2013年由講談社出版,但中譯本在十年後的今年,而且是在作者過世之後才在內地出版。在日文書題旁邊,大江以片假名標示「イン・レイト•スタイル」,即英文 “In Late Style” 的意思。而這個副題,呼應的是大江的好友、已故文學評論家薩伊德(Edward Said)的遺作"On Late Style"。薩伊德論述晚期風格,而大江以晚期風格寫作,所以由 “on” 轉換成 “in”,由評論回到創作。這是大江作為學術型小說家最為熟練的方法。
鄧正健曾在《明報》「星期日生活」撰文,稱大江健三郎為「『完成度』極高的作家」,他所指的是「作家在漫長的創作生涯中,是否能夠透過作品築構一個完整、複雜而具深度的文學體系。」在這個定義下,大江健三郎的確是少數能夠以整個人生來經營特定主題、建立明確體系的作家。但是,如果從「晚期風格」的角度,大江的作品也同時是「未完成的」。「完成度」(degree of completion)和「未完成性」(incompleteness)不但並不互相排斥,反而形成弔詭關係。這也可以理解為大江最重視的文學特質——曖昩(ambiguous)。
「未完成性」是薩伊德「晚期風格論」的一個要素。「晚期風格」本身不是一套完整理論,而是一個文學評論上的洞見(insight)。最早提出「晚期風格」這個說法的,是文化理論家阿當諾(Theodor Adorno)。他用這個觀念來闡釋晚期貝多芬的音樂。「晚期風格」不是指狹義的年齡上的分期,也不是指成熟、洗練、安祥、和諧、圓滿、昇華、超越等,這些通常在晚期達至的藝術境界。相反,具有「晚期風格」的創作者,最經常展現出的是下面的特質:不完整和非延續性;內在衝突與張力;疏離、異化和自我放逐;面對死亡的憤懣、對過去的拆解和重整;艱深、拒絕理解、不能調解的否定性;甚至是更極端的、失去整體性的「災難」。( “Late works are the catastrophes.”)
薩伊德以阿當諾的觀察為依據,把「晚期風格」延伸至文學批評,但他未及把見解整理成書,便在2003年因白血病逝世。學術界友人把相關的遺稿輯錄成《論晚期風格》。大江健三郎在《晚年樣式集》的前言〈作為開場白〉中,寫到他探望病中的薩伊德的時候,談起對方的「晚期風格」研究,並表示自己「想用詼諧模仿你的書名的標題來從事最後的工作」。那時候大江所說的是「晚期工作」(Late Work),也即是以「晚期」的心態去進行的寫作。十年後,也即是2013年,大江以《晚期風格》為題,寫出最後一本作品,一方面可以視為一個「總結」,但也同時是一個終極的「中止」。那個不得不中止的契機,不是無可抗拒的衰老和機能衰退,而是當代日本(及世界)的最大危機——三一一大地震和福島核事故。
《晚年樣式集》不是大江十年前預期的「詼諧模仿」,而是名副其實的「災難」。它不只是一部「面對災難的作品」,也是「作為災難的作品」,the work as catastrophe。它無可避免地表現出小說的「未完成性」。不只是由於種種內在和外在因素而「未曾完成」,而是在根本上「不可能完成」,或者是「只能以未完成的方式來完成」。為何會如此?因為時代與身處其中的創作自我錯開了,無法達至同一。薩伊德把這個時間上的錯位稱為「不合時宜」(untimeliness)。在英語中的 “late”,除了指「晚期」、「後期」,也指「遲到」,意味著錯過或錯失。自身與時代「錯失」,這是大江親身經歷的災難。
在1995年的演講稿〈時代賦予我主題〉中,大江引述南非小說家納丁.戈爾默(Nadine Gordimer)的話說:「不是作家選擇主題,而是主題選擇作家。」這也是大江自己的小說信念。他自言時代賦予他三個重大主題:戰後民主主義的解放、核能對世界造成的危機,以及與先天殘疾的兒子共生。大江以一生貫徹這三個主題,以小說的形式不斷進行探索,同時在現實人生中努力尋求實現。可是,到了晚年,他發現這些主題就算在虛構世界(小說)取得甚麼進展或成就,在現實世界中卻是毫無寸進,甚至可以說是完全失敗。(連對第三項也存疑!)
《晚年樣式集》就是在這樣的深深的挫敗感中展開。小說幾乎沒有故事性,因為在末日來臨之時,「故事」已經不再可能。作者的化身長江古義人,在三一一後陷入嚴重的憂鬱,連帶跟家人的關係也變得疏離,特別是跟智障兒子亮。小說分為兩層,第一層由家庭中的「三個女人」(作家的妹妹、妻子及女兒)當敘述者,合寫一份「家庭雜誌」,在其中表白對身為哥哥、丈夫和父親的作家的批判。當中妹妹亞沙對哥哥的批判最為尖銳,主要是針對古義人長年在小說中把家人(父親、母親、妹妹、妻子、兒女)當作原型,寫成虛構人物這種做法。她認為這種寫法是對當事人的不尊重、不公平和不誠實。而女兒真木對父親的不滿亦異常激烈,主要環繞古義人對長子亮(即真木哥哥)的態度。她認為爸爸嘴邊一直掛著與殘疾兒子共生的漂亮說辭,但其實沒有真正尊重哥哥內心的感受。自哥哥步入中年以後,與父親的關係出現隔膜,兩人談話減少,而父親卻沒有認真對待,甚至出現向哥哥無理發怒的情況,導致兩人陷入冷戰。至於妻子千樫,雖然較接近中間人的角色,但並沒有明顯站在丈夫這一邊。
小說的另一層,是三一一之後發生在古義人家庭的幾件事。首先,由於亮與父親的疏離,以及真木對父親的反抗,兩人決定要從父親的壓迫之下獨立,結伴回到位於四國森林的老家。(背後也包含逃避東京遭受核污染的考慮。)與此同時,古義人的舊友、比他年紀稍長的義兄的兒子義.二世,從美國再次到訪。從《致令人懷念年代的信》(1987)開始,義兄是大江小說中多次出現的人物。他是年輕古義人的啟蒙者,在四國家鄉從事農村土地改革,建設獨立運動的根據地,但曾因性侵和殺人事件而入獄,後來更被伏擊而淹死於人工湖中。在最新的版本中,義兄的兒子在美國長大後,讀了古義人的小說,對當中關於父親的描寫感到困惑,決定親自回國向作者查探。身為製片人,義.二世乘採訪福島核事故之便,到東京為長江古義人拍攝錄影訪談,並對其展開詰問。同一時間,家鄉的年輕音樂教師阿律,在真木和亮的協助下,以《致令人懷念年代的信》為藍本,創作了一首合唱曲,作為關於亞洲新青年的影視節目的內容。義.二世就是這個節目的製作人。最後所有人回到四國家鄉,在森林裡聆聽亮重新創作的曲子《森林裡的奇異音樂》。在此期間,故友吾良在柏林結識的女友島浦再次現身,要求古義人澄清在前作中所寫的關於吾良的細節。
上面所說的兩層,其實是糾纏在一起、互為表裡的,分別只是說話者和敘述觀點。但無論在哪一層,情緒低落的古義人都處於被動的,甚至是捱打的狀態。讀者會感到奇怪,這一切跟三一一有甚麼關係?無論三一一令作家如何憤怒和沮喪,也沒有理由反過來把矛頭指向自己,對自己的創作方式和家庭關係作出如此毫不留情的鞭撻吧?在大江小說中,自我反思並不是新事物,但如此尖銳和不留餘地,確實是令人驚訝的。那就好像作者真的跟自己分裂了,而自我對辯或對質最後並沒有帶來和解。結尾的那場森林音樂會,以及其中的「重生」主題,讀來頗為牽強,幾乎沒有鼓舞力量。至少,這個「正面」的「肯定」並沒有真正解決任何問題,而且力度遠遠不及整部小說的「負面性」或「否定性」(negativity)。
然而,與其爭論《晚年樣式集》究竟在傳達希望還是絕望,不如說,希望和絕望、肯定與否定,也是大江所重視的「擺盪」中的兩端。(Vacillation的觀念首出於《燃燒的綠樹》中引用葉慈的詩歌。)當擺盪和時間進程結合,就是遞歸(recursivity)。整部小說的構思方式,不是線性的、向前的敘事,而是不斷製造回顧、重訪及重寫自己的舊作的契機。就好像一生的作品中,還存在未有定論的、懸而未決的千頭萬緒。事實上,這種「以退為進」的寫法,早在《換取的孩子》已經出現,而且持續重複。幾乎每一次都以深入時代與自我的「負面」或「否定」開始,最後以某種臨時的「正面」或「肯定」作結,但下次又會再出現反覆。
如果說「回顧」和「重整」(recapitulation)是「晚期風格」的其中一個要素,大江在這部小說中除了納入了舊作的內容和線索,也通過「三個女人」的批判而對自己做了一次大清算。對此古義人沒有任何招架能力,幾乎只能低頭。時代賦予大江一生的三大主題,在這裡可謂遭到全盤挫敗。公共領域中的民主主義失守和核危機惡化,在三一一事故中表露無遺,而小說家在災難當前軟弱無力、毫無作為。甚至連「個人體驗」領域中與殘疾兒子共生,也出現了難以挽回的變化。作者苦苦經營的「康復家庭」,到頭來變成了四分五裂的「爭議家庭」。就「主題」而言,可以說是全部以失落和失敗告終。我們看到的不是一個圓滿地完成人生使命的大師,而是一個憂鬱悲憤的失敗者,一個情緒失控、頻頻失言和失態的糟老頭。他唯一的作為,是召喚死者的回歸。於是六隅老師、吾良、義兄、篁等亡魂(還有薩伊德)一一重新登場。
《晚年樣式集》是一本邁向死亡的書。不但是作者(大江健三郎/長江古義人)的死亡,也是小說本身的死亡。大江在九十年代中與柄谷行人的對談中,已談到「小說的終結」。我初時以為,他是受到柄谷的「現代文學終結論」影響,但這絕不可能。大江一定是自行達到這個結論的。就現代小說的定義來說,大江的最後小說其實是《空翻》。自《換取的孩子》開始(也即是自伊丹十三自殺身亡之後),大江以分身長江古義人登場,表示他已經放棄了「小說」。代之而起的,是對自己過去的小說(無論是主題還是內容)的不斷「引述」和「重寫」。他甚至提出了「帶有變異的重複」這樣的理論觀點。這也是大江正式進入「晚期」的時刻。在十多年間,總共六部的長江古義人小說,其實已經不是傳統意義的小說,而是對自身的小說和廣義的小說的無限遞歸。也因此是「未完成的」,「不可能完成的」。只有如此,才能無限延遲「小說的終結」,但也唯有如此,才能徹底實現「小說的終結」。《晚年樣式集》不是一個完成任務的終點,不是一個圓滿的總結,而是一個戛然而止的、未完的樂句。但是,就像巴哈的遺作《賦格的藝術》中未完成的最後一曲,在那音符懸空的地方,蘊含了創作者的整個生命。(極富意味的是,未完成的賦格是自我指涉的 “BACH motif” B♭–A–C–B♮。)
在這本最後小說中,大江健三郎罕有地以一首詩來結尾。〈遺物之歌〉是古義人在2007年1月發表在《新潮》雜誌上的作品,當中講述了晚期風格的特質,後來成為亮重新創作《森林裡的奇異音樂》的藍本。千樫在給亞沙的信中說:「長江把自己七十歲時其長孫誕生之事寫進了那首詩裡。」當時真木還抗議說:「自己被涉及已是無可奈何了,但不要連第三代也給捲進去!」問題是,在設定於2013年的小說時空中,真木未曾結婚、古義人也沒有孫兒!在小說結尾真木才出乎意料地表示會嫁給義.二世。女兒早已結婚並誕下長孫的,是現實裡的大江健三郎。那麼,引用這首六年前為長孫誕生而寫的詩,是小說家的失誤嗎?是他把現實寫進小說的時候,一時忘記了兩個世界的事實有所衝突嗎?在小說家創作生涯完結之最重要時刻,在最後一部作品的結尾,出現這樣的失誤,能原諒嗎?或者更根本地說:可能嗎?
我傾向認為,這是一個失誤,但大江是刻意的。在這個刻意的失誤中,小說家跨越了虛構與現實的邊界,拆毀了小說與人生的壁壘。長江古義人就是大江健三郎。人物就是作者。這不是回到傳統的私小說嗎?不是,這是小說的解體。《晚年樣式集》示範了小說的解體方式,也標示了現代小說的終結。因此,它是一本無法閱讀(unreadable)的書。只有大江的長期忠實讀者,極少數的知音人,才能體會其中深意。我不會把這本書推薦給不熟識或不喜愛大江的讀者,因為對大部分人來說,這本書簡直不知所云,猶如一個失智老人的囈語。但是,如果讀懂它的話,你會深切地感受到,時代與個人斷裂的痛楚。
原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30.7.2023
🦊 收藏本文NF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