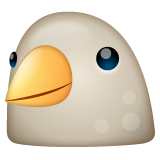写作复健: 三年与转变 | 二〇·一——二二·十二
一如二〇年一月六日,担心抢不到回家的票,提前回家享受天伦之乐的我,没有想到在家一待就是半年;二二年十二月六日,因为学校顾全大局保护学生的政策,窝在宿舍里腐烂发臭的我,没有想到一觉醒来所有的以人类之名的反人类措施都被取消。一时间简中互联网一片歌舞升平景象,像是经过三年自然灾害后的恢复期,或者是打倒四人帮的调整期——“形势一片大好”,上面是这么对我们说的。我们走了一些弯路,甚至某些地方的财政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正如在这三年里我们反复吟唱的一句话,时代的一粒灰——落在身上就是一座山。一如彼时的反思文学一样,我们需要回忆我们走过的山,不管身后有多少座。
求职
二二年秋招卷的程度,不论是不是亲历者相比都能有所感受,缩招的企鹅,摆烂的华子,被赶鸭子上架的国字号,各大高校摇旗呐喊的选调牲(点名某师范)……再加上今年尴尬的经济增长率,一家还能继续招人的企业其存在和行动本身就已经是足够有社会责任感的表现了。其残酷程度具体来说就是,在前程无忧上随便投一个薪酬中等、预期稳定的行业,如果公告已经发布了一周,那你的简历编号恐怕很难会低于两千——而这个公司招募的岗位可能只有两位数,这意味着随便一个还算不错的企业其竞争难度和国考省考都能掰掰手腕——而后者可能还包含了近三年或者是社会考生。另一个痛苦的表现大概是,硕士牲在今年彻底成了就业市场上满地爬的生物。三年前的那次试图挽救学生与就业市场的大规模扩招,并没有给本就迷茫的青春大学生带来他们期待的光明的未来,反而是在明天会更好的自我催眠下,迎接各种意义上的最难就业季:需求方的紧缩以及大量被学校释出的研究生。以至于,彼时还能找到一些不错的、招本科生的国企,而现在,研究生成了卷进体制内的基操——这或许也是读研给大学生带来的唯一一个可能是稳赚不赔的利好。
这从而引出了另一个话题,好像“体制内”这三个字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能够吸引刻板印象里朝气蓬勃的大学生的青睐,而前者的刻板印象恰恰是截然相反的了无生气。还记得头一年选调生报名时候的景象吗?那时候福利还算真挺不错,竞争也还得当,那时候大学生村官也名噪一时,国家也以理想和共同富裕之名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基层建设,但在三年后,选调生被在实际操作中被祛除了理想主义的光环,成为了应届毕业生进入体制内的一条更体面的捷径——除了选调生之外还可以调剂进其他岗位或者储备人才。同时,受热捧的永远是江浙沪、珠三角和Peking,而相对的,中西部的选调大多数成为了被调侃的对象,“入职时候的一次性补助有可能是这辈子见过最多的一笔钱”。原因无他,地方财政还是选调生薪资的最主要来源,而这个来源的稳定性在这三年期间确实不断地被挑战。更重要的,基层工作的琐碎早就将其光环击得粉碎,徒留一地狼藉,细小碎片所能积蓄的庞大负面能量也在这三年里得到了见证。在剥去了所有美好和理想的外衣之后,它仅剩的内核只是一份相对体面且流程没那么残酷的工作,因而也不难理解,对于一份工作而言,它首要的价值是满足人的生存需要。
除了选调生,各类国企和人才引进也备受青睐,原本被视作夕阳的行业和岗位一个个又重新被炒热成了早晨六点钟的太阳。我们借助推拉模型简单理解一下:首先,以“互联网”笼统指代的一系列企业在困难时期,特别是中国大陆独具的不确定性面前,表现出抗风险能力并没有那么强,同时它能提供的岗位并不如勃发期那么充足,再卷进去,在没有新的业务增长点出现的情况下,并不是一个很有性价比的行为;其次,眼下中国发生的种种令人啧啧称奇的怪相,都让先前被提出的“中国梦”和奋斗化为泡影,在没有一个新的理念支撑的情况下,我们只能从自身得到救赎;这也是当代的大学生被认为不再像当年那样充满朝气的原因,因为“充满朝气”本身就是一种捆绑式的庸见,它以一种反智的刻板印象把青年人捆绑在了中国特色新自由主义的战车之上,在这里根本没有任何喘息和停歇的机会,多元的生活方式被主流意识形态以“躺平”一言以蔽之,而这种滥用和自嘲在某种程度上也实现了一种奇特的二分——牺牲与反牺牲:实现财务自由并不是唯一的自由,打工人是时候把目光转移回打工人自身了,而在这个基础上,一切为了自身考虑的行动都被称之为躺平。这种为自身考虑的行为,某种程度上把被意识形态裹挟的职业生涯观念扳回一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先富带动后富;爱拼才会赢……也不需要用小确幸来形容自己的选择,对自己最合适的选择就是最高。
涌向最能吸金的工作不再成为首选,对确定性的追求、对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以及更充足的度过时间可能是我一下子能想到的最关键的三大要点,它们也分别对应贯穿人类社会至今的逃避主义、蓬勃旺盛发展的消费社会与个人主义在国内的兴起,市场化之后快速推进的职住分离已不再可能维持下去了,因为此时的家是否还能称之为作为避风港的家宅还只是作为居住的场所我们都很难区分,去除了这一段通勤仪式后,工作和生活势必是相融的,而生活不论是俗称慢节奏快节奏,稳定还是冒险,其节奏和韵律都是由不同的乐章组成,它有间歇的仪式作为高潮来调节,同样也有重复的和弦;而随着市场化推进与单位制在中国的完全解体,消费社会和个体化的进程都在快速推进,个体实现自我发展的途径变得多种多样,山崎提及的发展性的消费其核心是“更充足地度过时间”,其强调首先是有消费的可能,其次是有消费的选择,这都是在疲惫工作后的打工人所难以支持的,因为发展性的消费不是一种条件反射,而是结合自身需求和情境的选择,它是一个过程,不是周末到街上放松就是一种发展性消费,更多的程度上,它可能只能称之为一种疲劳的消除,是为了下周能够更好地投入工作。
在这个基础上,一些国企的一些岗位受到了毕业生热捧,它们具有以下或其中几种特点:工作付出及其回报性价比较高,不需要加班或有稳定双休,离家近或者提供宿舍,工作内容及流程模式化,在某一领域能够创造非凡的社会价值等。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这只是一种取向,而这种取向一直都存在,它是否可以被称之为主流则是另一回事,但这种热捧则是我们所需要注意的。而且我们要注意到不管在好年坏年,都不是所有人都能找到心仪的职位,而工作最核心的需求在新时代的中国仍然是提供生存和生活所需,这三年间所经历的种种都暗示了或许只有团结在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身旁,方能在这片土地上求得稳定生存。
生涯
一如我之前反复唠叨的那样,体制内的求职热并不完全是一种功利性盲从,或者用一句俗话来说,反正都是拿钱办事儿,但确实在这股“倒车”背后是一种中国特色式的委曲求全:相比于投身游走于灰色地带、生死存亡系于某一稳定存在的不确定性的新兴产业,索性与投身于这一不确定性的确定性之中,更何况前者所代表的更高的挑战性、发展前景与货币自由,连带着早已在这个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中撕下伪善面具的新自由主义,已经一起以观念上或者付诸行动的形式,被身心俱疲的虚无主义大学牲口扫进日常生活的角落里,同在那个角落里的,可能还有健康码、学习强国和企业微信等等试图从各种缝隙侵占并捆绑个体私人生活的权力和资本。换句更简单直接的话,这次学牲们不想做牲口了,口粮早已不是唯一的衡量要素,工作和生活的尊严同样甚至更为重要,它们想做个人;而如何实现由工具到人的转变,比较显而易见的方式是,找回并重新定义风格化的日常生活,这种日常生活不再和工作割裂,不再被各种符号风格填充,也拥有足够的方式以抵御权力和资本的侵袭。换言之,工作不再只是谋生的手段,它本身也是丰富日常生活的推动者或成为其本身的组成部分,日常生活的闲暇不再是简单的调用或者是生产性的消费,而是为了个人发展和充实地度过时间,我们有充足的时间和空间以武装我们的意识、身体和其栖居的场所,并将其组成三位一体的统一战线以对抗各种不确定性的侵袭。试想,如果失去和地方的联系、维持基本生存的来源以及自反的时间空间,我们在通勤的地铁上、逼仄的格子间里,就如同乱世之浮萍、狂风之飘絮。
本人就是今年秋招的巨变浪潮里绽放的一朵水花,每次笔试或者HR提问关于未来的职业生涯规划时,我都会故作幽默道,“三年前我想挣大钱,两年前我想搞学术,一年前想至少好好把毕业论文搞完,今年我只想做个人,做个‘好’人”。我还记得三年前,一九年的秋天,发现自己能够着推免的边儿,随即屁颠儿屁颠儿糊弄了所有的面试跑去搞预推免,甚至腾讯捞我的时候我都义正词严地回道,“我要念书”。投身于日常生活和地方的研究,日后致力于社区营造和地方志创作成了彼时我的人生理想。研一结束时,对民俗学理想的破灭,让我重新燃起了回去打工的念头,我也捡起老本行,实习开卷。但到研二上学期结束时,各项课程的高分,和最后两篇小论文极好的手感,让我突然错误地生出了一种“我好像有读博的潜力”这种错觉,于是下定决心接受好好搞毕业论文。
但等我接受导师的好意,满怀壮志豪情奔赴甘南,准备大展身手时,2022年的噩梦也终于开始了。先是在甘肃的工作让人疲惫,自己从志愿者变成了打工人且不说,连带着对藏区和自然也有了一些负面情绪,以至于我对藏区的经济人类学选题也有点泄气。但给我的精神状态以最深之迎头痛击的,还是在三月份踏上归途之时,全中国骤然升温的管制政策,各大城市遇事不决都举起了封城、静默、网格化管理等大旗,尤其是兰州、西安、汉中等地相继升至高风险后,我被迫辗转红军长征路线经玛曲、舟曲、陇南、广元、阆中、南充回到了三门峡,然后继续居家检测和随机静默抽奖。不断地静默、解封、静默、解封……这个看不到尽头的循环过程着实是让我对未来了无期待,我的脚步也仅限于三门峡一隅,连市区都不一定能去,老家的几条街、一条铁路和几座山构成了全部,我的日常交往也以家人和初高中的同学为主,甚至难得参与了清明节、奶奶姥姥的大寿,可以说是完完全全把“故乡”祛魅回“附近”。而促使我的生涯观念转变的最直接原因,还是七月开始在长沙出版社的实习。
苟完开题之后,我决定奋起加入暑期实习大军,提前备战秋招。令人遗憾的是,虽然我这次实习真的摆烂,但没想到烂得这么彻底,以前还给个面试机会的腾讯、网易和阿里在笔试完之后了无音讯,中国银行的面试直接被我错过了,唯一一个推进到终面的竟然是招行卡中心, 然后面试的时候因为回答不小心歪到了品牌上悲惨离世。最终是北京的一个品牌和长沙的出版社给了我机会,考虑到我对北京一直以来的敌意,我还是选择了长沙,同时出版也是我一直好奇但没踏足的领域,尤其是在阅文的漫画编辑实习结束后,我发现自己对纸质出版物的好奇只增不减。这种好奇在进入出版实务也转化成了动力,这份伴随着自我学习提升与传播知识的工作着实让我有一种为人类普遍幸福和进步而奋斗的感觉。
同时,更重要是,三个月在长沙的生活,有单位提供住房、餐补和还算差不多的工资,和一八年下半年在台湾一样,我不需要考虑任何除了自我提升和休闲之外的任何事情,一切都有充分的保障,甚至长沙在公共卫生政策上也十分弹性。在工作氛围上,和罗罗姐的合作十分愉快,与舍友、工友的相处也十分融洽,每天的工作非常稳定,下班后也有充足的时间选择健身、阅读、观影、游戏等休闲活动,周末我在长沙市内的老旧家属院和寻常巷弄里任意穿行,人送外号老长沙。等到十月底历经艰险一路爬回上海,过回猪圈牲口的日子之后,看着我欠佳的精神状态,朋友们都说在长沙的三个月确实是我精神状态最好的时光。
于是,今年的秋招,出版社成为了我的主攻方向,某种意义上研究生对我职业生涯规划影响最大的,就是接触了编辑这一岗位,踏足了出版这一领域,让我找到了一份可以兼顾稳定生计、终身学习与增进人类福祉的工作。而且,久居长沙、广州后,长沙的房价也让我看到了安居的可能,丰富的夜间生活和市井文化也提供了消费的多样性。这同样指向了疫情给我们带来的另一重影响。
地方
我在校招开发一周后投递了中南传媒的简历,那时编号已经排到了两千,等再过几天我同学投的时候就已经是三千多四千了。确实是有不少清华北大的人选择来长沙卷,是北上深的竞争力大不如前了吗?虽然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可以解释这一转变,譬如经济景气不再,北上广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数量大不如前,同时占更大比重的国企、事业单位以及中小企业,其薪资水平和生活成本相比也让应届毕业生倍感压力,而相比之下二线城市和老家的企事业单位则更具性价比等等。不论从推力、拉力还是情境因素去考虑,最终其实都难以脱离一种疏离感,这种疏离来自于自己究竟能否在一个超大型城市长期居住以及这种居住是否值得的疑问,如果说最终都会回到老家,那这种奋斗是否值得?大城市在开放性和流动性表现得更为良好,虽然可以很快融入,但自己究竟可以成为在地人吗?这种对自己和地方未来关系的自省,虽然总是存在,但在经济景气的情况下往往被增长率和开放政策带来的乐观所掩盖,而在这变幻莫测的三年里,这些问题随着未来的不确定性被反复提起,暴露或加剧了地方感迷失的问题。
在二〇年中,随着新型冠状肺炎初次流行稍缓,各界开始对封城这一现象进行反思,“附近的再发现”就是传播广泛的成果之一。在封闭期间,我们重新发现并回顾住宅的作用,其功能价值和意义价值,搭建或再搭建邻里间的关系,实现小区向社区的回归;在解封后,我们恍如昨日地以陌生却又熟悉的眼光再审视熟悉却又陌生的街道和城市,那些原本习以为常的现象再次被我们认知到其存在是如此的令人欢欣鼓舞……移动性在外部压力强迫下的消失,日常生活节奏和韵律强制地反复和弦演奏和芭蕾舞动,都让人不得不去重新思考自我与街区之间的关系,从而夺回了作为最小尺度的眼前的附近,它的单位可能是社区和街道。将这种夺回表现得最为彻底的莫过于二二年上半年发生在上海的种种,由于公权力角色功能的缺失,封城体制下市场和资本流动性停滞,原本细胞化的社区其活力被唤起,或者说人们不得不联合起来发挥自身的能动性以维持日常生活不至于完全崩塌。如果说在经历天灾人祸的过程中,个体和社区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非凡韧性,原本僵化或者去核化的社区重新焕发了活力并组成了有机的整体,而对一种普遍的社会福祉的关注也让个体加强了对其他地域境况的人道主义关心——“远方的人们都与我有关”,种种迹象表明我们重新赢得了微观和宏观的尺度,但似乎我们和作为中观/次宏观的城市越来越陌生了。
我们完全将大学校园当作一个小的社区,它是城市中极为特别的一个存在:既不属于城市,也不属于乡村。对于市中心的校区来说,它有城中村的某些特点;对于郊区的校区来说,它在荒野中又显得有些突兀。它是被植入城市的一个异类,它不具有大学的开放性,这在一九年以降体现得最为明显:大门一关,学生们的衣食住行都在逼仄的宿舍、原始的校园中进行,和城市生活没什么关系,大家在伊甸园的宿舍区内生活,通过互联网和远方无数的人们共情,但对这座城市,他们知之甚少。就如同屠宰场的牲畜一样,它们也生长在城市,但只有在被当作资源被流转在市场上之后,才和这种城市的气质发生联系——在还以生物存活在世上的时候,它们仍是没那么现代的,只是城市的附庸。那这个类比可以平移到大学校园中,大学牲可能只有在最后一年的出栏季才被人力资源市场挂念,或者是被当作衡量一个城市竞争力的指标之一被量化对待,除此之外,它们在更多的时间里被视为一种不稳定、不成熟的因素,或者是一种产业集群和新城发展的配套资源形式,被部署和安置在市郊。如果一个城市的市中心仍有一些校园存在,可能是占地规模不大、历史悠久以及校友资源丰富,因而在城市空间里占有一个较高的位置,同时它们也会被市郊的同侪们艳羡不已:周边更浓厚的生活气息、市区更丰富的就业资源以及更便捷的配套基础设施。当市郊的同侪们鸣不平的时候,“幽静便宜学习,地价低便于兴建各类设施……”一类的话便可以将它们搪塞过去,但当封闭式管理降临的时候,不论位于市郊还是市中心,大学牲作为物种不同的二等公民,由于居住密度较高、配给压力较大、感染风险较高等原因,迅速被视为影响城市稳定大局的最危险分子,并长久被封闭在房间、楼层、宿舍区之中,即使是放开已成定局,他们依然要享受最为严苛的安保待遇。
我以前想将大学校园称之为贫民窟或者城中村,因为考虑到两者居住条件、生活水平、流动性、市民权等方面的相似性,但在日常生活实践,特别是在对公权力的柔性抵抗方面,大学牲就如同猪狗之于屠宰场一样,毫无还手之力,因为他们在整体上不具有维持基本生活的条件,并处于公权力的全方面、多维度监管和管制之下。他们大多数的要求都被视为是逾矩的,因为这是一种恩赐而不是他们所应得;他们大多数的提议都被视为是可笑的,因为他们还幼稚并缺乏生活经验;他们大多数的激情都被视为是一种反动,因为他们天生就缺乏判断力且容易被煽动……但实际上,关于对学生蔑视的一切和更多的一切,都来自于公权力本身:高等教育被视为一种学不到东西的东西,加强政治站位的同时让大学校园去政治化,社会实践和专业实习在落实上缺乏积极性……一切种种让大学教育变成了一种十分个人化的事情: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相对于义务教育阶段的花样频出,高等教育反而在向新时代跃进时显得大步后退。
这也不难理解,城市和城市里的一所大学,往往在气质上没有什么相似点,城市的氛围是城市的氛围,大学校园则是象牙塔。那一九、二〇年入学的同学们又如何呢?像笼中鸟一样高高挂起在象牙塔尖。如果对一座城市缺乏足够多的探索经历,那又何谈认同、依恋进而留下来呢?在这里我的探索经历指的是深入到城市发展的脉络和建设的肌理之中,领会城市的人文精神和历史传统,而不仅仅是一个城市的观光客和消费者,前者始终带着一种猎奇的眼光去观测这个城市,他不断索取符号和特征以丰富自己的见识,而后者依靠在不同的街道中穿梭寻找新的发现以填补内心的空虚,他始终流动而没有想停下来建立联系,他们可能可以对一座城市的大小餐馆、街道风貌如数家珍,但他们也可以如此对待别的城市,因为这些资料确实存在于脑海之中任凭调用,而谈到那些具体的魂牵梦萦的经历,他们却支支吾吾。对一个大学或者研究生来说,学习和学校并不是他们生活的全部,或者说,并不是只有学校才是知识的全部,那些街道和行人背后组成着这个城市的全部活力,而学校本身反而是这座城市的附庸,如果学生是学校的附庸,那附庸的附庸又如何呢?当多年后回想起在某间大学里求学的经历,记忆中缺少对某一城市的印象,一定会被嘲笑的吧,就如同之前所说的一样,封闭让我们找回附近与远方,但是却和身处的城市越走越远:那些行将毕业的人,在难以自由移动的校园和其所在的城市里生活了三年,是大学的75%,或者是整个人生的接近二十分之一。
这同样还带来另一个问题,即对城市的光晕。如果说我们前面讨论的更多是关于进入/观看一座城市,那现在我们讨论的是关于退出/告别一座城市。如果说,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是进入一座城市最早也可能是最好进入仪式,那校园和学生的身份则是观看城市的原点和身份:在大多数时刻,宿舍是你出发探索一所城市的起点和终点,同时学生的身份也是你在某座城市行走时所持有的身份。这种身份具有的特点就是时空的高自由度:你可以在你空闲的时间以几乎任何可以选择的方式探索城市的近乎全部场所,而宿舍作为彼时的居所很大程度影响你探索的先后次序和半径,进而影响对城市的整体印象——一个闵行校区的学生不可能观测到和中北校区的学生一样的上海。那退出又是如何理解呢?我们先前借用仪式的概念,某种程度上录取通知书和开学系列活动是一个学生以一个新身份加入一座城市的起点,换言之,包含领取毕业证、毕业照和毕业典礼在内的一系列活动则是一个学生告别原先所持有的学生身份并以新的坐标和身份(例如打工人和旅客)观看这座城市的起点——它们都代表了一种转变,而这种转变如果没有以一个完整且合适的方式完成,那自然,一个人仍会不可避免带有先前的眼光去看待先前所居的城市,虽然他已明知自己不再可能以那种身份那种眼光去观看。
在二〇年六月底回到广州时,迎接我的是满目疮痍的宿舍,三三两两的同学,和聊胜于无的纪念活动。因为补办毕业证证明的缘故,我在广州又多待了两个月,在那段时间里我仍像先前一样和朋友们碰面,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里穿梭,我不觉得我和这所城市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什么转变,虽然我知道我和这座城市在未来的联系不可能再像之前那样密切,但由于被夺走的半年,我失去了和那些承载我记忆的场所和友人告别的机会:卖茶永远不在了,220和214的八人组也没有再集合起来打王者的机会,明三的天台少了好再来和两个人,中环也少了疾驰的身影……一切种种都给人一种错觉,这种错觉来自于没能打包好的情绪,和不愿意一段时光草草收尾的逆反心理,而这种逆反又进一步强化一种广州依旧是第二故乡的心理暗示,它如同乡愁一般,代表了一种停滞的原初性,同时过度美化使得这种原初替代了对这座城市的真实印象。这种光晕,直到时隔两年再次造访广州时才被狠狠驱散,因为身上所具有的两种身份——中大遗民和华师新人此消彼长,而不断的心理暗示也拔高了美化程度从而导致了更大的落差。光晕的驱散带来的不是顺利进入新生活——新的生活不可避免的要进入,而是对过往存在价值的粉碎——那些坚信、缅怀并作为支撑的美好回忆体系的崩解,这种信念的消失加剧了无根感和悬浮感。
上海在二二年的封锁则让我几乎一整年和这座城市毫无联系,由于封控集体记忆的缺失,我和华师在微观层面上也缺少认同,而一年足以让人对一座城市感到陌生——重新坐上三号线我甚至有一种新鲜感,而当那种新鲜感产生的时候,我也随即产生一种遗憾:我和这座城市就像正常生活的回归一样,也需要复健,我一次次回到那些熟悉的街道、店铺,和朋友们见面,以与这座城市断点续传:至少整理完这三年。某些时刻,我甚至无比怀念在长沙的生活,在长沙三个月的安定给了我很大正向反馈,我也确实接受了打工人的身份,未能完成整理的身份也多了一重。回到上海的我更难以重新过渡回学生的身份,一年的奔波和断裂让我有些无所适从,或许正如同学所说,没想到我还在念书。而对于经历了封锁的人来说,那一段可以说是求生生涯里最昏暗的时光之一,而它也是城市经历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校园也是城市里的一个空间。
总之,三年期间不断的封闭与奔波,实际上对应了移动性的两个极端——但这种极化实际上并不来自于病毒本身:要么是迅猛的移动,要么是长时的静止。它所带来的断裂和间隔阻碍了对一个城市的正常探索,由于缺少具体经历,让城市对个体而言具有意义是一种奢望;而另一方面,校园生活的不完整所带来的对一座城市或负面或美化的行动,也影响了个体对一座城市的情感和关系。同时,这两方面都对一个城市整体印象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从而进一步影响了毕业生的地方感和就业取向——出于光晕的考量以及规避经历中的风险。
这三年对二三届毕业生的影响绝不止上述,比如在对前途绝望后摆烂式内卷秋招的同侪们不计其数,而突然的放开又打乱了原本的策略。但总的而言,生涯规划上对不确定性的规避、柔性个人主义的发展以及地方感的寻求,是我眼中这三年对我和我眼中的同侪们影响较大的三个方面,希望能对大家的自反和应对有些许帮助。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