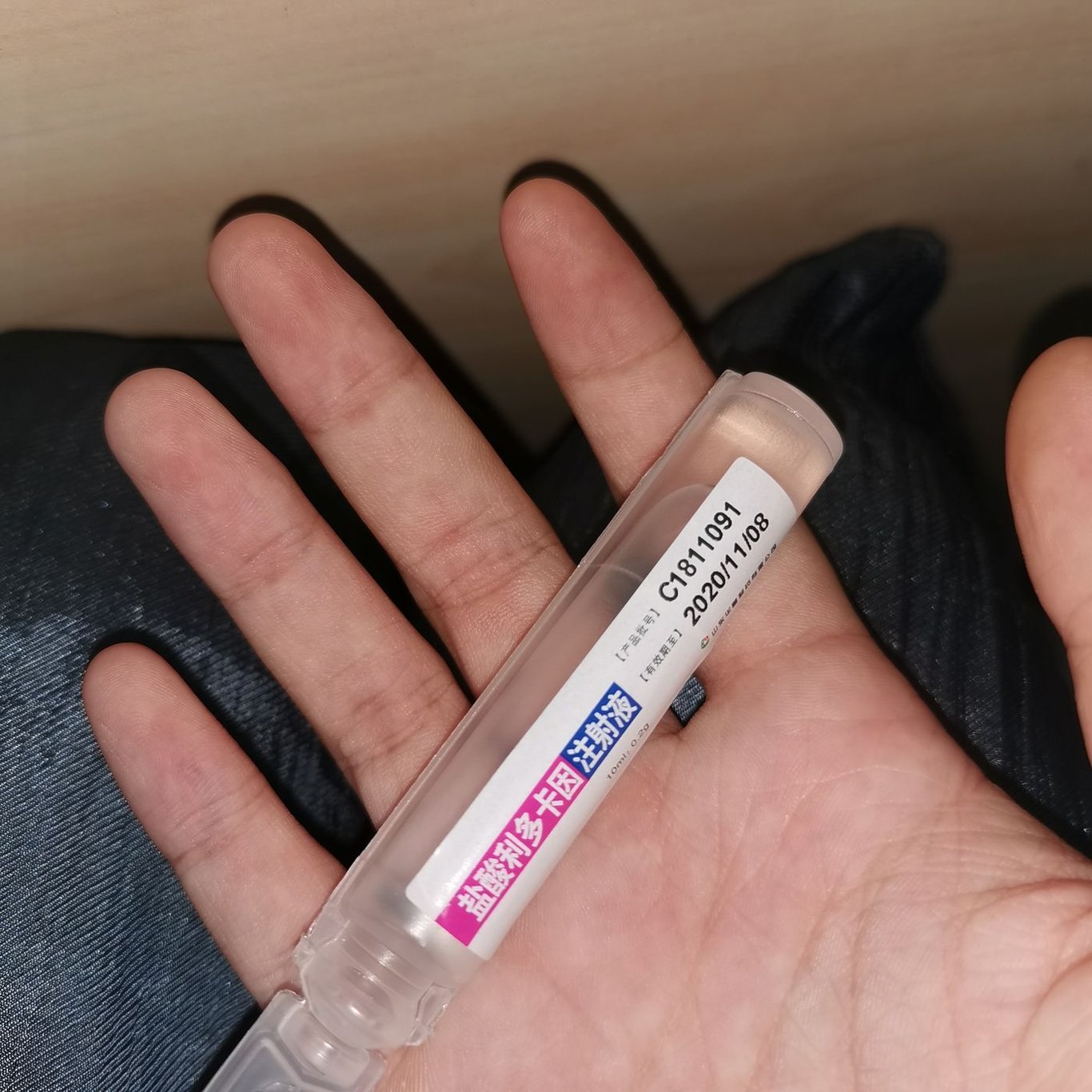當我們丟失故鄉
我是1997年出生的人,如果我稍晚幾天,趕在七月初時離開母體,也許我會跟那個時代的許多男嬰、女嬰一樣,擁有一個與香港回歸相關聯的一個名字——大概是什麽“紫荊”、“回歸”之類的字眼。
沒有在我的大名裏冠上這些龐大的字眼,在今天的我看來是一件“幸運”的事。我接受的教育或是弄巧成拙形成的價值觀,讓我對於關於家國的、民族的、宏大的敘述無法共情。甚至,更多的時候,當我回望我生長的城市,或者更小的,撫育我成長的家庭時,我都在愈漸長大的年歲裏更多地品嘗到一種格格不入和抽離:我已成爲我家庭中的過客,或是,我已決議成爲一種過客。
我所屬的地方
五月,從上海返回家鄉前與將要畢業的師姐們見面。大約三年前,她們來到這個學校讀碩士,當時的我还在考慮如何寫作與上海影展文化相關的論文。那是我第一次做一個自己喜歡的研究設計,和一個完整的社科論文寫作。我在課程上第一次見到入學的師姐,知道她是導師的新學生。而後又是兩三年,我順利升學,繼續留在本校。我們在疫情時封閉的校園裏一起跟將要畢業的師姐拍照,我在公寓的南部,她們在公寓的北部。公寓因疫情原因被隔離成了破碎的幾片,我們隔著鐵絲網和圍欄拍下合照。當時我還沒有意識到,這極有可能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
師姐的畢業并不順利,因學院老師的派系鬥爭和莫須有的罪名,她遭受了許多不應有和不公平的打壓。她在學術上是讓人敬佩的存在,同樣也是我們師門中充滿魅力的夥伴。
六月,回鄉時在自家距離三公里的老舊賓館裏隔離。這個自詡以旅游為開發噱頭的城市。年久失修的賓館被徵用來對付像我這樣從疫區“逃跑”的大學生、青年務工者。我在賓館的抽屜裏發現2015年的旅游手冊,上面寫著“中國旅游之都,xxxx,熱烈歡迎您的到來”字樣。那是一份地圖、出行指南、飲食推薦。它太過時了,甚至讓人覺得有些可笑。
六月,仍舊滯留在疫區的朋友們受夠了封禁和疫情政治,企圖去更加“自由”的地方度假或放松。普遍线上工作的情况給了他們這樣的機會,但是同樣,行程碼中帶星號的城市,又讓他們無法真正的自由。
等待十四天:十四天后我們就可以洗掉“不幹淨”的行程痕跡。大家都這樣想,不論是在哪一個城市駐留或中轉,唯一希求的是保存這個“所在地”的乾净。以至於在這個過程中,同樣輾轉一個個十四天的我總是在想:我到底該如何描述自己“從哪裏來”、“是哪裏人”?
在家庭裏扮演一個合格的晚輩
許多時候我又在想象,當我們丟失故鄉、丟失關於家的依戀時,我們又如何塑造我們自己?但是,當我們被困于家鄉,困於這個小鎮的人情關聯時,我們又如何保持我們自己?
家裏最大的姐姐畢業后在二綫城市工作幾年,最後還是回到了這個家鄉,安穩工作、結婚生子;另一個姐姐近年讓我旁觀和目睹的,盡是她的戀愛和婚姻如何在家長的干預下一步步形成了他們期待的樣子,以至於,在結婚前夕他們仍舊會擔憂“我的女兒丟失工作后會不會搞黃她快成的婚事”。
而最早結婚的姐姐,如今也將要誕下第二個寶寶。在我聽聞這個消息時,我甚至無法用我的語言去由衷地祝福她:因在我習得和慣常的語言中,生育一個孩子給女性帶來的“痛苦”遠遠大於她爲人母的“幸福”——這當然也有我杞人憂天的擔憂,但更多的是,我擔心她的辛苦,是否會被掩蓋在所有人對一個“成功女性”的想象中:子女環繞、相夫教子。
我無法由衷地祝福她,也無法用“啓蒙”的口吻來指摘她的人生。在這種複雜的心思之中,唯一僅存可以被導出的,只是對她的關心和體諒。我已經距離她生活的世界太過於遙遠,以至於我們時而也會無法交流令各自開懷的瑣事。
家裏的長輩已經到了行動無法自理的年紀。生老病死都是可以預見的今天或明天。儅父母忙碌于照料他們的父母時,我作爲晚輩,和一個“路過”這個傢的人,常常感受到無力和局促。我無法真正地為他們分擔這件事,且更多的時候,他們只是需要我存在于這個家裏這件事帶來的意義,一個在外求學的孫女回到家看望祖父母的戲碼。而我無法為他們“生活得更好”這件事帶來任何的改變,因他們已不希望自己能夠更加健康,能夠更加自由了。
如果“孝”是一種困擾所有中國人一生的命題,那麽這種“做孝”的技能在我們逐漸遠離家鄉的過程中變得越來越缺失。他們希望看到的孝,是女孩按部就班的工作、結婚、生子,讓長輩參與她們撫育下一代的工作,再見證新一輩的子女完成如上的循環。他們希望看到的孝,是子女繞膝的想象,是關於傳宗接代、關於活出一種標準化的人生的圖景。
而我對此已經越來越陌生。我無法參考姐姐們生活的軌跡來完成這樣的任務,也同時煩惱于她們無法逃離家庭的圈套的煩惱。儅她們的父母以血緣關係相逼,希望促成她們在這些事上樁樁件件的圓滿時,我只能旁觀,而無法用“叛逆”的語言來干擾她們被形塑的幸福和價值。
想象自己的遠方和田野
當我聲嘶力竭地在與母親的對話中道出我對這個家庭的不滿、對這個環境的不滿時,她也只是說”希望以後在外面你能夠照顧好自己”。我并不寄希望於我的父母可以爲我鋪就在外生活的坦途,但是卻又不甘於呆在這個日復一日可以看到未來重複的每一天的城市。他們深知自己已無法再阻止生活的慣性,起碼對於母親來説,她最大的支持就是不阻攔我的出逃。
我們可以定義自己的故鄉,或是自己歸屬的地方嗎?當我在外求學時,我很少會意識到我從一個怎樣不發達的城市裏成長起來。學生的身份和暫時不需憂慮的經濟,讓我能夠極大可能地享受一個大城市帶給我的歡愉和便利。而當我回到家鄉,我發現已無法適應小城市中低效率的行政和機械、緩慢、複雜的人際關係。
我們被超級城市的規則所左右,被城市的聲色所迷惑時,也會討厭這種鄉土和自然帶來的不穩定性。它代表一種困囿于人情社會的世故與連帶關係,那確實生於斯長於斯的我無法學到的智慧與道行。
冬天時,我去到省内隔壁的城市游玩。爬雪山、鉆山洞,騎著摩托。這些都是從小到大能夠見到的平常風景,但在當時卻覺得感慨。如果山川和河流構成我成長的蹤跡,那麽這些也構成了無數夢裏我對田野和遠方的想象。儘管我也會迷失在城市的光鮮裏,但最終還是希望歸屬于這樣一個人烟稀少的土地。
2022年的疫情,無疑從某些程度上摧毀了我對生活在一個大型城市的幻想。我目睹上海遭遇的困難,也體驗到自己被封禁在一個空間裏的痛苦。2020年沒有讓我體會到的,2022年讓我真實地感受到了。當我們認爲這個高速運轉的城市可以保障生活中的效率和喘息空間時,上海用一個個悲慘的案例告訴我們它可以失控到何種無法想象的程度。
我當然也沒有真正地“丟失”故鄉,又或者,我經歷的只是匆忙的路過、返回、路過的循環。我無法確定未來的我會生活在何處,也有可能,但是此時的擔憂的煩惱,不過是基於我仍以爲自己尚有選擇餘地的一種幻想罷了。我們都很難能夠複製父輩的生活方式:環繞在父母周圍,成爲一個可以被稱作“孝”的子孫,也許就是他們畢生奮鬥,可稱之爲成功的一個徽號。而我們在此中的無所適從,也許從我們離開家去往幾千公里外求學時就埋下了種子。我們自認爲學習到的引以爲傲的邏輯和規則,永遠無法帶回到這個樸素的、人情密佈的家庭之中。
扮演一個合格的晚輩,或者引導一種在當地可以被看作是足夠是成功和標準的人生,也未必比我們孤身一人在外更加輕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