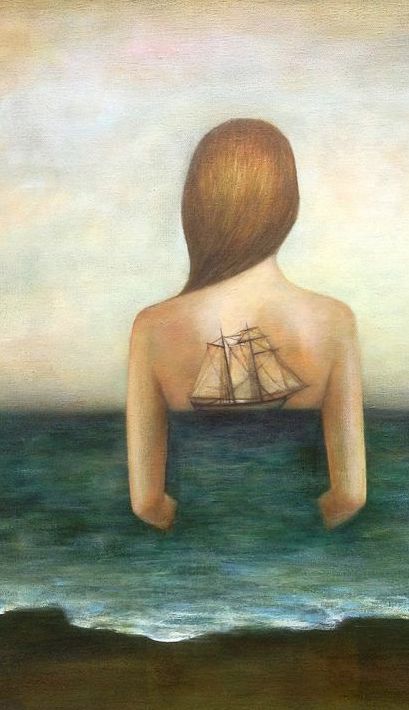影像世界之真实:延伸苏珊桑塔格「论摄影」(三)
一张照片是一个故事,观看一张照片分享了一个在地的二手经验。然而苏珊桑塔格不曾亲历数码照片的时代。今天的人还得考虑的一点是影像不仅是二手经验的载体,还是原先载体的数码复制品。
假设以每个人的手机屏幕——手机屏幕很重要,想象不同型号和版本的手机大小,色差,甚至是久了不同主人磨损出的裂痕吧,这些都是看照片的「周遭」——为单位给一张数码照片标号,复制品的号码是难以穷尽的。本雅明认为机械复制即是「把原件的复制本放置在原件本身遥不可及的环境中。」但这句话产生于胶片拍摄出的照片被印刷在纸媒上的时代。今天的情况已经不再是(相机中的)原件与其复制品(印刷的照片之照片)的关系,而是(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 / 打水印的)复制品与其(二次传播 / 截图 / 观影时屏摄)孪生复制品们的关系。如此,二手经验被进一步稀释成三手,四手,直至完全剥离语境。
// 屏摄指在观看院线电影时用手机拍摄荧幕上的电影画面。如果留心「少年的你」院线场,或许你能从后排看到前排高高举起,对准某一演员的手机摄像头。
今日的世界是影像的世界。然而从充沛的影像里回到未经调味的现实时,人觉得嘴里寡淡。一方面,现实不如影像激动人心。这反过来激励我们在每一个「可拍摄」的时刻留下影像,佐证自己的生活并非乏善可陈。另一方面,影像给予一种虚幻的精神饱腹感。这即是苏珊桑塔格在忧伤的物件一章中说的「摄影那超流动的凝视使观者感到惬意,创造一种虚假的无所不在之感,一种欺骗性的见多识广。」我们已然「见过」富士山峰,看过「非洲大草原」,浏览过「贫民窟人的生活境况」,但不曾目睹。
相反,新的无信仰时代加强了对影像的效忠。原本已不再相信以影像的形式来理解现实,现在却相信把现实理解为即是影像。费尔巴哈在其《基督教的本质》第二版( 1843)前言中谈到“我们的时代”时说,它“重影像而轻实在,重副本而轻原件,重表现而轻现实,重外表而轻本质”——同时却又意识到正在这样做。
——苏珊桑塔格
歌颂摄影,尤其手机摄影,是歌颂人人皆有创造影像之权力的民主。传统美术里,「有些表现对象被认为是重要、深刻、高贵的,另一些是不重要、琐碎、卑劣的。」摄影将整个世界,连同它的乏味尴尬腐坏丑陋,作为素材,推上舞台。那些不忍画下的景象,就让相机(手机摄像头)完成。而无论按下快门有多么轻巧,摄影不可避免地是从某双眼睛望出去的景象。一张照片让人对摄影者所处的位置浮想联翩,因为摄影必须有一双主体的眼睛。镜头替人观看。
这看似对动态摄影是一样的。纪录片和电影的影像也存在一个隐没在镜头后的主体。对纪录片来说这个主体常常就是摄影师本人,偶尔是被拍摄对象。电影则有更多可能性,通常是虚构的人物,有时是监控摄像头,还有时是诡秘的幽灵(壁橱缝隙中,天花板上,下水沟里——各种人不去的位置);试图打破次元壁的电影则把主体放做导演本人。 影像的主体譬如是受欺负的小男孩,大概会引起观者的同情;如果主体视角突然切换到疯子,鬼魂或者突然跳出次元壁的导演之类,则是个对无法代入主体的观者的一次提醒,造成出离或戏剧感。
动态影像的创造者对她们的作品有极大的掌控力:在既定的几个小时里,你的视角受摄像头的摆布。静态影像则不同。这是由于单张影像缺乏语境,也无法对观者形成控制——同读书那样,我们能控制盯着一张照片多久,又怎么盯着它。
此外,数码照片可被直接保存截屏屏摄,这类进一步将一张照片拽离它本身的语境的动作让观者也能轻易修改并再次发布影像,在复刻的动作中成为诠释者之一。有时传播者带着无辜的意图,有时却可能意在创造奇观,引发骚动。总之,影像被再创造,再限制,再篡改的同时,其真实性也落入一个谜团。
——也落入了福柯定义的权利网络:「权力以网络的形式运作在这个网上,个人不仅流动着,而且他们总是既处于服从的地位又同时运用权力。」在人与人的网络中,人人是媒体,人人定义其影像;经验被复制,被再创造。
照片并非只是记录现实,而是已成为事物如何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准则,从而改变了现实这一概念,也改变了现实主义者一概念。
——苏珊桑塔格
相机捕捉一只飞鸟的动作十分短暂,但已经在飞鸟的影像与飞鸟之间创造了一道不可见的物理关系:飞鸟的影像具有索引(indexicality)性,令人索引到鸟本身。一种 Truth Claim 就伴随摄影诞生了,这种信念认为传统摄影总忠实刻画真实(reality)。事实上,摄影一度成为形容某事「精确真实」的修辞。(否则『实物不符图片』时,我们也不会这么愤怒。)摄影,本是薄切的生鲜现实。
对摄影的信任也传递到动态影像里。电影有个古老的名字:动态图片(motion pictures)。如果说静态图片仅仅捕捉一个同时孕育过去未来的时刻,电影真正捕捉过去与未来。Lev Manovich 称之索引的艺术(art of the index)。遇见罕见的奇观——一幕落日,一次别离,一场地震——感叹之余,人人喃喃「简直和电影一样」。
不过,今天我们默认摄影与电影不真实的时候更普遍,而这不仅仅是说后期用技术处理过的摄影和电影。这是因为「生命不是关于一些意味深长的细节,被一道闪光照亮,永远地凝固。」照片却是。影像通过摒除人在场时感官接收到的杂音,重新表征一层真实。这个摒除可以通过十分简易的环节完成:取景,旋转裁切,调色,甚至是抹除。
而得益于技术进步与商业浪潮,杂音不仅是能被抹除,而且是「一键抹除。」照片后期软件不仅简化这些环节,而且标准化自动化它们。拍甜品有专门的色调;夏天有自己的滤镜;拍摄自然风光和人像需要的氛围感也都被精心营造;还有齐齐消失的面部斑点和皱纹。不仅是照片后期软件,照片呈现的媒介也大力推动这一标准过程——每张16:9, 2:3, 3:4, 5:4规格的照片都被平等地分配进1:1的模具中,成为2x2, 或3x3的格子之一。
//有标准化,就有有心的创作者极力摆脱这一标准:给横幅照片加上上下白边,竖幅加上左右白边以控制照片在流媒体上的呈现如她所愿。
在传统美术里,无数笔触叠加下颜料能顺着力道拱起又落下,形成可触摸的纹路;或是难以盖严实的涂错的棕褐色丙烯,在一次次鲜红和米白的混合下,渐渐将后者化作低饱和的灰粉。揣测一幅画的原初形态很难,但并非不可能。摄影下的影像呢?胶片的加工或许可以,而数码照片被涂抹了多少层「真实」是不可眼见的。
如今面对照片,我们已经不能确定它的本体,它的源头,以及它的涂层数量。唯一警醒感官的是直觉,一种隐隐作响在心头的不真实感:
我所看到的是真实吗。
“谁告诉你的?”
卡夫卡把头歪向肩膀。
“摄影把你的眼光集中在表面的东西上。因此,它遮掩了那隐藏的生命,那生命像光和影的运动那样闪烁着穿过事物的轮廓。你哪怕用最敏感的镜头也捕捉不到它。你得靠感觉去把握它……这部自动相机不会增加人的眼睛,而只是提供一种奇怪地简化的苍蝇的眼光。”
——古斯塔夫·亚瑙赫,《卡夫卡谈话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