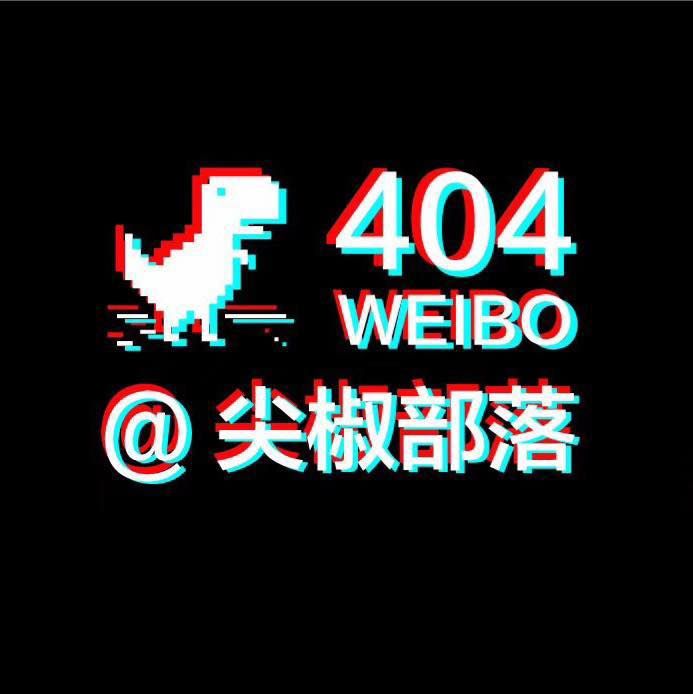疫情下的特殊“困境”:家政工不能返工,家务该谁来做? 【疫情下的家务承担者 04】
原文发布于2020年3月20日,尖椒部落原创首发。
作者:园园、青青草
编辑:雅清
家务劳动常常和女性捆绑在一起,在传统的观念里,“好女人”的特质里必然少不了擅长做家务,照顾老人和孩子更是被认为是女性的分内事。因此有观点认为,家政服务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是对女性的解放:通过购买家政服务,一部分女性从家庭内部冗杂的“义务”中解脱出来,得以投身实现个人价值的活动。
而另一方面,作为被“购买”的一方,从农村进入城市务工的女性是家政行业的主要从业者。她们离开自己的家庭,进入雇主家里,继续承担家务和家庭照顾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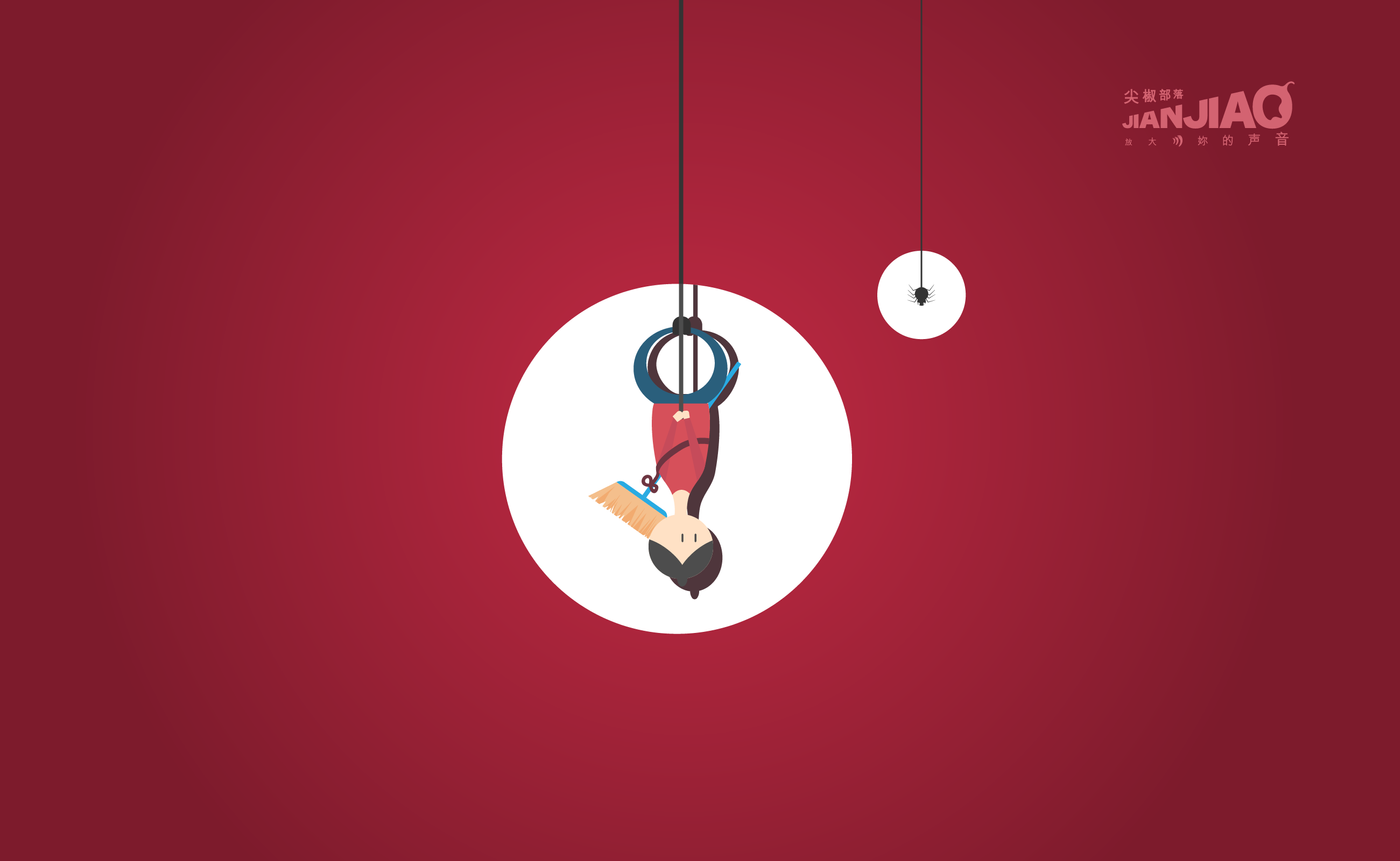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家政服务业发展报告(2018)》显示,近年来,我国家政服务业产业规模继续扩大,连续保持20%以上的年增长率。2018年,我国家政服务业的经营规模达到5762亿元,同比增长27.9%,从业人员总量已超过3000万人。
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的意见》称:“家政服务业作为新兴产业,对促进就业、精准脱贫、保障民生具有重要作用。”提出要提高家政从业人员素质,推进服务标准化和规范化。
但随着1月底新冠疫情越来越严峻,武汉及湖北多地的封城,乃至全国的人口流动管制,使得平日里通过金钱购买劳动的良好运作戛然而止。被困在家中的,不仅是不能返工的家政工,还有失去了家政工的“家务劳动”。
“我不喜欢做家务,一点不喜欢!”
郭叔叔和曹阿姨是一对退休夫妻,两人和曹阿姨的父亲同住在深圳。曹阿姨退休后被返聘回原来的工作单位,郭叔叔则开始了创业,两人的忙碌程度甚至超过了退休以前。为了兼顾照料家里的老人,多年来他们一直都请钟点工来家里,为老人做饭和处理家务。
现任的钟点工姓黄,郭叔叔会叫她黄女士或小黄。她来工作已经七八年了,郭叔叔说,他们相处得很好,还去过她家里吃饭。
黄女士是湖北人,和郭叔叔是同乡,年前回老家,一切如常,还说好了年后回来要带上自己做的腊肉。结果回去后就封村了,至今未能反深。黄女士跟郭叔叔打了招呼,说暂时回不来,询问会不会另外找人。郭叔叔认为现在是有一些不方便,但是因为跟黄女士建立了很好的信任关系,所以一定会等她回来。
钟点工的工作包括给家里的老人做饭和打扫房间,一天两个小时。现在这些活需要三个人(郭叔叔、曹阿姨和老人家)一起来分摊。过年放假的时候影响不大,但最近曹阿姨要开始工作了,她是学校老师,要准备网课,家务就主要落到时间比较灵活的郭叔叔身上。
“只能说现在还勉勉强强能对付过来。但如果小黄一直没法回来,肯定不行了。疫情总会过去的,不可能一直不让人动。在那之前我们尽量克服,实在做不了的事就先放一放,总有办法的。”

婷婷夫妻是湛江人,在广州工作,原本这个时候早就应该回去上班了,但现在她还在老家。她的孩子10个月大,原来住家的家政工因为担心广州疫情严重,不愿意一起回去。
家政工“阿姨”和婷婷是远房亲戚,小时候婷婷就是被她带大的。现在阿姨又在照顾她的孩子。
因为夫妻俩都常常加班,怀孕的时候,婷婷就开始担心孩子的照顾问题。自己和丈夫两边都是多子女家庭,长辈们照顾哥哥姐姐们的孩子已经忙不过来,没有人能过来广州帮他们。之前创业失败欠着债务,婷婷不可能辞去工作,只靠丈夫的收入养家,何况她认为女人也一定要有一份工作。找到阿姨之前,她一点想法都没有,无解。
“我丈夫大大咧咧,觉得可以把孩子送回老家。他一点都不觉得孩子不在我们身边长大是不好的,也不担心隔代教育的问题。全世界好像只有我在担心这件事。”
阿姨来到广州后,婷婷上班的时候不用时刻担心孩子,着实长松了一口气。年前夫妻俩带着孩子,跟阿姨一起回的老家,原计划是年后也一起上广州。新冠病毒打破了这个计划。
阿姨很担心,老家确诊的只有几个,而广州有几百个,她不肯回广州了。婷婷没有办法,只能向公司请长假,待在老家,等疫情过去再劝阿姨回去。她安慰自己,即使回到广州,也要照顾孩子,没法上班,还不如在老家安全一些。问题是:“我也不能一直请假呀。”
婷婷的工作是由家人介绍的,有一点“关系”,目前看来请假到3月还是可以的。她相信不会只有她面临这样的困境,但能像她这样请假的应该很少,不知道其他家庭怎么办。

小脸夫妻是双职工家庭,没有跟长辈一起住,有两个孩子:老大6岁,老二1岁多。为了照顾孩子,家里请了住家的家政工阿姨。年后阿姨被困重庆,小脸“一拖二”照顾两个孩子,只能咬着牙应付。
阿姨在的时候,主要负责做家务和照顾年龄小的孩子。阿姨不在的这段时间里,这些任务都落在小脸身上,丈夫下班回来会分担一点,“这段时间做饭的事主要是他来”。
小脸丈夫是自己创业,疫情这段时间特别忙,基本没休息。而小脸在高校,正值假期,所以时间相对宽松一些,家务也就做得更多一些。她说,其实不是身体有多累,更多的是精神压力大。孩子在家闹腾,这个哭完那个哭,要指导老大学习,要陪老二玩,她自己的事情一样也做不了,想起来就觉得心里很难受。 阿姨的作用可太大了。
阿姨会陪弟弟玩,小脸就不需要兼顾两个孩子,也不用做饭,还可以有一段自己的时间,完成手上的工作。而阿姨走后,“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带两个孩子,还要做饭,快累死了,一天从早到晚都不能休息”。
小脸会因为家里这些琐碎事跟丈夫吵架,如果有人承担家务,她情绪不再紧绷,心情好,整个家就和谐了。但阿姨还没能回来之前,只能咬着牙应付。“否则能怎么办?”
不过,现在小脸的心情是放松的,因为阿姨已经顺利回来。
重庆不在疫区,还算好办,身在湖北的家政工们返工可能是更漫长的过程,小脸表示,一个好的阿姨很难遇到,能等肯定是尽可能等的,但等不了就只能换人了。 经过这段超过一个月的家政真空期,小脸说:“因为疫情,才深刻体会到阿姨的重要性,感谢她。我不喜欢做家务,一点不喜欢!”
“保姆”这个词,带来一种自卑感
一边是面对家务焦头烂额的雇主,而另一边,因为疫情而无法复工的家政工们,生活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阿兰是“住家保姆”,6年前跟着女儿一起来深圳。工厂工作不好找,企业招聘都不要年纪大的人,阿兰也觉得自己的视力不如年轻人,没法做一些费眼睛的细活,而且工厂经常会加班加点,年龄大了精神跟不上,通宵上夜班肯定吃不消。于是她经人介绍,进入了家政行业。
第一份工作是照顾一个80多岁的老奶奶,每个月工资3000多,包吃住,没有社保。雇主待人很友善,家里除了阿兰,还另外请了一个家政工负责做饭和打扫卫生,阿兰的活不算太累。但老人家不怎么出门,阿兰整天和她待在一间小小的屋子里,很少有机会说话聊天,老人半夜频繁地起夜,阿兰也跟着整晚睡不好觉。做了半年多,她觉得特别压抑,就离职了。
后来阿兰又自己去家政公司,找的还是住家的工作。对她来说,家政工作有好的一面:年龄上的要求比较宽松,找工作相对比较容易,工资也比工厂要高。而且雇主家包吃住,所有的日常用品都是雇主家来承担,减少了很多额外的生活费用。
但同时,这份工作也有“不好的方面”。除了双方约定的工资以外,公司和雇主都没有帮阿兰购买五险一金,家政中介只是跟雇主签订合同,而家政工和雇主、中介都没有签合同,缺乏个人保障。
阿兰在精神上也常常会有很强烈的孤独感。她现在这份工作要24小时看护孩子,几乎没有一点自己的时间,晚上也睡不好觉。阿兰担心这样的日子久了,会得抑郁症或者老年痴呆。而且住在雇主家里,虽然雇主一家表面上说话还是挺友善,但在自己心里还是会感受到有地位高低之别,不是在自己的“地盘”,说话做事都得小心谨慎,总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
“很多时候好想找一些姐妹朋友,一起开开心心地聊聊天说说话,一起逛逛街散散心呀。可一起做家政工作的姐妹是很难遇到在同一天休息的,因为每个雇主家的情况不一样,所以大家的调休时间也不同。其他行业的工友更是很少机会接触和认识,所以做保姆工作的,社交朋友圈也会变小。”
阿兰说,在外界很多人眼里,“保姆”就相当于旧社会的“佣人”,要看别人的脸色吃饭,是一份“地位低下”的工作。很多人宁愿在工厂拿着比家政工少很多的工资,也不愿意做家政工作,她们会觉得做“保姆”很没面子 。
“保姆”这个词,也一直带给阿兰一种自卑感。但她现在处在尴尬的年龄,“退而不休”,别无选择。为了生活,为了工作,也顾及不了别人眼里的“面子”。
只是在疫情期间,即使想要工作,也无法返工。阿兰在家里等待,疫情结束后,她还是会回到现在的岗位上。

同样出生于70年代的洋芋,也是因为女儿来到深圳。最近女儿想考公务员,让洋芋过来照顾并督促她的学习。洋芋以前做过酒水销售。做过饮食生意,直到女儿上大学,她去到上海,给弟弟家帮忙带孩子带了好多年。
洋芋说,在上海给弟弟带孩子的那段时间,她第一次接触了外面的世界,这对她来说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朋友在深圳做家政工,洋芋在她那里了解了家政行业,觉得钟点工时间比较灵活,挺适合自己,就跟朋友一起做起了钟点工。
她们在一家家政平台接单,入职要交几百块的平台培训费,家政公司接单后会再从工钱里抽成,到了家政工手上,大概30元一小时。在平台接单分为派单和抢单两种方式。派单的模式自己没有选择权,如果拒绝平台分派的单,还会有惩罚(就是下一单不支付工钱),根本没法自由控制时间;而抢单则需要有几天的实习期,得免费干几天,要求使用平台的工具,还得交工具费。个人能接到的单很有限,平台会优先把单给家政公司,家政公司再在微信群里发布接单信息。
接到单后,等待客户的时间和路上赶车的时间是没法算工时的,被客户差评还要被扣钱。洋芋说,客户给了差评,家政工看似可以申诉,但实际上是很难申诉成功的,“平台对于我们劳动者没有任何保障制度”。
目前她做兼职钟点工,手上有一些“固定单”,月收入是4000左右。朋友工作很努力,月收入可以达到一万。
“高工资”背后,是高强度的劳动。洋芋做的钟点工,每小时的费用标准是最低的,如果做“深度保洁”,费用就会高一些。很多雇主会认为,花钱买了服务,家政工就要做足够的活,遇上很挑剔的雇主,从进门那一刻开始,就必须抓紧一分一秒不停地做,喝水的时间都没有,更没法看手机,一个地方被盯着反复擦上好几遍,还会觉得弄得不够干净。在被雇主“监工”的整个工作过程中,神经全程紧绷,身心都觉得非常疲倦。
“我感觉长期全职做这样工作的人,会把钱看得很重,也会很孤独。因为同事之间都是竞争关系,工作的时候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交朋友,工作完一整天下来会非常的累。”
洋芋认为,家政服务只是一份工作,而不是一个身份。家政工也有选择权:你不尊重我,我可以拒绝服务你。她希望家政平台可以建立一些双向评价的机制,除了让雇主选择家政工,让家政工也能筛选一些雇特别不友好的雇主。但又觉得,平台都为抢客源,倾向于维护客户的利益,不太可能会这么做。
疫情期间,洋芋每天在家里画画、听音乐、学乐器、看电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特殊的日子里,她反而过得比较平和。“我暂时没有太大的负担,我不打算长期做钟点工,我也有很多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