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十岁逃离城市,返乡青年们在想什么|野聲电台

在三十岁之前,湘妹子蔺桃对自己的人生有着足够的掌控感,无论是走出湖南老家,进入媒体行业闯荡,还是毅然辞职,成为第一届赴台陆生,出版第一本书,都是一步一个脚印。但在迈过三十岁之后,移居美国的她突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和焦虑,为此她发起了“返乡青年”项目,历时五年写成了新书《三十岁,回乡去》。在本期电台中,我们请蔺桃分享了她的心路历程,一起讨论年龄焦虑、返乡青年和迁徙者们的“乡愁”,并倾听这一刻的《风吹麦浪》。

三十岁,你在焦虑什么
秋凉:对于很多人来说,三十岁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那之前,想干什么都还有机会去做,而三十岁之后,人生似乎就被定型了,想要干点出格的事儿,就算没人阻止你,自己心里也要掂量一下。像我就是赶在三十岁之前出国留学了,当时脑袋里有个特别强烈的声音一直在说“再不走就来不及了”,之前我们有期节目讲街头表演,Adon也说到自己有过类似的年龄焦虑,不过是在27岁。
Adon:对,当时刚好是我读米理硕士的最后一年,那个时候我是26岁,比较了解摇滚乐历史的朋友会知道有个“27 Forever Club”(指由一群过世时全为27岁的伟大摇滚与蓝调音乐家所组成的“俱乐部”),它可以说是巧合,主要是因为3J奠定了这个传说的基础。不过我觉得不是年龄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到了一个阶段,本质上是想要改变,想要do something,情绪累积到爆发的那一刻,你用一个年龄当成deadline,寻找一个可以改变的年龄。
秋凉:我觉得这种年龄焦虑挺普遍的,就像洪水一样,来的时候特别吓人,但出来这几年,我渐渐觉得年龄其实就是个数字,对于这种焦虑也是有解法的。比如我的朋友蔺桃,最近写了一本书叫《三十岁,回乡去》,讲述的就是一群返乡青年的故事,他们在三十岁左右决定回归田园,并由此走出了一片新天地。让我们欢迎本书的作者蔺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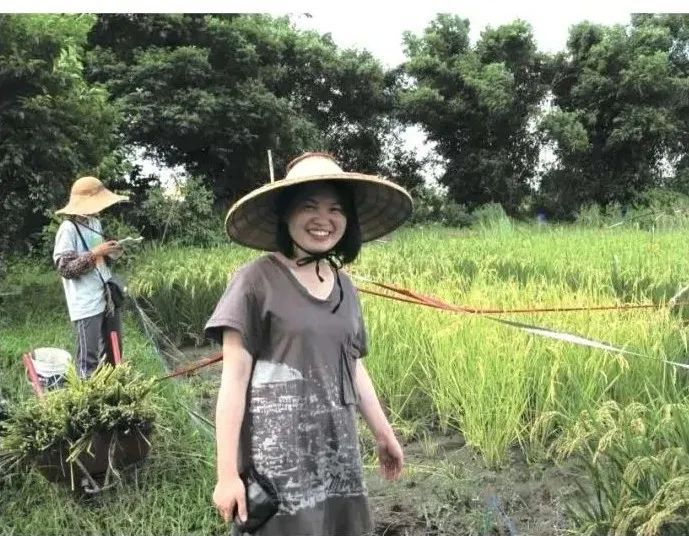
蔺桃:野聲电台的朋友好,大家好,我是蔺桃(桃子),我现在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盖恩斯威尔这个小城市,在这个地方一边种菜一边带孩子和写作,最近出了一本书《三十岁,回乡去》。
秋凉:桃子好久不见!上次我们见面还是2016年在台湾的时候,那时候你女儿还是个一岁多的小宝宝,现在都要上小学啦。你们那儿的疫情还好吗?
蔺桃:我们现在因为学校开学,一天增了500例,如果只是盯着数字的话一天都生活不下去,就恨不得立马回国,但现在我们哪里也不去,就呆在家里面,已经七个月没出(远)门了。我们家门口有个小小的游乐场,带孩子去踢踢球,玩玩水,荡荡秋千,戴口罩去菜地干干活,湖边散散步,就这样过了七个月,幸好我们有这个环境,还是比较幸运的。
秋凉:我朋友圈里也有些在海外带娃的家长,疫情期间孩子不能上学,大人得天天在家陪着,真的挺辛苦的。你们家平时是怎么分配家务和带娃的呢?
蔺桃:我们现在就分工,但有时候也很灵活,比如他赶报告或者要交论文,就我来带,我赶稿的时候就他来带,保证两个人又能带孩子又能保持产出,做饭也是这样,带孩子的那天一个人做饭,另一个人洗碗。每个学期我们都会调整家庭的责任分工,不至于让我一个人被家务和带孩子淹没掉。我觉得这个还是在乎夫妻之间怎么认同,他在读书的时候为了保证我的睡眠,一边看书一边帮我带孩子,可以说功不可没的,包括我出这本书也是他鼓励我找出版社,帮我整理好邮件,说“我还是个比较好的伯乐吧”,没有他确实走不到这一步。(笑)

秋凉:桃子的老公黄庆明也是在三十岁的时候决定到美国读政治学博士,收到佛罗里达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他们的女儿才刚出生一小时,可以说很戏剧性了。可能许多人会理解不了一个年轻父亲作出这样的决定,但是桃子非常支持她老公追求梦想,在女儿四个多月的时候举家前往美国,住在佛大的校舍里面。辞职之前两人都在媒体工作了多年,没有离开过中文区,夫妻俩带着一个新生儿在美国生活的这五年,真的非常不容易。桃子你是怎么看我们这种渴望改变的“三十岁”心态呢?
蔺桃:其实我不太能直接地分析出来,但我觉得很有意思,我有个女朋友比我大两岁,她三十岁的时候非常惶恐,虽然她的事业很成功,我不太能理解,等到我三十的时候才能理解。包括我老公三十岁的时候,我们女儿刚出生,他刚做这个决定(去美国读博)的时候我非常害怕,那个时候我很犹豫,觉得虽然和他已经非常心意相同,但还是没办法感同身受。到我三十岁的时候,好像天“哐当”一下砸下来了,感觉自己一事无成,以前认定的价值感突然一夜之间消失了,完全陷入自我否定:“我的人生是不是就这样了,我错过了转型,以后是不是就只能是全职太太了,会不会跟不上节奏,我老公越来越优秀,我却在原地踏步。”当时我经常晚上睡不着觉,辗转反侧,就像在悬崖边上,一旦自己踏错一步好像就会万劫不复一样的。我是遇到问题就想要解答的人,就做了这个“三十返乡”的提案,得到了公众号“乡愁经济”的支持。我可能觉得说,因为我自己有这样的焦虑感和彷徨感,才促使我去做这件事情,我在采访的过程中发现别人也和我有一样的想法,原来我不是一个人,不是特立独行和特别矫情的一个人。其实每个人在三十岁之前都有“人生是不是到此为止”的焦虑感,看他们怎么去突破自己,我的心也会慢慢踏实安静下来。

秋凉:在《三十岁,回乡去》这本书里,你采访的对象都是三十岁左右吗,大概在什么年龄范围呢?
蔺桃:有大概十岁左右的差别,年纪最小的是陈茹萍,她是今年才三十岁,年龄最大的是四十岁,但他们是返乡时间比较早,有的差不多是在十年前开始探索返乡,想要做不一样的工作,虽然他们在既定的工作岗位上做得挺好,但在三十岁左右的时候他们想“为什么我的生活是这样的,换个生活应该怎么办”,做其他的探索。

比如夏莉莉,本来在北京呆着,做清华大学的一个教学助理,她的工作其实蛮稳定的,也结了婚,但她还是想要回到都江堰老家,继续做一个面向儿童和社会的书屋,甚至走得更远,从这个书屋向社群营造、乡土教育去走,后来她就带着老公孩子,三个人跑遍了全国的农场,看看哪个地方可以当作自己的家乡,最后决定定居在明月村,卖了北京的房子,毅然地在那里流转了一个土地,建了一个学校学校,现在已经在建了,这样的人生也蛮有意思的。

秋凉:今年受疫情影响,加上你长居美国,采访起来会不会有难度,他们的项目你都有实地查探过吗?
蔺桃:大部分是在网上了解,包括现场面对面的几位,因为我是2014年从台湾毕业回来以后开始采访这些人,其实我是很想自己进入新农村这一块,当时也去了一些农业公司应聘,但没有特别满意的,没有办法就回到了传统媒体继续工作,做写作这块,有采访返乡选题的时候我都主动去报名。比如那时候我采访周华诚,他是我的同事,我是都市快报的,他是杭州日报的,那个时候他做“父亲的水稻田”,我在网上看到他信息的时候激动得都流泪了,觉得他就是我要找的那种既有情怀又有创意,保持了一颗赤子之心的人,在这个行业里面他是做生态农业的,不是朝着钱去的,有自己的梦想在那里。我们第一次见面就在报社楼下的休息区,聊着聊着就写了篇文章出来,当时想去他家那里看看,后来我怀孕生子就到美国来了,所以很多事情都不在自己的想象之中。

秋凉:那说到乡村,桃子也在乡村生活过吗,会怀念自己的家乡吗?
蔺桃:我就是乡村长大的,还不是“小镇青年”,最近不是流行“小镇做题家”嘛,我是土生土长村子里长大的小孩,很小的去趟镇上都要坐一两个小时的车,后来通了公路后五分钟就能到路上,但以前没有路的时候就是这么难。后来我去镇上读小学,再后来去县里面读高中,再去省城读大学,工作以后去了福州和杭州工作,实习时候去北京,工作两年后去台北,再后来来美国,感觉就是从一个村子里的女孩长大后慢慢往外走。一直以来我们接受的教育就是“应该往外走”,好像乡村和城市是二元对立的,如果说城市意味着繁荣、发达、光鲜亮丽,那农村就是一切的反义词。
但是每个人的乡村体验是不一样的,我记得我遇到我老公的时候,聊到小时候的经历,发现他的经历和我完全不一样的。他是县城郊区的小孩,也是有田的,晚上蛙声一片,秋天大家一起去割稻子,割完后在稻田里玩捉迷藏,玩大富翁游戏,夏天的时候他和邻居家三个男孩子一起躺在屋顶上,吃芭乐之类的应季水果,一起吹风、看星星……他跟我讲述的乡村生活会让我回想自己的乡村生活,其实也是有美好的瞬间的,比如我跟着我爸去巡田,看水坝里的小彩虹,现在想起来都很美好,秋天的时候落日黄昏照在晒谷场,我写了篇作文就形容这种美的感受和带给我的畅想,还被老师念出来,后来成为我喜欢文学的一个起点。其实乡村生活带给我们很多滋养,但是我们长期以来思维都被训练成“要离开乡村”,而且这样的经历不仅是我采访的,包括我在台湾采访的人也是跟我一样的,有个云林长大的女孩后来读了硕士然后去宜兰种田,她还比我大两岁,但她和我的经历一模一样的。所以我就想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乡村长大的孩子隔着千山万水,我们的经历和感受却都是一样的,这说明社会单线发展的思路是全覆盖的,没有哪个地方可以幸免。
秋凉:蔺桃刚才的讲述真的非常有画面感,现在正好也到了收获的季节了,我想到李健有首歌叫《风吹麦浪》,很多人都翻唱过,是一首特别能唤起乡愁的歌,我们请Adon来介绍一下。
Adon:这首《风吹麦浪》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非常温柔,我在街头也会常常翻唱它,受原唱李健的影响,我唱的时候也尽量字正腔圆,感觉是非常享受的。而且我觉得如果一首歌让你唱的时候有画面感,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就像周云蓬的《九月》,它们的情绪都很平稳,但是让你感触很深远。
秋凉:那让我们一起欣赏Adon带来的《风吹麦浪》。

从普拉托到甘城,种子的迁徙从未停止
秋凉:去年我参加博洛尼亚一个非营利组织WUXU组织的“普拉托计划”,有幸认识了一位意大利的人类学家和艺术家叫Leone Contini,他是研究人类学背景下的移民和迁徙话题,做过一个非常好玩的项目,就是跟普拉托华人学种菜。

这里呢我简单介绍一下普拉托,它是意大利中北部托斯卡纳大区的一个城市,曾经是意大利重要的纺织基地之一,八十年代的时候有很多华人移民来到这里开办制衣厂,现在是意大利第二大华人聚居地,仅次于米兰。央视曾经播过一部电视剧叫《温州一家人》,就是讲述普拉托华人的奋斗故事。

对于普拉托当地的意大利人来说,华人带来的不光是新面孔、新语言,还有新的文化,典型的就是在吃这一块,许多华人带了国内的种子来种植自己熟悉的蔬菜,像葫芦啊蒲瓜啊什么的,慢慢变成了华人圈里的一类生意,这就引起当地媒体的关注,特别有些右翼势力会煽风点火,把这个话题政治化,煽动种族歧视。这位意大利的人类学家Leone就特别看不爽这些媒体的抨击,他认为“种子天生就是移民”,种子的到来和传播正反映了华人社区在普拉托当地的影响力。他曾经非常怀念他祖母家乡(Agrigento)的一种蔬菜汤,但在整个托斯卡纳地区都找不到这种蔬菜,反而在一个普拉托的华人农民那里,他喝到了童年记忆中的味道,其实就是“蒲瓜”。对于一些排外的意大利人来说,华人带来的新种子可能是在“污染”他们的本地蔬菜,但对于这位人类学家来说,他反而因此找回了一段家族记忆。所以他就通过实践种菜,去研究这种跨文化冲突和权力关系如何影响植物景观,并把自己的发现变成艺术项目。蔺桃目前生活的佛罗里达大学校园里,也有一块多元融合的菜地,被你们成为“秘密花园”。


蔺桃: 嗯,你刚讲的时候我想到这其实不是中国人的特性,而是人的特性。我们现在种菜的地方是“多族群生态园地”,是一个农林混合的园地,有树、有香草和多年生的灌木,可以种蔬菜,我们这里的人来自不同国家,每次我带不同国家的朋友去的时候,他们都能够在那里找到他们老家的东西。像我们的日本老师在那里发现了一棵银杏树,印度朋友找到了一棵咖喱树,中国人可以看到枸杞、月桂树,墨西哥的同学找到了他们日常吃的仙人掌,还用我们菜地的仙人掌做了一次仙人掌塔可的厨艺课,东南亚的朋友更能找到各种各样可以吃的,还有南美洲的朋友可以找到叫做Chaya的树,它的叶子可以吃但是要炒一下或用水焯过以后,还有很多野菜,比如说荠菜,很多人就不懂,除了真正了解各种文化的人都不知道它们是可以吃的。像马齿苋是土耳其的朋友最喜欢吃的,这种就是共同语言,我们也吃马齿苋,但他们的吃法和我们不一样的,感觉特别有意思。你想这个菜地大概是1980年代种的,那时候就有这么多不同种类的东西,很有可能就是当时的留学生带过来的,种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其他地方看不到,因为是有规划的,没有让它四处蔓延,感觉这不是中国单一的民族特性,我反而觉得越是文化古老的悠久的地方,像南美洲啊东南亚啊,这些地方的人比较容易像中国人一样保持着和土地亲近性的民族。
我去年参加了一个园艺大师(Master Gardener)的志愿者项目,去收集一个种子项目,发现他们那里的种子居然有中国的红菜苔、雪豆等等,我就特别惊讶,向他们介绍我们是怎么做红菜苔的,去网上找了扶霞(《鱼翅与花椒》一书作者)的英文文章给他们看,大家都非常惊喜,这些种子至少都流传了一二十年了吧,它们已经被本地的种子机构接受,所以不是一个外来物种入侵,而是作为一种蔬菜,放在亚洲蔬菜下面,就跟上海青(Bok Choy)一样,它非常新鲜口感好,比美国人常吃的生菜、菠菜还要贵,也是从一个外来的,好像不太被主流接受的品种,慢慢成为一种大家日常当中比较熟悉的一种,还能卖得比较好的价格,还蛮有意思的,可能和移民的心态有点相似吧。

秋凉:我们家长一般教导小朋友吃饭,说要样样吃,不要挑食,人们在餐桌上还有可能达成一致,一起享受美食,但是一谈论政治就好像很难一团和气,往往就是对立甚至撕裂。
蔺桃:我觉得你的视角和我有点相似,但我是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我是从台湾这样政治对立比较明显的地方过来的,(在台湾)冲击也是有的,到美国后我就不太关心政治了,因为觉得政治在很多问题上是不可调和的,同一个家庭可能讨论政治的话是不可开交的。但是食物特别有意思,哪怕生活态度不一样,好不好吃大家基本都能达到共识。我之前在安娜堡采访过一个政治活动家,后来他回到社区里帮助建立一个“消费者共同合作社”,说自己为什么进入到民生消费领域,是因为食物本身可以沟通起不同政见的人,但政治本身不能,当时让我心里有很大触动。
我觉得食物是很好的媒介,比如种菜的时候其实没有更深层次的交流,但如果搞活动,大家一个人带一个菜,放在一起分享,美国的文化叫百乐餐,大家就特别聊得来。像中国的端午节,我做了粽子,大家都很愿意去了解,问这个食材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么好吃,我们用的豆豉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做鱼啊,我们怎么吃鱼啊,珍珠丸子代表什么意思啊,平时干完活就走的人就很愿意过来跟你聊很多。我记得有个美国的犹太背景的小男孩,就跟我聊他们的春节和中国的春节有什么相似的地方,说他们也要守岁,是用水把坏的东西冲走,我们是用红色和爆竹送走。虽然我英语还不能畅通无阻,但真的是可以意会的,食物真的可以沟通起不同文化、不同政见。包括我们群体里有印度教的有不吃牛肉的,有的印度教是不吃肉,有的是穆斯林就不吃猪,有些是素食者,不吃肉类,像我们这样杂食者什么都吃,但我们在一起不会因为聚餐有很大问题,比如我带了肉类,素食者会选他自己能吃的,没有很强的壁垒感,会让你很舒适,这是食物本身带来的魔力。
秋凉:你们这个菜园的参与者都是佛罗里达大学的学生们吗?
蔺桃:基本上都是学生,有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生,我们也会把周边的邻居尤其是爷爷奶奶,他们来这里带孩子可能没有什么其他乐趣,我带他们去他们都会蛮开心,参加些活动看看菜地,摘些菜回家,我们总的来说跟学生打交道更多。

返乡,为了更美好的生活
秋凉:那说回“返乡青年”,像移民往往会面临种族融合的矛盾,返乡青年中很多也是高学历的海归青年,他们在乡村和当地人沟通的时候,会有困难和阻力吗?
蔺桃:我觉得每一个返乡青年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包括我在台湾采访的返乡青年,他们可能会遇到两个矛盾,一个是你说的高知识青年和保守的本地居民的差别,还有一个是外来者和本地人的矛盾,但每一个人面对的具体情况都不一样。比如唐亮是放弃了重庆的工作,回到四川成都金堂县福兴镇牛角村老家,他遇到的问题首先是家庭性的,因为他要把在外打工的家人一点点劝回来,他选择的是“我先做我的事情,你们有兴趣来谈”,先慢慢地把和他想法相近的弟弟和弟妹劝回来和他合作,当他们家好起来之后去成都生活市集摆摊,带他们的叔叔辈们去参加生态农业的培训,大家的眼界都开阔了,对这个事情的理解就比较统一,他们一起建起了自己的房子,带领村民去修路,这个事情就不存在一个外来者和本地人的矛盾,只是眼界高低的区别,你可以去沟通和弥补。

有些人回到了不是自己的家乡,就遇到了需要融入去沟通的(情况),会有个融入的问题。我觉得这要看你个人的能量,像夏莉莉这样去找一个和你气质相似的村子,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进入到完全陌生的环境,否则你受挫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我还写过杨阳,她是云南曲靖人,到上海做过媒体行业,觉得不适应,后来决定回云南,在一个烟企里面工作,后来转入公益行业,最后受到内心的感召,想过更简单的知行合一的生活,所以就去了泰国学习可持续生活,做了很多自我调整,回到云南后去了好几个村庄,最后找到了昆明市郊的墨雨村,那里已经有一批实现永续生活的人,已经打好了一定的群众基础,有个云南大学的老师叫李婷婷,把永续生活的理念带进去,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不同目的的人,形成了一个“新村民社区”,所以你去的时候不是一个单打独斗的状态,那里的本地居民已经被这些理念所影响,不会觉得你是个很怪异的人。所以她后来就和李婷婷合作,做她的食物森林,也是从头探索这个事情。其实无论大陆还是台湾的村子,对年轻人的渴望还是蛮大的,年轻人能带来年轻的生活方式,活力都会不一样,他们跟本地老年人的关系都搞得很好,一边搞农业有机生活,一边在当地做调研,一起清理街道运动,当地人都很配合。老一代并不是那么固执觉得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最好的,是可以看到好的效果,他们是可以沟通和克服的。

秋凉:说到大墨雨村,我有个关注很久的平台“彩虹宝宝”的创办人就在这里生活,是一对女同伴侣,叫豆子和芝麻饼,2016年她们通过试管技术生了一对混血宝宝,身体力行地实践着“多元成家”的理念。2017年她们来到大墨雨并租下院子20年,改建后在这里定居,2018年她们租下了村里的一块公共用地,用于建设“墨雨村学”,做了很多关于儿童教育和女性心灵成长方面的项目。根据“彩虹宝宝”平台上的介绍,大墨雨村是昆明近郊一个有着400年历史的彝族村庄,近年来吸引了200多位新村民在这里安家,其中有公益人、设计师、画家、手作人、飞行员等等,他们互不相识,却在这个小村庄里找到了自己的归属感,而且也使这个彝族村庄以一种自由的状态不断变化生长。

蔺桃:对,我觉得很有意思,像这种新乡村社区会越来越多元。我在台湾有个非常喜欢的村子叫深沟村,采访过赖青松,他是回到妻子的家乡租了田,建了一个像谷仓一样的房子,一开始也是为了孩子的教育,后来是希望孩子能够接受跟土地相关,有人情和乡村氛围的地方,知道自己有一个家乡,而不是房子拆掉了家乡就再也不存在了。慢慢地有越来越多的返乡青年,他们本来没有自己的“乡”,这时候文化包容性就体现出来了,比如有很多外国人,美国的、日本的、南非的,去那里开店、打工、种田,还有一个多元成家,有五六个女性组成了一个团体,像一个真正的家庭住在一个房子里,财务都在一起。可能进入到某个时代乡村的可能性反而比城市更多,这是我看了很多的案例后得出的一个感觉。
我们这里属于一个大学城,中不溜秋的小城市,是个又洋气又土气的一个地方,就有很多搞农业的人,有各种各样的永续生活,你能找到很多跟你志向相同的人组成Group。比如有段时间我很喜欢蘑菇,就有个蘑菇的Hunting俱乐部,大家一起来研究蘑菇,有段时间我对堆肥很感兴趣,你可以加入堆肥的俱乐部,还有做自然教育的,做可持续生活的都有,你在这里找到跟你志向相同的人还蛮多的。某种程度上乡村不会是我们想的很落后、很保守的、不开放的地方,反而有可能代表了另一个意思,代表了传统、有人情味、有包容力,同时还代表着创新和相互交流,我希望有一天看到的乡村是这样的。
秋凉:最近有位研究乡村振兴的孙君教授批评浙江是“有钱任性”,用城市发展的思维来推动资本改造乡村,搞了一堆花里胡哨的农业现代化新模式,但实质上是把农民推离土地、农业和乡村,并消灭乡村文化,剥夺乡村自治的现实基础,所以他提了一个药方,是重振集体经济、恢复乡贤乡绅自治。你们俩怎么看呢?

蔺桃:我可能有意无意地避开这样的群体,因为我刚开始的时候比较害怕这种被资本进入的农业状态,但我后来有机会采访做乡村民宿的人,这也是他们中很多人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这个不是我擅长的,所以就不往深里谈的。但我想事情都有两面性,举个例子,我采访过一个返乡青年叫吴志轩,他在江西婺源做古建筑的维护和开发,把婺源当地乡下有几百年历史的明清时期的老房子租下来,然后做古建筑维护,先保持“古”的状态,弄完后作为高端民宿包装出去,配合度假旅游来做,他的公司在很长一段时间包了好几个这样的项目,所以你能完全否认他们对乡村的意义吗?其实是有的,因为这样的房子留在乡村,如果没有有识之士发现它们,就会一直破败下去,而当地政府并没有足够的资源能力去保护起来,但另一面,可能另一部分建筑就被放弃和破坏掉了。
后来他们的经营思路做了一个转向,不再做单纯的古建筑保护旅游,放弃了一部分,而是找到了一个整村的文化,叫虹关村,村子符合我们对于江南的想象,“小桥流水人家”的古典诗意感觉,他们把村子里的运营给包下来了,他们的思路是把村子当成他们的家园,把城市人带到这边来不只是来住一两个晚上,而是这个地方相当于你的另一个故乡,你可以来这里住好多回,购买的是好几年的居住权、使用权,旅游度假的内容也变了,不再是吃个野菜,搞个农家乐,而是真正进入到乡村氛围里面,比如组织村民一起清理河道,搞卫生,去村里抓鱼,看星星,体验当地的徽墨文化,过节的时候扎草龙来舞龙……他们其实是把村子的文化核心提炼出来,通过商业化的包装吸引城里来的人,很多人说“啊这就是我们想象的向往的乡下”,这是跟城里的生活截然不同的方式。你觉得这样的操作思路是毁坏还是帮助?我觉得从他们做的事情来看是有帮助的,而且也给很多本地村民带来很多工作机会,比如他的团队里面基本都是本地人,包括修缮工人啊,厨师啊,带孩子摘野菜摘果子的人都是本地人,本地的年轻人也可以找到工作机会。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我觉得不能笼统地说“资本是在毁坏乡村”,其实是看你的操作思路是怎样的,你能不能给当地人提供一个良好的互动,从这个角度来说不能只能靠良心,你的创意和眼界是非常重要的。吴的眼界是非常开阔的,他已经从高端旅游度假转向了乡村建设,这个边界是有模糊在一起的,我反而觉得资本可能会是乡建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力量。

Adon:台湾的政治其实还蛮有趣的,你看到台面上的一线政治人物,他们和美国的精英政治一样,都是学历经历各种占优的精英分子,家族资源也非常雄厚,但是在台湾的基层倒还蛮有在地化的特色,和乡绅和公庙这些派系是很难分开的。常常看到在台湾选举的时候,候选人去拜两三千庙,其实他们就是为了巩固基层系统,基层有农会、鱼会、水利会,这些是盘根错节的在地的利益系统,和在地的宗亲系统也很有关系,所以在地的婚丧喜庆,这些事情都是跑不掉的,完全在巩固这些人脉关系。像这种传统文化在台湾还是蛮根深蒂固的,虽然之前有一些台面上的人物想改变这个现象,可能因为觉得不是最理想的民主政治的模板,但是想要改变还是会碰到蛮多的阻力,这个系统从里长到县议员,与地方性的选举关系很大。在中央的立法单位有分区和不分区立委,分区立委代表这一地区的民意,必须要去影响立法提案,对那区的选民有所交代,那不分区的立委往往是政党价值的展现,往往由学者和专家来担任,所以你看这个党提名的立委就可以了解到基本的价值观,那它的分区立委呢其实就是和乡绅、公庙、宗亲这些系统去打交道。
在意大利我们也常常看到很耸动的新闻标题,例如“西西里岛1欧可以买到传统庄园”,这个其实是意大利政府农村改造的一个手段。因为意大利的人口外移是非常严重的,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他们曾经有过经济起飞的阶段,但这几十年经济一直在下滑,很多年轻人都没有希望,只能去大城市或者出国,导致在意大利很多漂亮的地方,除了观光或者继承家族手艺,空屋是很多的,这些看似很吸引人的标题,其实背后承担的东西还蛮多的。一方面这是因为意大利的建筑法规非常严格,你要改动你买来的房子是非常困难的,而且你必须承担修缮的责任,不能按照自己的喜好,而是按照当地政府的指示修缮整理,每年都会有人来检查你的修缮状况,这个花费也不低,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个维持修缮的能力的话,这个买房条约就不能生效。我觉得意大利传统包袱重有好有坏,对老房子或者说旧纹理的维护还是很成功的,从上到下都有“维持”的观念,他们的政府官员在审查的时候其实也有一定的理想性。

秋凉:不论是改造自己的家乡还是寻求新家园,都是人们寻求幸福的方式。桃子你在杭州、北京、台北都生活过,现在在美国生活,觉得在哪里最安心,最有归属感呢?
蔺桃:我在很多地方都有想法“哎,是不是留在这里成为家乡“,其实我对自己家乡好像没有那么强的归属感,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它是你出生长大的地方,但你一开始想的是“离开这个地方”,所以我对我的家乡(湖南浏阳人)其实并不了解,也许只有你了解了才会有喜欢的可能。包括在杭州、台北还有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你越了解当地的文化和社区感,才会有“我属于这个地方”的感觉。我觉得人都是想要自己过得舒服的,过得舒服的很重要的一个点,是你的内心要达到一种安宁和稳定感,为此你必须要锚固在某个土地上,这种锚固感就来自于熟悉和了解,只有你了解了才有可能会喜爱。我感觉未来无论我在哪个地方,可能都会试着去了解和喜爱这个地方,通过和自然、和人群去接触,创造一种自己想要的生活,某种意义上是我“返乡”的状态,这个乡不是某一个固定的点,而是你有这种“返乡”的能力,你可以去了解,去真正地耕作,了解这里的土地文化,跟这里的人打交道,过当地的生活,同时也把你自己的生活方式带过来,稍微影响一部分人,形成一个“同温层”,为自己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交的状态,这样的能力可能才能够让你无论去到什么地方,都能找到这样一个“乡”,这种内心的安宁和稳定的状态。
秋凉:这就又让我想起那位意大利人类学家Leone的话,“种子天生就是要迁徙的”,人也可以是一颗种子,携带着自己的家族记忆和基因,只要你是一颗有生命力的种子,在合适的温度和阳光之下就会生根发芽,慢慢地形成自己的村落和宇宙。我觉得在哪里都能生根发芽,可以说是一种获得幸福的能力。《三十岁,回乡去》这本书是蔺桃历经五年深度调研所写成的,相信会让你收获满满。

蔺桃:大家如果对返乡、新乡村建设、乡村振兴或者新的生活方式感兴趣的,可以到当当上购买我的新书《三十岁,回乡去》,谢谢大家!

秋凉:在此感谢蔺桃做客「野聲」电台,也祝福每一位听众都拥有迁徙的自由和扎根生长的能力。感谢收听「野聲」电台,我们下期再见。❤️
注: 返乡青年相关配图来自微信公众号“乡愁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