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群算法(2): 爱和看见
五月底的四天,我在福罗里达西南部的Archbold生态调查站拜访挚友悠。
临行前,悠在电话里说:“太期待你來了。你想去湖里游泳嗎?有天晚上我在湖里游泳,感覺我是一條魚或者一隻蟲。水有20米深,暖和。剛跳進去的時候,魚全都跟著溫度游過來。遊的時候他們就會碰我。不是漂亮魚,是長得很「魚」的魚,有點醜。鱷魚要來吃我的話我也逃不開,他們遊的比我快多了。真的需要把自己暴露在死亡面前。”

Archbold生态站在福罗里达最高点Lake Wales Ridge,也是全世界闪电最密集的地方。很久以前Lake Wales Ridge是一个岛,岛的生态系统由闪电驱动:每十年左右闪电会纵火,森林烧了后死树变成昆虫的养料和肥沃土壤,继续生态循环。随着地质时间过去,海水散去,岛和北美大陆链接。现在这里大部分地面还是沙滩。上个世纪更多人来这里建房子,火就很难散播,岛上的很多稀有物种面临危机。
生态站本身是二战期间一个富豪博物学家用自己的地改造的。之后的70年间,生态站作为非盈利组织靠私人捐赠和董事会维持。生态站除了常年驻扎的植物、鸟类、昆虫、鱼类研究学者,还有来帮助种植和人工纵火的志愿者和来徒步和看动物的游客。
在鱼群算法(1)里介绍过,过去两年我在探索动物群体是怎么通过不同的感知和互动模式(比如密度和数量)来调整群体的动态结构和信息处理速度的。不过因为是理论组,探索主要是通过读论文,写模型,看模拟动画。
所以临行前我很期待与动物和生态学者接触,向他们请教自然世界中真实的动物群体是怎么互动、集群和传播的,有什么和模型类似的例子,有什么微妙的细节差异。
四天里我意外地除了知识例子还收获了微妙的关于“看见和爱”的感受。下面分享三则:
1偷窥和逃离,2匮乏和合作,3猎奇和保护。

1: 偷窥和逃离
我挨个问了生态站的成员们他们知道的集体信息传递的例子。他们告诉我群体行为和信号沟通特别多样。
来自波多黎各的鸟类组实习生E举了个经典实验:人类拿着一只死乌鸦进入一群乌鸦的栖息地。过了一阵子,乌鸦群里更新换代有了没见过那只死乌鸦和人类的新乌鸦。但是等那个人类再次来时,所有见过和没见过她的乌鸦全部开始向她尖叫恐吓。这代表乌鸦能够识别具体人类个体,还能向无论有无血缘关系的群体成员通过叫声和其他沟通方式快速传达要恐吓的信号。
E说,沟通协调是很多泛化种用来快速应对位置环境的方案。泛化种(generalist)对比特化种(specialist)指的是能吃更多种物种,因此能在更多资源不同的环境下生存的物种。在遇见“厄运”(拿着死去的同伴的人类)时,他们需要快速识别危险和资源,串联起来决定逃离还是对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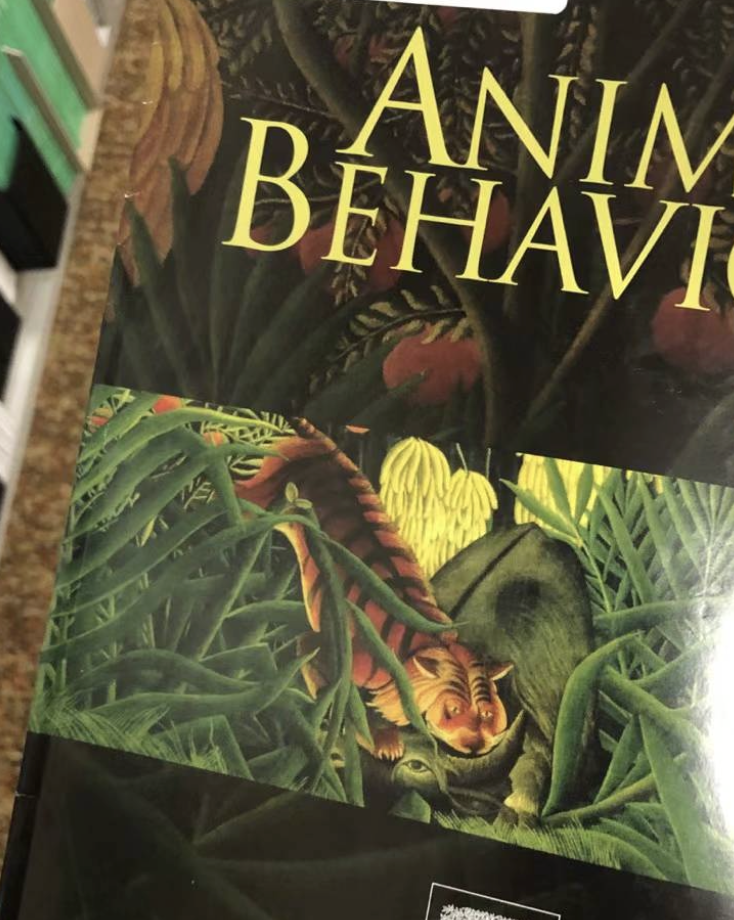
我发现“识别和逃避危险”是个很常见的信息需求。
在Archbold期间我们去海里玩。在大腿深的海水里有一大片大概几百只的银色小鱼在透明的水里游。看着它们离我也就一米,我就想去摸。但还没等我走近或下手,它们就很整齐地向反方向游走了。海浪惯性很大,我都被推着不能控制我的方向,而它们似乎还是能选择特定方向而且大部分和鱼群对齐。
回到生态站我就和E讲抓海鱼比我想象的难好多。E说肯定的,这些鱼能预判你的意图,所以你需要非常缓慢地下网而且也反向预判它们的逃逸方向才能抓住它们。鱼群是怎么预判我的意图的呢?也许是它们能水压上感觉到我靠近时的水流,也许是它们能视觉上看见我靠近的影子,也许受惊的鱼会让别的鱼意识到危险并反应。不论机制如何,【跟水流合作】都是群体和个体的必修技能。毕竟小鱼的生存很依靠它们能在任何水流中都继续游而且不被抓到。比如在美国很多地方是入侵物种的mosquito minnow就是在下雨时都能游到房子前面水洼里,靠这种“咋样都行”的能力来适应一切。
很有意思的是,生态学家们想要观察动物来不影响但同时了解它们。但是动物并不想被发现!自然中想看见它的通常是想吃掉它的家伙。于是生态学家们的入门手艺就是学习【看】。E说,他刚来福罗里达的时候跟前辈在田野里走什么鸟都看不到,也识别不出。过了一段时间,他才感觉视野变得分散和展开,对他们在意的鸟也变得敏锐和熟悉。不满足于肉眼局限,生态学家们还借助各种机器来偷窥和追踪:用GPS检测熊的地盘轨迹,用录像机来分析鱼群受惊时同时用尾巴拍打水面的行为,用每天去田野里记录哪只鸟在巢里来分析鸟的社会结构和行为。
2:匮乏和合作
早上6点我们和来自台湾台中的昆虫生态学生S去附近的两条沙滩树林里找一种只在这个地区有的稀有甲虫(scrub beetle)。他说这种甲虫在过去20年里只找到过15个,相比之下长得很像但更常见的一种甲虫在一小时里就能找到10个。甲虫比较小,而且作为分解者一般藏在土壤和腐烂的死树里,所以抓和识别甲虫是个手艺。虽然甲虫组成了地球生态多样性的25%,但是他们比起更大只的鸟就不那么受爱戴,也获得更少的研究和保护资金。
S拿着斧子去劈沙土路边烧焦的树,摸接近树根的部分判断是不是甲虫喜欢的湿度。他说这种甲虫从来都是两只或更多只在一起被发现,更不会有幼虫独自出现。这是因为scrub beetle需要的腐烂树木不是很常见,一旦他们在走来走去后通过各种随机性和信号找到一个合适的树后,就会在那里呆到吃完。并且幼虫的肠道菌群不能消化纤维,所以需要吃成年甲虫的大便。觅食和进食这两个行为对于甲虫们来说都是需要依赖同伴和家庭的。

而资源对群体里的互动不只是在昆虫里能看见,植物里也很常见。
下午我们在植物组的论文俱乐部边喝啤酒边讨论了一篇关于stress对植物是合作还是竞争的影响。stress大概是指环境里资源多么稀缺,还有环境里有没有扰动植物生存的事件,比如火和入侵物种。合作是指植物用化学媒介分享资源或者帮别的个体提前分解营养,而竞争是指争夺资源和空间或者阻止其他个体生长和吸收。植物互动领域里默认理论是资源越少,个体之间就更倾向于合作而不是竞争。但是这个论文通过实验发现在密度小的情况下,资源稀缺到一定程度时植物不会增加合作而是会又趋向竞争。小组的讨论结果是这个规律可能对他们目前要做的种植项目有启发,于是他们准备根据模型的变量去测量他们实验,然后决定什么设置最有助于那个本地植物的生存。
对我来说有意思的点是,群体信息处理和行为在植物里和动物里很不同。植物不能移动,只能生长。植物的互动网络不是及时变动的,而是真的通过根部和化学物质有持久连接。不过在甲虫的例子里,菌群其实也是实际的化学互动。
3:猎奇和保护
和生物学家人类们的互动中,我能感受到他们在跟我讲解某个物种的特性时的兴奋和谦卑,还有他们对某种生态多样性保护的责任感。我有些嫉妒他们能够【看见】这么多细微又具体的生命,和【看见】他们自己行动与世界其他生命的连接。我更羡慕有人能【爱】其他生命,能为了爱去【理解】和【保护】他们。
我在想,猎奇和负责的爱的区别也许是你有多少个感官接触了它,你有多少时间和它一起生活。我正巧遇见了一首诗,虽然我找不到原文但翻译大致是这样:
《看见》伯特海灵格
当你只注意一个人的行为,你没有看见他;
当你关注一个人的行为背后的意图,你开始看他;
当你关心一个人意图后面的需要和感受,你看见他了。
透过你的心看见另一颗心,这是一个生命看见另一个生命,
也是生命与生命相遇了,爱就发生了,
爱会开始在心之间流动,喜悅而动人!
在来之前我对计算模型只能看见抽象行为和揣测进化意图有感觉被局限。在这里我遇见的生态爱好者、学习者、保护者花了更多年和更多耐心去注意一个个具体的生物。他们是不是作为一个生命看见另一个生命?GPS追踪和拉丁分类是在拉近人对动物的感受理解,还是跑偏了?通过人工纵火和杂交濒危物种来保护生态多样性对他们和我们的需求的真正结果是什么?
几个瞬间里我也有我和其他人、其他生命是同类的感觉。
一次是在找甲虫时我低头看见一只小鼹鼠。S把它捡起来,抚摸了它的背毛。我把它接过来,发现它的身体很僵硬,但是毛很软。“可能是昨天晚上刚死的,” S说。我看着它没有眼睛的脸,和它跟我肤色一样的手掌。它离我那么近,我所有感官都专注于它。它那么小。
另一次是天气非常热的上午,我感觉脾气焦躁一遇到小挫折就想吼叫,头和身体疲乏在外面走几步就想进空调房睡觉。刚出去抓鱼也回来睡觉的姐姐说天热,scrub jay鸟都躲起来不去树上呆着了,鳄鱼也用泥巴盖住自己降温。我瞬间觉得我的心情其实也是动物性,而且能量低真的除了睡觉没有什么效率大法能够调整。

从福罗里达回到北卡罗来纳的细胞实验室,回到在暗房里用显微镜屏幕看静止的细胞。我多么希望可以像生态学家或者其他文化里和自然沟通的人那样,在细胞里走路,抬头低头看在移动的细胞核,伸手翻开一个蛋白粘团,戳戳它的弹性质感。
再次打开动物集群模拟的代码编辑器时,我有很多想要用模型来说的问题和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