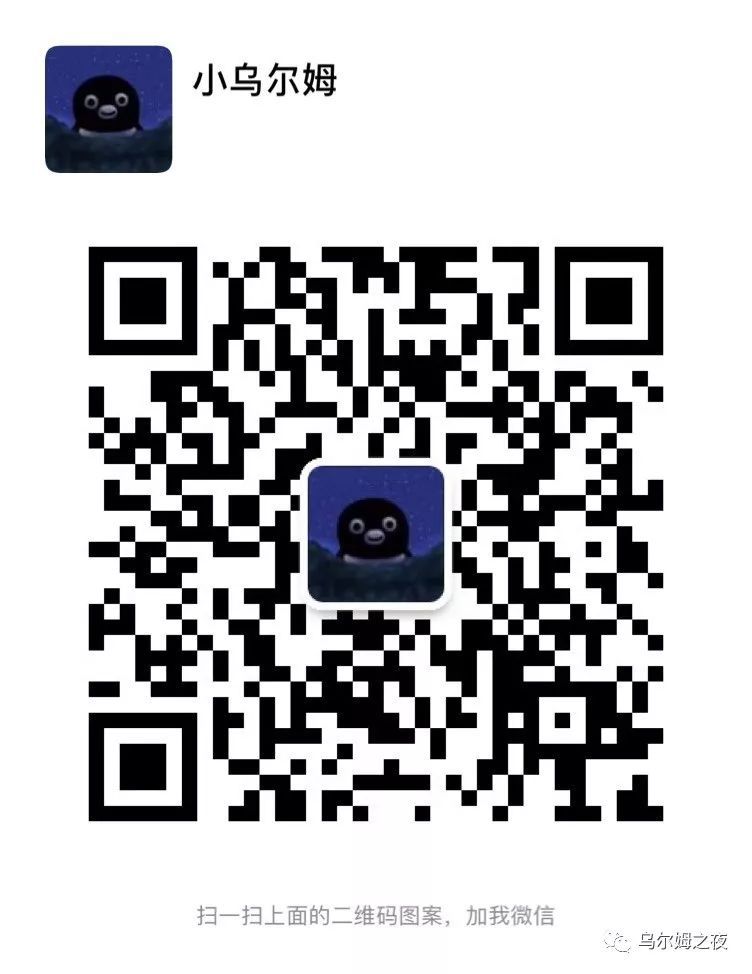「乌尔姆第二夜」从「全面内战」到「例外状态」:香港问题讨论
本文是”乌尔姆第二夜“演讲者文稿及现场讨论的文字回顾。2019.10.25
文:⛱️、🦆、乌尔姆动物园
编辑:不不
图片:蒋三
文稿录音整理:Nullepart、蒋不

上半夜——内战导论 /⛱️
⛱️:我想通过最近听过比较多的两种对于香港问题的论调及其反驳来进入主题。
1、经济问题是香港问题的根源,如果经济弄好了那么问题就全解决了。但是这一观点基本上经不起推敲。因为很简单,欧洲这样的更加平均化和发达的经济体也没能停止暴动(看看去年的法国,现在的加泰罗尼亚还有智利就知道了)。
2、经济决定论破产之后,就会出现另一种理论:历史阶段理论。这一理论承认,经济水平或分配水平和暴乱之间没有关系。但是要区分不同的暴乱:在某一个历史阶段,暴动是合法的,因为它带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而在另一个历史阶段,暴动是非法的,因为它纯粹在捣乱。比如,法国大革命和中国1949年以前的革命是合法的,而香港或者很多当代的革命就是不合法的。但实际上,如果不能接受现在的社会运动,那么自然也不可能接受法国大革命这样的运动。为什么呢?这就是今天我想谈的一个主题:即无论是过去还是当代的社会运动,它们皆不是为了达到任何所谓的历史目的或具体目的而发动的,换句话说,它们都在“捣乱”。如何理解这一点?我首先引用Kant的《Le conflit des facultés》(《系科之争》)中一个著名段落,这的段落比较著名的引用是福柯在一篇名为《Qu’est-ce que les Lumières ?》的文章中的引用(福柯有两篇《Qu’est-ce que les Lumières?》的文章,讨论Kant这一段的那一篇没有被翻译成中文),这个段落Kant表达了自己对于法国大革命的看法:
« Peu importe si la révolution d’un peuple plein d’esprit, que nous avons vu s’effectuer de nos jours, réussit ou échoue, peu importe si elle accumule misère et atrocités au point qu’un homme sensé qui la referait avec l’espoir de la mener à bien, ne se résoudrait jamais néanmoins à tenter l’expérience à ce prix. » (翻译:无论这场革命成功还是失败,无论它充满着多少悲惨和恐怖,以至于一个理智的人如果抱着实现它的愿望再次进行尝试,就决不会以这样的代价进行这场实验。)
我们注意最后一句话:为什么一个想要达到这一目的的理性人不会再去进行这场实验?很明显,这暗示着:不是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达到这些目的,也许还有其他更好的方式,所谓更好,就是代价更小、更经济、更快捷的方式。因此如果我们更重视那个目的的话,就不应该仅仅拘泥于“革命”这一种手段。所以可以说,革命在这里被证明是一种对于目的拖延,甚至是摒弃,或者说,纯粹捣乱。
但在这里我想提醒一点:Kant并没有像一个保守主义者那样批判法国大革命,这一点我们随后会看到。
Kant对革命的看法在它之后以及当代有很多呼应,在这里我想举两个比较经典的例子。
1. 第一个例子比较当代。高盛集团曾经做过一个模型(债务免除和宏观经济的收益之间的关系),这个模型的结果就是,如果给负债者(例如房贷负债者)免债,那么经济收益从长期来看是增长性的。换句话说,免你的债比逼你还债对宏观经济更有利(比如考虑到社会运动的治安成本和它的暴力性对经济长期的影响)。其实理解这一点也无需高盛的模型,从另一个角度,即古代文明的大赦制度就可以看出来,大赦制度就是为了解决周期性社会危机而采取的制度。因此一个以经济为目的的社运团体在此时最好的做法就是将斗争限制在一定程度,以敦促资本家作出让步,同时遏制激进派将斗争进一步升级到革命的企图。为什么呢?因为激进派对UBI是持批评态度的。可以说,免债是UBI的一个变种。我们知道,现在的大资本家都是UBI的支持者,例如扎克伯格和伊隆马斯克,它们支持的理由和高盛的理由是一样的。(更多问题就不展开了,关于大资本家对UBI的支持态度,以及一些激进学者对UBI的批判,可以参考这一文章:Against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 Ben Kunkler)
2. 第二个例子有关德国社会保障制度。1880年,德国总理俾斯麦提交了一份议案:在法律上定义社会主义运动为非法。之后,他立即引入了社会保障制度,从此进入了现代福利国家的第一步。可以看到,他与资本家的共同点在于支持引入某种福利制度,然而不同点在于,他禁止了社会主义运动。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他清楚地知道,社会主义运动的真实目的根本不是它们口中所呼吁的东西,就算福利制度被建立起来,他们还是会没完没了。
俾斯麦或者康德的这一洞见在当代的文学对应物是什么?那就是反乌托邦文学,其中比较典型和直接的就是黑客帝国。其中Matrix可以说是国家福利制度所能达到的终极版本,然而在其中依旧有人感到不满,要搞革命……
我想重新强调一下基本论点,然后结尾:革命是一种对目的的拖延,甚至是摒弃和捣乱。那么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得到另一个结论:革命之后秩序的重建(无论是走向新秩序还是复辟回旧秩序),都意味着革命的失败。法国大革命之后的世界就是法国大革命失败后的世界,而非它的革命果实。此外,如果一个人认为现在的社会运动是在捣乱,那么它也有必要认为过去的社会运动也是在捣乱,这样逻辑才是一致的。
还剩最后一个问题:革命者究竟不满什么?革命者究竟想要什么?
在这里有必要回到刚刚Kant的段落,他接下来非常激昂地说道:« cette révolution, dis-je, trouve quand même dans les esprits de tous les spectateurs (qui ne sont pas eux-mêmes engagés dans ce jeu) une sympathie d’aspiration qui frise l’enthousiasme. »
在Kant那里,革命涉及一种”enthousiasme”。我想提请大家注意,Kant的这个选词不是偶然,这个词源于希腊语,在希腊语中“en-thou-siasme”中的thou这个部分即theós,意为“神”……我知道一讲到神大家就想睡觉,我就不继续了。这个更为重要的问题(革命者究竟想要什么?)如果有机会,明年继续聊。
现场讨论
- 🐔:关于福利和UBI的问题,这是一个立场的矛盾。假设说一般意义上的激进左派批评福利制度,不要福利制度。这个问题同样可以提给齐泽克。齐泽克说得很清楚:“最坏的奴隶主是对努力最好的奴隶主。”因为他们会完全打消奴隶的革命意愿。但当我们从理论的角度回到现实,这个问题就变得很奇怪——比如你和一个普通法国人或者一个有某些社会需求的人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一个人告诉他,我们每月给你更多的工资更好的福利,另一个人告诉他不要,不要这种虚假的生活。你越惨越好,最好惨到一无所有。等到你真正一无所有的时候,你就会革命,就会挣脱所有的锁链。但在现实中这其实是一个很矛盾的立场。
- 🐦:UBI不是一个哲学问题,更多是一个社会问题,可以从三个角度思考。一个是UBI可能导致的结果是零工经济和不稳定就业,一个是UBI是否会取代社会保险和福利制度?将政府的责任转嫁给了公众,我们拥有UBI之后,社会保障是否会被削弱?最后一点在于,毫无疑问UBI一定是有国界的,如果在美国或者北欧实行UBI,这对全球化生产体系里被剥削的南方国家是否是一个不平等的问题。
- ⛱️:我想回应一下🐔说的有关贫困的问题。激进左派并没有简单地认为贫困和革命之间有着必然联系,而是看到了一个很明显的事实——贫困和重大革命之间没有任何关系。《黑客帝国》这部电影就很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Matrix整个系统里面大家都活得非常好,但是依然有人想要革命,革命和贫困没有任何必然联系。
- 🐔:这里提到了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内战,第二个是捣乱,第三个是革命。你说革命和贫困没有必然联系,这个立场我同意。但更多的问题是,当你在谈捣乱本身的合法性,它的目的是否是为了实现某个特定的东西?或者只是说“造反有理”?我认为我们应该区分革命和一般意义上的动乱,或者说区分不同性质的革命。一个法西斯主义的群众运动和一个共产主义的群众运动应该有本质上的区别,这就回到了一个非常经典的对二十世纪革命历史的批评——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实践本质上是无非是一个群氓的运动。
- ⛱️:你说的需要对不同革命作出区分我很同意,但是在这里我的重点是使用另外一种范畴——“混乱”和“秩序”——来进行划分,在这个划分中,革命后的法西斯主义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同属于“秩序”。
- 🐱:我觉得你完全陷入了一种形式主义,你谈论秩序与非秩序,把革命当作一个空洞的词语,一种形式上的反抗。但没有考虑到革命究竟带来的是什么,究竟在哪一种历史条件下反对哪一种制度。我们不能空泛地谈论革命,斯巴达克斯和法国大革命是一样的性质吗?你恰好陷入的康德的错误——用哲学去谈论政治——没有尊重政治本身的独立性,列宁说“革命是什么?革命就是两个人打架,你无法确定哪一拳是必要的,哪一拳是不必要的,把他打倒就行。”我们在讨论政治问题时,不能用哲学的视野,我们只能把他打倒,如何最快达到我的目标,而不是精确地计算哪一拳把他打倒。革命不是势均力敌的两个人进行对打,革命是从无到有的过程,要把一切推到顶点。
- ⛱️:康德的意思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需要大革命,法国就可以进入革命之后的世界。但他没有说进入那个世界不需要政治斗争。他是认为法国大革命这样最极端的斗争对于形成之后的世界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法国大革命的收场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如果让其中的每个人反思是否要通过革命抵达它之后的那个世界,可能很多人不会选择革命。把革命推到顶点,把混乱上升到最大的时候,这个目的就摇摇欲坠了。
- 🐱:法国大革命的目的和其实际行动就是不相吻合的,包括人人平等和一些普世价值,本身就有其激进性在里面,所以法国大革命必然达不到它的目的。我们不应该讨论革命的形式,而应该讨论革命的内容。
- ⛱️:但是法国大革命之后法国的社会内容的确发生了改变,而达到这样的改变无须法国大革命。
- 🦆:在康德、黑格尔这样的德国观念论看来,革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不需要这么血腥。
- 🐔:不需要法国大革命就可以达成这种变化,这只是康德的观点,但不能上升到通论。至少作为一个历史观点我是不同意的。如果你以“混乱”和“秩序”来做区分,那么想要的是否是一种无限的、永久的革命?
- ⛱️:我只是用混乱和秩序的这样的范畴来进行历史的观察,并没有倾向性,二者也许都会存在。如果用一块布象征着长久的秩序,而革命就是在上面打的几个洞,而这些洞又会反过来被秩序所吞没。
- 🐔:革命之后,总要建立一个我们更想要的秩序,如果没有的话,可能这种观点就更偏向无政府主义。法国人天天上街,大家很高兴,天天跳舞唱歌喝酒扔燃烧瓶,齐泽克问的一个问题是,“那明天早上呢?”,尤其在当今资本主义形态的运作下,所有的游行都变成了有限游行,要么是讨价还价的谈判,要么是群情激愤地发泄一下不满情绪,第二天生活照旧。齐泽克一直想要的是改变第二天的日常生活。重要的不仅是革命这个洞,而且还有打破旧布之后的新布。
- ⛱️:我想引用一句德里达的话来回应你——所有文化都是殖民。
下半夜——例外状态与全球内战 / 🦆
🦆:你的这个入神搞得我有点上头。我得冷静一下,避免再次神棍化。
其实⛱️的演讲是个很好的内战导论,起码提升了政治的独立地位,政治关涉到一种最强程度的紧张,即区分敌友。其他领域的紧张到达一定程度,也就变成政治的了。但经济、道德、审美的紧张与政治的紧张不可同日而语,政治关乎生死。就让政治的归政治,经济的归经济。
既然政治是区分敌友,就有必要引入阿甘本的内战学(stasiologie),即通过内战来理解政治。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城邦是家庭的放大版,但他没有解释家庭生活(oikos,economy)关乎的肉体生命(zoe)如何形变为公民的政治生命(bios)。城邦内战是一种在家庭和城邦、血缘和公民权之间的界限,通过家庭政治化(极端形式就是杀兄),血缘的fraternité变为挑选阵营的政治的fraternité,政治化得以完成。在索伦法中,内战中没有选择阵营的人是要被剥夺公民权的。问题在于内战如何平息?通过一种城邦的家庭化,即去政治化,通过遗忘(amnestie),不审判,不归罪,血迹被时间清除,城邦重归安宁。这是古希腊人的美德,即承认政治立场相反的人不是十恶不赦的恶魔,而是平等的值得尊重的对手。左派施米特主义者尚塔尔墨菲就用agonistique(agora广场)来弱化施米特的敌人概念,在这里,敌人是私敌(enemy)而不是整个族群一起面对的公敌(foe)。schwarb这么解释旧约中的一句话“爱你的敌人”,是爱你的私敌,即犹太同胞。
那么香港作为城邦,毫无疑问正在进行内战,如果不考虑地缘政治因素,内战胜负早已定局,新的和平会产生。但香港问题特殊性使其无法决定自己的政治命运。
阿甘本在解释现代主权国家奠基性文本《利维坦》的时候,同样使用了内战学。霍布斯区分了populus和multitudo,前者是有单一意志的政治人,而后者是诸众,前者是主权者(souverain或者assemblée),后者是citoyens。那么诸众如何政治化呢?阿甘本画了一个循环:multitude désunie(立约前的自然状态)-populus/rex-multitudo dissoute(立约后,公民再次解散成为诸众,但是和立约前的诸众不同)-guerre civile-multitude désunie(回到自然状态),因此,霍布斯的国家并不是牢不可破的,一旦主权者无法照料好民众的salut,是可能回到内战,即自然状态中的。
如果不考虑地缘政治,香港的情况就是,原先的主权者-议会结构已经失效,新的主权者正在形成。我们可以顺便思考一下全球民粹政治崛起的现象,显而易见,这是一场代议制的危机。主权者-议会-政治人三者之间的纽带已经很脆弱,即议会作为中间机构很难传递政治人的意愿,政治人的行动,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是在唤醒主权者。
香港问题牵涉到太多因素,我们必须引入全球内战的概念。古典内战是在一定框架内进行的,比如确定的战斗场地、区分战斗人员和平民、提前宣战等,这样可以确保战争规模在一定限度内。如果把主权国家当作战争主体,那么古典欧洲的主要战场其实是在殖民地。和无主之地最配的就是anomie!那么anomie都被引到了无主之地,欧洲主权国家的法权建构(nomos)就得以实现了。现在的问题是,已经没有无主之地,相当于没有战斗场地,anomie无处安顿,就会和nomos混淆,在全球无区别地展开。全球内战不区分场所、不区分规模、不提前宣战。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恐怖主义、信息战、经济战。和平与战争的阶段性更迭已经被无时无刻无孔不入的战争状态,即渗透进生命政治之中的全球内战所取代。香港的案例除了作为城邦的内战,还必须被理解为一场全球内战。
怎么办?只有找到一块全新的无主之地,飞向太空,星际殖民,把anomie引到那里。
内战与例外状态具有同构性。内战是把非政治型构为政治,而例外状态是把无法(anomie)型构为法(nomos),我们可以用例外状态来分析香港的情形。在古典时代,例外状态只是一种临时状态,当罗马遇到紧急情况,执政官会被授予特权,不在法律框架内行动,但是紧急情况一旦消除,这一委任的独裁权也随之撤销。也就是说,罗马时代的例外状态并不产生新法,只是对其临时悬置。现代的例外状态是民主革命的产物,法国大革命后,例外状态逐渐变成了立新法的机制。如何操作?经典案例是纳粹德国,在德语中,例外状态叫Ausnahmezustand,aus代表排除,ahme是nehmen(拿)的名词形式,排除和拿两个概念看似矛盾,但正是通过这一排除性纳入的机制,旧法被(悬置),比如保障人权的宪法条文,与此同时新法被树立,这种新法的形式多为反人权的条例,参考911之后的爱国者法案,以及近期香港的反蒙面法。通过这一机制,例外状态情况下的无法anomie变为nomos,用本雅明的话来说,例外状态常态化了。
例外状态原本是为了被动抵御威胁,在生命政治的时代变为了主动预防。比如为了防止恐怖犯罪或是防止分裂国家。有一点我一直怀疑,反分裂国家法究竟有没有合法性?法律能否惩罚意图而不只是行为?恐怖主义真的能预防吗?还是说法治国为了自身的权威,需要制造出恐怖以确认自身的合法性?阿甘本在le monde上发表的《从法治国到安全国》,对此做出了否定的回答。
如果联系上次演讲提到的《暴力批判》,例外状态的立法功能和立法暴力是一致的。立法完了就该护法了,最可怕的是立法暴力和护法暴力混淆不分,比如警察的滥权。那么有没有机会逃离例外状态的暴力?我们重新阅读一下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第八条:
被压迫者的传统告诉我们,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所谓“紧急状态”并非什么例外,而是一种常规。我们必须具有一个同这一观察相一致的历史概念。这样我们就会清楚地意识到。我们的任务是带来一种真正的紧急状态,从而改善我们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地位。法西斯主义之所有有机可乘,原因之一是它的对手在进步的名义下把它看成一种历史的常态。我们对正在经历的事情在二十世纪“还”会发生感到惊诧,然而这种惊诧并不包含哲理,因为它不是认识的开端,它还没有认识到它由已产生的历史观本身是站不住脚的。
什么是真正的例外状态?即一种脱离了关系,脱离了具体诉求,脱离了立法尝试的状态。从这一点看,香港的革命行动,意图砍下主权者的头,是为了另立新头。无可厚非,林郑作为前主权者可以决定例外状态(反蒙面法),内战中的新生成的主权者也可以决断《马鞍山宣言》,主权者就是决断例外状态,问题在于谁是主权者。
但是这一革命仍然没有脱离历史,或者说是不彻底的,因为它有具体的五大诉求。哪种例外状态是真正的例外状态呢?只唱情歌看不到坦克。六四总体上来讲只有抽象的民主自由诉求,并非争夺权力或立新法,这是一种抗拒国家体制本身的行动,用激进左派的观点看,这是纯粹的革命行为。但是,弥赛亚还迷失在如墨的夜色中。用阿甘本在《将来的共同体》最后一句话总结“无论何处出现这般和平展示他们的共同存在,就会有天安门,而迟早坦克将出现。”
现场讨论
- 🐱:阿甘本的观点认为五大诉求太具体了,因此丧失了革命的性质。五大诉求中最重要的就是“双普选”,“双普选”是否就是要重新找到主权者?阿甘本很悲观,是因为他认为香港人们没有重新立一个主权者。
- 🦆:我解释一下,香港人民的“革命”行为,是为了去掉林郑这个旧有的主权者和旧有的议会,而去形成一个新的主权者,但这仍然是在历史之中, 仍然是一种通过例外状态进行的立法行为。激进左派会认为香港的革命不彻底,仍然在历史的漩涡中进行暴力的循环。政治是人与人的关系,所谓的解放所谓的革命,就是没有政治。
- 🐔:这种东西设想都无法设想,这是一种都不用批评的纯乌托邦。
- 🐟:阿甘本就是这样,把余民的两种制度都破坏掉,变成非余,非余民和余民竞争,出现非非余民。有点类似德勒兹提出的游牧的概念。我认为阿甘本对香港问题应该持乐观态度。
- 🐔:我认为游牧和定居的核心区分,是动还是静的问题。定居是一种很稳定的状态,政治上对应着一种确切的政治状态,德勒兹的语境中在讲欲望的问题,欲望是被编码的——比如你每天都想喝雀巢的咖啡,浑浑噩噩地过完一生。所谓游牧,要走出既定的领域,也就是走出territoire,产生新的欲望。
- 🦆:我可以用另外的方式来解释一下。法这个东西是nomos,按照施密特的理解是从德语的动词nehmen过来的, nehmen是拿,占取,占取一块领地,定居下来,设立围墙,就是立法。Utopie就是无topos,无疆域,呈现一种游牧的状态。
- 🐱:我反对极左派认为革命之后就没有政治的说法,只是部分极左派这么认为。包括列宁、托洛茨基、阿尔都塞都考虑过在共产主义中的政治,政治是否有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是否能独立于阶级斗争本身,是否存在一种在阶级斗争之外的政治?在共产主义之后是否还有政治?比如去火星的政治,比如科技进步的政治。极左派之间也有不同的观念分歧,是否可能存在一种与阶级斗争无关的政治?
- 🦆:我是用历史终结论来理解解放的,历史终结之后就没有政治了。你所说的科技的政治是政治吗?科技需要区分敌我吗?那是一种游戏而不是政治。
- 🐔:什么程度才叫敌我?如何界定一个人是否是敌人?
- 🦆:这是公敌和私敌的区分,在同一个城邦里我有私敌,我是平等主义者,对门是民主主义者,我们广场上吵一架打一架就完事了。公敌就是城邦的敌人,比如波斯人,需要肉体消灭的才是公敌,这是对立的强度问题。如果你是一个世界主义者,没有敌人,但如果现在还是主权国家的话,当然存在敌人。
- 🐔:我今天来有一个很个人的目的,我很好奇施密特左派到底是什么主张。(笑)当你讨论“敌人”时,你的核心概念是疆域或者城邦,按照施密特的观点,对立总是回归到两个共同体之间的对立。我不赞同这种地缘政治看问题的视角,我认为真正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如果把阶级矛盾转化为国家矛盾,希特勒屠犹就是可以理解的。
- 🐔:我们来梳理一下,公敌的问题是共同体对立的问题,私敌可以有观点之间的对立。我和🐱的观点是真正的矛盾在于阶级对立,这是马克思的观点,也是所有左派的观点。如果你把所有的公敌都用私敌的方式来理解,那你把阶级矛盾放在什么地方?
- 🦆:我给共产主义扒个皮,施密特认为,包括我也这样认为。共产主义提出的阶级敌人的概念就是公敌,启示录级别上的公敌,要在肉体上消灭,所以共产主义是很危险的。
- 🐔:马克思说我们要消灭资本家,从来不是因为资本家是个坏人。我们可以和资本家关系很好,但是政治意义上的敌人。革命有它残忍的一面,《毛选》上来就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一点不构成对马克思主义根本上的批评。我们和施密特左派的观点分歧主要在于敌我关系的基本界定,到底是共同体对立还是阶级对立。
- 🦆:左派施密特主义者认为,应该限定公敌的概念,把公敌引入私敌。
- 🐱:并不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发动战争,而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发动战争,问题在于,你不能只看无产阶级发动革命杀了沙皇一家,同时也要看沙皇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伤害了多少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战争已经持续几百年了,无产阶级被迫自卫。民族国家的和平是虚伪的,其实内部有剥削和战争。

自由讨论:
a-大家觉得香港的民族发明学是否能够成立?
b-我觉得港人并没有太强烈的欲望,比起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国家的话,除了少部分勇武派。
a- 但是如果看民调会发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b- 民调对警察和政府的信任下滑崩溃,并不是说他们要将香港变成一个新的民族。
c- 我认为很难,以台湾为例子,台湾民族论有一定基础,作为一个亚细亚孤岛,长期殖民历史(葡萄牙到荷兰到日本最后到国民党),但是香港实际上如果我们回顾的话,英国殖民政策和法国不同,法国是要将阿尔及利亚完全变成法国本土,强力推行法制东西。而英国不同,参见澳大利亚,倾向管理好一段时间再交回去,黄之锋在柏林说“将渔村看做是新冷战时期的柏林”,实际上在上世纪冷战期间,香港也是小的冷战秩序聚集地。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香港人,或者说更早南派文人的移民就已经有过这种体验。总而言之,香港受中华文化影响很深。我认为中国可以用儒家思想来团结香港,儒家中存在着民主思想,过度的自由资本产生了例如房价涨高的问题。此外香港的独立是在逃避作为中国人的责任,有时候讨论民主不代表真的民主。
b-最大的问题就是这种民族主义。任何跟随民族主义的运动最终会失败。站在民族主义的角度上的运动是最容易定义的,其中会出现很多民粹或者大众运动的右倾。帝国主义最根本的是从民族主义开始,Francois Fanon有讨论到面对某一种法国的殖民主义我们要如何抵抗的问题,他是说在一种communauté 在opérée的情况下如何抵抗,而不是大一统的观念——比如我们如何壮大中华民族,这个简单的论调非常容易导向右倾。关于儒家问题,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统治者都想用儒家思想都想用来做道德的标志,从这个方面看是有问题的,如同天主教曾经提供给西方社会那样。教条式的的价值评判体恤比如现在中国的信用制度系统,就是要用这个价值去合理化整个系统,他们说要重建我们的道德。我们不能总是s’adopter儒家价值。
c- 你是用西方哲学讨论社会问题,那么是否可以提一个方案出来?另外不能将共产主义和儒家搞混,前者在偷换概念,如果真正了解儒家的话是能发现民主的概念。
b- 并不反对这个概念,或许有这个可能,但是从一般情况来说,一般来说我们将一种思想和社会形态放在一起是非常危险的。
d-关于solidarité以及在Nantes和Paris在法港人活动的问题,我的疑惑在于现在香港人更多希望和西方极左派进行联合,还是和普遍意义的左派?目前看到更多的是法国的anarchistes在支持香港的活动,难道欧洲的左派看到的是一个滤镜下的香港?潘毅老师认为香港应该和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进行一个联合。
b- 确实存在着不知道如何跟所谓被压迫的大众中国人交流的问题。被压迫的有几个层次,其中一部分majorité silencieuse,受到所谓传统的家庭制约,是不能出来反抗的,当他们不得不反抗的时候已经没有战友了。但是大多的是感觉到无关的人,这种人是很难动员的。
香港的分离分子是一种réaction,action是中国政府的爱国教育。香港分几代人,比如80后,90后,两代人是所谓的大众化一代,为什么他们说自己是香港人而不是中国人,因为受到的压迫太大了。这不是一个作用力而是一个反作用力。和老一代不同,老一代他们有一种虚荣感,自己在大陆生活过,现在大陆不一样了。而70代之后的人就不同了。中国政府并没有能抓住(机会),他只是想统治。所以被压迫的时候,香港人为什么要承认自己的中国人身份?和很多移民到香港的大陆人交流(雨伞运动之前),我会产生一种沮丧感,他们已经在发起一种爱国运动,我们能观察的到,他们并不是在说一些民主问题或者不正义问题,他们很难沟通和合作。
d-因为有朋友在香港,所以有时候的印象是,在港的大陆人在参与运动时会有被排斥的感觉,一般来说运动的步骤是论述-组织-行动,但是现在的香港更注重于的是行动,在论述和组织上会有缺陷(去中心化),当我们只注重行动的时候,可能会伤害运动的效果,导致很多大陆人难以参与的感觉,找不到自己的声音。
b-最初香港的前线是欢迎内地的学生的,但是操作上,会出现所谓的五毛装作支持派进运动然后闹得很不愉快,几轮之后,就很会引起疑心。他们(香港人)在用一些方法去识别参与者是否是间谍,所以仍然是action/réaction的问题。“我支持但是共产党也有自己的难处…”这类说法香港人会很反感。
d-我们sans frontière的左派应该如何行动?
e-关于叙述和叙事的问题,我发现我们存在着叙述的断裂,我说的是审查之外的问题,叙述本身的问题,比如在微博,香港问题和粉圈文化有紧密的联系,这一文化把国家拟人化了——你需要承认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一旦将民族主义和粉圈文化联系起来,会成为一个非常有利的生产方式,因为他会生产——让国家和人民之间产生联系。虽然我们鄙视这种叙述方式,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模式分布的非常广,那么问题在于如果我们不赞同这种叙述方式,我们能够寻找到一种有效的新的叙述方式?
f-现在自由主义的办法或许不适合后现代主义的叙述方式,是无法反抗中共这种propagande的叙述方式的。
g-但是这个的确非常的有利,从结果上看的话,也不得不承认它很成功,也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
a-这个问题回到刚刚讲的内战学的政治化-去政治化。因为阿中哥哥、祖国母亲这种话语,是家庭话语,本质上不构成政治。家庭和政治之间的流动变换如果被阻塞了,政治问题就会家庭化。
b-关于香港人的政治倾向:在香港有分左派(亲共的)和左翼。左派的没落是和欧洲的右转的开始时间相互吻合。有左翼的倾向有各种流派,从近期的来看,大部分可能是apolitique或者反资本家的,关于极右派,黄毓民是想要在选举中壮大他在本土的声势,但是他失败了,毕竟他自己都是新移民,后来又更多本土派的人已经不相信本土化,更类似美国的apotilique。
d-左派在国内已经失去自己
h-至少在大陆,左翼是没有任何话语权的,这可能是和香港的区别,在香港是有力量的,大部分的左翼都是中产阶级,他们是有分量的。但是在大陆媒体上根本看不到一种左翼的发声,这是一个很悲观的观察,从粉圈文化到报刊媒体,激进型的法国出版物在国内其激进型会被消解掉。
e-我们可以想象苏联的厨房异见分子,和你在厨房谈论政治的分子可能转眼就举报你。这是一个历史上出现的情况,和叙述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有一种可能的写作/发生方式,至少是一个最低程度的反抗方式?在苏联一段时期内甚至阅读也是一种政治行为。
d-从去年开始,很难有效的在大陆建议一种有效的左翼的association,比如做女权,或者农民工教育的,政府会非常严格的审查他们的经济来源,是否有接受境外资助。但是国外比如福特公司,他们本身就是有对于民间组织进行资助的传统的。
h-国内左翼学术也是很奇怪的,比如激萌团体(公众号),是真的存在一种人喜欢这种酷炫隔靴搔痒的写作,所谓看的和写的对不上。
b-回到民族论,我们是否要区分民族主义和本土主义,民族主义首先是一个现象,他要求一个相对完备的经济结构,是否有可能香港进行一种民族论呢?毕竟香港存在对外的经济依赖问题,这种情况下如何进行一种独立论述呢?是否比中共崩溃更加困难呢?
乌尔姆第三夜:2019-11-11
主题:”监控社会与数字集权“
上半场:主题演讲
演讲人:诡谲子,Jacque
下半场:自由讨论
未来讨论活动,主题开放,不限学科,由参与者共同讨论决定。活动目前限于巴黎,想要参与活动或加入我们团队请联系小乌尔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