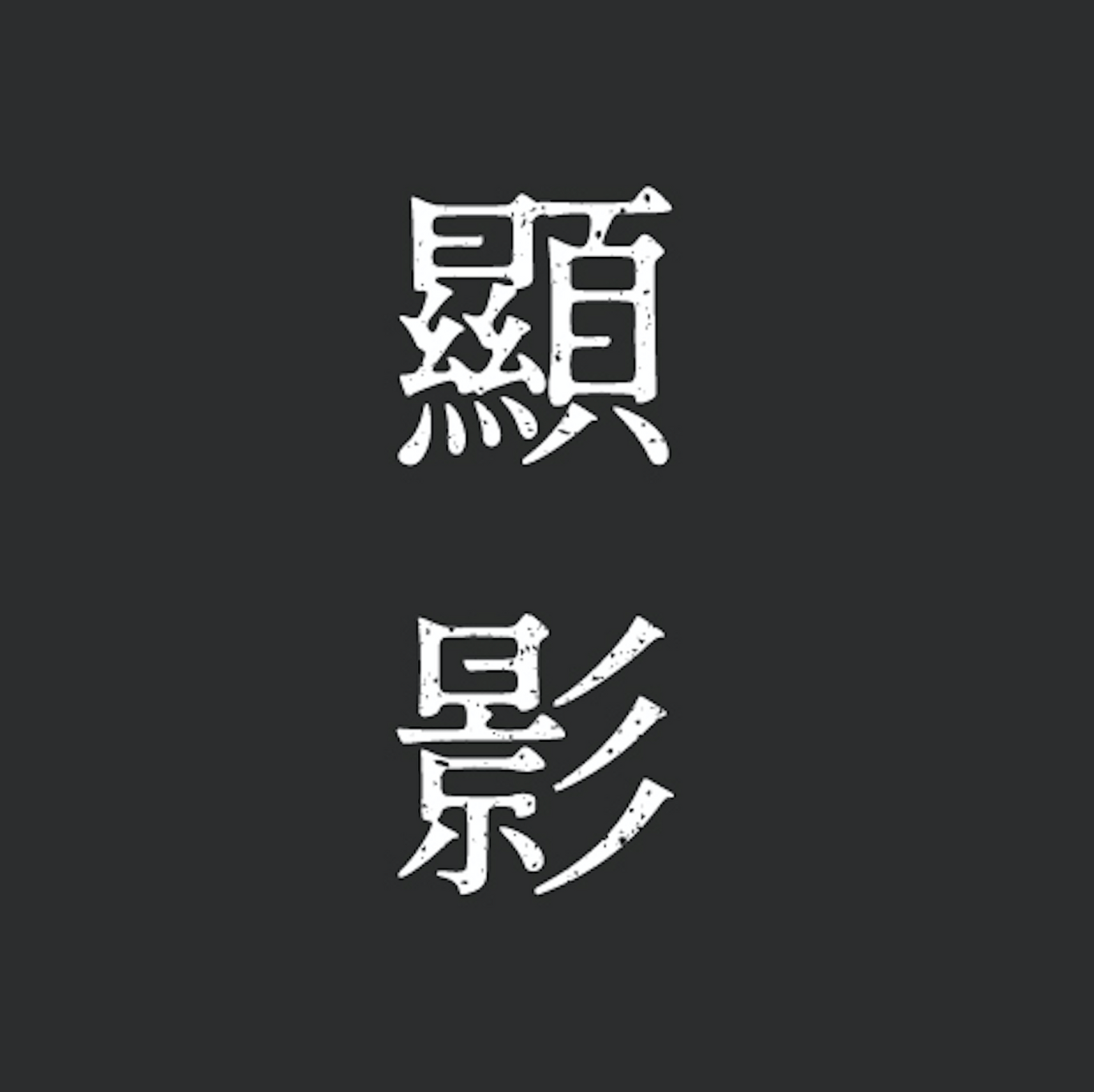【電影人系列】侯孝賢的武俠視野
筆者任職雜誌及報社近十年,雖說不是主力撰寫電影及娛樂人物文章,但因工作關係也訪問過一些導演及演員。換過幾份工作、也換過電腦,才發現有些多年前書寫的訪問文稿早已遺失,縱使不是妙筆生花,也着實可惜。
去年侯孝賢導演獲得台灣金馬獎「終身成就獎」時,已有舊文重溫的念頭,所以最近也想藉着Matters這個平台,分享關於電影人的訪問,以【電影人系列】統稱這些文章,當作一個整理或記錄。首先分享的是關於侯孝賢的訪談,2015年他到香港宣傳《刺客聶隱娘》,文章刊於蘋果日報副刊。

曾經,台灣導演侯孝賢笑言自己拍攝的電影沒一部完美,即使獲得威尼斯影展金獅獎的《悲情城市》,也僅以「爛片」來形容。如今,《刺客聶隱娘》(下稱《聶》)上演在即,他一改口風說終於有勉強完美之作,還有所期待。「假使這個片子賣得不錯的話,我還想拍多一部古裝片。我比較喜歡唐朝,因為《唐人小說》裏的故事很多,這個成功了,下一個找錢也比較容易,容易就可以再拍。」
記憶還停留在侯孝賢在康城得獎後,他一身西裝、戴着煲呔見記者的場面,所以當看到一身牛仔褲襯白T恤黑風褸的導演時,忍不住定了睛,畢竟這種樸素的風格,才更像真正的他。一向少做訪問的侯導,當天卻一口氣接受了七、八個訪問,他亦毫不掩飾,直認不諱:「我去歐洲以前也很少宣傳,主要是因為這個片子在康城得獎,很多地方都買了版權,影片上映就要你去宣傳。你說去不去呢?不去也不行。」原來,大導演也有無奈之時。
侯孝賢是一位很真的人,於電影,是種真實感,時代的背景、角色的狀態,他務求自然寫實,做到盡善盡美,八年磨一片拍攝《刺客聶隱娘》,用數年時間籌備資料、劇本前後易稿三十多次,為的正是更好地還原唐代背景。於個人,是種坦誠,他不羞於談起過去時常打架的壞孩子經歷,也敢於向社會不公發聲。聊起「台灣高中歷史新課綱」淡化二二八事件一事,他有所感觸說:「人,不能夠隨便殺人。」1989年,解除戒嚴後他的首部電影《悲情城市》講的正是這段歷史,透過一個啞巴角色為台灣鏗鏘發聲。「我感覺最終還是會還原歷史,該是鎮壓就是鎮壓,逃不掉的,不用刻意掩飾。」
回到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年,他生於廣東梅縣,出生翌年被家人抱到台灣,這段國民政府軍隊鎮壓台灣人民的歷史他沒有親身經歷,之後讀書才得以了解,得悉真相後很憤怒,最終以一部《悲情城市》來直接挑戰當時台灣社會的禁忌話題。「我的想法是人不能為任何目的殺人,包括政治,任何國家也不能隨便侵略別的國家,絕對不能。」

「人不能夠隨便殺人」
26年後的這部《聶》,理念仍如出一轍。聶隱娘自小被道姑訓練成殺手,先是因為有小孩在,動了惻隱之心而不忍殺人,後則因怕殺一人而天下大亂,選擇捨身取義。侯導想呈現的世界不是武俠片裏的江湖俠義,而是「人不能夠隨便殺人」。刺客殺人猶懂得要有名目,不能淪為執行任務的工具,當權者又何以不明白?「《聶》基本上是一個刺客不能殺人,最終了解自己的過程。」
未讀懂侯導的人,或許會認為他口中的「真」永遠充滿矛盾。一個不主張殺戮的人,卻拍刺客武俠片;喜歡寫實,卻從芸芸唐代武俠故事中,千挑萬選情節神怪的聶隱娘。原來,侯導早有拍武俠片的想法,小學五、六年級開始愛上武俠小說,之後看日本的武士道影片,甚至在《讀者文摘》追看《教父》小說。他的武俠世界觀不是少林武當,而是更寫實的歷史背景。「讀藝專時看了《唐人小說》,覺得聶隱娘這個刺客很有意思,聶是三個耳朵,是隱藏在樹上聽聲音的,就想把這個結合唐代背景來拍。」想法醞釀許久,直至遇到舒淇,一位從《千禧曼波》到《最好的時光》一直合作的演員,小說裏的聶隱娘,終於有了人選,《刺客聶隱娘》也慢慢水到渠成。
《聶》收錄於唐代文學家裴鉶的短篇小說集,原文只有1,700多字,有不少神怪奇異的情節,如其中一場打鬥戲聶隱娘變成了一面旗幟。追求真實感的侯導覺得沒說服力,就把整個故事改編了,幾乎成了原創劇本。「我覺得還是要符合真實情況與歷史背景,所以把後面的情節都捨棄了,只保留聶隱娘被道姑帶走的情節。」最後的劇本基本上與原著迥異,是侯導在研究小說之後,把《新唐書》、《舊唐書》、《資治通鑑》等書中的相關內容找出來,然後在這個框架裏,與朱天文、鍾阿城兩位編劇慢慢整理出來的。
傳統的武俠片,千軍萬馬、飛簷走壁,打鬥場景你來我往驚心動魄,《聶》裏只有很短的寥寥數場,難免有人大呼不過癮。「刺客都不是光明正大打來打去的,不是正常武俠片那種打法,都是在一個地方埋伏刺殺的,《刺客列傳》裏都是這樣。」侯導冷靜解釋道,答案似乎已重複多次。他從小對武俠片的夢想,原來不是童年經歷的打打殺殺,而是一種以靜制動的人生沉澱。

「經歷是活過的痕迹」
侯導善於用獨特的電影語言訴說情感,是現實也是個人經歷的反映。早期的《風櫃來的人》、《悲情城市》、《南國再見,南國》,是他審視台灣歷史及個人經歷的代表作,電影中的打鬥場景,源自他的自身體驗。「小時候住在(高雄)鳳山,以前有角頭,就是地方的聚落,那時候常打架。」他說男生喜歡耍酷,動不動就打架,單打獨鬥、群毆都試過,警察都記住了這個壞小孩。那時候他愛看武打片,尤其日本武士道影片,《里見八犬傳》、《三日月童子》、《宮本武藏》等,奇連伊士活(Clint Eastwood)的西部片也看,如《荒野大鏢客》(A Fistful of Dollars)。「男孩都喜歡看打鬥的,比槍決鬥的,日本就是武士道。因為武士道一直仍在,拍起來比較真實,所以喜歡看。」
高中沒畢業,侯孝賢跑去服兵役,服完兵役回鳳山還因有案底差點被抓去管訓。之後輾轉到台北的藝術專科學校讀電影,由場務做到導演。匆匆數十年,贏盡掌聲與名譽,他反而覺得自己最好的時光是那段渾沌的日子。「感覺那段時間甚麼都不懂,對很多事情都好奇,看小說看電影打架服兵役,經歷了很多事情,加上家庭的變化,父母祖母去世,都是那段時間。這段時間是我成長當兵之前的一個了斷,這段經歷對我很特別,其實就是面對自己,逃無可逃。」
這份真性情,對應《聶》中的寫實:風來了吹動紗帳、光線曼妙變化,在破舊木屋裏用鐵鍋煮湯及取暖,他為重現唐朝生活質感做了許多考究,點點滴滴都在創造出真實生活的感覺,正如與過去經歷赤裸裸地面對面,逃無可逃,都是生命中活過的痕迹。

後記:文字訪談vs影像Trailer
侯導說若沒有童年那段閱讀的經驗,不可能有今天這些影片。「閱讀的影響很大,如果沒有養成閱讀文學的習慣,可能就會停留在某個階段。」他看孫中山傳記、看馬奎斯的《百年孤寂》、看卡爾維諾的《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文字是有結構、輕重的,影像其實也是一樣的道理。」
說起文字,他忽然有些感慨,「有時候覺得做訪問也沒甚麼意思,還是把預告片剪輯好更重要。」他說網絡時代,好的預告片效果更強,能夠引起大眾關注的,應該是影像。「世代不同了,現在讀文字的人已經越來越少了,那種深度的訪談,可以留着給想看的人閱讀。」
開創台灣電影新浪潮
侯孝賢在1973年踏入電影界,曾為李行、賴成英等導演擔任場記、編劇、副導演等職務。1980年執導首部電影《就是溜溜的她》。從1983年《風櫃來的人》開始轉向寫實風格,開創台灣新浪潮電影之風,《童年往事》、《戀戀風塵》均獲好評,1989年的《悲情城市》更讓他獲得威尼斯影展金獅獎。2003年,侯孝賢應邀為紀念日本導演小津安二郎百年誕辰拍攝日語電影《珈琲時光》,2007年應法國奧塞美術館之邀拍攝法語電影《紅氣球之旅》,2009年起擔任金馬獎主席。卸任後籌備拍攝首部武俠電影《刺客聶隱娘》(2015年),並在康城影展勇奪最佳導演獎,2020年獲得台灣金馬獎「終身成就獎」。
·顯影 Instagram / Linkin.bio